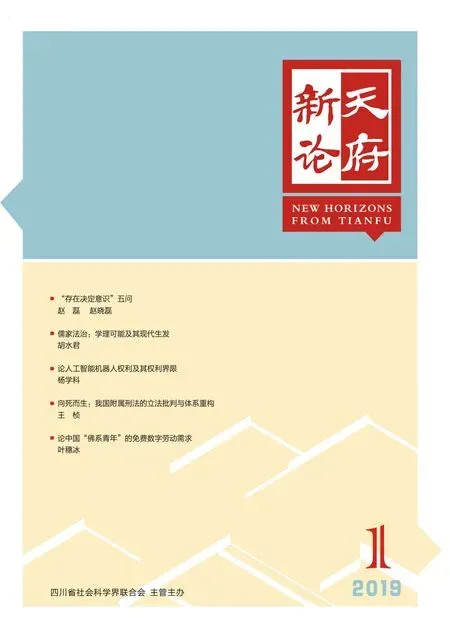以氣代天和儀禮分裂背景下的孔子民德守護
——從生、性概念的系譜學分析入手
張可越
段注《說文解字》“人”字條注曰:“性,古文以為生字。《左傳》:‘正德、利用、厚生。’《國語》作‘厚性’。是也。”[注]許慎,段玉裁:《說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65頁。俞樾《群經平議·孟子二》曰:“性與生,古字通用。”[注]俞樾:《群經平議》卷三十三,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春在堂全書》本。在甲骨文、金文和出土文獻中,往往有“生”而無“性”,如漢墓馬王堆出土的帛書老子《五行》篇曰:“循草木之生而生焉,而無仁義焉。……循人之生而蔚然知其好仁義也。”[注]轉引自徐洪火:《老子甲本卷后古佚書之一釋文校補》,《社會科學戰線》編輯部:《古籍論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7頁。可見,生字早出,性字晚出,在古文獻中生性混用的例子很多,單從字面上是無法區分這兩個概念的。
在《說文解字》中,東漢許慎對“生”的定義是:“進也。象草木生出土上。凡生之屬皆從生。”對“性”的定義是:“人之陽氣,性善者也。”“生”指世間萬物的生長活動,在人則是“食、色,性也”,亦即自然情欲[注]情欲概念在中國哲學中,除儒家明里暗里地提倡襄助外,往往是被消極對待的。先秦墨家節用、道家寡欲,勢均極盛。到秦漢,新法家韓非、賈誼均主張君子心靜無欲以反照萬物之理,把懸擱欲望當作認識論的初步。新儒家董仲舒主張性陽情陰、克己愛人,僅允許合于公羊學天理的情欲滿足,將道德無限拔高到“殺人”的地步。漢代經學深受法、道家影響(馬端臨、錢穆對此均有充分論述),故能一變而為魏晉老學,對情欲戒備到無以復加的地步,連最感人的音聲樂也被論為無情,又用服藥取代了食谷,樣樣跟常人情欲作對。直至王弼、向秀、郭象主張圣人有情,情欲才被稍稍挽回,可這些圣人又是無為的,所以實在不能體會真實情欲。唐代佛學實承敘老學基本思想,連當時力主儒家復興的李翱也不免受佛老影響而主滅情。直到宋代,隨著近世市民社會的成熟化,象征平民最大特質的情欲才被道學家們肯定,但又在概念中做了嚴苛限定。情欲,又作人欲、物欲、私欲,特指罔公顧私、傷害他人的異化情欲,這種限定客觀上把自然情欲以及建立在其基礎之上的孝親、友愛、夫婦等道德情欲解放了出來,終于有了一種健康的情欲哲學。本文將不憚使用和暢談情欲,但也是有所區分的:情欲的基礎是自然情欲,即生性,這是孟子所謂的“種之美者”,天然靜好。情欲的社會形態則有兩種:一是自然情欲符合社會公益,即生生,筆者稱之為道德情欲,這是孟子所謂“熟之而已矣”;二是自然情欲無視社會公益,筆者稱之為異化情欲,這是孟子所謂“西子蒙不潔”者。,這是無分善惡的。“性”則專指人性的倫理道德層面,這是純善的,且與氣密切相關。許慎基于漢代經學家的視角,使生、性二字從意義上區分開來。本文將繼承這點,統稱自然之“生”為生性,倫理之“性”為氣性。
然而,生性果如許慎所釋無關乎道德倫理嗎?氣性又真的是善嗎?筆者以為不然。倘對西周、春秋文獻做一番探賾,會發現生性概念出現較早,且關聯著天命、民意,又常作“生生”,這就從一人之生擴充到萬民共生,道德內涵亦因之而起。而氣性概念則出現較晚,且關聯著氣、命、禮等概念,強調個人修養,以期趨利避害。倘以西學概念對觀,則生性概念側重主體間性,氣性概念側重主體性。不過,西方進路卻正相反。在基督教時代,彼岸世界壓抑此岸世界,上帝本體壓抑人類主體;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對此的反撥又導致主體性的過度張揚,以至于人成為新的上帝,理性和感性相繼成為壓迫性力量,阻礙著人對真實自我的認識,即一個世俗而非神圣、理欲平衡而非沖突分裂的我,他既不否定自身也不凌駕世界。因此,西人是從主體性轉入其反題主體間性的。這種思想直到尼采19世紀末提出視角主義,胡塞爾20世紀初提出主體交互理論才得以站立,卻又始終站不穩,因為他們對于如何協調主體間的關系缺乏相關思想資源。時至今日的英美政派中,自由和保守仍是爭論不休的兩大陣營,有主張極度社會化趨于宗教團體的一極,也有主張極度個人化趨于孤獨原子的一極。
而在中國,東周以前的文獻中并沒有類似西方的創世神話[注]④張光直:《青銅揮麈》,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第150頁,第153頁。(而這是生成彼岸世界和本體論的重要資源)。其生性概念所蘊含的主體間性思想,更將民意與天命結合起來,主張對國人要生長、求足欲的合理要求,君主應順并協調之,此為有德且能常葆天命。這也與中東古國的神權統治有著極大差別。王國維在《殷周制度論》中熱情贊頌“中國政治與文化之變革莫劇于殷周之際”,“殷周之興亡乃有德與無德之興亡”,其核心在“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注]王國維:《觀堂集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31頁、第232頁、第244頁。。筆者以為,這大概便是孔子常欲夢見周公的原因。然而,隨著氣性概念及主體性思想的不斷張揚,中國文化中要求戒備、壓制情欲的聲音也越來越大,個人自求避禍的理想遠遠拋開了國人的幸福事業。同時,東周以后的文獻中也開始出現關于神仙彼岸世界的神話傳說④,世界被從本體(比如道)中創造出來。可見,生性、氣性兩概念的興替乃中國思想史繼商周轉變后又一重要的轉捩點。筆者以為,對此不妨借助西哲尼采所開創的系譜學(Genealogy)方法,通過探究概念演變生發處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力量博弈,既厘清傳統,也為今日社會貢獻一些可資參校的寶貴思想資源。
一、商周文獻中的生性概念組:天命、民意與君德
商朝末年發生了一件事,即西伯戡黎。黎是商王朝西北部作為其屏障的一個小國(今山西長治南面的壺關境內),戡黎是西周進取中原道路上的重要戰略步驟,因為這里已離朝歌(今河南鶴壁)不遠了。此事引發商朝上層巨大震動。《史記·殷本紀》載:“及西伯伐饑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而其所奔告的內容,見載于今文《商書·西伯戡黎》:
(祖伊)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非先王不相我后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臺?”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祖伊告訴紂王,因為你的行為自絕于天,所以殷的天命就要完結了。而紂王非常疑惑,難道天不是站在我這邊的嗎?這段對話揭示了商代末年的兩種天觀:紂王代表著神意/宗法天觀,殷人認為歷代祖先都和天神在一起守護著殷的天命,兒子有錯,神父神祖總不會自斬血脈,放棄血食吧?所以理所當然地認為我生有命在天。祖伊則代表著更為先進的民意天觀,天棄殷其實就是民棄殷,“我民罔弗欲喪”才是最可怕的[注]需要注意,這里的民、人民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全體人民,而主要指居住在國都附近的“鄉”中的自由公民,確切地說是國人,他們享有政治和經濟權利,承擔生產和軍事任務。參見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20-425頁。。這里出現了“天性”概念,它和本文討論的生性、氣性是什么關系呢?劉起釪先生在《尚書校釋譯論》中列出了兩種理解:
《殷本紀》作“不虞知天性”,段玉裁、陳喬樅等謂此為今文。“虞”,《爾雅·釋言》釋為“度”,《集解》引鄭玄釋句為“逆亂陰陽,不度天性”。然牟庭《同文尚書》據《白虎通·號篇》“虞者,樂也”,《文選·羽獵賦》注“虞與娛古字通”。又孫詒讓《尚書駢枝》、章炳麟《古文尚書拾遺定本》也都以“虞”為“娛”,皆以為“不虞天性”就是“不樂天性”。此釋較妥。[注]③④⑤⑥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第1051頁,第1051頁,第1051頁,第1069頁,第1070頁。
劉先生選擇樂生之義,天性即我們所謂生性,此義較古,應當從之。而對于天性所在的整句話,也有兩種理解:一種是鄭玄的解讀:“王暴虐于民,使不得安食”③,則“不虞天性,不迪率典”者是民,是說商紂讓他們無法樂生,因此憎恨并反抗其統治;另一種是江聲的解讀:“我殷不得安食,非言民不得安食”④。從劉先生對這句話的翻譯來看,他采用了模糊處理,并不點明樂生者為誰。但從該篇創作年代及其作者是周人還是商人的角度去分析,我們或許是可以得出答案的。劉先生指出,“商人從來不稱自己是‘衣’或‘殷’,而只自稱為‘商’”⑤。所以,他認為本篇應是周人偽托而作,且即便“不是周人所作,也可說明商人入周日久,已受周人很深的同化了”⑥。所以,這篇的祖伊大概代表了周初人的思想。而與此情況類似的則是另一篇今文《商書·盤庚中》,據說是盤庚動員當時的貴族和國人遷都時說的,其中有這樣的文句: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劉起釪翻譯:我想起我們的先王使用你們的先人,就記掛你們,要養育得你們好好的。是這樣的呵!可是由于沒處理好,延到現在還住在這有災難的地方,先王就重重地降下責罰,說道:“你為什么要這樣地虐待我的人民呢?”若是你們無數人民不肯去孜孜努力求取美好的生活,和我同心遷去,先王便要重重地責罰你們,說道:“你們為什么不和我幼小的孫兒同心協力,卻對他三心二意呢?上帝絕不會饒恕你們的,你們也決沒有法子可以避免這個責罰。……去吧!努力追求美好的生活吧!現在我要把你們遷過去了;在那邊,希望一勞永逸地建立好你們的家國。[注]③④⑤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第950-951頁,第1283頁,第1593頁,第1443頁。)
對于這篇文獻,劉先生的看法也認為是周初偽作。裘錫珪先生也說:“《商書》用詞行文的習慣,往往與甲骨卜辭不合,如《盤庚》喜歡用‘民’字,在卜辭中卻還沒有發現過同樣用法的‘民’字。”[注]裘錫珪:《談地下材料在古籍中的作用》,轉引自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年,第954-965頁。結合兩篇分析,可知民之樂生乃周人自有之思想,卻又偽托商人表述出來。而上引《盤庚》篇中對民的嚴厲威脅,說些天會降罰的話語,則是模仿商人筆調;抑或原有一些商人文獻材料,周人又再以民意、生生之論潤色之,也就成了現在這個樣子。如此則《西伯戡黎》中不得虞性樂生者,也應是民,而這是周人思想。
至于在周人自己的文獻中,則大可不必如此曲折,民意、天命早就牢牢地固結在一起,成為君德的標準了。且看:
今文《周書·大誥》: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劉起釪翻譯:所以我要深切地告誡各個邦君們,老天爺并不是隨便信任我個人的,它只是為了要安定我們人民的原故才有這樣的表示的。我怎么敢不為先王遺下的偉大功業爭取一個最后的勝利呢?③)
今文《周書·君奭》:周公若曰:“君奭!弗吊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后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劉起釪譯:周公這樣說:“君奭呵!由于殷人干盡了壞事,所以老天把喪亡之禍降給了殷人。現在殷人已墮失了他們的天命,由我有周承受了,但我不敢說我有周已開始的基業就能這樣可靠地永遠美好下去;也由于即使天是不可信賴的,我也不敢說我們有周的國運最后必然是不美好的。唉!您已說同意我的看法對,我也不敢以為可以安然信賴于天命,也不敢不長遠敬念上天之威嚴與我下民,不尤怨于人呀!倘使我們后嗣子孫不能奉承天地上下,不能繼承發揚文王武王之光輝事業,不知天命之不易,那就天也難于信賴,就會墮失自己的天命!因而不能繼續經營文王武王的大業,也無從恭奉他們的明德了。現在我小子旦,不能有所匡正于上,惟有以文王武王之光烈移于我們的好小子(成王)身上了。”周公又說道:“天是不可無條件信賴的,只有我們繼承和發展文王之德所孕育的光輝大業,才會使上天不厭棄文王受的大命。”④)
今文《周書·召誥》: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王引之《經義述聞》:不以小民非彝而殄戮之者,先教化而后刑罰也用此治民乃能有功。⑤),亦敢殄戮用乂民。
今文《周書·洛誥》: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李民、王健譯:周公說:“唉!您作為年輕人,要考慮完成先王的事業,要認真觀察諸侯們覲見時的貢享,也要記下那些未曾貢享的者侯。貢享應當重視禮儀。如果貢品豐富卻忽略禮儀,也可以說和沒有貢享一樣。他們沒有用心于貢享,所以民眾就說他們不遵守貢享之禮,這樣王事就會受到輕慢,并出現差錯。希望年輕的王趕快前來分擔政務,我無暇顧及那么多政事。我教給您輔助民眾的常法,您如果不努力去做,您的統治就不會長久啊。厚待您的同姓諸侯,使他們無不像我一樣,不敢廢棄您的命令。您前往洛邑要恭敬謹慎啊!在這里我們要勤勉努力啊。同姓諸侯教導我們的民眾,這樣無論多遠,民眾也會來歸附您的。”[注]李民,王健:《尚書譯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99頁。)
今文《周書·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威威,顯民。……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惟民其敕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解見下文)
從上引佶屈聱牙的文字中,我們可以得出這些作者(據說是周公、召公)有如下政治思想:
1.天命在民意(“天棐忱辭,其考我民”,“永遠念天威越我民”)。
2.掌握民意/順應天命是一件很難的事情(“天命不易,天難諶”)。
3.人民的疾苦是要關心的(“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
4.人民的幸福/欲望是多歧的,而這正是天命難測的根源。對于民欲,需要極小心地處理。首先,應當保持寬容(“勿以小民淫用非彝”)。其次,應查明其罪過,若是無心之過,罪雖大也應留給一條生路(“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若是有心之過,且是一貫,更成為人民的壞榜樣,則罪雖小也要堅決處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還有一點很關鍵,即法律要讓人民知道(“威威,顯民”)。
這種政治思想的哲學基礎,其實正建立在對生性/情欲的充分理解之上。善和惡的標準,并不在于有無情欲或欲望大小,而在于情欲是否能與社會其他主體相和諧,情欲本身是被肯定的,這就把民生放在了第一位。以生性為基礎,天命、民意、君德就被統合在了一起,形成一種主體間性思想:君主應引導百姓共同足欲,這是順天命、合民意。但由于社會資源是有限的,所以每個人都不可能窮盡其欲,這就需要有德明君以己度人地理解民欲,又通過其智慧手段來妥善引導、調節民欲,在必要時施以刑罰,使社會情欲在一個歷史時期內得到合理地、最大化地滿足,從而百姓樂從、四方來服。這樣的政治理念,即便放在今日世界恐亦不失其合理性。唯一的難點在于有沒有這樣的調節者,這是非有大德性、大智慧,且能大力學行之人而不克當之的。故此《周書·召誥》曰:“今天其命哲”。在古代社會這顯然是很難的。
二、春秋文獻中的氣性概念組:主體間性向主體性的滑落
所以到西周后期,生性概念組開始分裂,主體間性失落了。一是君德崩潰,周王專利。這顯著體現在厲、幽二王身上,他們是“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大雅·蕩》)。二是隨著經濟發展,社會矛盾激化、貧富差距拉大,民意協調也變得愈來愈困難。《小雅·正月》就反映了幽王時期一位底層官吏對上層統治者的怨憎,“彼有旨酒,又有嘉殽。……念我獨無,憂心殷殷”。貧富分化不應被僅僅視為罪惡,而要首先注意到這往往是經濟發展的產物。西周初年政局動蕩,民心思安但求溫飽,那時的民意是好順應的、天命是好承繼的;西周末年則不然,經濟發展帶來情欲多歧,飽暖則思淫欲。即如宣王中興,亦只曇花一現,最終還是輸在籍田問題上的民意分歧,所以西周還是衰敗了。這是歷史的局限與無奈。而隨著君、民的異化,聯結君德與民意的天命,也變得迷離難測(《大雅·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和充滿危機(《大雅·板》:“天之方虐,無然謔謔”)。但這不過是西周貴族利用天來表達自身既厭惡君主又懼怕國人暴動的矛盾心理而已。
春秋時期的禮崩樂壞是這一過程的進一步發展。學界普遍認同西周政治是以禮為中心的人文政治。在周初政治文獻如《洛誥》 《君奭》中,禮多指宗教儀式,用于祭祀神明祖先,這是繼承殷禮的。與之相關的還有彝的概念。但徐復觀先生認為禮主祭祀、彝主道德,是毫無關系的:
歸納起來,(彝)包括有“常”字的意義,如“彝酒”“彝訓”“彝教”者是。有的是法典、規范的意義,如“殷彝”“非彝”者是。而《酒誥》的“非彝”,系以上文的“縱淫浹”及連同下文的“用燕喪威儀”為其內容,則是一般生活中的威儀亦稱為彝。就《康誥》“民彝”的上文“矧惟不孝不友”數語觀之,則孝友之德,也包括在彝里面。由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周初的所謂彝,完全系“人文”的觀念,與祭祀毫無關系。……春秋時代所稱的“周公制周禮”,惟“儀”的觀念足以當之;而周初以宗教儀式為主的禮的觀念,決不足以當此。[注]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徐復觀文集》(第三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53頁。
這種看法乃是受天、人二分西方思想影響的產物,但在周人看來,天、人卻密不可分。統治者正是利用祭祀、大蒐、籍田、鄉飲酒禮等儀式性活動使君、天、民充分溝通,如籍田之禮,就包含生產的督促和民心的團結,籍田的收獲除供祭祀之用以外,還要施舍給窮困農夫,用于社會救濟[注]楊寬:《西周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68-282頁。。再如《孟子·梁惠王下》就引述晏子之論巡狩之禮,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補不足、助不給,亦可見禮與民生和道德的關系。孔子亦曾嘉許公西華“愿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愿為小相焉”的政治理想,認為“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論語·先進》)所以,禮作為制度形式,彝作為道德內涵,乃是表里互用之關系,是不應被分裂看待的。禮崩樂壞則是二者的同時崩壞。表面看來這是諸侯卿大夫僭越的產物;深層看來則是天命、民意和主體間性的一并遺失。宣公三年楚王問鼎,實有爭霸之意,他關心的不是治國愛民,而是凌駕諸侯的政治權威。于是,禮作為形式就從主體間性的民德儀式轉變為主體性的君威儀式;而彝作為內涵則脫離形式,轉變成一種主體性的個人道德。但主體性的確立,還需要更為基礎的哲學范式轉化,那便是春秋時代的以氣代天和氣性對生性的徹底取代。
在《左傳》中,我們仍能看到一些生性概念的主體間性思想,它們大多出現于春秋前中期。比如:
桓公六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莊公三二年: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饞,其何土之能得?
文公七年: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
昭公十九年:吾聞撫民者,節用于內,而樹德于外,民樂其性,而無寇仇。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死轉,忘寢與食,非撫之也。
但氣性概念及主體性思想也開始生成。《左傳·成公十三年》記載了劉康公論氣的一段話:
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杜注:養威儀以致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惰則失中和之氣。其不反乎!
康公發此語是因為成子不循祭祀之禮,但勤禮致敬是為了養神,養神是為了定命,說到底是為了個人,可以說是一種自求多福的私德儀式。儀式是為社會公益開展的,倘只為個人修福,則大可不必費此周章,越清凈越宜于自修。所以,后來子大叔干脆主張儀禮不同、棄儀取禮,實承此而下達。另外,康公認為“民受天地之中”而生,“中”就是“中和之氣”。這里含有兩個重要轉變,一是以氣代天,從天生萬物變成了受氣自生。二是以氣性代生性,不言“中和之性”而曰“中和之氣”。可惜這里論得還不夠明晰。我們不妨再參考《左傳·昭公元年》醫和從醫學角度對氣作出的更精密論述:
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征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這就道出了氣和天的差異:天重在生成之本源,是從萬物共生的主體間性、群體性視角看的;氣重在生成之結果,是從一物自生的主體性、個體性視角看的,強調主體內部的陰陽平衡。視角的轉換帶來了善惡標準的變革:從天和生性角度看,首先應肯定每個主體的生存和情欲;其次則是從主體間共生關系上考慮情欲善惡,對傷害他人的情欲加以抑制,對與人和諧的情欲加以肯定。但若從氣和氣性的角度看,由于缺失他主體維度,也就喪失了相對、動態的價值參照系,對情欲的判斷標準就從質的關系變為量的多寡(淫與不淫),成了一種絕對標準。而這進一步發展,就成了《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所論的新禮和新人性:
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
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
“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
“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子大叔直接表明儀和禮不同,要棄儀取禮[注]由于禮、彝、儀這幾個概念在本文所征引的文獻中多次出現,且不斷轉義,實有必要厘清:子大叔說的儀,即周初祭祀之禮。子大叔說的禮,即周初人文之彝,但其主體間性的生生內涵已被主體性的節性所替換。。這令簡子疑惑,于是子大叔進一步結合氣論闡述了他的新禮義。通過前文的分析我們已知,氣性是主體性,現在子大叔指出它是二歧的,一種是善的氣性,即主體情欲合禮、有度,又稱為“天地之性”(我們不妨簡稱其為天性。本文開篇所引許慎“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實亦出于此系統,正即此天性);一種是惡的氣性,即主體情欲非禮、無度,子大叔甚至不愿給它稱謂,認為這不是性,論為“淫則昏亂,民失其性”(這又是上承醫和的“淫生六疾”說)。這樣,禮就成了氣性善惡的法則,其核心在于節制情欲,這便是子大叔的新禮義。這樣一來,禮和情欲的關系變得極為緊張,它成了一套與社會情欲發展不相適應的僵化的制度,本質上則是違背人性的。依著這個思路,也就不難理解《禮記·樂記·樂本》篇中把情欲既論為性又論為非性的矛盾了:
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聲噍以殺。其樂心感者,其聲嘽以緩。其喜心感者,其聲發以散。其怒心感者,其聲粗以厲。其敬心感者,其聲直以廉。其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動。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惡形焉。好惡無節于內,知誘于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人生而靜,情欲寡淡,這是“天之性”;長而動,情欲轉濃,這是“性之欲”,但它又被視為“非性也”。禮和情欲的緊張關系已發展到用天性否定氣性的地步了。《樂記》是一個集合戰國時期很多關于音樂的論文而成的本子,其最早的編纂者應為河間獻王[注]孫少華:《漢初〈禮記·樂記〉的版本材料與成書問題》,《孔子研究》2006年第6期。。但學界仍視其為一人之作,且為其年代和作者爭論不休,主流意見認為它是公孫尼子所作,郭沫若、蔣伯潛、楊公驥、李學勤等均持此說;但也有學者認為《樂記》中的氣論思想要到漢代才有[注]蔡仲德:《〈樂記〉〈聲無哀樂論〉注釋與研究》,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1997年;章啟群:《論〈樂論〉與〈樂記〉的根本區別——兼論占星學對于先秦儒家禮樂思想的沖擊與整合》,《哲學研究》2010年第2期;姚春鵬,姚丹:《從郭店楚簡再論〈樂記〉成書年代》,《孔子研究》2011年第4期。,他們的主要依據是其中的陰陽五行思想并非戰國時內容,但若結合上引《左傳》材料我們不難發現,氣論和陰陽思想至少在子大叔時代就已發展得頗為完整了。筆者以為上引《樂本》篇應是公孫尼子所作,他是孔、孟之間的儒學宗師。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也記載過他關于養氣的言論,既與上引無悖,也與子大叔無異。王充《論衡》又載“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一并提到的幾位都是七十子儒學宗師。所謂善惡,正是天性善氣性惡,他們都是秉持主體性思想的。
這種人生而靜的思想肯定初生嬰兒態,卻戒備人生向社會面的成長和發展,可謂逆天取義。道家思想在節制欲望方面也與公孫尼子同調。他們在春秋戰國時代蔚然成風,孔子周游列國時碰到的隱士大抵持論如此,他們對孔子的求仕行義冷嘲熱諷,認為“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然而孔子只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論語·微子》)。因為這些人雖然無為,究還是有道德操守的,與那些問鼎中原或殺父弒君的野心家相比好多了,所以孔子對他們始終充滿敬意。只是他們愈演愈烈,更以此種學問要君授徒,尤在齊稷下學宮中充斥洋溢,這便有誤國誤民之虞。所以終于出現了孟子批判陳仲蚓操,荀子批判觙子自空、宋钘寡欲的言論,這些批判的核心都在于質問人豈能無欲。
據陸德明說,《禮記·緇衣》也是公孫尼子所作[注]陸德明:《經典釋文》,轉引自鄭玄,孔穎達:《禮記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750頁。。這篇著重談君德,卻與周初與民同樂的君德不同,而是威儀堂堂、作民表率的君德。開篇便說“為上易事也,為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遁心。”這是說禮勝于法,因禮簡明易知,民可以很好地遵它行事;若如法一般繁雜,民將無所適從矣。但什么樣的君主才可以制定出這樣好的禮呢?“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原來是以節制情欲為民表率。這里的邏輯非常奇怪,它認為人民是君主情欲的翻倍器,君主衣帛食肉,人民就要奇裝異服、魚翅燕窩。所以,君主必須話很少說、事很少做,因為做得越多越沒威儀,人民也翻倍得越壞,“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于言而慎于行。《詩》云:‘慎爾出話,敬爾威儀。’”人民既是這樣情欲未滿,又怎能教得成呢?所以“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鄭玄注為“言百姓效禹為仁,非本性能仁也”。可見,人民的本性很壞,雖然其中的大多數能在表面上做到仁,心里就不盡然了。這和孟子、荀子主張人人都可以為禹舜大相徑庭(《孟子·盡心上》說“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并不認為人民富裕是有害的)。《緇衣》篇可說是把《樂記》中的主體清修功夫推而廣之,先推給君主,再想方設法推給人民。可人民實在辦不到,因為有欲有為才有飯吃,所以就只能是“豈必盡仁”了。
《禮記》雖說是儒家經典,可類似《樂記》 《緇衣》這樣的篇目實在不少。康有為藉以闡發大同思想的《禮運》篇細讀之下竟也一樣。或人有疑,大同不正要天下同樂嗎?余以為稱謂“天下同”則可,“樂”卻未必然。南海先生作為一代宗師,其所闡發的思想固是瑰瑋雄奇且切于時弊;然其呼吁憲政,要亦在一禮字爾。先生言曰:“今者,中國已小康矣,而不求進化,泥守舊方,是失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注]②康有為:《禮運注》,《康有為全集》(第五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553頁,第554頁。(此判斷施諸當時之中國或也并不盡然)。而其進化之標的乃在“禮者,猶希臘之言憲法,特兼該神道,較廣大耳。此篇明孔子禮治之本,大義微言多在”②。而《禮運》篇所托引孔子之言禮如下:“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于天,淆于地,列于鬼神……故圣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識者詳味,此與子大叔乃同唱一調,且先生更點明了這禮的實質也還是法(希臘憲法),不過是法化入心,成為道德而顯得超越于法,目的在于使人民心悅誠服地按一種外在律條行事,康公稱其為“文明之法”。《禮運》則描述此狀態為“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只出力,不享受,這實在是尼采所感嘆的一種人性的、太人性的理想,它的道德境界已超絕個體生命之上,縹緲入神,誠非人民所能企及者,又或許這便是孔子所稱引的“誠不以富,亦只以異”(《論語·顏淵》)者乎?總之,此禮既出,氣必隨至。果然該篇說:“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談禮談氣,就是要把情欲斷案得明明白白,然而倘若法不以情欲關懷為本,是否終將毀傷人性天然呢?《禮運》篇如此論禮,其與今文《尚書》的民生思想實相違背,而主今文學的康公卻格外看重該篇,這是一種矛盾。不過,在其老師廖平那里,這篇卻是被算為今古文混雜之作的[注]廖平:《今古學考卷上》,《廖平全集》(第一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2頁。,然而廖是否知解共生足欲的意思,余意恐未必然。
這里不妨再談一下晉人梅賾的偽古文《尚書》。《大禹謨》和《樂記》一樣,將氣性稱為人心,其合禮而善者稱為道心,并視道心為精一。《商書·咸有一德》與之同調,認為“天佑于一德……民歸于一德。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兇。”“精一”、“一德”和道家的“道生一”實出一脈,都主張從物質世界收攝退守內心,體察“人生而靜”的無欲無為氣象。而主體間性的共生理想卻不會產生這種靜和一,相反,它追求多,要求主體以博愛之心廣泛地見聞萬物,再通過沉靜思索,找出一條最適合萬物發展的道路。所以孟子明確批判這種執一的思想家子莫子,說:“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盡心下》)荀子進一步指出:“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壹。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解蔽》)這里當然也有一,卻是兼知而守貞之一[注]對于荀子虛壹靜心法的解讀,可參廖明春:《荀子“虛壹而靜”說新釋》,《荀子新探》,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25-234頁。;也有靜,卻是動而不亂之靜。這是儒學的理路,宋代道學亦如此。雖然他們大量使用天性氣性、人心道心、惟精惟一等概念,但都已將其內涵通過周敦頤太極說、張載氣論和二程理一分殊說加以改造,認為人心道心通為一心[注]《朱子語類》卷四,論人心道心,“‘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都是心,不成只道心是心,人心不是心”。《朱子語類》卷十二,論佛家作用是性,“人心是個無揀擇底心,道心是個有揀擇底心。佛氏也不可謂之邪,只是個無揀擇底心。到心存時,已無大段不是處了”。見朱熹:《朱子全書》(第十四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92頁,第383頁。,氣性天性本為一性[注]張載在《正蒙·乾稱》論天性氣性,“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烏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見《張載集》,中華書局,1978年,第63頁。,靜中不僅有物[注]《二程遺書》卷十八,程頤曰:“靜中須有物始得。這里便是難處,學者莫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見程顥,程頤《二程集》,中華書局,1981年,第201頁。而且須見須聞[注]《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八《答呂子約書》:“蓋心之有知,與耳之有聞、目之有見,為一等時節:雖未發而未嘗無”。見朱熹:《朱子全書》(第二十二冊),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23頁。,這便從子大叔、公孫尼子、道家及其后的中國大乘佛教思想回轉到了儒家初義,即肯定生生不息的生命活動。而在這個回轉過程中,孔子起了重要作用,在那個以氣代天、儀禮分裂的主體性時代里,孔子卻主張復禮、仁愛、知人,這便如同一座燈塔,引導著后來的中國哲學迷航者們重尋人性的方向。這一切則要從孔子的民德守護說起。
三、孔子的民德守護:以仁溝通天-氣概念組
孔子大約是子大叔同時代的人,子大叔棄儀從禮的時候,孔子三十五歲,還是個年輕人。孔子走的是一條和子大叔完全不同的路線,他要“復禮”,也就是追回禮彝互用的周初政治,其根本訴求在于“夢見周公”,即以尋回民意、天命為己任。此時天已退場,且孔子無位,本著“君子思不出其位”的原則,孔子罕言天命,以至子貢表示“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治長》)。但孔子對天命實非常清楚,首先,他教育弟子“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這才引發了子貢對天命的追問,雖然孔子表示“予欲無言”,可隨即又對子貢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這段話其實已明確道出了天命內涵,那就是“百物生焉”的生生理想。后來《中庸》更進一步說“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就天命之“大德”點明出來,《易傳》“生生之謂易”亦同于此。子貢“不可得而聞”,或是他還不能領悟及此,這是我們消極的理解;或是他已深刻體會,知道此種共生之理不是聽聞講說便可領會的,而必須體物不遺、終身踐行,這是我們積極的理解,也是孔子所以罕言天命的更深層原因。
孔子自己也是選擇從仁下手而非直取天命。樊遲問仁、知,孔子答以愛人和知人。這正是在轉述周公的民意政治思想:君主應當關愛百姓,厚其生性,但基于社會資源有限,欲望不能窮盡,所以又應當知人,合理分配使各自情欲在最大程度上滿足。愛人、知人都是主體性活動,愛人是一種道德情欲(希望他人與己同欲同樂),知人則是從愛人中生發出來的道德認識(同情之理解),是愛人的延伸,這就使主體間性的天命落實到了主體性上,把生性、氣性升華為一種仁性。愛人知人的另一種說法是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衛靈公》)。《大學》對此加以演繹:“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但這對于追求“人生而靜”的一派是很難理解的,因為他們只看向自己的內心,一層層剝去世俗的情欲,剝到極致也就和普通人民天懸地隔,又哪會有什么真實的恕、愛、知可言呢?所以,仁是孔子積極吸收當時已經形成的氣性/主體性理論而又用生性/主體間性理論對其加以改造的產物,他把氣論對情欲的戒備轉化為對情欲的肯定和升華,最后著落在一個“性”字上。孔子固罕言性,但也明確說過“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陽貨》)。“性相近”,是指人人都有情欲,且情欲有個體差異,所以是相近而非全同的;但通過道德升華(愛和知),又完全可以交流溝通、互相包容,正所謂“君子和而不同”。如何兼容差異,既足己欲又不害人欲,這就需要“習”。習的程度大段有別,否則圣賢不會如此稀少;但習的可能性卻人人都有,《中庸》說“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圣人亦有所不能焉”,正是此意。經今古文學派爭論的焦點問題之一就是孔子之于文武周公的態度:今文派認為孔子是托古改制的革命哲學家;古文派認為孔子是繼承周公的保守歷史家[注]此經今古文學之總結源于周予同先生,詳參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4頁。。而以筆者視之,此皆有偏,孔子實在是既復古又革新的。他正是利用仁這個概念,把周初的民意君德完全落實在了春秋時的主體個人身上:不止君主,人人都可以為堯舜,這是孔子最大的革新;而為堯舜就是要為人人(包括堯舜自己)的情欲滿足而奮斗,這又是孔子最大的復古。偉哉斯人!大哉斯人!
孔子對性/情欲的態度,又可參考以下雖未言“性”乃實出之的文本:
《學而》: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里仁》: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于是,顛沛必于是。
《述而》: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述而》: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
《顏淵》: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祗以異”。
《憲問》: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憲問》: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
《憲問》:(憲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富、貴、谷,都是情欲的代名詞,這些是人生性所求而無可厚非。但求之之道卻大有講究,如把自身情欲滿足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如邦無道而富者,那是發國難財以自肥,這樣的富貴孔子絕不求。但若全無情欲,如原憲所謂“欲不行”,孔子也并不肯定,只說這是很難的(因為違背人性),而未必是仁的要求。只有“富而好禮”最是光輝,即情欲的滿足符合社會的、道德的公益。
可見,孔子的仁學根本上還是以人性為本、以情欲為基礎的。而在這個基礎上,孔子力主學、行《詩》、《書》、禮、樂,以更好地愛人、知人。首先,在學習的方法上,孔子主張學思并用,“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但二者之中學更基礎,“吾常終日不食,終夜不寐,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衛靈公》)。力學求知是孔門入德之門,這點也體現在《大學》以格物為首上,荀子對學更格外推重,惟孟子似談得較少些,然此有其特定學派論爭背景需另加辨證。孔子之學并非尋章摘句的專門化研究,而必求學行合一,以實踐避開知識的形式化沉淪。其次,就學習內容而言,“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述而》),君子當“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泰伯》),這是層層進階的。《詩》既能錘煉言辭,也是出使專對的政治工具,更揭示了道德情欲的方向,此即《左傳·襄公二十七年》趙文子告于叔向所謂“詩以言志”,荀子《儒效》所謂“詩言是其志也”。它是基礎性的,但言辭華美易流于形式,所以孔子對此格外戒備,要求“聽其言而觀其行”,空說可不行,“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子路》)《書》則是先代政事法典,正是本文開篇所引佶屈聱牙的《尚書》一類文字,學此可知先王之道,荀子所謂“書言是其事也”(《儒效》)。
《詩》《書》都是實體性的,體現在典籍中。禮、樂則是實踐性的,故又稱為“執禮”。孔子所主張的禮,既是主體個人的道德要求,也是主體間社群調節的規范化活動,個人和群體密合,儀彝重新統一。“君子博學于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這說的是彝,亦即“克己”,是個人修養,子大叔所主張的禮被包含其中;但“弗畔”一詞又關切到一種社群性。“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先進》),這說的是儀,但孔子反對空洞的君威或私德儀式,要追回周初的民德儀式,此即“復禮”,所以感嘆“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里仁》)又反問“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陽貨》)鄭玄注為:“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注]何晏,邢昺:《論語注疏》,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271頁。可謂得之。孔子認為樂較禮更為究極,因為它更貼近人民的情欲且能引導其和諧發展,其境界是眾樂樂而非獨樂,故將其安置在詩、禮之上,視為成者。孔子極好樂,聞韶而三月不知肉味;更尊敬樂者,見瞽者必作必趨。孔子的下學經過《詩》、《書》、禮、樂的層層推進,終于可以上達,“不怨天,不由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所謂上達就是對天命民意有廣博切實的體認,“五十而知天命”(《為政》);繼而對仁性有發自內心的堅守,主體間性思想徹上徹下,“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為政》)。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罕》),筆者認為這句話或可用以解說孔子的哲學總綱。利即自然情欲,這是人人都有且必須得到合理滿足的,此不必言。命取決于主體對情欲的管理,從《詩》、《書》、禮、樂中所學的,都是如何管理情欲,是把個人情欲放置在社會中考量,與他人和諧共生呢?還是無視他人滿足私欲?抑或逃離社會清凈寡欲?什么樣的個人選擇就有什么樣的個人命運,因為天命在民心,得民心者得天命,反之亦然。但由于春秋時期天命已失、民心已散,所以個人命運就格外渺茫難測,比如孔子就既無人民支持,也乏君主肯定,但他卻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憲問》),在各種挫折下仍說出“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這樣積極的話語,這是對自身學問、道德的堅定信念使然。在這種情形下孔子依然選擇盡其在我者,“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以有教無類、廣開求學之門的方式,不斷為社會播撒良知、化導民心,甚至有些改天換命的色彩,所以后來才有荀子《天論》中“與制天命而用之”這樣剛健進取精神的產生(當然荀子這里指自然天)。如此為仁,便活出了本真的主體性;而仁的關鍵是實干而非空談,所以利、命、仁,孔子都“罕言”,但又都很清楚。這固然是孔子的偉大之處,但也是孔子學派的遺憾之處,因為孔子死后,儒分為八,弟子中卻少有能領悟其核心思想并與社會實踐結合者,加之其他學派思想的引誘、羼雜,儒學也終于變得駁雜起來,比如前文所引述的公孫尼子就可算是背離了孔子之道。所以到了后來,就連“孔子”也可以問禮于老子,且竟能悵然自失地領悟出一些“若一志”、“聽以心”、“集虛”、“心齋”這樣的話來(《莊子·天下》),天命、民意到底還是失守了。
而澄清異說的使命則落在了孟子和荀子身上。孔子的仁學大抵有兩路:一是愛人,二是知人。孟子偏于愛人,荀子偏于知人,是在這兩條道路上充分發揮卻又漸行漸遠者,然皆流出不遠,所以他們又有許多相似處。比如,都在自然情欲的基礎上要求將其升華為道德情欲和道德理念;都反對無所作為的靜中天性;都秉持著強烈的真理使命感而不斷與其他學派或儒學中的異說持續辯論著;都和孔子類似,一生郁郁不得志,以道德干謁君王、拋棄君王,不斷地為民請命。孟子說“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上》),他一生奉行的是“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滕文公上》)的人生信條。荀子說“以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己至道,是民德也。……平正和民之善,億萬之眾而搏若一人:如是,則可謂圣人矣”(《儒效》),并引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王制》)的古語勸誡君王。這兩位夫子可謂孔子之后續火傳薪的新型民德守護者,實皆有大功于圣門者。而孟、荀之后,這樣的精神傳遞也不曾中斷,此即儒家所謂道統。儒家思想的生命力是極頑強的,雖然時或為法、道、玄、釋所遮蔽或雜糅,但因其根脈牢牢扎在生生、天命、民意這組概念之中,所以總能在民族危難之際應時而起,因為人民的聲音是永遠不會被淹沒的。而這一繼往開來的歷史時至今日仍在延續,如何從傳統文化中去粗取精,并會通中西,為中華民族的發展注入新的動力,這也將是儒學研究者的熾誠的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