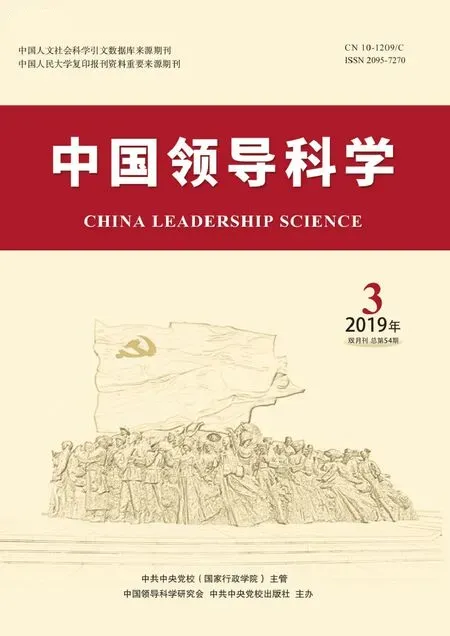《孟子》的“義利”觀與領導決策
◎任俊華 胡丹丹
孟子名軻,戰國時期鄒國人,魯國貴族孟孫氏之后。根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記載,孟子曾“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是孔子的孫子,由此奠定了孟子在儒家學脈中的繼承者地位。孟子樂于以孔子繼承者自命,曾說:“乃所愿,則學孔子也。”(《孟子·公孫丑上》)孟子一生,與孔子有很多相似之處,都經歷了讀書、游歷、教書三個階段,被后世尊稱為“孔子之后第一人”。他的言行被集中整理在《孟子》一書中。孟子的“義利”觀是其“仁政”思想的具體體現。通過對“仁”“義”“利”的思想闡發,孟子將儒家的政治思想落實到具體的政策制定之中,建立起一套立民、養民、樂民的政治倫理思想體系。
一、“正人心而存仁義”的立民觀
孟子的仁義思想,與《周易》的“立人之道”思想一脈相承。《周易》是我國現存最古老的一部哲學專著,冠居“群經之首”。《周易·說卦傳》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首次提出了“仁”“義”思想,并將“仁”“義”作為挺立人道運行的倫理基礎。圣人以陰陽立天道,剛柔立地道。“陰陽”“剛柔”表現為一種物質屬性,而挺立人道的“仁”與“義”,包含了人類社會獨有的倫理道德屬性。《周易》將此作為建立人類社會基本秩序的根本價值準則。
孟子延續儒家一脈,以“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思想構筑其“仁政”思想的基本內核。《禮記·學記》云:“建國君民,教學為先。”教學的涵義并不是狹隘的課堂教學模式,而是在社會的政策制定、公共宣傳、社會輿論、社會教育等各個公共領域挺立起“仁義”之道,用道德“立民”,匡正人心,弘揚倫理。儒家思想將“教以立民”作為政治治理的最高目標。孔子到衛國,冉有為夫子駕車。孔子感嘆道:“庶矣哉!”是說人口已經很多了。冉有問夫子,人口已經很多了,接下來該做什么?夫子回答“富之”。冉有接著問夫子,百姓生活富裕了之后呢?孔子回答“教之”。百姓的基本生活得以保障之后,就要重點致力于教化工作,從道德品質、思想情操上引導百姓挺立起高尚的人格。
孟子以“性善”的人性論為理論基點,對“仁”“義”思想進行了具體的闡發:“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知之端也。”(《孟子·公孫丑上》)孔子云“仁者愛人”,惻隱同情之心是“愛人”的發端,如同孺子入井,人人都會不假思索地去阻止孩子掉入井中。本性純善而推己及人,是人心本有的能力,也是一切美善德性得以建立、顯發的根本點。“義”之端點,來自于“羞惡之心”,欲知羞恥,必先明了善惡是非、人倫正道,自知行之不正,才會產生知過、悔過、恥于行惡的念頭。仁、義兩端,不僅是人區別于禽獸的立身之本,也是為政者“立民”之本,舜王就以“仁義”之道治理天下。因此,挺立起百姓本有良善人格是政者教化百姓的基礎,也是政治治理的最終歸宿。
孟子提倡執政者通過“善教”安定民心。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盡心上》)以強制性的手段迫使百姓遵守政策命令,百姓只是因為畏懼受到懲罰而遵循之,并非發自內心地做事,所以并不能得到“民心”;要使百姓心悅誠服,只能通過“善教”。執政者制定仁義為核心的教育內容,通過大眾喜聞樂見的方法引導百姓,規勸百姓導之向善,順應人之本有善性而不致其失,這是得民心的重要途徑。教育是百姓安身立命的方法,如果失去了教育一環,人們“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與禽獸”(《孟子·滕文公上》)教育的目的,在于使百姓在滿足生存需要的基礎上,重視德性的修養,“夭壽不二,修身以俟之”(《孟子·盡心上》),修養己性,把道義作為行事的根本價值原則,在生活的點滴中涵養高尚的道德情操。
為政者以仁義之道立民,需反求于己,從自身做起“由仁義行”。孟子在文中多次提到“君仁”的重要意義:“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離婁下》)君主如果仁愛待人,那么人人都心向仁愛、友善待人。君主為人正義,人人都會效而法之實踐道義,維護社會正義。對待身邊的大臣,也要行仁義之道。“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之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之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君主以手足之情對待臣下,臣下就會把君主當作腹心;君主把臣下當作犬馬一樣使喚,那么臣下就會把君主當作平民;君主把臣下當作狗或馬,臣下就會把君主當作仇敵。為政者自身實踐仁義大道,從而影響到身邊的大臣,乃至百姓,由此達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決策效果。
二、“不與民爭利”的守位觀
孟子傳承孔子的思想,將孔子的“仁”“義”思想進一步吸收、發展和完善,成為“仁政”治國戰略的核心要義。戰國時期政治動亂,禮崩樂壞,各國君主去“義”而趨“利”,為了擴大自身的領土而發動無休止的戰爭,導致國無寧日,民不聊生。這樣的背景下,“義”“利”之爭成為君主治國戰略價值選擇的主要矛盾。梁惠王見到孟子遠道而來,見面就提出了這個問題:“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吾國乎?”可見對自己國家有利是當時君主戰略決策的基本原則。
孟子認為重利輕義,是產生爭奪、交戰的根本原因。孟子回答梁惠王:“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茍為后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未有義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
在社會尚未進入民主的時代,在民主制度不完善的國度,權位就是資產,而且是一種萬能的資產,就像錢幣作為一種通貨一樣,隨時可以轉化為自己需要的商品,乃至并非商品的商品。而這種資產的限額,又是由掌管權位大小的人來決定的,權位愈高,資產愈大。大夫掌管一地,擁有一地的資產;諸侯掌管一國,擁有一國的資產;天子掌管天下,擁有天下的資產。這樣,位與德的關系被扭曲成位與利的關系。唯其他是被扭曲了的,非正常的,歷史上無時不處不有因位地利,同時又因利丟位乃至喪生的事例。所以,孟子守位的另一要訣是不與民爭利。不僅不能爭利,而且也不能隨便言利。
孟子在這里說的不言利,實際上是說不能倡利。如果國家的領導者一味言利,提倡利,鼓吹利,乃至爭利,就會造成“上下交爭利”的爭奪傾軋局面,國家就會瓦解。那么是否可以完全不要利而只講義呢?不是,孟子主張的是先義而后利,并不是有義而無利。只是義利的先后次序不能顛倒。“茍為后義而先利”,就會形成公開的爭奪,因為不掠奪別人,自己就無法滿足。這就叫“不奪不饜”。權位是最能滿足個人欲望的,因而也就成了優先搶奪的對象。故國君倡利就可能自失其位。
孟子的主張和《易》的德位觀點是一致的,因為義是德的一個重要方面,不過通過利的反面的義來表現罷了。這里的義與利是作為道德范疇的一對矛盾提出的。不少人曲解了孟子的思想,以為孟子只講義,不講利,只要精神,不要物質。這些人實質上是把生存需要和道德需要混為一談了,最終混淆了人與動物的區別。人和動物都需要生存條件,但人的獲取是必須符合義的原則的,只有動物的獲取才會不擇手段。然而動物不擇手段的獲取又隨時可以成為另一動物獲取的對象,這就是權位力得而不能力守的原因所在。
三、“仁民而愛物”的財用觀
孟子重義,并不是不要義,而是在利的獲取上,同樣要以“義”為先導原則。為政者要使百姓樂而無憂,根本還是要先解決溫飽問題,使百姓能夠生活。如何才能使民溫飽,孟子從三個方面闡發他的觀點。
(一)以愛惜萬物為政策制定的原則,順應動植物的生長節奏,維持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義”,古注有“合宜”的意思。四季輪回,天道運轉,萬物有其生長的時節環境。人們順應自然規律,就是以萬物的生命節奏為根本依據制定相關農事政策,合其時宜。孟子說:“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林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林木不可勝用,是視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提出的條款雖然不多,但卻帶有根本性質。不違農時,是保證谷物生長的根本;不竭澤而漁,使魚類保持旺盛的繁殖能力,是魚鱉不乏的根本。至于禁止亂砍濫伐,不僅是木材供應的保證,更是生存環境的保證。
歷史的經驗證明,大凡一個地區、一個國度的災荒,往往直接間接地與執政失誤有關,或因戰爭,或興土木;或荒淫嬉戲,或任意指點。而這些都直接關系到民眾的生活,乃至他們的生死存亡,執政者做決策,是不可不慎重的。一旦能慎,也就是“王道之始”,就不必擔心權位不保了。
(二)制定“置民恒產”的土地政策,安定民心
為了實現國家的安定富強,發展農業生產是孟子考慮的重要問題。為了實現“養民”的目的,孟子提出了“置民恒產”的主張。《孟子·滕文公上》說:“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茍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己。”“恒產”是可以長期恒久占有的私有財產。“恒心”,指安定之心。在孟子看來,人們擁有一定數量的私有財產是鞏固社會秩序、保持社會安寧的必要條件。人民之所以“放辟邪侈”,在物質層面上講,是人們缺少長期擁有的基本資產,在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的情況下,放逸、乖僻、不正當的行為隨之產生,擾亂了和諧的社會秩序。于是提出要“制民之產”,在政策上保障人民一定的個人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使民“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置民恒產的具體內容,孟子是這樣規劃的:“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明顯意識到,家庭的富足是國家強盛的前提和基礎。一家興安,推而廣之,則一國興安。每一個家庭的老人都能得到贍養,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人倫和睦,衣食無憂,這個國家得不到興旺,這是從來沒有過的。
(三)制定“省刑罰、薄稅斂”的財政政策,節用而富民
政治權力是把雙刃劍,可益民,也可害民。如果權力應用不恰當,通過橫征暴斂的手段滿足執政者個人的私欲享樂,這就是“以刃與政”“帥獸食人”。孟子說道:“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帥獸而食人也。”(《孟子·梁惠王上》)饑荒的年代,執政者豐衣足食,百姓卻四散逃荒,妻離子散,家破人亡,這種極端的差異不得民心。“兇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孟子·梁惠王下》)災荒年歲,國家的糧倉殷實,庫房充足,有關官吏不把這種情況向上報告,這就是身居上位的人怠慢而殘害百姓。執政者以怎樣的態度對待百姓,最終百姓也會以怎樣的方式回饋執政者。孟子引用了曾子的話:“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所以只有實施仁政,減去不必要的刑罰,輕薄稅賦,重視農耕,用倫理道德實施教化,百姓才會從心里親近、感恩他們的上級,上級制定的政策才能得以順利貫徹實施。這就是得民心者得天下。百姓的生活富足,家庭和睦,社會安定,這個國家就王道大行“仁者無敵”了。
四、“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共享觀
孟子的王道政治思想,致力于通過保民、養民、教民的措施達到政治清明、百姓富足、社會有序的治理局面。要實現這個目標,最重要的是執政者善于站在百姓的角度思考問題,制定政策,使官民一體,雙方齊心協力維系良好的社會秩序。孟子說道:“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執政者與百姓同憂樂,百姓就會以執政者的憂樂而憂樂,努力響應執政者的號召,實現官民的良善互動。反之,執政者為了滿足私欲,無節制地享受財用帶來的快樂,將此建立在聚斂民財的百姓痛苦之上,政治權位就會陷入十分危險的境地。
賢良的執政者發布命令、制定政策,以百姓之憂樂為先,與民同甘共苦。孟子引用齊景公與晏子的一段對話,向齊宣王闡釋何為“樂以天下、憂以天下”。從前齊景公向晏子問道:“我想到轉附山、朝儛山去轉轉,沿海向南,直到瑯琊山,我該怎么做才能達到與古圣賢王出游一樣的效果呢?”孟子回答說:“這個問題問得好呀!天子到諸侯國去叫巡狩,諸侯來朝見天子叫述職,都是正事。天子巡狩,春天就考察耕作的情況而補助貧困者,秋天考察收獲的情況補助收成不足者。夏代的諺語說:‘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意思是說,我王不出來走走,我怎能得到休養?我王不出來轉轉,我怎能得到補助?我王出游,行恩布德,可以為諸侯的法度。)如今卻不是這樣,而是興師動眾,聚斂糧食,饑餓的人吃不上飯,勞苦的人得不到休息。人們側目而視,怨聲載道,百姓開始作亂。這樣的出游叫做‘虐民’。”景公聽了很高興,“大戒于國,出舍于郊,于是始興發補不足”。景公聽了晏子的話,出行前在國內大行戒備,預備補助之事,出舍于郊外,開倉放糧,賑濟貧民。天子出游,目的在于體察民情,對每一個地方的風土人情進行實地考察,救助貧苦百姓,給人們減少憂愁,帶去喜樂,這樣人們就真誠地愛戴天子,翹首期盼執政者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