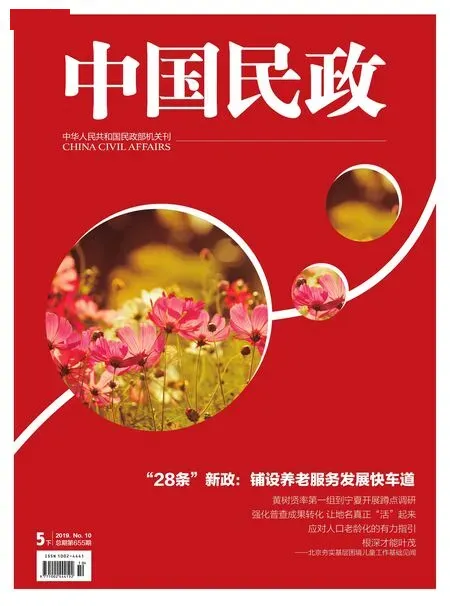根深才能葉茂 北京夯實基層困境兒童工作基礎見聞
彩繪門楣,紅色方柱,藍色桌椅,整潔而溫馨,幾個孩子在北京市通州區西集鎮兒童成長驛站內玩玩具,志愿者陪伴在側……
在豐臺區和義街道和義東里第三社區,社工崔超冉和同事正在困境兒童家中走訪……
中午放學后,女孩精靈回到房山區兒童福利院吃午飯,母親入獄,姥爺體弱,這里有她的“李媽媽”“徐媽媽”,是她的另一個家……
北京有262萬名兒童,其中困境兒童約2.2萬名,在困境兒童工作方面一直在探索:2013年入選民政部20個未成年人社會保護試點,2017年9月在全國省市民政廳局層面率先成立兒童福利和保護工作專門處室;但也面臨著難題:基層基礎能力薄弱,“尤其是基層社區作為兒童服務遞送體系‘最后一公里’,缺設施平臺、缺工作力量、缺工作機制。”2018年6月,北京市民政局兒童保護和福利處在一份材料中提及有待解決的問題時如是說。葉茂必得根深,這一年,通過不斷探索推進、總結提升,他們終于找到了破解之道。
兒童督導員、兒童主任、社工,各司其職
“兒童處成立時編制4人,這次機構改革,市委社工委和市民政局合署辦公,我們充實到了8個人。”北京市民政局兒童保護和福利處處長孫先禮說,機構改革為理順和強化兒童福利工作管理機制提供了契機,區縣層面實現了業務歸口管理,街道“大部制”改革中強化兒童福利等民生保障部門,明確街鄉、社區(村)力量配置。
與此同時,平臺正在搭建,規劃建設兒童福利服務指導中心、緊急庇護站以及兒童之家、兒童心理服務站;通過設立街鄉兒童督導員、社區(村)兒童主任,基層工作力量逐步加強。2018年8月底,北京331個街鄉、7097個社區(村)實現了兒童督導員、兒童主任配備,并制訂了隊伍實施管理意見,明確隊伍的來源、條件、任務、職責等等。
作為兒童福利遞送最末梢,兒童主任通常由社區工作者兼任,他是一個什么角色?兒童保護和福利處副處長喬偉圣這樣定義:問題發現者,政策宣傳者,資源鏈接者。“兒童主任、兒童督導員是一層一層的,兒童主任更多是預防,應對苗頭性、初級性問題;再嚴重的,可能要在街鄉層面解決,資源鏈接、政策幫扶;涉及監護侵害的突出個案,通過區級層面困境兒童和留守兒童保障聯席會議制度解決。”
一方面,基層工作繁雜,兒童主任、兒童督導員精力有限;另一方面,北京社工事務所500多個,做兒童工作的很多,應該充分調動社會力量參與,通過政府購買為困境兒童提供服務。
這一年,通州區兒童福利服務指導中心主任劉嵩體會到,兒童福利事業發展整體環境更好了,機制順了,基層力量充實了,針對困境兒童的成長驛站、普惠型的社區兒童之家正在建設,“我們拿到了中央和北京市兩級福彩公益金將近900萬元,在每個鄉鎮設立兒童成長驛站,對困境兒童進行幫扶。”
會都開到高法和民政部去了
“我們從2013年就開始做未成年人社會保護購買服務項目了,”中鼎社工事務所主任蘇峰說,項目開始實施沒幾天,豐臺區民政局轉給他一個案子,“這是項目第一個案子,也是最難的一個,持續了兩年,會開了十多次,都開到高法和民政部去了。”
在什剎海附近,一名女子帶著個4歲的孩子,白天乞討,晚上住窩棚。一查,女子是豐臺區東高地人,因家庭矛盾出走,孩子是非婚生。社工找到他們時,天寒地凍,孩子正在破帳篷里玩,頭發沒幾根,話也說不清;而媽媽則是精神異常。豐臺區民政局和社工把母子倆接回來,街道民政工作人員幫著租房子。女子依舊每天帶了孩子去乞討,社工只能跟著了解情況。
與此同時,社工找到了女子父親,老人年高體弱;又做孩子父親的工作,孩子出生后腳有殘疾,家里出錢給孩子做了手術,和孩子感情基礎還是有的,但已經結婚;最后,社工以孩子爺爺奶奶為突破口,多次溝通,老人表示愿意撫養孫子。
但如何帶走孩子,著實讓豐臺民政局和社工為難。此前溝通涉及母子倆流浪的西城區、孩子父母所在地朝陽區、豐臺區,以及民政、公安、城管、法院、婦聯,尚且能通過各種途徑協調;但帶走孩子不但關乎人情,還有法律。關鍵時刻,民政局領導給了社工很大的支持。最終在社工和律師的勸說努力下,孩子父親愿意出面溝通安置問題,并承擔了孩子的養育責任。
“2016年,孩子辦了戶口上了學,現在又彈琴又畫畫。”蘇峰邊說邊掏出手機,“春節晚上12點,孩子父親準會給我發孩子照片,一年比一年變化大。”
這個孩子只是豐臺區1403名困境兒童中的一個,他們為困境兒童家庭建立了信息檔案,對260戶重點家庭進行了風險評估,并為高風險家庭提供跟蹤服務;為712個家庭提供監護干預、社會救助、心理疏導、教育矯治、技能培訓等服務;并形成了源頭預防—強制報告—應急處置—評估幫扶—監護干預等五大機制。
蘇峰特別看重源頭預防。一次,有個孩子因家暴找到社工,并報了警,蘇峰希望警察可以對孩子媽媽進行訓誡,警察卻勸孩子“你媽多不容易”,結果從晚上6點溝通到凌晨。“兒童福利觀念需要宣傳,相關技能更需要學習。”
“我從他的眼神里看到了對生活的信心”
2017年4月,微弱的嬰兒哭聲從一間女廁傳出,保潔員發現后馬上報了警。2018年12月,嬰兒媽媽馬某因遺棄罪被判刑一年六個月。
孩子在醫院完成治療后,被送到北京市兒童福利院養育,但監護權仍舊懸而未決。事發地海淀區民政局提起撤銷監護人資格訴訟,并找到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律師張雪梅,她曾代理了北京市第一例民政部門申請撤銷監護人資格案件。
“我們要先確定孩子生父、外祖父母能不能養。”張雪梅說。調查結果是:孩子生父不明;外祖父養著馬某的一個孩子,外祖母是繼母,也帶著一個孩子,生活壓力較大。最終,法院撤銷了馬某的監護權,指定海淀區民政局擔任監護人。
這或許不是事件的終點,兒童利益在每個階段可能是不一樣的。孩子后續的安置如何貫徹“兒童利益最大化”這一原則?在母親身邊長大無疑是最優選擇,母親是否愿意撫養孩子,恢復監護人資格是否可行?民政局和福利院正在研究,但也存在法律困境:按照《民法總則》,對被監護人實施故意犯罪的不能恢復監護人資格。
其實,民政部門履行對未成年人國家監護的兜底責任,北京從2003年就開始探索了。當年,張雪梅曾承辦過這樣一起案件。一個又聾又啞還有肢體殘疾的女人因家庭矛盾被接回娘家,后來女人丈夫去世,留下了10歲的孩子。孩子找到媽媽住處,砸門呼喊,奈何一墻之隔的媽媽根本聽不到。父親去世,母親不具備監護能力,是否啟動國家監護?經過一年多協調,民政積極作為,擔任孩子的監護人,協調了福利院,落實了國家監護。
這一案例也直接推動了《北京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2003年修訂時第十五條的出臺,父母死亡、喪失監護能力或者監護人監護資格被依法撤銷的未成年人,村居委會也不具備監護條件的,可以由民政部門依法擔任監護人,2017年《民法總則》確定了這一原則。
2017年底,一個小伙子找到了張雪梅,就是十幾年前那個孩子。他已經工作了,但不想離開福利院,“我的行李在那,就覺得那是我的家,我是有家的人。”一番勸解后,他決定離開福利院,“媽媽很不容易,將來我養她。”
“他走的時候,我從他的眼神里看到了對生活的信心,”張雪梅感嘆,“國家監護及時補位了,及時保障了,使他成為一個有能力的人,同時還能解決媽媽監護養老問題,這是多好的循環。”
如何守住陣地、探索邊界、形成合力
基層基礎能力提升,為北京困境兒童工作帶來了新發展,也提出了新要求。“首先,社工能力建設還不足,他們應該熟知各部門保障政策,還需要了解孩子心理建設能力。其次,政府購買服務的標準,目前沒有指導性意見,我們參照的是2017年三社聯動的資金使用標準,肯定比現在低。這意味著社會組織可能在掙很少的錢甚至不掙錢的情況下做事,不利于社會組織健康成長,也不利于社工職業發展。最后就是疑難個案,基本靠專家出主意,我們和相關部門協調,特別牽扯精力,有時甚至束手無策。”劉嵩說。
實踐中如何守住陣地、探索邊界、形成合力,這不僅是劉嵩面臨的問題,孫先禮也在思考。“兒童工作各個方面跟民政都有關系,各部門也在從不同角度做,民政作為牽頭,不可能包打天下。根據民政的職能,我們的主責主業是什么,配合協同是什么?聯席會議制度要發揮引導協調作用,任務如何分解、部署給誰,既各司其職又能相互配合,形成合力?”
兒童福利從補缺到適度普惠,未來是面對所有兒童的普惠,這也是北京民政人在研究的。“究竟做什么才能體現普惠?哪些需要民政做,哪些需要其他部門做?民政應該怎么做,工作切入點在哪兒?這還需要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