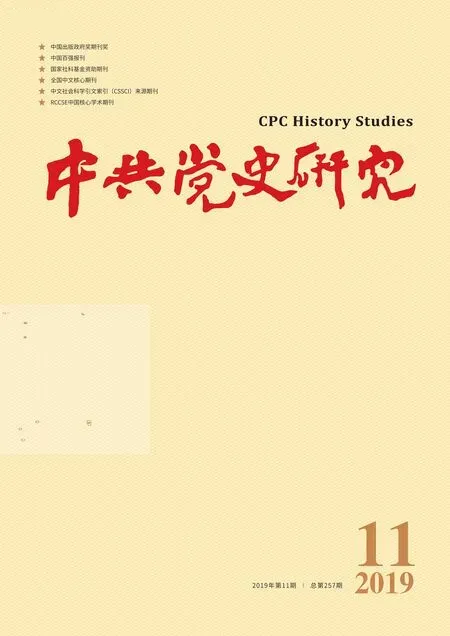知識分子視野下的“新革命史”研究*
唐小兵
近些年來,“新革命史”成為歷史學界研究20世紀中國歷史的一種新的學術取向。這種研究注重從政治史、社會史、文化史、心態史等不同視角,通過搜集、整理與解讀檔案、文集、報刊、書信、日記、回憶錄等多元史料來重構20世紀中國革命的歷史圖景,在“問題意識”、理論假設、學術路徑和解釋框架等方面都取得較大突破,比較有代表性的成果是王奇生、楊奎松、黃道炫、張濟順、裴宜理、石川禎浩等教授的研究著作和專題論文。這種“新革命史”的學術潮流不僅對于史學界內部重新認識和闡釋20世紀中國革命發生了重要影響,而且溢出了史學界,對于文學、政治學、法學和社會學等不同學科的學術研究都在發揮重要而持久的影響。可以說,“新革命史”正在形成一種新穎而有生命力的研究范式。
在“新革命史”的學術脈動之中,從知識分子的視角重審20世紀中國革命是一股特別值得重視的潮流。這一視角對于知識分子研究本身的深化和革命史研究的拓展都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知識分子研究注重的是在具體的歷史語境里既有意識又有行動的個體,關切的往往是知識人的政治、生活與觀念,而“新革命史”關注的往往是近代中國社會變革的動力、邏輯與機制,二者的結合自然會產生相得益彰的學術效果。
中國革命尤其共產主義革命恰恰是某種歷史規律的“例外”,依照陳旭麓的名言,中國的近代化并不是如朱維錚所言的“走出中世紀”,而是被“轟出中世紀”(1)《陳旭麓文集》第5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109頁。,可以說是伴隨著一系列外敵入侵之屈辱記憶的被動近代化過程。正因如此,社會的經濟基礎和基本結構并未滋長發育到與其時引入中國的思想潮流相匹配的程度,反而是先知先覺的士大夫和后來的新式知識人利用西方思想理論、按照各種藍圖來試圖全面改造中國社會。知識分子在近代中國的歷史變遷乃至后來的革命歷程中就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20世紀中國的三次革命,基本上是兩代知識分子領導的。其實不僅革命,近代以來所有改革、救國方案的提出和實施,無一不是知識分子主導的。近代中國的危機,源發于外,在西方列強有形的壓迫和無形的壓力下,知識分子先知先覺,也最敏銳,故而成為變革的先驅和革命的先行者”(2)王奇生:《高山滾石——20世紀中國革命的連續與遞進》,王奇生主編:《新史學》第7卷“20世紀中國革命的再闡釋”,中華書局,2013年,第3頁。。
知識分子視野的引入,對于拓展和深化“新革命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具有歷史的正當性、道德的正當性和意識形態的正當性,這三種正當性的建構都與知識分子階層具有密切關系。共產主義革命是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探求救國救民的真理和道路多次嘗試后的抉擇,是后五四時代大部分中小知識青年在紛繁復雜的各種主義潮流中的自覺選擇,這彰顯了革命的歷史正當性。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是為無產階級和底層庶民進行的社會革命,20世紀20年代初期的安源罷工就喊出了“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的響亮口號,這說明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具有解救受苦受難的勞苦大眾的道德正當性。共產主義革命的宣傳與動員依托于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等一整套社會理論學說,因此也具有意識形態維度的正當性。從這三方面來說,知識分子在共產主義革命歷史中具有相當重要的地位。進而言之,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具有神圣性和世俗性的雙重面孔,而神圣性源于超越對于一己私利之追逐,來源于對深受政治、經濟和精神壓迫的民眾的同情與解放的沖動,這種神圣性更多的是在投身共產主義革命的知識分子身上得以彰顯。
知識分子視野引入“新革命史”研究之后,大大拓展了“新革命史”的研究范圍與學術路徑,深化了“新革命史”研究的“問題意識”,也豐富了整個革命史研究的議題范疇。在傳統的革命史研究中,與工農階級相比較,知識分子處于相對邊緣的位置,而在城市與鄉村的對比中,又偏向于對農村根據地革命的研究,因為“農村包圍城市”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革命成功道路的經典論述。知識分子視野引入革命史研究以后,有助于破解此前單向度的歷史目的論式的論述,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復雜性尤其是相對于馬克思主義論述的革命普遍性模式的特殊性就能夠得到一定凸顯。可以說,知識分子視野是理解20世紀中國革命最重要的維度之一。
首先,知識分子視野有利于增強對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之理論性的重視。這種理論性不但包括革命理論從西方或日本進入中國的傳播、翻譯和接受過程,也包括這種革命理論是如何被本土的革命領袖和理論工作者進行再闡釋的。石川禎浩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指出:“重新審視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我們可以說那是‘天時、地利、人和’相互結合的結果。也就是,同一時期馬克思主義思潮在日本恰好重新復蘇并傳向中國,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基礎(天時);來自蘇俄的積極推動由于陸地相接而成為可能(地利);五四運動后信仰共產主義的中國知識分子的集結(人和)。”(3)〔日〕石川禎浩著,袁廣泉譯:《中國共產黨成立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第12—13頁。在這樣一種在地化和本土化的歷史脈絡中,研究者才能理解具有中國本土特質的革命思想觀念的歷史建構是如何完成的。源自西方的革命經典理論與具體的革命實踐之間的張力與對話,催生出共產黨人自覺追尋具有中國獨特性的一套革命思想的精神動力,而對這一過程的歷史性回溯與清理,無疑有助于理解“五四”啟蒙觀念、蘇俄外來理論學說與根據地革命形成的思想體系之間的長期沖突與磨合過程。正是在這樣一種視野中,艾思奇、柳湜、胡繩、胡喬木等左翼知識分子的本土論述的生產機制和傳播機制才變得可以理解,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也只有納入知識分子的理論視角才能得到完整理解,畢竟“中國知識分子在馬克思主義中發現了對于思想、價值和社會組織的功能性的解釋,它加強了新文化運動所認為的傳統價值與制度在當代中國無效的理論表述。新的出發點以跨歷史的訴求來拒斥中國傳統,這比起以源于西方價值的名義對于中國傳統的自由主義式的攻擊,要顯得更為合理和更具確定性——通過辯論傳統的史實性(historicity),唯物主義的觀點使得東方與西方之間的沖突成為多余”(4)〔美〕德里克著,翁賀凱譯:《革命與歷史:中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起源(1919—1937)》,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頁。。
其次,知識分子視野有利于彰顯和理解20世紀中國共產主義革命進程中城市的重要性。此前,一談到中國革命,習慣化地認為這是一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鄉村革命,是鄉村包圍城市、邊緣顛覆中心的階級革命。因此,挖掘中國革命中的鄉村元素,就成為論證中國革命具有本土性乃至民族性、中國性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如果尊重歷史事實,我們會發現中國革命的起源與發展其實與城市具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最早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和小組是在北京和上海出現的,中國共產黨也是在上海成立的。近代中國的城市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潮提供了新式學校、各種社團和現代大眾傳播媒介,而這些傳播新思潮的公共空間在中國的鄉村社會基本上是不具備的。或許正因為此,最早的一批共產黨員多是成長于城鎮的知識分子。城市為革命知識人的成長和交往提供了全新的空間,比如租界、學校、電影院、咖啡館、書店、報館、亭子間等共同塑造了知識人的價值理念、行為模式和情感方式。當我們把“城市性”這個因素帶回到中國革命的歷史闡釋中來,很多新的歷史研究論域就被打開了,比如城市的國際性與區域性問題,尤其上海作為現代中國最具有國際性的都市與東京、歐美城市之間的左翼思想和人員流動,城市與周邊乃至鄉村之間的思想、書籍、信息和人員的流動與互動,長期扎根鄉村的中共入城以后與城市的運作模式、管理方式乃至精神氣質之間的融合問題,等等。在這方面,最新的研究如高崢《接管杭州:城市改造與干部蟬變(1949—1954)》(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年)、張濟順《遠去的都市:1950年代的上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等便涉及這個問題。從更早的研究中,還可以看到葉文心筆下的施存統在金華、杭州與上海這幾座城市之間的穿越,蕭邦奇筆下的沈定一在衙前、杭州與上海之間的奔走,等等。回溯傳統革命史的已有論述,在很大意義上,晚清民國所形成的城市性被簡化為資產階級文化的象征,而在這些城市里寄身活動的知識人也就成為具有“原罪”的階層。從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來看,南北問題、城市文化與鄉土文化、中心與邊緣、國統區與解放區等問題,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脈動里成為長久困擾其進程的重大議題。
再次,知識分子視野有利于在一個更為縱深和廣闊的脈絡里理解這個階層在中國革命中實際扮演的角色和發揮的作用。在此前的不少革命史書寫里,知識分子總是作為“皮之不存毛將焉附”論中的“毛”而存在,是一種被嚴重低估了能動性和主體性的歷史存在。事實上,知識分子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動員、宣傳與組織過程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可以說是一場由先知先覺并且富有歷史使命感的知識分子發動起來的革命,是以新思潮、新理論、新觀念等革命理論掀動中國社會的革命。就此而言,無論怎樣評估知識階層的作用都不為過。王奇生曾有一個判斷:“五四以后,知識分子最鮮明特質不是‘邊緣化’,而是革命化。正是全面性的危機,導致知識界全體性的激化。”(5)王奇生:《高山滾石——20世紀中國革命的連續與遞進》,王奇生主編:《新史學》第7卷“20世紀中國革命的再闡釋”,第10頁。張灝也曾指出:“中國近代思想在1895年以后,傳統的核心價值與宇宙觀開始解體,在知識分子里產生普遍的精神失落與思想迷惘。在惶惶的文化解體過程中,他們急需一種新的個人與群體生命的方向感、文化認同與精神的歸屬感。到了五四時代,這種精神失落已經變得很普遍,形成一種文化基本取向的危機。五四健將羅家倫用‘回旋時代’來描寫當時他們所面對天旋地轉的精神世界,最能凸顯這種文化取向的危機震撼。”(6)張灝:《五四與中共革命:中國現代思想史上的激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總第77期,2012年9月,第15頁。在政治秩序與心靈秩序的雙重危機之中,知識分子既是這種危機最敏銳的感知者和直接的見證人,也是最努力試圖改變中國危機狀況的社會精英,革命就成為最重要的社會變革方式之一。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于知識分子在革命過程中的角色、處境與功能的研究,就成為“新革命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
就動員而言,中共在鄉土中國對農民等底層民眾的動員,很大程度上依托于鄉村小學教師。鄉村的地方文化精英和小知識分子成為革命理論的“二傳手”,他們成為聯結城市革命精英與鄉村普羅大眾的最佳中介。按照劉昶的說法,這群人是中國革命的“普羅米修斯”(7)參見劉昶:《革命的普羅米修斯:民國時期的鄉村教師》,黃宗智主編:《中國鄉村研究》第6輯,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42—71頁。;最近應星的歷史社會學研究也指出了這一面相(8)參見應星:《新教育場域的興起(1895—1926)》,北京三聯書店,2017年,第209—222頁。。《中國青年》曾發文指出:“中國的小學教員,在客觀上至少也應當是國民黨左派的群眾,階級認識更清楚的進步分子應當毫不畏懼地站在共產黨和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紅旗之下。他們應當是社會各階級建立聯合戰線的‘連鎖’;他們應當是農民運動的最適宜的人才;他們應當是鄉村文化運動中心的力量;他們應當是散布革命種子在各地建筑革命勢力的先鋒!小學教員在社會的地位,一面可以與紳士、商家、地主相接近,同時也可與農民工人相接近。他與資產階級利害的沖突沒有工農的明顯,而他的一點師長的威信,又可獲得封建觀念未消滅的鄉村人民的相當敬意。農民對于小學教員的尊敬信仰,更不用說,所以小學教員如果以民族的利益來號召,必然能在鄉村中建立各階級的聯合戰線而無疑。這種聯合戰線的建立,對于民族、對于工農,對于小學教員本身,都有絕對的利益。但是如果除去這介于中間的小學教員與學生做連鎖,這個聯合戰線時時都有破裂的危機。”(9)砍石:《怎樣做小學教師》,《中國青年》第138期,1926年10月。在城市里,無論發動工人參加罷工還是吸納中小知識青年投身左翼文化運動乃至共產主義革命,都離不開知識分子的作用。如裴宜理研究安源這座小城的罷工政治,就敏銳地注意到李立三、毛澤東、劉少奇等人是如何充分利用基層社會尊重讀書人這一文化傳統來進行“文化置位”的。可以說,離開了知識分子,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就無從談起。就宣傳而言,中共自20年代一誕生就一枝獨秀,在意識形態競逐的場域里一直處于主導地位,這與一批卓越的宣傳家比如早期的陳獨秀、瞿秋白、惲代英、蕭楚女、彭述之以及后來的胡喬木、鄧拓等發揮的歷史作用密不可分,而這些人無一例外都是知識分子出身。從知識分子的視野切入,重新審視20年代中共與國民黨尤其是中國青年黨的理論競爭和思想激辯——其實質是爭奪被政治化的進步青年——就可以為打開這個影響中國至深且遠的“1920年代”提供最有效的歷史路徑,比如在《中國青年》《向導》等期刊上進行的中共與醒獅派、國家主義者的大論戰。就組織而言,中共從一產生就深受蘇俄組織體制之影響,后來又派出劉少奇、蔡和森、李立三等一大批知識分子黨員到莫斯科東方大學等學習蘇俄的組織方式,而在大革命失敗后面對國民黨的高壓更是逐步錘煉其組織的嚴密性與靈活性。相對于國民政府黨政系統的二元化傾向及其帶來的組織系統的分散(10)參見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國民黨的組織形態》,華文出版社,2010年。,中共在純化組織隊伍和灌注革命意識形態等方面都有可圈可點之處,而這些都離不開知識分子群體在其間扮演的重要角色。
最后,知識分子視野有利于拓寬“新革命史”的研究路徑以及深化相關議題的討論。一提到革命史研究,習以為常的學術路徑是政治史、社會史等研究方法,預設的往往是政黨如何動員和組織民眾,對于1949年后的當代史研究也經常是預設了一些基本問題,如政治力量和意識形態話語是如何伸展到基層社會和地域社會的或不同地域社會和文化對于革命政治的差異化應對。但若將知識分子視野引入,對于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研究將能由此及彼、由表入里,精神史、心靈史和思想史等學術路徑都可以逐步導入。按照一些學者的分析,中共與知識分子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關系曾經發生過多次變化。在筆者看來,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共產主義革命按經典定義應該是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革命和政治革命,但事實上不得不在較大程度上依靠小資產階級和沒落士紳家庭出身的知識分子,革命的理論預設與革命的實際運作之間存在一種無法消解的悖論。正因如此,在40年代的延安,黨的刊物就曾提出“知識分子的工農群眾化”和“工農干部的知識分子化”這一看上去似乎矛盾的命題(11)《中央關于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共產黨人》第1卷第3期,1939年12月1日。。事實上,若從共產主義革命的長程和特征來看則絲毫不讓人費解,前者表征著對知識分子進行改造的意圖,而后者是在實際的革命過程里覺得必須提升工農的文化水準才能有效開展工作。正是知識分子的參與,帶來了這場革命的豐富面相,也給這場革命帶來了一種天然的崇高性與超越性,更賦予這場革命以一種不容忽視的復雜內涵。
知識分子視野的引入使得“新革命史”研究的內涵與外延得到極大豐富,而中共革命與知識分子尤其是邊緣知識分子的深刻而復雜的關系也在“新革命史”研究的推進過程中得到更有力的揭示。有學者指出:“近代以還,由于上升性社會變動的途徑多在城市,邊緣知識分子自然不愿認同于鄉村;但其在城市謀生甚難,又無法認同于城市,故其對城鄉分離的情勢感觸最深。他們不中不西,不新不舊;中學、西學、新學、舊學的訓練都不夠系統,但又粗通文墨,能讀報紙;因科舉的廢除已不能居鄉村走耕讀仕進之路,在城市又缺乏‘上進’甚至謀生的本領;既不能為桐城之文、同光之詩而為遺老所容納,又不會做‘八行書’以進入衙門或做漂亮駢文以為軍閥起草通電,更無資本和學力去修習西人的‘蟹行文字’從而進入留學精英群體。他們身處新興的城市與衰落的鄉村以及精英與大眾之間,兩頭不沾邊也兩頭都不能認同——實際上當然希望認同于城市和精英一邊而不太為其所接受。”(12)羅志田:《權勢轉移:近代中國的思想與社會》,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34頁。這些在社會流動中居于邊緣的知識群體,相當一部分因為理想主義的感召、民族主義的刺激和現實生活的困頓而投身改造社會和改造自我的革命之中。邊緣知識分子在中共革命中的位置、處境、角色與命運,賦予了這場革命不同于辛亥革命和國民革命的特質與底色,比如共產主義革命中的群眾性與階級性、革命在城市里對中小知識青年的動員和吸納等,而這恰恰是“新革命史”研究值得進一步去探尋和挖掘的學術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