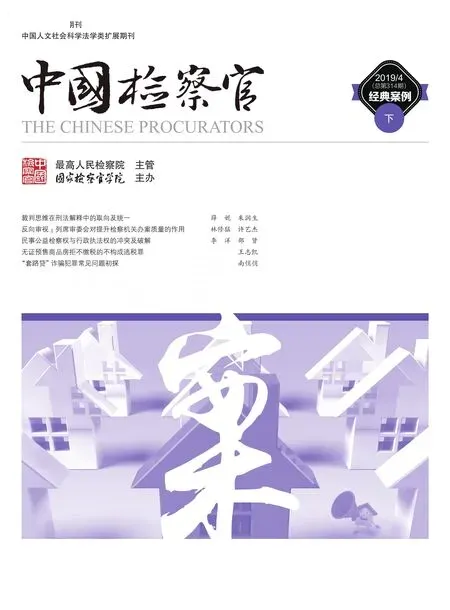主客觀一致原則在審查確證販賣毒品數量中的運用
/文
一、案例及問題
(一)基本案情
2017年12月12日17時許,被告人劉某以人民幣100元的價格販賣1袋白色晶體給張某,后被公安民警查獲。民警從被告人劉某身上搜出販毒所得毒資100元,從其居住房屋二樓抽屜搜出1袋白色晶體(凈重3.98克),從購買毒品的張某身上搜出1袋白色晶體(凈重0.28克)。經公安機關物證部門檢驗,上述2袋白色晶體中均檢出甲基苯丙胺成分。此外,偵查人員還從劉某房屋二樓樓梯吊頂處搜出3袋白色晶體,凈重分別是19.2克、47.14克、48.5克。凈重47.14克的1袋白色晶體中檢出甲基苯丙胺成分,含量為1.3%,其余2袋白色晶體中未檢出甲基苯丙胺成分。劉某辯稱3袋白色晶體是別人送的,準備冒充真冰毒出售,但由于顏色、外形與真冰毒相差太大,并不打算出售。檢出甲基苯丙胺成分的1袋白色晶體(凈重47.14克),因原外包裝破損,曾用裝過真冰毒的封口袋換裝,當時袋壁上殘留有冰毒成分。
(二)本案中的問題
本案劉某構成販賣毒品罪無爭議,對不準備出售但檢出甲基苯丙胺成分的1袋白色晶體(凈重47.14克)應否計入販賣數量,存在較大分歧。依據《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釋規定,販毒人員被抓獲后,對于從其住所、車輛等處查獲的毒品,一般均應認定為其販賣的毒品。根據認定犯罪主客觀一致原則,劉某對47.14克白色晶體不打算出售,即沒有販賣的故意,不能計入販賣數量。再者,如果計入販賣數量,則販賣總數量將超過50克,對劉某將在15年有期徒刑以上量刑,似乎又太重。于是,有人提出折衷方案,該部分毒品不宜認定為販賣毒品數量,但可以認定為非法持有的數量,按非法持有毒品罪處理;或將47.14克白色晶體中的毒品部分計入販賣數量,即按1.3%的比例折算后計入販賣數量。還有人認為劉某歸案后為逃避法律處罰,謊稱不準備販賣,實為準備販賣,其抗辯屬于“幽靈抗辯”,不應采信。
本案既有證據采信問題,也有客觀事實認定問題,還有法律及司法解釋的適用問題,多個問題交織,使本案處理較為棘手。應對此類疑難復雜案件,首先從證據分析論證入手,認定犯罪嫌疑人的抗辯理由能否成立。其次,在證據基礎上準確還原案件的事實,力爭使司法認定事實無限接近于客觀事實。再次,在認定的案件事實基礎上考慮法律適用問題,不僅要考慮當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釋規定,還要考慮法律適用的一般原則等。最后,要從法律適用效果反過來檢驗法律適用的正確性。該過程正如張明楷教授所言,身為司法者,當內心永遠充滿正義,目光不斷往返于規范與事實之間,最終實現刑法的正義性、安定性與合目的性。
二、全面審查證據、還原案件客觀事實
有人認為,劉某歸案后為逃避處罰,謊稱該袋毒品不準備出售,不能輕信其辯解。要對案件作出正確的處理,必須建立在對現有證據的分析論證基礎上,關于劉某辯解能否成立,事實究竟如何認定,是本案首先要解決的問題。
對此袋毒品的用途,劉某供述前后矛盾,先是供述給女朋友買來做美容產品,叫“二甲汾研”,后來又供述是一個叫“勇娃”的朋友送給自己,自己準備用來當真冰毒賣的。但拿回家后發現3袋假毒品與真毒品外觀差別很大,賣不出去,所以并不打算出售。其供述中提到的“勇娃”偵查人員無法查找到。關于從1袋白色晶體中檢出甲基苯丙胺成分的問題,劉某辯解是用包裝過真冰毒的袋子裝該包白色晶體,因袋壁上殘留有真冰毒,故檢出甲基苯丙胺成分。從檢測結果來看,也支持了劉某的供述,只有1包冰毒檢出甲基苯丙胺成分,含量為1.3%,另2包白色晶體中沒有檢出甲基苯丙胺成分。這3包白色晶體外觀與偵查人員從劉某處查獲的真冰毒明顯不同,顏色偏黃。從搜查筆錄、存放位置、檢測結果等支持了劉某的供述。對于劉某故意混裝,準備將該袋白色晶體當真毒品出售的假設,不能獲得在案證據的支持,該假設不能成立。
三、遵循主客觀一致原則、準確認定販賣的毒品罪數量
(一)販賣毒品數量認定應遵循主客觀一致原則
我國《刑法》總則規定了主客觀一致的歸罪原則,學者們普遍認為,從《刑法》體例安排來看,總則和分則兩者間的關系是一種抽象與具體、普遍與特殊的關系。總則規定指導分則,分則條款受總則條款的約束,總則規定的一般性規定,適用于分則條款。如《刑法》總則第14條規定,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并且希望或放任這種結果發生,因而構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反之,沒有犯罪故意的行為,只能評價為過失或意外事件。對于過失犯罪,法律有規定的才負刑事責任,沒有規定的,即便產生了危害后果,也不負刑事責任。換言之,對沒有犯罪故意的行為評價為故意犯罪,沒有遵循主客觀一致原則,屬客觀歸罪。
從刑法規定的毒品犯罪來看,所有的毒品犯罪均是故意犯罪,過失販賣、運輸、持有毒品的,均不能按犯罪來處理。涉案的1袋白色晶體,被告人劉某雖存放在家中,但不準備用于販賣,其主觀上沒有販賣的故意。反之,如果從販毒分子住處搜出的毒品,不管犯罪分子是否用來販賣,一律認定為販賣數量,有客觀歸罪之嫌。同理,在劉某看來,這就是1袋白色晶體,其主觀上也沒有當作毒品來持有,沒有持有毒品的犯罪故意,也不能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關于折算的觀點,袋壁殘留的1.3%的真毒品,在與冒充假毒品的白色晶體混同前,可能是準備用于吸食或者用于販賣,按司法解釋規定計入販賣數量沒有爭議。但與冒充真毒品的白色晶體混同后,劉某主觀上并沒有打算將該袋白色晶體(含1.3%毒品成分)出售,按主客觀一致的歸罪原則,將折算后的毒品成分計入販賣數量也不妥當。
(二)販賣沒有毒品成分的假毒品應定性為詐騙
《刑法》第13條規定了犯罪含義,即有社會危害性且達到一定程度的行為,才是犯罪行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認定劉某的行為是否成立犯罪,前提和基礎是該行為必須具備社會危害性。劉某本打算將白色晶體冒充真毒品出售,但由于外觀與真毒品差異較大,遂擱置在家里,沒有對外出售。“兩高”解釋及司法實踐中,對以假毒品冒充真毒品出售的,數額較大,一般按詐騙罪來處理。劉某拿假毒品回家存放準備對外出售,屬于為了實施詐騙犯罪而準備工具、制造條件的行為,只能認定為詐騙罪的預備犯。后來,因為客觀原因,放棄出售該部分假毒品,可以評價為預備階段的犯罪中止,根據《刑法》第22條、第24條規定及詐騙罪的相關司法解釋,對于詐騙罪的預備犯,且系犯罪中止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一般不予處罰。所以,對劉某也不能按詐騙罪來處理。
(三)適用司法解釋不得違背刑法的基本原則
法律賦予“兩高”司法解釋權,目的在于填補法律漏洞,指導辦案,因而具有普遍效力。在法律適用過程中,通過對法律文本的解釋,雖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立法的不足與缺陷,使法律趨于完備。但是,如同立法,司法解釋是在人的認知基礎上的法律再造,同樣不能擺脫類似立法一樣的窘境,在解決當下法律缺陷時,必會形成新的缺陷。有的辦案者高度依賴司法解釋,不分情形不加考慮拿來就用,勢必與法律規定的原則、精神相違背,也難以得出令公眾信服的結論。所以,我們應當理性看待司法解釋,在法律規定的原則框架內適用。就本案而言,司法解釋規定從販毒分子住處搜出的毒品算作販賣的數量,暗含的前提是販毒分子本身是要準備出售該部分毒品,此種情形計入販賣數量沒有多大問題。但如果販毒分子對查獲的毒品本不打算販賣,如認定販賣數量則違背刑法的定罪原則。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再來看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一方面規定從販賣人員住處、車輛等處查獲的毒品,一般均應認定為其販賣的毒品;另一方面又規定,確有證據證明查獲的毒品并非販毒人員用于販賣,其行為另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窩藏毒品等其他犯罪的,依法定罪處罰。這里,解釋用的“一般均應認定”,也就是說還有不認定的情形,還可另行認定非法持有、窩藏類毒品犯罪。當然,依據主觀故意的不同內容,在特殊情況下也可能出現不認定為犯罪的情形,這樣解釋也符合司法解釋本來的含義。
四、刑事辦案應實現政治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統一
《刑法》第5條規定:“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所犯罪行重的,承擔較重的刑事責任,所犯罪行較輕的,承擔較輕的刑事責任。劉某實際販賣及查獲的準備用于販賣的毒品數量4.26克,不足10克,如果加上爭議的1包白色晶體,數量將超過50克,按《刑法》第347條第2款的規定,法定最低刑為15年。從案情來看,劉某是以販養吸,是在一線從事零包販毒的小毒販,處在販賣毒品網絡的最底層,查證屬實的販賣數量也較小,如果除去自己吸食部分,販賣數量更少,根據司法解釋規定要酌情從輕處罰。對這樣一個小毒販來說,處以15年有期徒刑,怎么都覺得不合適。
也許有人認為,法律本身就是這樣規定,作為執法者應當嚴格遵循法律規定,既然查獲了這么多毒品,就應當按法律及司法解釋的規定執行,如果說對劉某判刑重了不合適,是法律規定本身不合理,與辦案人員無關。在新時代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背景下,對司法機關執法辦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僅要追求辦案的法律效果,更要追求辦案的政治效果和社會效果,做到三個效果的統一。許多案件,我們按法律的規定得出案件處理結論,但與人們期待相差甚遠,甚至引發道德滑坡,未能倡導良善的社會價值等,因而受到人民群眾的質疑。有的司法人員在辦案中,習慣于將法條或司法解釋拿來就用,沒有更深層次考慮案件辦理的社會效果,所做的司法裁判、決定等難以獲得人民的認同。可喜的是,現在的司法辦案者更加注意傾聽人民的呼聲,如江蘇昆山龍哥砍人反被砍案中,司法機關以“正不能向不正讓步”為理由,認定本案中的正當防衛情節,作撤案處理,獲得老百姓點贊。對案件的處理,除法律效果外,辦案人員很大程度上也考慮了辦案的社會效果。在嚴格解釋法律基礎上,得出對本案中劉某不打算販賣的那袋白色晶體不計入販賣數量的結論,實現罰當其罪。
張軍檢察長要求全體檢察辦案人員不僅要做辦案的“工匠”,而且還要做辦案的“大師”,要通過辦案倡導良善的社會價值觀,傳遞社會正能量,讓人民群眾從檢察執法辦案中感受到公平正義,這是每名檢察辦案人員的奮斗目標。劉某案中,對其販賣的毒品數量的審查確證,就是貫徹張軍檢察長新要求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