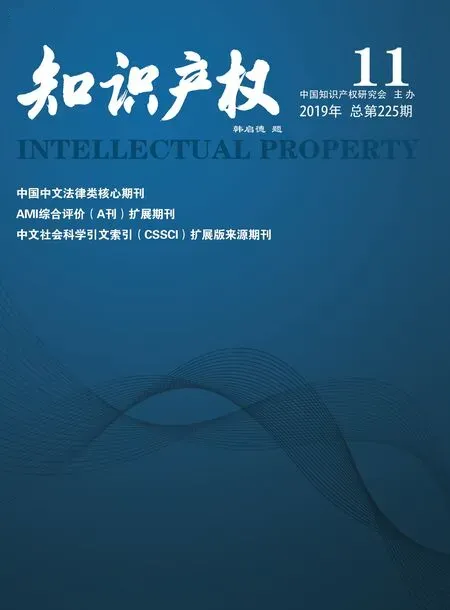論書刊版式專有權(quán)的保護(hù)范圍
——關(guān)于《著作權(quán)法》第36條的解釋論問題
李 楊
內(nèi)容提要:書刊版式專有權(quán)是我國(guó)《著作權(quán)法》第36條授予出版者的一項(xiàng)著作鄰接權(quán)。從歷史之維考察,版式專有權(quán)與著作權(quán)之間存在著緊密的特定聯(lián)系,重在發(fā)揮制止版式影印盜版等摹本復(fù)制和非法傳播這一反不正當(dāng)競(jìng)爭(zhēng)機(jī)制本應(yīng)具備的功能。版式專有權(quán)的保護(hù)范圍問題應(yīng)當(dāng)從權(quán)利客體和權(quán)能范圍兩個(gè)維度進(jìn)行考察:從權(quán)利客體來看,版式專有權(quán)并非設(shè)計(jì)人針對(duì)圖文版面布局所提出來的獨(dú)創(chuàng)性表達(dá)部分,而是書刊版面布局經(jīng)過排版制作、編輯及加工之后的最終呈現(xiàn)形式——版面形式,不應(yīng)參照作品的獨(dú)創(chuàng)性要件來認(rèn)定是否受著作權(quán)法保護(hù)。同時(shí),版式專有權(quán)應(yīng)理解為出版者對(duì)同一出版內(nèi)容之出版物的版面形式所享有的權(quán)利。從權(quán)能范圍來看,版式專有權(quán)主要規(guī)制以影印或類似方式對(duì)版面形式實(shí)施的摹本復(fù)制,實(shí)際上關(guān)注從客體保護(hù)邊界而非行為模式范疇對(duì)其保護(hù)范圍進(jìn)行界定。通過考察各國(guó)立法例和法解釋學(xué)分析,無論是從實(shí)然還是應(yīng)然層面,版式專有權(quán)的權(quán)能范圍都有必要延伸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利益。
一、問題的提出
一本優(yōu)秀的出版物是傳播內(nèi)容(由作者創(chuàng)作)和出版形式(由出版者編排)的有機(jī)結(jié)合。①陳傳夫編著:《著作權(quán)概論》,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93年版,第127 頁(yè)。書刊版式專有權(quán)是我國(guó)授予出版者享有的一項(xiàng)法定權(quán)利,著作權(quán)法將其客體表述為“版式設(shè)計(jì)”。從狹義來看,版式設(shè)計(jì)是“出版者在編輯加工作品時(shí)完成的勞動(dòng)成果”,體現(xiàn)為“對(duì)印刷品的版心、排式、用字、行距、標(biāo)點(diǎn)等版面布局因素的安排”。②胡康生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著作權(quán)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49 頁(yè)。作為我國(guó)法定的著作鄰接權(quán)之一,版式專有權(quán)同表演者權(quán)、錄音錄像制作者權(quán)以及廣播組織權(quán)等一起,被設(shè)置在著作權(quán)法的鄰接權(quán)部分。司法實(shí)踐中,出版者多以出版合同為基礎(chǔ)的專有出版權(quán)來保護(hù)相關(guān)利益,以版式專有權(quán)主張權(quán)益的案件數(shù)量并不太多,學(xué)術(shù)論著對(duì)版式專有權(quán)的理論解釋也極為簡(jiǎn)略。版式保護(hù)條文看似簡(jiǎn)易清晰,實(shí)則對(duì)版式專有權(quán)的內(nèi)涵、保護(hù)范圍等并未進(jìn)行明確界定。依據(jù)我國(guó)《著作權(quán)法》第36條的規(guī)定,出版者有權(quán)許可或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圖書、期刊的版式設(shè)計(jì);書刊版式專有權(quán)的保護(hù)期為十年,截止于使用該版式設(shè)計(jì)的圖書、期刊首次出版后第十年的12月31日。然而,該條文至少有以下幾個(gè)問題亟待澄清。
首先,版式專有權(quán)究竟保護(hù)什么,是否應(yīng)以客體的獨(dú)創(chuàng)性要件作為權(quán)利保護(hù)的基礎(chǔ)?對(duì)此,司法實(shí)務(wù)和理論界存有較大分歧: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版式專有權(quán)保護(hù)的是一種智力成果,需要由設(shè)計(jì)者進(jìn)行獨(dú)立的智力創(chuàng)作。如在吉林美術(shù)出版社訴海南出版社一案再審裁定中,最高人民法院認(rèn)為:“在判斷出版者是否享有版式設(shè)計(jì)專用權(quán)時(shí)……應(yīng)由原告對(duì)版式設(shè)計(jì)是否系其獨(dú)立創(chuàng)作進(jìn)行舉證,就版式設(shè)計(jì)的意圖、特點(diǎn)、設(shè)計(jì)元素、布局及安排等獨(dú)創(chuàng)部分進(jìn)行說明。”③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150 號(hào)民事裁定書。而另一種觀點(diǎn)則認(rèn)為版式設(shè)計(jì)與作品不同,難以達(dá)到獨(dú)創(chuàng)性的要求。著作權(quán)法保護(hù)版式專有權(quán)是考慮到出版者在傳播作品的過程中投入了勞動(dòng)和大量資金,“雖然出版社的版式設(shè)計(jì)難以達(dá)到獨(dú)創(chuàng)性的要求,但如果放任其他出版社在出版作品時(shí)隨意地使用其版式設(shè)計(jì),……這顯然是不公平的。”④王遷著:《著作權(quán)法》,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299 頁(yè)。
其次,是否可以脫離出版內(nèi)容對(duì)版式專有權(quán)進(jìn)行獨(dú)立保護(hù)?在前述案件再審裁定中,最高人民法院主張“版式設(shè)計(jì)是一種融合多種設(shè)計(jì)元素的布局……版式設(shè)計(jì)雖服務(wù)于內(nèi)容,但獨(dú)立于內(nèi)容而存在”⑤同注釋③。。依此邏輯,即便出版物的內(nèi)容并不相同,但若使用與他人相同的版式設(shè)計(jì),仍可能構(gòu)成對(duì)他人版式專有權(quán)的侵害。另有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出版物的版式畢竟是有限的,對(duì)于不同的出版物,即使借用了他人的版式設(shè)計(jì),也會(huì)因圖書內(nèi)容的不同而導(dǎo)致最終呈現(xiàn)出不同的效果。⑥蘇志甫:《〈侵害著作權(quán)案件審理指南〉條文解讀(六)》,載http://www.sohu.com/a/245445454_221481,最后訪問日期:2019年3月5日。因此,“只能將版式設(shè)計(jì)權(quán)理解為對(duì)同一本出版物,出版者有權(quán)禁止他人進(jìn)行完全或基本相同的復(fù)制”。⑦王遷著:《著作權(quán)法》,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299 頁(yè)。
再者,如何理解版式專有權(quán)的專有“使用”權(quán)能以及該權(quán)能可否延伸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利益?在中國(guó)建筑工業(yè)出版社訴北京怡生樂居信息服務(wù)公司案終審中,上訴人主張《著作權(quán)法》第36條規(guī)定出版者享有對(duì)版式設(shè)計(jì)的專有“使用”權(quán)應(yīng)當(dāng)包括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利益,“使用”并非局限于“復(fù)制”,“復(fù)制”只是“使用”的環(huán)節(jié)之一。對(duì)此,北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維持一審裁判解釋,認(rèn)為版式專有權(quán)的保護(hù)范圍較狹小,一般以專有復(fù)制權(quán)為限。同時(shí),依《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保護(hù)條例》第2條的規(guī)定,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的權(quán)利客體僅限于作品、表演及錄音錄像制品,并未涵蓋版式設(shè)計(jì),故法院對(duì)版式專有權(quán)應(yīng)包括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利益的原告主張未予支持。⑧參見北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2017)京73 民終164 號(hào)民事判決書。
由上可知,我國(guó)《著作權(quán)法》第36條的相關(guān)規(guī)定含混不清,司法實(shí)務(wù)和學(xué)界對(duì)版式專有權(quán)的認(rèn)識(shí)和理解仍存在分歧,莫衷一是。這些問題源自對(duì)版式專有權(quán)保護(hù)范圍的研究不夠深入,既欠缺對(duì)版式專有權(quán)保護(hù)基礎(chǔ)的方法論解釋,又在版式專有權(quán)的內(nèi)涵、客體與權(quán)利內(nèi)容等精細(xì)化解釋上亟待完善。在本文看來,書刊版式專有權(quán)的保護(hù)范圍問題需要從權(quán)利客體和權(quán)能范圍兩個(gè)維度進(jìn)行考察,這些解釋論問題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shí)踐意義,值得進(jìn)一步研究。
二、書刊版式專有權(quán)與著作權(quán)之譜系溯源
作為出版者在作品編輯加工時(shí)享有的一項(xiàng)權(quán)利,版式專有權(quán)在歷史形成脈絡(luò)中與著作權(quán)之間存在著緊密的特定聯(lián)系。一直以來,出版者通過出版合同約定取得作者授予的包括復(fù)制權(quán)、發(fā)行權(quán)在內(nèi)的專有出版權(quán)。通常情況下,出版者僅依專有出版權(quán)就可以獲得對(duì)編排出版作品相關(guān)利益的有效保護(hù)。然而,自19世紀(jì)后期圖文版面布局編排和制作技藝發(fā)生巨大變革與改進(jìn)以來(特別是影印技術(shù)在一戰(zhàn)期間的飛躍式發(fā)展),圖文印版能夠以影印方式被他人輕松地精準(zhǔn)復(fù)制。這引起了出版商們的憂慮,他們很擔(dān)心在經(jīng)典出版物中投入大量勞動(dòng)和技藝的版面形式會(huì)被其他不法商販以摹本復(fù)制(making a facsimile copy)的影印方式惡意侵占。⑨See Newspaper Licensing Agency Limited v.Marks &Spencer PLC [2001]UKHL 38,para.6.由此,出版商們開始呼吁在出版合同約定的專有出版權(quán)以外專門獲得一項(xiàng)對(duì)版面形式的特別權(quán)利保護(hù)。
在1935年,英國(guó)出版者協(xié)會(huì)向國(guó)際著作權(quán)專業(yè)委員會(huì)提交請(qǐng)?jiān)笗?qǐng)求他們?cè)诓疇柲峁s修訂會(huì)議中提議創(chuàng)設(shè)一項(xiàng)版式著作權(quán)。國(guó)際著作權(quán)專業(yè)委員會(huì)隨后在1935年5月的伯爾尼公約修訂議程報(bào)告中提及該請(qǐng)?jiān)竷?nèi)容,但各國(guó)與會(huì)代表對(duì)此并未作出積極回應(yīng)。直到二戰(zhàn)以后,英國(guó)出版者協(xié)會(huì)借英國(guó)啟動(dòng)著作權(quán)法修訂工作之機(jī),再次向國(guó)際著作權(quán)委員會(huì)提交請(qǐng)?jiān)笗笤谛滦抻喌牧⒎ㄎ谋局屑尤氚媸街鳈?quán)保護(hù)條款,受到英國(guó)立法機(jī)關(guān)的重視。正如英國(guó)著作權(quán)委員會(huì)在1952年10月向議會(huì)提交的修訂報(bào)告中所言:“為了防止文學(xué)或音樂作品的特定出版物被不法商販以影印或類似的不正當(dāng)方式實(shí)施直接且精準(zhǔn)的拷貝,出版者協(xié)會(huì)請(qǐng)求創(chuàng)設(shè)一項(xiàng)版式著作權(quán)來保護(hù)相關(guān)利益是合理的……此項(xiàng)利益在其他一些國(guó)家可以通過反不正當(dāng)競(jìng)爭(zhēng)法予以保護(hù),但在英國(guó)卻難以獲得類似的充分救濟(jì)。”⑩UK Copyright Committee Report of October 1952,para.306.由于英國(guó)著作權(quán)法律體系沒有鄰接權(quán)制度,故著作權(quán)委員會(huì)建議在著作權(quán)客體中直接加入出版物的“版式編排(typographical arrangement)”,限定其權(quán)利范圍僅在于禁止以影印或類似方式對(duì)“版式編排”實(shí)施的摹本復(fù)制,確立出版者為其作者和著作權(quán)主體。該建議被立法機(jī)關(guān)采納,最終在1956年英國(guó)著作權(quán)法中得以體現(xiàn),一直沿用至今。在立法者看來,英國(guó)的版式著作權(quán)旨在保護(hù)編排和制作出版物之特定版面形式所付出的勞動(dòng)和投資,重在發(fā)揮制止版式影印盜版等摹本復(fù)制和非法傳播這一反不正當(dāng)競(jìng)爭(zhēng)機(jī)制本應(yīng)具備的功能。
同樣是采用著作權(quán)保護(hù)模式,法國(guó)并未將圖文裝幀與版式作嚴(yán)格區(qū)分,仍以獨(dú)創(chuàng)性作為構(gòu)成要件和保護(hù)基礎(chǔ),于1985年在法國(guó)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典修訂中創(chuàng)設(shè)了一項(xiàng)獨(dú)立的“裝幀及版式作品”(works of graphiques et typographiques)類型。?《法國(guó)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典(法律部分)》,黃暉、朱志剛譯,商務(wù)印書館2017年版,第5 頁(yè)。依據(jù)《法國(guó)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典(法律部分)》L.112-2條的規(guī)定,裝幀及版式作品可以構(gòu)成具有獨(dú)創(chuàng)性的作品類型之一,其權(quán)利內(nèi)容、保護(hù)期限等與其他作品并無實(shí)質(zhì)性差別,著作權(quán)仍歸屬于享有作者身份的制版設(shè)計(jì)人。而同為大陸法系的德國(guó)與我國(guó)臺(tái)灣地區(qū),則對(duì)特定出版物的版面形式采用著作鄰接權(quán)的保護(hù)模式。例如《德國(guó)著作權(quán)法》在著作權(quán)之外賦予整理人(而非出版者)對(duì)古籍科學(xué)版本享有一項(xiàng)特殊的著作鄰接權(quán),其不僅在版本發(fā)表之日起25年內(nèi)享有排他性的復(fù)制權(quán)與發(fā)行權(quán),還獨(dú)立享有公開再現(xiàn)權(quán),旨在保護(hù)整理人為科學(xué)版本形式所付出的勞動(dòng)投入。?[德]M.雷炳德著:《著作權(quán)法》,張恩民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99 頁(yè)。在我國(guó)臺(tái)灣地區(qū),為了應(yīng)對(duì)20世紀(jì)60年代以來對(duì)無著作權(quán)但經(jīng)出版業(yè)者加工排印之出版物的盜印泛濫現(xiàn)象,在我國(guó)臺(tái)北市教科書出版協(xié)會(huì)的多次請(qǐng)?jiān)竿苿?dòng)下,我國(guó)臺(tái)灣地區(qū)“著作權(quán)法”第79條針對(duì)無著作財(cái)產(chǎn)權(quán)或著作財(cái)產(chǎn)權(quán)消滅的文字或美術(shù)作品最終專設(shè)一項(xiàng)制版權(quán),旨在保護(hù)制版者對(duì)其版面以影印、印刷或類似方式復(fù)制的相關(guān)利益,其保護(hù)期自制版完成時(shí)起僅10年。?施文高著:《著作權(quán)法制原論》,我國(guó)臺(tái)灣地區(qū)商務(wù)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第370-376 頁(yè)。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guó)版式保護(hù)條款在文化部1985年頒布實(shí)施的《圖書、期刊版權(quán)保護(hù)試行條例實(shí)施細(xì)則》(以下簡(jiǎn)稱為《書刊版權(quán)實(shí)施細(xì)則》)中得以體現(xiàn)。根據(jù)其第13條的規(guī)定,出版單位對(duì)其出版的圖書,除在出版合同有效期內(nèi)享有作者根據(jù)合同轉(zhuǎn)讓的專有出版權(quán)和其他權(quán)利外,在圖書版權(quán)有效期內(nèi)對(duì)圖書的裝幀設(shè)計(jì)和版式設(shè)計(jì)享有版權(quán)。該裝幀設(shè)計(jì)和版式著作權(quán)獨(dú)立于圖書著作權(quán),即出版合同有效期滿,作者如收回出版權(quán),將作品轉(zhuǎn)移到另一出版單位出版,不得損害原出版單位對(duì)圖書的裝幀設(shè)計(jì)和版式設(shè)計(jì)的著作權(quán)。由此可見,1985年《書刊版權(quán)實(shí)施細(xì)則》賦予出版者專門對(duì)圖書(未包括期刊、報(bào)紙等)裝幀設(shè)計(jì)和版式設(shè)計(jì)享有著作權(quán),但未明確該版式著作權(quán)的權(quán)能范圍是否與一般作品的著作權(quán)相同。直到新中國(guó)第一部著作權(quán)法實(shí)施之際,1991年《著作權(quán)法實(shí)施條例》第38條明確規(guī)定出版者對(duì)其出版的圖書、報(bào)紙、雜志的版式、裝幀設(shè)計(jì)享有專有使用權(quán)。由于該條文被放在第五章“與著作權(quán)有關(guān)權(quán)益的行使與限制”部分,故該專有使用權(quán)從性質(zhì)上講與一般作品的著作權(quán)并不相同,屬于一種法定的著作鄰接權(quán)。為了順應(yīng)加入世界貿(mào)易組織的需要,我國(guó)于2001年修訂通過的《著作權(quán)法》對(duì)包括版式保護(hù)規(guī)定在內(nèi)的大多數(shù)條文進(jìn)行了修正,其中的版式保護(hù)條款一直沿用至今。在立法者看來,由于相互競(jìng)爭(zhēng)的出版單位之間通常不會(huì)抄襲報(bào)紙的版面形式,故版式專有權(quán)的保護(hù)對(duì)象主要是指圖書、期刊的版式設(shè)計(jì)。此外,因?yàn)檠b幀設(shè)計(jì)與版式設(shè)計(jì)之間存在著較大重合,其中屬于裝幀設(shè)計(jì)的封面部分可以通過美術(shù)作品加以保護(hù),故這次立法修訂刪除了裝幀設(shè)計(jì)的專有使用權(quán)規(guī)定,僅保留出版者對(duì)圖書、期刊的版式設(shè)計(jì)享有法定的版式專有權(quán)。?全國(guó)人大常委會(huì)法制工作委員會(huì)民法室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著作權(quán)法〉修改立法資料選》,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43-44 頁(yè)。至于該鄰接權(quán)的權(quán)能范圍究竟有多大,雖然《著作權(quán)法》并無明確界定,但全國(guó)人民代表大會(huì)法制工作委員會(huì)的官方解讀文本認(rèn)為其“除了出版者自己可以隨意使用其版式設(shè)計(jì)外,主要是指其他人未經(jīng)許可不得擅自按原樣復(fù)制”。?胡康生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著作權(quán)法釋義》,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 頁(yè)。
綜上可見,正是合同約定的專有出版權(quán)難以完全覆蓋對(duì)出版物的版面形式保護(hù),出版業(yè)團(tuán)體才會(huì)在著作權(quán)法律體系內(nèi)推動(dòng)對(duì)版式相關(guān)利益的特別權(quán)利保護(hù)。我國(guó)早期的版式專有權(quán)立法采用著作權(quán)保護(hù)模式并限定其出版物為圖書,可見這一時(shí)期更加認(rèn)同圖書版面形式一旦符合作品的獨(dú)創(chuàng)性要件,圖書的裝幀及版式設(shè)計(jì)應(yīng)享有完全脫離于出版作品的獨(dú)立著作權(quán)。1991年《著作權(quán)法實(shí)施條例》將版式專有權(quán)適用的出版物范圍拓展至圖書、期刊及報(bào)紙,同時(shí)在體例安排上將版式專有權(quán)納入著作鄰接權(quán)的法定范疇。經(jīng)過2001年立法修訂之后,立法者又將報(bào)紙從版式專有權(quán)適用的出版物范圍內(nèi)予以排除。雖然這一鄰接權(quán)保護(hù)模式從表面上看有別于英法等國(guó),但從性質(zhì)來看卻與英國(guó)的著作權(quán)特別保護(hù)模式并無差異。在英國(guó)著作權(quán)體系內(nèi),由于體例上沒有鄰接權(quán)制度,書刊版式著作權(quán)不得不被設(shè)計(jì)成不完整的財(cái)產(chǎn)利益,這與歐陸法系淡化書刊版面形式的獨(dú)創(chuàng)性要件、旨在回報(bào)出版者編排加工投入的鄰接權(quán)保護(hù)模式已無本質(zhì)區(qū)別。應(yīng)當(dāng)看到,書刊版式專有權(quán)與基于創(chuàng)作所產(chǎn)生的出版作品著作權(quán)的確不同:出版者的版式專有權(quán)“支持在出版加工過程中的努力和投資,鼓勵(lì)將作品提供給公眾使用的出版活動(dòng)”?[西]德利婭 · 利普希克著:《著作權(quán)與鄰接權(quán)》,聯(lián)合國(guó)教科文組織譯,中國(guó)對(duì)外翻譯出版公司2000 版,第241 頁(yè)。,其源自對(duì)編排加工作品出版物的勞動(dòng)付出,產(chǎn)生于出版作品的傳播之中。
三、書刊版式專有權(quán)的權(quán)利客體考辨
(一)我國(guó)版式專有權(quán)客體的獨(dú)創(chuàng)性審視
我國(guó)《著作權(quán)法》第36條將版式專有權(quán)的客體表述為“版式設(shè)計(jì)”。從字面來看,“設(shè)計(jì)”這一用語似乎可以推定版式專有權(quán)的保護(hù)基礎(chǔ)在于其客體具備一定獨(dú)創(chuàng)性。在著作權(quán)法2001年修訂意見征集過程中,部分專家對(duì)這一觀點(diǎn)表示支持。他們認(rèn)為“版式設(shè)計(jì)包含了不同版本的字體設(shè)計(jì)、格式編排等,尤其是音樂作品的版式設(shè)計(jì)(如不同版本的音樂繪譜、曲目編排、音符邊距等)更具有獨(dú)創(chuàng)性”?同注釋②。,似乎暗示受保護(hù)的版式設(shè)計(jì)應(yīng)當(dāng)符合獨(dú)創(chuàng)性要件。司法實(shí)踐中,大多數(shù)法院在認(rèn)定版式設(shè)計(jì)是否受保護(hù)時(shí)也遵循獨(dú)創(chuàng)性標(biāo)準(zhǔn)的裁判思路。例如在北京創(chuàng)世卓越文化有限公司訴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一案中,法院認(rèn)定涉案出版物的版式設(shè)計(jì)匯集了多種設(shè)計(jì)元素,“通過不同元素之間特定的組合形式及搭配方式,體現(xiàn)其設(shè)計(jì)者的獨(dú)特構(gòu)思以及取舍、選擇和編排,具有較強(qiáng)的個(gè)性化色彩,屬于應(yīng)受著作權(quán)法保護(hù)的版式設(shè)計(jì)”。?北京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院(2015)京知民終字第922 號(hào)民事判決書。在一些案件中,法院甚至將版式專有權(quán)進(jìn)一步定義為“對(duì)版面文字、圖片和空間布局中具有獨(dú)創(chuàng)性的設(shè)計(jì)部分所享有的專有權(quán)利”。?云南省昆明市中級(jí)人民法院(2014)昆知民初字第411 號(hào)民事判決書。更有甚者,如在前引吉林美術(shù)出版社訴海南出版社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參照作品的獨(dú)創(chuàng)性要求,強(qiáng)調(diào)除了考察出版者是否享有版式專有權(quán)時(shí)應(yīng)由原告就版式設(shè)計(jì)是否系其獨(dú)立創(chuàng)作以及版式設(shè)計(jì)的獨(dú)創(chuàng)性部分進(jìn)行舉證說明之外,還要求在厘定版式專有權(quán)的保護(hù)范圍時(shí),應(yīng)充分考量版式專有權(quán)與創(chuàng)作空間的關(guān)系。?參見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申字第1150 號(hào)民事裁定書。可見,支持獨(dú)創(chuàng)性要件說的主流觀點(diǎn)認(rèn)為,版式設(shè)計(jì)是否受著作權(quán)法的保護(hù)應(yīng)從獨(dú)創(chuàng)性來證立其合理性,作品的獨(dú)創(chuàng)性要件可以類推適用到版式設(shè)計(jì)當(dāng)中,“只有具有獨(dú)創(chuàng)性的版式設(shè)計(jì)才受到著作權(quán)法的保護(hù),獨(dú)創(chuàng)性決定了著作權(quán)以及版式專有權(quán)等鄰接權(quán)的保護(hù)范圍和邊界”。?錢小紅:《版式設(shè)計(jì)專用權(quán)的司法認(rèn)定》,載《人民司法(案例)》2013年第20 期,第4-8 頁(yè)。
然而,版式設(shè)計(jì)保護(hù)的獨(dú)創(chuàng)性要件在司法實(shí)踐中也帶來一些困擾:由于版式設(shè)計(jì)的獨(dú)創(chuàng)性部分主要表現(xiàn)在設(shè)計(jì)者的獨(dú)特構(gòu)思以及對(duì)不同設(shè)計(jì)元素的取舍、選擇和編排等方面。因此,版式專有權(quán)從邏輯上本應(yīng)屬于設(shè)計(jì)人。但依我國(guó)《著作權(quán)法》第36條的規(guī)定,版式專有權(quán)是出版者享有的一項(xiàng)法定鄰接權(quán),這與版式設(shè)計(jì)符合獨(dú)創(chuàng)性要求即可以保護(hù)實(shí)際設(shè)計(jì)人的認(rèn)識(shí)顯得有些格格不入。這一問題在前引創(chuàng)世卓越文化有限公司訴內(nèi)蒙古人民出版社案中尤為突出。在該案中,原告創(chuàng)世卓越公司曾與涉案出版物的出版單位、版式及裝幀設(shè)計(jì)人之間都簽訂過出版及裝幀設(shè)計(jì)合作協(xié)議。為了說明原告系版式專有權(quán)的適格主體,法院只得作出法條文義以外的擴(kuò)張性解釋:“雖然版式設(shè)計(jì)保護(hù)的權(quán)利人主要為出版者,但隨著出版行業(yè)的產(chǎn)業(yè)化及行業(yè)分工的發(fā)展,版式設(shè)計(jì)可以有專門的設(shè)計(jì)人,當(dāng)出版者與版式設(shè)計(jì)人出現(xiàn)不一致的情形,應(yīng)當(dāng)根據(jù)具體事實(shí),認(rèn)定實(shí)際的版式設(shè)計(jì)人對(duì)其設(shè)計(jì)的版式設(shè)計(jì)享有專用權(quán)……可以認(rèn)定創(chuàng)世卓越公司依約定取得了涉案出版物的版式設(shè)計(jì)專用權(quán)。”?同注釋?。依此觀點(diǎn),版式專有權(quán)應(yīng)當(dāng)歸實(shí)際設(shè)計(jì)人享有,仍可依約定轉(zhuǎn)移給其他民事主體,但同時(shí)也會(huì)產(chǎn)生以下問題:首先,由于都參照并類推適用作品的獨(dú)創(chuàng)性要件來判斷是否應(yīng)受保護(hù)以及推定權(quán)利的原始?xì)w屬,法院在該案中只得放棄對(duì)版式設(shè)計(jì)與裝幀設(shè)計(jì)等進(jìn)行嚴(yán)格區(qū)分,否則就會(huì)產(chǎn)生著作權(quán)法對(duì)裝幀(封面等)設(shè)計(jì)與版式設(shè)計(jì)二者的“歧視”保護(hù)困擾,即同樣符合獨(dú)創(chuàng)性要件,裝幀設(shè)計(jì)中的封面可能構(gòu)成美術(shù)作品,平面圖形設(shè)計(jì)人可以享有較全面的著作權(quán),而版式設(shè)計(jì)僅構(gòu)成一種鄰接權(quán)客體,其權(quán)能保護(hù)范圍卻遠(yuǎn)小于前者。其次,即便未作區(qū)分,法院對(duì)版式設(shè)計(jì)和裝幀設(shè)計(jì)等概念的混用也會(huì)進(jìn)一步模糊版式專有權(quán)客體與作品之間的界限,甚至難以解釋同樣符合獨(dú)創(chuàng)性要件,版式專有權(quán)何以遠(yuǎn)小于著作權(quán)的權(quán)能范圍。再者,《著作權(quán)法》第36條的理論依據(jù)似乎與作品的獨(dú)創(chuàng)性標(biāo)準(zhǔn)以及法院遵循的“誰創(chuàng)作誰享有”之著作權(quán)歸屬邏輯并不一致,其立法目的旨在激勵(lì)回報(bào)出版單位促進(jìn)作品傳播活動(dòng)而付出的勞動(dòng)及投資,該條文明確將版式專有權(quán)授予出版者即已表達(dá)這一立場(chǎng)。
從國(guó)內(nèi)外立法例來看,雖然我國(guó)著作權(quán)法將版式專有權(quán)客體表述為“版式設(shè)計(jì)”,但在世界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組織網(wǎng)站公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著作權(quán)法》官方譯本中使用的英文表述卻是“typographical arrangement”而非“typographical design”,中文可翻譯為“版式編排”。?See Copyrigh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36,p.17,at https://wipolex.wipo.int/en/text/186569,last visited:2019-03-05.這一用詞與英國(guó)著作權(quán)法的表述相同。盡管英國(guó)將“版式編排”視為作品的特殊類型之一,但從權(quán)利主體、保護(hù)期限及其著作權(quán)主要規(guī)制他人以影印或類似方式對(duì)“版式編排”實(shí)施的摹本復(fù)制這一權(quán)能范圍來看,英國(guó)著作權(quán)法專為出版者設(shè)立的版式著作權(quán)與一般作品的著作權(quán)有很大區(qū)別,實(shí)際上是在沒有鄰接權(quán)制度的基礎(chǔ)上所采用的一種特別保護(hù)模式。英國(guó)并沒有將“版式編排”與其他一般作品等同對(duì)待,由于英國(guó)判例法體系對(duì)“仿冒之訴”(passing off)規(guī)則解釋得較為保守,英國(guó)版式著作權(quán)的特別保護(hù)模式實(shí)際上發(fā)揮了制止版式影印盜版這一反不正當(dāng)競(jìng)爭(zhēng)機(jī)制的相應(yīng)功能。司法實(shí)踐表明,英國(guó)著作權(quán)法所要保護(hù)的版式利益并非能夠編排出圖文版面式樣的原創(chuàng)性成分,而是特定出版物的版面布局式樣,即版面的最終呈現(xiàn)形式。?See Nationwide News Pty Ltd v.Copyright Agency Ltd [1995]136 ALR 273,p.291.可見,英國(guó)將裝幀設(shè)計(jì)中的平面圖形(如封面等)與版面呈現(xiàn)形式加以區(qū)分,前者以是否滿足獨(dú)創(chuàng)性要件來判斷設(shè)計(jì)者是否享有較全面的著作權(quán),而后者更側(cè)重于考察出版者是否已付出持續(xù)穩(wěn)定的組織性勞動(dòng)和投資,僅提供一種有限保護(hù)范圍的版式“著作權(quán)”。在這一點(diǎn)上,我國(guó)鄰接權(quán)制度中的版式專有權(quán)實(shí)際上與英國(guó)版式著作權(quán)的特別保護(hù)模式并無本質(zhì)差別。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法國(guó)同英國(guó)一樣采用版式著作權(quán)模式,但卻選擇一條較嚴(yán)格的保護(hù)路徑。由于《法國(guó)民法典》一般侵權(quán)條款為制止版式影印盜版行為提供了堅(jiān)實(shí)的反不正當(dāng)競(jìng)爭(zhēng)法適用依據(jù)?參見《法國(guó)民法典》第1382 條和第1383 條的相關(guān)規(guī)定。,《法國(guó)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典》在立法設(shè)計(jì)上選擇將裝幀及版式設(shè)計(jì)等概念并用,在著作權(quán)客體類型中專設(shè)一項(xiàng)“裝幀及版式作品”,故版式著作權(quán)與一般作品的著作權(quán)并無區(qū)別。在法國(guó)立法者看來,裝幀和版式設(shè)計(jì)等概念難以完全剝離,無論是裝幀設(shè)計(jì)中的平面圖形(如封面)還是版式設(shè)計(jì),只有符合作品的獨(dú)創(chuàng)性要件才會(huì)受到著作權(quán)法的保護(hù),作者(即設(shè)計(jì)人而非出版者)才能享有一般作品那樣較全面的著作權(quán)。司法實(shí)踐中,我國(guó)多數(shù)法院支持以獨(dú)創(chuàng)性標(biāo)準(zhǔn)來判斷版式“設(shè)計(jì)”是否受著作權(quán)法保護(hù),即錯(cuò)誤套用法國(guó)版式著作權(quán)的立法邏輯來解釋作為法定鄰接權(quán)的版式專有權(quán),進(jìn)而引發(fā)不得不放棄對(duì)裝幀設(shè)計(jì)和版式“設(shè)計(jì)”等概念進(jìn)行區(qū)分的窘境,更無法解釋同樣符合獨(dú)創(chuàng)性要件,二者的權(quán)能范圍何以截然不同這一邏輯失洽的問題。
實(shí)際上,要澄清版式專有權(quán)的客體究竟為何以及是否以獨(dú)創(chuàng)性要件作為保護(hù)基礎(chǔ)等問題,需要結(jié)合出版物的版式制作過程和步驟來加以理解。如在圖書制版工作中,出版單位首先需要安排專業(yè)的美工編輯或委托設(shè)計(jì)師設(shè)計(jì)出圖文版面編排與總體布局的版式設(shè)計(jì)方案,再將符合要求并確定下來的版式設(shè)計(jì)方案提交給排版公司,由排版公司工作人員按上述方案對(duì)圖文版面進(jìn)行具體編排操作,進(jìn)而形成圖文版面布局經(jīng)過排版制作、編輯及加工之后的最終呈現(xiàn)形式。就獨(dú)立(非連續(xù))發(fā)行的圖文出版物而言,這一最終呈現(xiàn)形式(即特定的版本形式)經(jīng)過上述版式制作和編排流程以后,出版作品最終被加工制作成一種文化產(chǎn)品——內(nèi)容與形式有機(jī)結(jié)合在一起的出版物。在整個(gè)過程中,無論是美工編輯或設(shè)計(jì)師提供的版式設(shè)計(jì)方案,還是排版公司工作人員的具體編排工作,出版單位都會(huì)支付相應(yīng)報(bào)酬,這些費(fèi)用也將計(jì)入圖書出版的直接成本當(dāng)中。?感謝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出版社李琳女士向筆者詳細(xì)介紹圖書的制版編排過程,另參見于文:《論我國(guó)著作權(quán)法中出版者權(quán)的客體重置》,載《科技與出版》2016年第4 期,第60-63 頁(yè)。可見,從出版作品的圖文版面布局設(shè)計(jì)到編輯排版工作的具體實(shí)施,再到出版物的印刷出版,無不凝聚著出版單位在作品傳播過程中的組織性勞動(dòng)和投資。我國(guó)著作權(quán)法之所以將版式專有權(quán)授予出版者,一方面是考慮到出版單位在圖文制版、編排以及整個(gè)出版過程中所發(fā)揮的主導(dǎo)作用,同時(shí)也認(rèn)同該權(quán)利配置模式將有利于提高出版流轉(zhuǎn)授權(quán)的總體實(shí)施效率。進(jìn)言之,作為出版者享有的一項(xiàng)法定鄰接權(quán),版式專有權(quán)的保護(hù)基礎(chǔ)并非來源于實(shí)際設(shè)計(jì)人(如美工編輯等)的創(chuàng)造性智力勞動(dòng),而在于出版者在傳播作品的整個(gè)過程中投入了大量資金和勞動(dòng),承擔(dān)了主要的商業(yè)風(fēng)險(xiǎn)。因此,我國(guó)著作權(quán)法保護(hù)的版式專有權(quán)客體并非實(shí)際設(shè)計(jì)人針對(duì)圖文版面布局所提出來的獨(dú)創(chuàng)性表達(dá)部分(如版式“設(shè)計(jì)”方案),而是書刊版面布局經(jīng)過排版制作、編輯及加工之后的最終呈現(xiàn)形式——版面形式,不應(yīng)參照作品的獨(dú)創(chuàng)性要件來認(rèn)定是否受著作權(quán)法保護(hù)。
(二)版式專有權(quán)客體與出版內(nèi)容的關(guān)聯(lián)性考察
由上可知,版式專有權(quán)的客體實(shí)為書刊版面布局經(jīng)過編排加工之后的最終呈現(xiàn)形式,不以獨(dú)創(chuàng)性要件作為保護(hù)基礎(chǔ)。那么,這一最終呈現(xiàn)形式可否完全脫離出版內(nèi)容而受到獨(dú)立保護(hù)呢?進(jìn)言之,如果他人只是挪用出版者制版中的版面布局結(jié)構(gòu),但出版的具體內(nèi)容(如圖文等)卻不相同,是否仍會(huì)侵害出版者的版式專有權(quán)?本文以為,在不考慮法定阻卻事由的基礎(chǔ)上,版式專有權(quán)的侵權(quán)認(rèn)定仍以實(shí)質(zhì)性相似規(guī)則為基準(zhǔn)。?See Newspaper Licensing Agency Limited v.Marks &Spencer PLC [2001]UKHL 38,para.7.上述問題應(yīng)當(dāng)分情況探討,首先需要區(qū)分狹義與廣義上的書刊版式專有權(quán)客體。二者之間的區(qū)別主要是版面呈現(xiàn)元素不同:前者以印刷字面版式為主,故其元素主要是指印刷品的版心、排式、用字、行距、標(biāo)點(diǎn)等;而后者則以圖文組合版式為主,除上述元素以外,還包括圖文組合中的配圖、表格、頁(yè)面底色以及水印等。總體來看,無論是印刷字面版式還是圖文組合版式,書刊版面布局的最終呈現(xiàn)形式都可以被視為由各種元素和材料經(jīng)取舍、選擇及編排后組合而成的一種匯編物。
就廣義的版面形式而言,版式專有權(quán)作為一項(xiàng)法定的鄰接權(quán),雖不以客體的獨(dú)創(chuàng)性要件作為保護(hù)基礎(chǔ),但不排除圖文版面布局經(jīng)過編排加工之后的最終呈現(xiàn)形式可能具有獨(dú)創(chuàng)性。這是因?yàn)樵谟∷⒆置姘媸街校淖肿煮w的選擇、行距、頁(yè)邊距等版面安排主要服務(wù)于閱讀習(xí)慣,而在圖文組合版式中,文字可能作為繪畫設(shè)計(jì)的藝術(shù)表現(xiàn)手段。?參見何懷文著:《中國(guó)著作權(quán)法:判例綜述與規(guī)范解釋》,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6年版,第439 頁(yè)。如果圖文組合版式具有一定獨(dú)創(chuàng)性,則主要是在圖文版面布局諸元素之間的組合形式及搭配方式上體現(xiàn)對(duì)各元素具有個(gè)性化的取舍、選擇及編排,從性質(zhì)上類似于匯編作品這樣“一種以體系化的方式呈現(xiàn)的作品、數(shù)據(jù)或其他信息的集合”。?王遷著:《著作權(quán)法》,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15年版,第126 頁(yè)。實(shí)際上,匯編作品并非獨(dú)立的作品類型,如果對(duì)創(chuàng)作素材作獨(dú)創(chuàng)性的選擇或編排形成的是能夠獨(dú)立表現(xiàn)思想或文學(xué)藝術(shù)美感的內(nèi)容,則選擇或編排僅僅是創(chuàng)作各種法定類型作品的手段,并不產(chǎn)生文字表達(dá)、美術(shù)、音樂等作品法定類型之外的“匯編”作品。從這層意義來看,文字作品或文字片段經(jīng)匯編后組合形成的作品還是“文字作品”,作品的匯編權(quán)實(shí)際上在利用方式上可以被復(fù)制權(quán)所涵蓋。因此,匯編作品的著作權(quán)取得與行使具有依附性,派生于匯編作品的組成元素和材料——作品、作品片段或其他信息。對(duì)匯編作品的利用也同時(shí)構(gòu)成對(duì)匯編內(nèi)部單個(gè)元素的利用,“對(duì)匯編作品的著作權(quán)侵害,比如翻印匯編作品,同時(shí)對(duì)匯編作品內(nèi)容的權(quán)利人也構(gòu)成損害”。?[德]M.雷炳德著:《著作權(quán)法》,張恩民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171 頁(yè)。可見,作為具有一定獨(dú)創(chuàng)性的匯編作品,圖文組合版式尚無法完全剝離出版內(nèi)容而受到獨(dú)立保護(hù)。反推之,當(dāng)圖文組合版式不具有獨(dú)創(chuàng)性時(shí),出版內(nèi)容更融入圖文版面布局的最終呈現(xiàn)形式中,類同“脫離具體數(shù)據(jù)、純粹的數(shù)據(jù)庫(kù)結(jié)構(gòu)是不應(yīng)當(dāng)受版權(quán)保護(hù)”?張柳堅(jiān):《對(duì)數(shù)據(jù)庫(kù)結(jié)構(gòu)能否享有版權(quán)問題的討論》,載《電子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1997年第12 期,第6-9 頁(yè)。的觀點(diǎn)一樣,他人僅挪用出版內(nèi)容以外的版面布局結(jié)構(gòu),將很難認(rèn)定侵害出版者的版式專有權(quán)。
就狹義的版面形式而言,由于印刷字面呈現(xiàn)元素(包括版心、排式、用字、行距、標(biāo)點(diǎn)等)極為有限,各元素組合及搭配方式很難顯現(xiàn)出取舍、選擇及編排方面的個(gè)性化特征,故版面布局結(jié)構(gòu)更多體現(xiàn)為一種技術(shù)性安排。印刷字面版式之所以需要保護(hù),誠(chéng)如前述,主要出于激勵(lì)回報(bào)出版者在傳播作品中的組織性勞動(dòng)與投資。基于此,通說認(rèn)為版式專有權(quán)僅限于排除不法競(jìng)爭(zhēng)者以影印或類似方式對(duì)印刷字面版式進(jìn)行原樣或無明顯改動(dòng)的使用。在認(rèn)定版式專有權(quán)是否被侵害時(shí),實(shí)質(zhì)性相似判斷傾向于印刷字面最終呈現(xiàn)形式的無實(shí)質(zhì)性差別考察,即相較一般作品侵權(quán)認(rèn)定而言,更應(yīng)側(cè)重于“量”而非“質(zhì)”意義上的比對(duì)考察。?See Ladbroke (Football) Ltd v.William Hill (Football) Ltd [1964]1 WLR 273,pp.276-293.進(jìn)言之,只有在原被告的印刷字面最終呈現(xiàn)形式之間已達(dá)到無明顯改動(dòng)的近似程度,才能認(rèn)定被告侵害了原告的版式專有權(quán)。盡管印刷字面版式與出版內(nèi)容(如文字作品)在權(quán)利基礎(chǔ)上相互獨(dú)立且各不相同,但印刷字面最終呈現(xiàn)形式依附于出版內(nèi)容——文字作品本身,若他人排除文字作品的具體內(nèi)容,僅挪用由其他有限元素搭配、組合而成的版面布局結(jié)構(gòu),會(huì)導(dǎo)致最終呈現(xiàn)形式的效果不同,版式專有權(quán)的侵權(quán)認(rèn)定也將難以通過實(shí)質(zhì)性相似考察。因此,如果他人只是挪用印刷字面版式的版面布局結(jié)構(gòu),出版的文字作品內(nèi)容卻不同,也不會(huì)侵害出版者的版式專有權(quán)。
綜上所述,無論是狹義上的印刷字面版面形式還是廣義上的圖文組合版面形式,書刊版式專有權(quán)都應(yīng)理解為對(duì)同一出版內(nèi)容的出版物,出版者有權(quán)禁止他人進(jìn)行原樣或無明顯改動(dòng)的利用。
四、書刊版式專有權(quán)的權(quán)能范圍厘定
雖然我國(guó)《著作權(quán)法》第36條規(guī)定“出版者有權(quán)許可或禁止他人使用其出版的圖書、期刊的版式設(shè)計(jì)(即本文指涉的版面形式)”,但在官方立法解釋和司法實(shí)踐中,主流觀點(diǎn)認(rèn)同版式專有權(quán)的權(quán)能范圍較小,其專有“使用”權(quán)僅體現(xiàn)為專有復(fù)制權(quán),并不能當(dāng)然延及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利益。一般認(rèn)為,除了出版者自行使用其版式設(shè)計(jì)以外,其他人未經(jīng)許可不得對(duì)版式設(shè)計(jì)實(shí)施摹本復(fù)制。依據(jù)版式專有權(quán),出版者僅可以禁止他人對(duì)版面形式進(jìn)行原樣復(fù)制或無明顯改動(dòng)的復(fù)制(如簡(jiǎn)單且改動(dòng)很小的復(fù)制、變化比例尺寸的復(fù)制等)。此外,依《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保護(hù)條例》第2條的規(guī)定,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的適用客體被限定為作品、表演和錄音錄像制品三類,并未包含版式專有權(quán)客體,從反向也否定了版式專有權(quán)的權(quán)能范圍可以延伸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利益。因此,主流觀點(diǎn)認(rèn)為版式專有權(quán)的權(quán)能范圍并不包括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
針對(duì)他人將書刊版面形式掃描復(fù)制后在互聯(lián)網(wǎng)傳播的行為,較權(quán)威的司法實(shí)務(wù)觀點(diǎn)主張應(yīng)把它區(qū)分為掃描復(fù)制行為以及后續(xù)的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行為兩個(gè)階段:后一階段行為由于屬于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的調(diào)整范圍,不應(yīng)認(rèn)定為侵害版式專有權(quán);對(duì)于前一階段行為,應(yīng)納入復(fù)制權(quán)的調(diào)整范圍,可以認(rèn)定構(gòu)成對(duì)版式專有權(quán)的侵害。?同注釋⑥。因此,他人未經(jīng)出版者許可,“將圖書、報(bào)刊掃描復(fù)制后在互聯(lián)網(wǎng)傳播的”,構(gòu)成侵害版式專有權(quán)。?參見2018年北京市高級(jí)人民法院《侵害著作權(quán)案件審理指南》第6.6 條的相關(guān)規(guī)定。然而在數(shù)字技術(shù)時(shí)代,以互聯(lián)網(wǎng)傳播的前置行為包括復(fù)制為由(即通過掃描復(fù)制行為來規(guī)制后續(xù)的互聯(lián)網(wǎng)傳播行為),在司法實(shí)務(wù)操作中有些不切實(shí)際。由于數(shù)字技術(shù)與傳統(tǒng)印刷技術(shù)時(shí)期的復(fù)制、傳播特征并不相同,無論是掃描、翻拍還是上傳服務(wù)器,雖然都形成數(shù)字化復(fù)制件,但這種復(fù)制行為是一次性的,復(fù)制件也只有一份。這意味著如果出版者以對(duì)版面形式的專有復(fù)制權(quán)受侵害為由提起訴訟,出版者無法獲得停止侵權(quán)的法律救濟(jì),因?yàn)閽呙鑿?fù)制行為已經(jīng)實(shí)施完畢,而公眾接觸又不受該復(fù)制權(quán)的控制,相應(yīng)的損害賠償也只能按侵權(quán)人產(chǎn)生的復(fù)制件數(shù)量(一份)來計(jì)算,將無法有效彌補(bǔ)出版者的實(shí)際損失和威懾侵權(quán)人。?參見王遷著:《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中的著作權(quán)保護(hù)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 頁(yè);于文:《論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下版式設(shè)計(jì)權(quán)的擴(kuò)張》,載《編輯學(xué)刊》2016年第3 期,第29-33 頁(yè)。此外,這種將書刊版面形式掃描復(fù)制后在互聯(lián)網(wǎng)傳播的行為強(qiáng)行分割為兩個(gè)階段,僅承認(rèn)前一項(xiàng)行為侵害版式專有權(quán)的“一刀切”做法,容易助長(zhǎng)非法傳播者惡意規(guī)避前一項(xiàng)行為的復(fù)制侵權(quán)責(zé)任,僅實(shí)施單一的非法傳播行為,不利于版式專有權(quán)的有效保護(hù)。可見,在數(shù)字技術(shù)時(shí)代,版式專有權(quán)僅以專有復(fù)制權(quán)為權(quán)能范圍,難以實(shí)現(xiàn)與出版者相匹配的經(jīng)濟(jì)利益訴求,也無法實(shí)現(xiàn)版式專有權(quán)激勵(lì)、回報(bào)出版者在出版加工過程中付出組織性努力和投資的立法目的。
從書刊版式專有權(quán)與著作權(quán)之譜系溯源來看,版式專有權(quán)產(chǎn)生于互聯(lián)網(wǎng)尚未普及的前數(shù)字技術(shù)時(shí)期,立法者最初的立法意圖就是為了防止他人未經(jīng)許可通過復(fù)制方式使用已出版書刊的版面形式。這是因?yàn)樵趥鹘y(tǒng)印刷技術(shù)的特定歷史時(shí)期,復(fù)制與發(fā)行存在著天然的因果聯(lián)系,即一個(gè)人在未制作復(fù)制件的前提下,不可能向公眾發(fā)行這些復(fù)制件。由于復(fù)制在傳統(tǒng)印刷時(shí)期是傳播發(fā)生的主要乃至唯一渠道,控制復(fù)制就等于控制住了傳播,復(fù)制權(quán)替代了發(fā)行權(quán)的主要功能。作為一種“預(yù)示權(quán)”(predicate right),復(fù)制權(quán)因具備判斷后續(xù)侵權(quán)發(fā)生的預(yù)兆功能而得以存在,是前數(shù)字技術(shù)時(shí)期作為判斷是否侵權(quán)的重要依據(jù)。?See L.Ray Patterson,Understanding Fair Use,55 SPG Law &Contrmp.Probs,262(1992).這一思路從法國(guó)對(duì)“復(fù)制”的定義也可見端倪。根據(jù)《法國(guó)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法典(法律部分)》L.122-3條的規(guī)定:“復(fù)制是指以一切方式將作品固定在物質(zhì)上以便間接向公眾傳播。”?《十二國(guó)著作權(quán)法》翻譯組編:《十二國(guó)著作權(quán)法》,清華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第69 頁(yè)。在法國(guó)立法者看來,“復(fù)制權(quán)”本身就融入了“發(fā)行權(quán)”,規(guī)制“復(fù)制”行為的目的就是為了禁止后續(xù)間接的“傳播”,這也解釋了法國(guó)何以沒有設(shè)立單獨(dú)的“發(fā)行權(quán)”。此外,《伯爾尼公約》《TRIPS協(xié)議》也未規(guī)定專門的發(fā)行權(quán)。直到1996年,“互聯(lián)網(wǎng)條約”(WCT、WPPT)文本中才明確規(guī)定了發(fā)行權(quán)。傳統(tǒng)意義上,發(fā)行與復(fù)制通常結(jié)合在一起,復(fù)制的目的是發(fā)行,發(fā)行是復(fù)制的必然結(jié)果,故人們把“復(fù)制”和“發(fā)行”統(tǒng)稱為“出版”。可見,復(fù)制權(quán)之所以成為版式專有權(quán)的權(quán)利基礎(chǔ),是由傳統(tǒng)印刷技術(shù)限制下的特定歷史條件所決定的,其本身就已經(jīng)融入權(quán)利人對(duì)版面形式的傳播利益訴求。
由上可知,版式專有權(quán)的傳統(tǒng)權(quán)能范圍僅以專有復(fù)制權(quán)為基礎(chǔ),是受到復(fù)制技術(shù)發(fā)展中的特定歷史條件限制所產(chǎn)生的結(jié)果。實(shí)際上,在理解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包括版式專有權(quán)等)的保護(hù)范圍時(shí),作為權(quán)利客體的抽象物與使用行為二者之間有時(shí)是難以嚴(yán)格區(qū)分的,其權(quán)利作用“焦點(diǎn)”(即理解該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什么以及保護(hù)到什么程度的連結(jié)點(diǎn))實(shí)為一種雙重構(gòu)造,包括行為模式和客體保護(hù)范疇。?參見李楊:《著作財(cái)產(chǎn)權(quán)客體結(jié)構(gòu)中的使用行為——審視著作權(quán)法權(quán)利作用“焦點(diǎn)”的一個(gè)闡釋進(jìn)路》,載《法制與社會(huì)發(fā)展》2012年第3 期,第17-27 頁(yè)。二者之間彼此聯(lián)系、互為印證:究竟怎樣的東西被視為客體——抽象物,其實(shí)是由“利用行為”的抽象化程度所決定;即使從類型化的行為范疇來判斷侵權(quán)問題,仍需要借助客體保護(hù)范疇來界定行為的性質(zhì)。從這層意義來看,版式專有權(quán)主要規(guī)制以影印或類似方式對(duì)版面形式實(shí)施的摹本復(fù)制(如原樣復(fù)制、簡(jiǎn)單且改動(dòng)很小的復(fù)制、變化比例尺寸的復(fù)制等),實(shí)際上關(guān)注從客體保護(hù)邊界而非行為模式范疇對(duì)版式專有權(quán)的保護(hù)范圍進(jìn)行界定。換言之,版式專有權(quán)禁止摹本復(fù)制主要以挪用的客體來源比重(即原被告版面形式是否完全相同、是否無明顯改動(dòng)以及是否僅變化了比例尺寸等)而非類型化的客體利用方式為規(guī)范基礎(chǔ),側(cè)重于考察對(duì)版面形式實(shí)施何種程度的挪用將構(gòu)成對(duì)版式專有權(quán)的侵害。
從各國(guó)立法例來看,版式專有權(quán)的權(quán)能范圍也從未明確排除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利益應(yīng)受到保護(hù)。就采用著作權(quán)保護(hù)模式的國(guó)家而言,法國(guó)規(guī)定“裝幀及版式作品”若符合獨(dú)創(chuàng)性要件可以構(gòu)成法定的作品類型之一,其著作權(quán)的權(quán)能范圍自當(dāng)與一般作品相同,理應(yīng)涵括著作權(quán)人的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利益。而同樣采用著作權(quán)保護(hù)模式的英國(guó)對(duì)“版式編排”則采用一種特別保護(hù)方式。從表面上看,英國(guó)規(guī)定版式著作權(quán)可以規(guī)制他人以影印或類似方式對(duì)“版式編排”實(shí)施摹本復(fù)制,似乎確立了版式著作權(quán)的權(quán)能范圍以專有復(fù)制權(quán)為主。但在版式著作權(quán)條款中,英國(guó)著作權(quán)法從未確立獨(dú)立且唯一的復(fù)制權(quán)(right of reproduction),僅規(guī)定他人未經(jīng)許可“對(duì)出版物的版式編排所實(shí)施的摹本復(fù)制才構(gòu)成抄襲(copying)”。?《英國(guó)著作權(quán)法》第17 條第(5)項(xiàng)的原文表述為:“Copying in relation to the typographical arrangement of a published edition means making a faxsimile copy of the arrangement.”誠(chéng)如前述,摹本復(fù)制的禁例條款主要以挪用的客體來源比重而非類型化的客體利用方式為規(guī)范基礎(chǔ),實(shí)際上僅確立相較一般作品要求更高的“實(shí)質(zhì)性相似”侵權(quán)判斷標(biāo)準(zhǔn),側(cè)重于從客體保護(hù)邊界而非行為模式范疇對(duì)版式專有權(quán)的保護(hù)范圍進(jìn)行界定。從這層意義上講,英國(guó)版式著作權(quán)的權(quán)能范圍除復(fù)制權(quán)以外,從未排除過可以延及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等其他使用權(quán)能。
就采用鄰接權(quán)保護(hù)模式的國(guó)家而言,德國(guó)為了給整理者對(duì)科學(xué)版本(包括版面形式)付出的勞動(dòng)和投資提供必要的激勵(lì)、回報(bào),專門對(duì)不受著作權(quán)保護(hù)的文稿科學(xué)版本提供一種鄰接權(quán)保護(hù)。根據(jù)《德國(guó)著作權(quán)法》第70條的規(guī)定,該著作鄰接權(quán)準(zhǔn)用一般作品的著作權(quán)內(nèi)容規(guī)定,即權(quán)能范圍從未限定于專有復(fù)制權(quán),整理者還享有排他性的發(fā)行權(quán)和公開再現(xiàn)權(quán),理應(yīng)對(duì)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利益進(jìn)行保護(hù)。此外,為了扭轉(zhuǎn)新型信息服務(wù)平臺(tái)(例如新聞聚合網(wǎng)站)利用報(bào)刊雜志無償提供的信息,分流報(bào)刊雜志網(wǎng)站點(diǎn)擊率的利益失衡局面,2013年修訂后的《德國(guó)著作權(quán)法》在第87條新增了一項(xiàng)鄰接權(quán)——新聞出版者權(quán),旨在保護(hù)報(bào)刊雜志出版者“為制作、出版新聞產(chǎn)品而提供的經(jīng)濟(jì)、組織及技術(shù)方面的業(yè)績(jī)和經(jīng)營(yíng)成果”,其保護(hù)期限雖只有一年?《德國(guó)著作權(quán)法》之所以為新聞出版者權(quán)僅規(guī)定一年的保護(hù)期限,主要考慮報(bào)紙類新聞信息的時(shí)效性較短。,但權(quán)利內(nèi)容卻主要表現(xiàn)為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即“通過有線或無線方式而使公眾可以在其選定的地點(diǎn)和時(shí)間獲取報(bào)刊新聞信息的權(quán)利”。?參見范長(zhǎng)軍:《新聞出版者權(quán)——德國(guó)著作權(quán)法的新修改》,載《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2015年第1 期,第86-92 頁(yè)。受德國(guó)法變革的影響,歐洲委員會(huì)在2016年啟動(dòng)歐盟數(shù)字單一市場(chǎng)指令的立法工作之后,也開始激烈討論加入該項(xiàng)新聞出版者權(quán)(以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為主)的可行性方案。?See Thomas Hoppner, EU Copyright Reform:The Case for a Publisher's Right,Intellectual Property Quarterly,issue 1/2018,p.27.我國(guó)臺(tái)灣地區(qū)“著作權(quán)法”第79條針對(duì)無著作財(cái)產(chǎn)權(quán)或著作財(cái)產(chǎn)權(quán)消滅的文字或美術(shù)作品則專設(shè)了一項(xiàng)制版權(quán),從條文看似乎僅為制版者提供一項(xiàng)“以影印、印刷或類似方式重制之權(quán)利”的復(fù)制權(quán)。然而,若從其第80條“制版權(quán)準(zhǔn)用著作財(cái)產(chǎn)權(quán)之限制規(guī)定”可以看出,出于教育、新聞報(bào)道等公益目的可以公開播送、傳輸或轉(zhuǎn)載制版者的版面形式。因此,制版權(quán)的權(quán)能范圍從表面上看僅限于復(fù)制權(quán),實(shí)則可以延及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利益等公開傳播權(quán)。可見,通過對(duì)各國(guó)立法例進(jìn)行實(shí)證考察,版式專有權(quán)的權(quán)能范圍應(yīng)當(dāng)排除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的結(jié)論也難以成立。
主張版式專有權(quán)的權(quán)能范圍不包括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的另一個(gè)論據(jù),主要是《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保護(hù)條例》第2條對(duì)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的適用客體規(guī)定,該條款并沒有將出版者的版式專有權(quán)客體納入其中。實(shí)際上,我國(guó)制定《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保護(hù)條例》的立法背景主要是為了順應(yīng)數(shù)字技術(shù)時(shí)代的法律訴求,遵守“互聯(lián)網(wǎng)條約”(WCT、WPPT)的成員國(guó)義務(wù)。雖然“互聯(lián)網(wǎng)條約”僅為作品、表演以及錄音制品提供了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的法律依據(jù)(例如WCT第8條為作品設(shè)置的向公眾傳播權(quán),WPPT第10條、第14條分別為表演、錄音制品等設(shè)置的向公眾提供權(quán)),但并不排除各成員國(guó)可以將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的適用客體范圍擴(kuò)大到其他客體。例如《德國(guó)著作權(quán)法》為報(bào)刊雜志出版者新增設(shè)的著作鄰接權(quán)——新聞出版者權(quán),即主要表現(xiàn)為一項(xiàng)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而我國(gu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保護(hù)條例》同樣也將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的適用客體從“錄音制品”擴(kuò)大至“錄音錄像制品”。此外,如果從法解釋學(xué)分析,國(guó)務(wù)院制定《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保護(hù)條例》的法律依據(jù)主要是我國(guó)《著作權(quán)法》第10條第12項(xiàng)以及“附則”第59條的有關(guān)規(guī)定。“附則”第59條確立“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的保護(hù)辦法由國(guó)務(wù)院另行規(guī)定”。而依據(jù)第10條第(十二)項(xiàng)對(duì)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的定義條款,“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屬于著作財(cái)產(chǎn)權(quán)的內(nèi)容之一,是指以有線或者無線方式向公眾提供“作品”,使公眾可以在其個(gè)人選定的時(shí)間和地點(diǎn)獲得“作品”的權(quán)利。既然《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保護(hù)條例》可以對(duì)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的定義進(jìn)行擴(kuò)張性解釋,將適用客體范圍從“作品”擴(kuò)大至“表演”“錄音錄像制品”,那么也無充足理由將版式專有權(quán)客體排除在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利益保護(hù)之外。
綜上所述,他人未經(jīng)許可對(duì)書刊版面布局的最終呈現(xiàn)形式或版面形式進(jìn)行無明顯改動(dòng)的網(wǎng)絡(luò)傳播行為可以也應(yīng)當(dāng)規(guī)制。在數(shù)字技術(shù)時(shí)代,我們有必要對(duì)《著作權(quán)法》第36條作出擴(kuò)張性解釋,將版式專有權(quán)的權(quán)能范圍延伸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利益。這不僅有利于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下對(duì)出版者利益進(jìn)行合理保護(hù),更有利于立法目的在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下得到有效貫徹。
結(jié)語
書刊版式專有權(quán)是我國(guó)《著作權(quán)法》授予出版者享有的一項(xiàng)法定鄰接權(quán)。從歷史之維分析,版式專有權(quán)與著作權(quán)之間存在著緊密的特定聯(lián)系。書刊版式專有權(quán)的確立,主要是為了激勵(lì)、回報(bào)作品出版加工過程中的努力和投資,鼓勵(lì)出版者將作品提供給公眾使用的出版活動(dòng)。我國(guó)著作權(quán)法保護(hù)的版式專有權(quán)客體并非設(shè)計(jì)人針對(duì)圖文版面布局所提出來的獨(dú)創(chuàng)性表達(dá)部分,而是書刊版面布局經(jīng)過排版制作、編輯及加工之后的最終呈現(xiàn)形式——版面形式,不應(yīng)參照作品的獨(dú)創(chuàng)性要件來認(rèn)定是否受著作權(quán)法保護(hù)。此外,無論是印刷字面版面形式還是圖文組合版面形式,書刊版式專有權(quán)都應(yīng)理解為出版者對(duì)同一出版內(nèi)容之出版物的版面形式所享有的一項(xiàng)權(quán)利。再者,從法解釋學(xué)分析,我國(guó)《著作權(quán)法》第36條在數(shù)字技術(shù)時(shí)代應(yīng)當(dāng)作出合理的擴(kuò)張性解釋,無論是從實(shí)然還是應(yīng)然層面上都有必要將版式專有權(quán)的權(quán)能范圍延伸至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利益。作為我國(guó)法定的著作鄰接權(quán)之一,書刊版式專有權(quán)主要保護(hù)出版者編排和制作出版物特定版面形式所付出的組織性勞動(dòng)和投資,重在發(fā)揮制止版式影印盜版等摹本復(fù)制和非法傳播這一反不正當(dāng)競(jìng)爭(zhēng)機(jī)制本應(yīng)具備的功能。從這層意義來看,如果我國(guó)《著作權(quán)法》不能為出版者的書刊版面形式提供充分的法律保護(hù),作為一種權(quán)宜之計(jì),《反不正當(dāng)競(jìng)爭(zhēng)法》第2條的準(zhǔn)一般適用條款也可以成為保護(hù)出版者相關(guān)利益的法律適用依據(j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