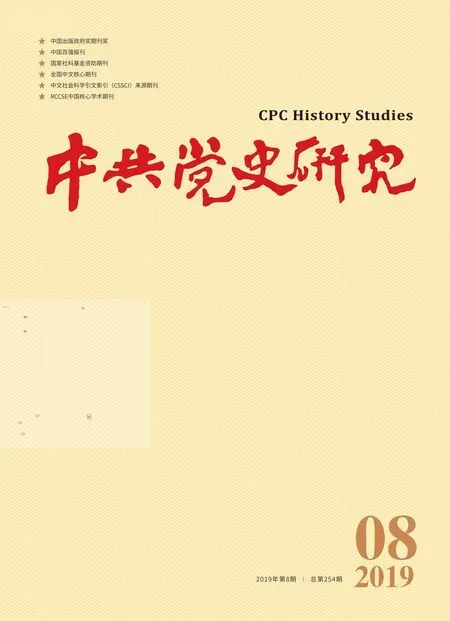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若干問題再探討
——與《留法勤工儉學群體接受馬克思主義過程再探討》一文商榷
賈 凱
《中共黨史研究》2018年第7期發表的陳少卿《留法勤工儉學群體接受馬克思主義過程再探討》一文(以下簡稱陳文),對留法勤工儉學運動趨于失敗時,工學世界社、勞動學會和部分工余社成員從沖突到聯合,最終拋棄勤工儉學理想、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進行了較為細致的考察,并認為:勤工儉學生接受馬克思主義,既是勤工儉學運動失敗的結果,又與其自身社會經濟處境密切相關,而這個過程某種意義上體現了五四運動的革命化。
陳文主要從“社會經濟角度”考察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實際上側重分析現實境遇變化的影響,對于學術界更為全面地了解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很有價值。但是筆者認為,陳文還有一些可以完善乃至再探討的問題,故而提出一些淺見,就教于陳少卿及學術界同仁。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謂“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指的是以蔡和森、趙世炎、周恩來等人為代表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中產生的中國共產黨人(1)中共成立初期,很多活動是以團組織的名義公開開展的,旅歐黨、團亦是如此。而且除個別年齡較大者外,旅歐中共黨員一般都具有團員身份,參加團的活動,團員后來也大多轉為黨員。因此,考察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一般情況下不必區分黨、團員。參見中共中央組織部等編:《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第1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第708—709頁。。
一、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的類型和特征
留法勤工儉學原本是李石曾、吳稚暉等無政府主義者發起、深受工讀主義影響的教育、文化運動。臺灣學者陳三井認為,李石曾等發起這場運動,“其動機除了讓歐美學術運河平均灌輸外,更崇高的理想便是要溝通東西文明,融合中外學術,另創一種新文明,為人類開一新紀元”(2)陳三井:《旅歐教育運動:民初融合世界學術的理想》,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13頁。。然而,運動的實際發展與其發起人之預想大相徑庭。一方面,多數勤工儉學生陷入失業、失學的困境,部分青年甚至絕望自殺。另一方面,這場運動遠遠超出教育、文化范疇,引發了二八運動、拒款運動、進占里昂中法大學等大規模革命活動;其中產生的中國共產黨人,更對近現代中國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這使得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留法勤工儉學生有著多重面相,不可簡單化論之。筆者認為,陳文在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類別、特征等方面的一些論述還有商榷之余地。
問題之一,對于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的類別,可以作出更合理的劃分。陳文在第四部分中將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分為“本有其他信仰的”和“游移不定的中間派”兩類,進而分別論述了他們最終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動機。與此同時,勤工儉學生轉向馬克思主義的動機其實與其赴法理想密切相關。對此,陳文在第一部分提到,勤工儉學生赴法的理想大概分兩種,“第一種是希望赴歐洲求取真理,從而完善個人、改造社會,這種理想為少數深受五四運動影響的青年所有;第二種是大部分人都有的理想,就是取得晉身之階”。由此而言,陳文大約是從兩個角度對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進行了分類:一是有無明確信仰;二是“為公”還是“為私”。
筆者認為,將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分為三類,可能更為恰當。第一類是深受五四新文化思潮影響,且有一定信仰或傾向者;第二類是或多或少受到各種五四新文化思潮影響,但沒有明確信仰或傾向者;第三類是因國內升學機會少、花費多,而赴法勤工儉學花費較少且能“出洋”,所以才選擇赴法的青年學生。第一類如陳文提到的陳延年、陳喬年,他們與吳稚暉、黃凌霜等無政府主義者有較多聯系,受工讀主義或無政府主義影響較深;第二類包括蔡和森等人,他們受新文化運動各種思潮影響,如蔡和森赴法前推崇墨子思想,但又或多或少認同俄國十月革命;第三類數量最多,他們響應李石曾等人赴法勤工儉學號召,赴法目的是“出洋求學”,同時又或多或少對現實社會感到不滿。筆者之所以不傾向于采用陳文的分類方法,主要基于以下兩點考慮。
一是很多青年對于某種主義的認識還達不到信仰的程度。以陳文提到的趙世炎為例,他在赴法之前已經加入北京的中共早期組織(3)參見《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1921—1997)》第1卷,第708頁。,但又有很長一段時間相信勤工儉學具有可行性,在二八運動之前與蔡和森、李維漢等人持相反觀點(4)參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3年,第16頁;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編:《趙世炎百年誕辰紀念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第79—80頁。。也就是說,此時的趙世炎既加入了中共早期組織,又受到工讀主義影響,很難稱得上有明確信仰。又如,李維漢回憶道:“華法教育會的李石曾、吳稚暉都標榜篤信無政府主義。華法教育會辦的《旅歐周刊》以及旅法華工會辦的《華工旬刊》也宣傳這些思想。這些書刊對我們有很大影響。”(5)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10頁。李維漢在提到李石曾、吳稚暉等人時,使用的是“篤信”一詞,可以說已經接近“信仰”的意思了,但對自己則只說“有很大影響”。而他所說的“我們”,指的是工學世界社的發起成員,可見無政府主義對勤工儉學生的影響是比較普遍的。因此,除陳延年、陳喬年受無政府主義影響較大,姑且能夠稱得上“信仰”之外,大多數留法勤工儉學生很難稱得上信仰某種主義。
二是很多青年并非單純地為個人發展而赴法勤工儉學。雖然陳文所說的“求晉身”確實是大多數人的真實想法,但最好能用“求學”等更加客觀、中性的表述。更重要的是,勤工儉學生赴法的動機極為復雜,在為自己謀求光明前途的同時,往往還有更高尚的理想追求,二者難以徹底分割。例如,李維漢曾對工學世界社成員赴法的原因作過集中概括。他寫道:“我們都是只受過中等教育的青年,有提高科學文化水平的愿望,但因家境貧寒,無力升學,一旦知道可以到法國經過勤工達到升學的目的,便想盡辦法奔向這條路上來。”這與陳文引述的陳毅的那段話,即“感到自己有辦法,有前途,可能爬上去”等等,顯然有異曲同工之處。不過,李維漢接著寫道:“我們又是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比較先進的青年,親受帝國主義侵略、軍閥戰爭和豪紳買辦階級的壓迫、剝削之苦,痛恨舊的社會制度。我們又多少參加過五四運動或者受過它的影響,向往科學與民主……救國之道如何?真理在何處?我們仍在蒙昧之中,頭腦里基本上還是一張白紙。”(6)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10頁。20世紀20年代初,留洋求學固然是科舉廢除后重要的“晉身之階”,但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興起的“勞工神圣”口號,以及勤工儉學著力打破“智識者”與“勞動者”差別的理念,使得“留法勤工儉學”不同于普通的留日、留美等“留學”。因此,將多數留法勤工儉學生稱之為“游移不定的中間派”,將其理想說成是“取得晉身之階”,或許還不夠準確。
問題之二,關于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的特征,似有值得商榷之處。陳文開篇即指出,與同時期國內的中共早期組織成員相比,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有一個迥異的特征——“作為無產階級一員,他們深受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壓迫”。根據對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家庭背景的分析可知,其中大部分人來自破產的地主家庭或農民家庭,可以歸入無產階級。但筆者認為,他們在法國求學未成、生存無果的狀態可能還算不上“深受發達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壓迫”,充其量只是留學理想破滅而已。
抵法之初,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對于法國社會的印象普遍很好。這一方面是出于實現赴法留學理想后的喜悅,另一方面則是因為當時的法國社會確實比中國更“先進”。例如徐特立認為,“法國人民尚平等自由”,并不因自己高齡入學而另眼相待,而且社會上并無“階級之見”,甚至“無所謂總統,無所謂平民,無所謂黑奴,無所謂文明種族,同為人類,即同為一家也”。這種評價并非個例,《晨報》刊載的一篇介紹留法勤工儉學詳情的文章,開篇即發出感慨:“來到這博愛、平等、自由的法國,耳濡目染,真是無處不促人反省,使人欽羨,令人愉快。”王若飛離開就讀的楓丹白露公學時也是戀戀不舍,認為該校“待遇中國同學,非常優厚,就是這地方的人,對于我們的感情,也還不壞”。(7)清華大學中共黨史教研組編:《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史料》第2冊(上),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192、256、214頁。又過了一段時間,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才親身感受到,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同樣存在對勞動者的壓迫。陷入求學未成、生存無果的窘境后,他們進一步意識到,個人發展問題在法國同樣無法得到解決。然而,這不意味著他們深受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壓迫,更很難說這是“迥異于同時期國內的中共黨小組成員”的特征。作為工人階級代表的中國共產黨,自籌建之日起便十分強調與勞動者相結合,因此很多在國內的中國共產黨人同樣感受到了資本主義的壓迫。中國這種“不發達資本主義”的壓迫甚至比發達資本主義的壓迫有過之而無不及。
二、工學世界社的緣起與性質
工學世界社是留法勤工儉學生中影響較大的一個組織,陳文對此已有充分介紹。新民學會則不僅同樣頗有影響,而且其在法會員與工學世界社成員是高度重合的。據鄭超麟回憶:“工學世界社的人可以說都參加了新民學會,但新民學會的人不見得都參加工學世界社。”(8)《鄭超麟回憶錄》(上),東方出版社,2004年,第364頁。陳文中有一句話,涉及兩個組織之間的關系:“在蔡和森、蕭子升等離湘赴法之前,新民學會就決定吸收外省成員,并在法國發展組織。這個決議的具體落實,就是1920年3月成立的新民學會外圍組織——勤工儉學勵進會;當年7月,工學勵進會又改組為工學世界社。”筆者認為這種說法不太準確,原因如下。
其一,陳文之所以認為勤工儉學勵進會的成立是對新民學會決議的落實,依據是《新民學會文獻匯編》。但實際上,相關文獻的原文為:“這次討論,集中‘會友向外發展’一點,對于留法運動認為必要,應盡力進行。”(9)湖南省博物館歷史部校編:《新民學會文獻匯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22頁。也就是說,蕭子升、蔡和森等人赴法前,新民學會討論的是“會友向外發展”,而不是“向外發展會友”。筆者認為,這里指的是希望會友能夠“走出去”,去法國留學,而不是在法國發展新的會友。陳文可能誤讀了這則材料。
其二,李維漢在談及勤工儉學勵進會成立時,完全沒有提到蔡和森、蕭子升的影響,反而說自己與蔡和森相距較遠,“僅有通信聯系”,“工學勵進會的情況就是由我告訴他,他又寫信回國告訴毛澤東同志的”(10)參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10—12頁。。實際上,該組織的發起成員均與李維漢同船抵達法國,卻不一定都是新民學會會員。此外,勤工儉學勵進會的指導思想是空想社會主義和無政府主義,與新民學會沒有直接傳承關系。
其三,兩個組織的成員雖然聯系頻繁,但組織本身卻相對獨立。蔡和森是新民學會主要領導人之一,但因為對工學主義不認可,不僅始終未加入工學世界社,而且積極引導該組織轉向共產主義。同時,工學世界社召開年會時曾邀請新民學會會員列席,在法新民學會會員1920年7月召開會議時也邀請工學世界社成員列席。二者顯然是相對獨立的。
陳文認為,工學世界社成立后,在留法學生中形成了一個以該團體成員為主的派別,并指出:工學世界社“最終認同了蔡和森的主張,決定以馬克思主義作為工學世界社的指導思想”。“工學世界社是最早統一了意識形態的旅法學生組織。”其中,關于工學世界社認同馬克思主義,陳文的基本依據是1920年12月29日的賀果日記。賀果寫道:“又談一天的話,到晚九時,才表決了個傾向,各個對現社會都不滿足,都以為要革命才行。可是數日的討論,得個結束,告一段落。”(11)賀培真:《留法勤工儉學日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1頁。的確,我們似乎可以根據這段資料得出結論:經過“數日的討論”,工學世界社在蔡和森的影響下,于1920年底成為“最早統一了意識形態的旅法學生組織”。然而筆者認為,這次“統一”可能僅僅是暫時的或初步的,依據包括以下兩個方面。
一方面,工學世界社的名稱并未變更。鄭超麟、李維漢的回憶都提到,蔡和森因為對“工學”二字不滿,拒絕加入工學世界社。如果工學世界社已經奉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那么為何不改變名稱呢?直至1921年7月,蔡和森主張將新成立的組織名稱定為“中國少年共產黨”時,仍因郭春濤反對而未獲通過(12)李永春編著:《蔡和森年譜》,湘潭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84頁。。同月,賀果日記記載:“我自己主張(1)假若是搞共產黨的組織,我以個性不任束縛的關系,必需退出社外。(2)假若是采普泛的組織,我仍在內”。工學世界社開會時,“修改名稱一項,引起大爭論,一方面主張‘名副其實’,必須改名,一方面主張應付事實上必要手段,無須改名,人數各半,卒以無法表決,暫時保留仍舊名”。(13)賀培真:《留法勤工儉學日記》,第104、107頁。顯然,此時的工學世界社仍有人并未接受馬克思主義,反對建立共產黨組織。
另一方面,工學世界社成員的思想轉變并未完成,或者后來又有反復。1921年1月14日,賀果在日記中寫道:“人的行為的動機,皆是出發于‘自利’之一念,無所謂利他利人。利他利人是因為要完成利己,所以才生出利他。凡一切人的行動,莫不如是。”(14)賀培真:《留法勤工儉學日記》,第46頁。這顯然不是馬克思主義人生觀的觀點。甚至1921年9月里大事件后,工學世界社的鄭超麟仍然“只把馬克思主義看作一種學說,同別的學說一般的地位”(15)《鄭超麟回憶錄》(上),第375頁。。
根據以上兩點可以推斷,1920年底工學世界社成員關于馬克思主義和革命問題的共識是暫時的、不穩固的。此時的工學世界社只能算暫時或初步統一了意識形態的旅法學生組織。這種不穩定性和暫時性,從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遲至1922年6月才成立這一情況中,也能看出一些端倪。
三、工學世界社與勞動學會何時盡釋前嫌
受蔡和森影響、以李維漢為核心的工學世界社和趙世炎、李立三領導的勞動學會,是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的兩個主要源頭。學界普遍認為,二八運動后,兩派開始逐漸靠攏。陳文則通過對多個人物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呈現出群體人物關系的復雜性,進而提出新見解:“二八運動后,兩派并未立即攜手,而仍互相攻擊,各自擴張勢力。例如,站在勞動學會一邊的張申府向蔡和森發起了筆戰。兩派聯合的契機到1921年的夏初才出現。”陳文還以汪頌魯拜訪工學世界社,邀請尹寬、鄭超麟參加“通信圖書館”為例,說明兩派的較早溝通“與中法借款一事泄露的時間吻合”,并認為1921年6月爆發的拒款運動是“兩派捐釋前嫌的臺階”。
分析兩個派別或群體之間的關系時,從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切入,無疑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度。但是,群體研究的困難和復雜性在于難以確定某個個體的思想、行為能否代表群體,以及群體成員的思想、行為是否同步。因此,前述問題肯定還有進一步探討的空間。筆者的看法是:二八運動后不久,工學世界社和勞動學會的領導人便開始推動兩派聯合;拒款運動是各旅法華人團體基于愛國主義的大聯合,也是工學世界社、勞動學會均參與的活動,但不是“兩派捐釋前嫌的臺階”。
依據之一,盡釋前嫌的前提是兩派消除誤解,而這一轉變很可能始于趙世炎、李立三等發表宣言。二八運動之前,圍繞著勤工儉學理想是否已經破滅,兩派之間的爭論十分激烈,甚至發傳單相互攻訐。由于趙世炎、李立三反對請愿,留法勤工儉學生中竟出現了兩人被中國駐法公使陳箓收買的謠言。為了澄清謠言、譴責法警毆打學生,趙世炎、李立三等發表聯合宣言,號召全體學生團結起來,反對中法兩國政府(16)宣言的發表時間應該是二八運動后不久,有學者認為是3月1日。參見李永春編著:《蔡和森年譜》,第79頁。。李立三回憶道:“至此,人們對我們的懷疑才解除了。”(17)《趙世炎百年誕辰紀念集》,第80頁。由攻訐、傳謠再到謠言解除,這應當是兩派關系轉變的第一步,畢竟謠言是因兩派分歧而傳出的。
依據之二,雙方主要領導人的通信和會談,推動兩派關系逐步緩和。李立三回憶說,大約在1921年三四月間,他和趙世炎離開巴黎,赴位于克魯梭的工廠做工。二人離開巴黎時,“決定主動的和他們(指蔡和森、李維漢等人——引者注)聯系,由世炎給和森寫信。以后世炎同志到克魯梭工廠時繞道到蒙達尼找和森等同志面談。談了兩三天,結果意見完全一致,雙方表示爭論已經過去,今后要共同研究問題,共同革命,大家都談馬克思主義”(18)《趙世炎百年誕辰紀念集》,第81—82頁。。據此可以推斷,此時兩派主要領導人已達成一定共識。從李維漢的回憶看,二八運動與兩派關系的變化頗有關聯。他寫道:“‘二八運動 ’教育了我們,迫切希望勤工儉學生內部加強團結。我們請勞動學會派代表到蒙達尼出席工學世界社的會議,相互加強聯系和了解。世炎、立三都到過蒙達尼交換意見不只一次。若飛則來蒙達尼和我們一起在膠鞋廠做工。通過交談,我們雙方的觀點和認識迅速取得一致,并且共同行動起來。”(19)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第17頁。盡管李立三回憶的時間未必完全準確,李維漢也沒有提到具體時間,但是二人不約而同地提到蒙達尼會談對推動兩派關系逐步緩和的重要作用,同時都沒有提及拒款運動的影響。這從側面反映出,兩派關系的發展與拒款運動沒有直接聯系。
依據之三,兩派不同成員在推動雙方關系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和態度不一致、不同步,甚至出現過激烈爭論。陳文以張申府發起對蔡和森的筆戰,以及汪頌魯主動拜訪尹寬、鄭超麟時的不愉快,證明工學世界社和勞動學會成員之間存在嫌隙。筆者贊同這個觀點。但同樣不能忽視的是蔡和森、李維漢等人與趙世炎、李立三等人對兩派關系發展的推動。這種不一致、不同步現象,不僅體現在前文所述工學世界社內部成員思想分歧方面,還始終貫穿于兩派組織的聯合過程之中。例如,趙世炎、李立三在克魯梭做工時,意識到應該加強對勤工儉學生的領導,希望成立共產主義同盟會,蔡和森對此表示同意。然而1921年7月召開的工學世界社第二次年會,在更名一事上并未達成共識。列席會議的李立三無奈地感嘆道:“我是贊成的(指贊成成立少年共產黨——引者注),但因為是客人所以只能發表個人意見,但不便爭論。”(20)《趙世炎百年誕辰紀念集》,第82頁。
基于以上三點,可以看出,工學世界社和勞動學會的聯合是一個錯綜復雜而又不斷推進的過程。二八運動后,兩派成員之間固然有一定的嫌隙,但雙方主要領導人很快盡釋前嫌,并不斷推進兩派聯合的進程。至拒款運動時期,兩派已經將成立共產主義組織提上議程。
四、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接受馬克思主義是一個“發展過程”
陳文認為,此前的一些研究成果“認定巴黎共產主義小組的成員在組織建立之初就已確立了馬克思主義信仰,而沒有考慮到他們先組織入黨,后精神入黨的特殊情況”,并指出:“勤工儉學運動的革命化是勤工儉學生親身作為無產階級一員參加和集體抗爭達成的,有先經歷實踐、后接受理論的特點。”陳文還強調,里大事件是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契機。對于陳文所述里大事件之后大部分留法勤工儉學生理想破滅的情況,筆者是認同的。但筆者認為,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對馬克思主義的接受,是一個在實踐中不斷研究、比較各種理論,進而確立信仰的過程。
首先,五四時期,包括工學世界社和勞動學會在內,學生社團信仰多種思潮的現象十分普遍。由其衍生出的地方中共組織或早期組織,同樣思想龐雜,甚至信仰非馬克思主義的也并不鮮見。(21)參見〔美〕舒衡哲著,李紹明譯:《張申府訪談錄》,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第111頁;黃金鳳:《早期中國共產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關系之研究——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創建與改組為中心》,《中共黨史研究》2014年第6期。從工學世界社和勞動學會到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的發展過程,既是清除非馬克思主義者特別是無政府主義者的過程,又是兩個團體的成員研究、比較各種主義進而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這一過程如果不是因為蔡和森、李立三等骨干被遣送回國,以及遇到了幾次運動而相對延長,那么倉促成立、沒有統一意識形態的旅法共產主義組織很有可能重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改組之覆轍。
其次,趙世炎、蔡和森這兩位主要領導人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的過程,很難用“先實踐,后理論”或“先理論,后實踐”來概括。趙世炎赴法前已加入北京的中共早期組織,赴法勤工儉學時又受到工讀主義影響。1921年春,他與張申府、陳公培組建了巴黎的中共早期組織。蔡和森抵達法國后,既沒有入學又沒有做工,而是通過“猛看猛譯”自學馬克思主義理論,不久便成為留法勤工儉學生中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但是,他在法期間始終未加入張申府建立的中共早期組織,其籌建共產黨組織的計劃也因種種原因未能成功。由是觀之,趙世炎、蔡和森這兩位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領導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其實是一個“發展過程”。
再次,里大事件發生于1921年9月,而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卻遲至1922年6月才成立,這同樣說明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成員接受馬克思主義需要一個“發展過程”。周恩來接受馬克思主義尚且經歷了一段時間,其他人需要的時間可能更長。一方面,群體成員的思想發展具有不同步性。蔡和森是留法勤工儉學生中第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先影響群體其他成員,群體成員又相互影響。到了后期,趙世炎、周恩來逐漸在影響其他成員、籌建共產主義組織的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22)有海外學者認為,周恩來轉向共產主義后,憑借其優秀的英文能力,在旅歐共產主義組織的籌建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參見Chae-Jin Lee,Zhou Enlai:The Early Year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p.155;李璜:《學鈍室回憶錄》,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第80頁。。工學世界社向共產主義組織的轉變,也反映出群體內部成員思想不一致現象的普遍性。例如,蔡和森以工學世界社為基礎籌建共產主義組織的計劃,因內部始終存在分歧而未能如愿。1922年,周恩來希望在“五一節”時成立共產主義組織,又因工學世界社想整體加入但內部又有分歧而被迫延期。此外,思想的不同步、不一致還意味著先進者一直在努力教育、引導落后者,否則該組織將因思想分歧而解散。另一方面,個體思想的發展往往具有反復性。例如,賀果原本在1920年底工學世界社年會上同意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本組織的指導思想,卻又在次年7月第二次年會上反對“搞共產黨的組織”。這種思想反復甚至相互矛盾的情況,在賀果日記中不勝枚舉。又如,陳毅原本因里大事件而放棄文藝救國理想,但回國后又經歷了一次動搖,“最后認識到不革命就沒有出路,才下決心干革命”(23)聶元素等編輯整理:《陳毅早年的回憶和文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6—37頁。。可見,不論是1920年底召開的工學世界社第一次年會,還是標志著留法勤工儉學理想破滅的里大事件,都推動著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接受馬克思主義,但個體思想發展的反復性又不可避免地影響了群體思想的接受進度。
總之,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作為一個整體接受馬克思主義,經歷了一個復雜的“發展過程”。雖然里大事件基本宣告留學理想破滅,但是他們可能很難在短時間內認清現實。畢竟趙世炎也一度躲到北方做工,意志十分消沉。因此,將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接受馬克思主義視為實踐與認識辯證互動、成員之間相互影響的發展過程,可能更為全面。
五、結 語
百年前興起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影響深遠,其中產生的蔡和森、趙世炎、周恩來、李維漢、李立三、鄧小平等中國共產黨人對近現代中國歷史產生了重要影響。對于這場運動及相關人物,學術界不可謂不重視,相關研究成果更是汗牛充棟。但遺憾的是,從群體維度和社會經濟視角開展的研究還較為缺乏。在這種情況下,陳文考察了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從群體視角而非領導個體視角切入,側重考察社會經濟環境所造成的影響,并將其置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背景下加以分析,推動了相關研究的廣度和深度。眾所周知,群體研究具有一定難度,尤其是在如何把握領導個體的特殊性與群體的一般性,以及群體成員個人的特征能否代表群體等問題上,陳文處理得較為妥當。其所運用的資料也較為全面、系統。本文無意推翻陳文的基本論述,只是認為其在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的類型和特征、工學世界社的發展歷程、工學世界社與勞動學會的關系、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等方面,尚有可再探討或深入研究的余地。總之,筆者認為,考察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和中共留法勤工儉學群體時,應當更全面地展現五四時期各種思潮對青年的復雜影響,以及“五四”一代接受馬克思主義過程的不同步性、反復性等諸多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