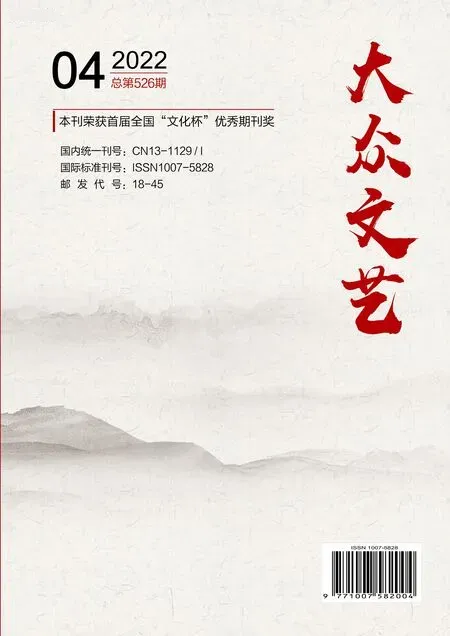多元化與邊緣化:拉美民間音樂與文學的互文性
洪思慧 (武漢大學文學院 430072)
本文以近現代拉丁美洲民間音樂/文學為關注點,從互文性角度探討音樂與文學創作靈感緣起的交互影響以及二者內在結構的相似性。廣義的互文性實指一個能夠自由對話的文化空間,由于文學與音樂的創作規律本質上具有交互作用的可能,而拉美文化普遍帶有殖民歷程、民族混血和邊緣化趨向,使其具備多元性的特征,特別適合其民間音樂與文學形成互為鏡像的照應對象。
一、多元化:拉美音樂與文學的殖民、混血特征
拉丁美洲包括墨西哥、中美地峽、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島和南美洲地域,現有5.77億人口,主要由印歐混血種人、黑白混血種人和印黑混血種人組成,此外還有黑人、印第安人、白種人、黃種人及其他外來移民人口。拉丁美洲文化是名副其實的混血文化,這種文化的成型過程中,殖民歷史對這片大陸的文化進行了重大改造。在長期殖民統治中,非洲黑人音樂/文學、歐洲白人音樂/文學和原住民印第安人音樂/文學,相互對話、交流、借鑒,對這片新大陸新文化的產生影響深遠,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拉美音樂/文學獨特風格的形成。
首先,談及黑人文化一般都要追溯至非洲大陸;談及非洲大陸,往往關涉到殖民、他者、權力、白人種族中心論和民族/個體認同問題。非洲音樂作為世界民族音樂大樹之根,在民族音樂學話語體系內占得舉足輕重的地位。然而在文學領域,非洲大陸則代表著另一套象征化的符號系統,從約瑟夫·康拉德的作品便可略知一二。康拉德擅長海洋文學、叢林文學并賦予其作品以政治批判的功用,從事航海生活20余年豐富了他在非洲、南美等地探險的經歷。從《黑暗之心》、《吉姆爺》沉重的話語敘述中不難體察殖民統治的社會歷史帶給非洲的苦難以及作者對黑人奴隸的同情。白人殖民者操縱著非洲大陸上空隱形的權力網,對黑人奴隸進行規訓。非洲民間音樂的開創性和卓越性在受統治時期幾乎被無視,“他者”形象成為歐洲人眼中黑人奴隸的另一符號身份,在一定程度上致使非洲音樂和文學傳統斷裂,民族認同發生扭曲。帶著這一色彩、帶著這一系列非洲符號,黑人奴隸來到了拉丁美洲,催生了拉美音樂的發展。
其次,作為殖民者的白人,在拉美音樂與文學方面的影響力同樣不可忽視。歐洲厚重的古典音樂傳統、章法嚴謹、體裁多樣的音樂作品、漂泊的游吟詩人、宗教與世俗相抗衡的藝術形態、獨特的民族民間樂器、記譜法與“標準”音高體系等等,都對拉美民族音樂產生潛移默化的溶蝕作用,其中歐洲傳教士們在拉美的音樂傳教活動功不可沒。文學亦如是——久居巴黎的科塔薩爾深受歐洲文藝價值體系的引導與啟發,其短篇小說均呈現如高超的對位法構成錯綜而協和的復調,雙線敘事游走在現實生活與藝術幻想之間,如同復調音樂的兩個聲部,互為補充。這種“多聲部”式寫作增加了文學與音樂敘事的張力,拓寬了藝術表現空間。歐洲傳統在拉美大陸的實踐衍生出超乎歐洲本土的“爆炸”式反應,這片混血大陸藝術創作的幻想和奇異性由此大大增強了。
最后,本土的原住民印第安人文化,依然保持生機。受制于安第斯高原和山脈的地理條件限制,外來殖民者的文化傳播受到一定阻礙。雖然這并不能阻止殖民者對原生文化的破壞;不過在音樂和文學領域中,曾經被神話傳說、宗教語言支配著的人們,在現代語境下仍擁有大批同類,印第安文化傳統得以保留發展。對當今民間音樂起到較大影響作用的部分源自印第安傳統民間樂器、民間舞及民間歌曲(曲調),一些民族傳統節日也被保留下來。未被物質文明和現代科技侵染毒害的原住民音樂文化,彰顯出一種混血大陸獨有的主體風格,在與歐洲、非洲的文化滲透過程中,具有抗爭和交融的二重性。
如同文學領域科塔薩爾直言自己受到歐洲寫作風格和價值體系影響一樣,拉美文化的“被影響”在他的小說中同樣表現得顯著而突出。其實,經歷著交匯、沖突、混合、滲透、融合的絕不僅是拉美音樂,科塔薩爾的小說創作也在不斷重復、變位、交匯、合一的幻境與現實中著筆,所有這些都是互文性關鍵要素“影響”的展現,促成了拉丁美洲文化被影響的一條主要途徑。
二、邊緣化:“個體模糊”與“集體無意識”的混合
由殖民和移民導致的拉丁美洲多元混血文化的形成,在豐富這一地域文化內涵的同時,幾乎不可避免地弱化了民族主體精神對民眾的影響。換言之,過于繁復的多民族性格交互使拉美缺乏一種一以貫之的民族個體意識,充滿不確定性的文化發展軌跡,造成斷裂式的民族認同形成過程,進而引發主體對自我身份確認的模糊,從而成為被審視的“他者”。
拉美文化中的“個體模糊”特征可被視作雅克·拉康鏡像體驗的前階段,即主體尚不能認識自我與他人的對立,現實與想象的情景意識在確立認知過程中被混淆,因此主體需要在“他者”目光中不斷探索找尋自我的確立。由于“他者”同樣具有“個體模糊”的危機,于是找尋“主體與自我”存在感的努力,成為拉美藝術家創作的原動力之一,其結果在拉美地區實際上形成一種封閉式的互為鏡像的體驗,主體身份依舊模糊。鏡像體驗并不一定需要一面鏡子,有時它可以借助一面玻璃,就像科塔薩爾《美西螈》中具有模糊性主體身份的、長久凝視美西螈并最終透過水族館玻璃變成一條美西螈的“我”。
“個體模糊”帶來的無疑是民間音樂與文學上的邊緣化趨向。這里的邊緣化并非指在世界舞臺上文化地位的邊緣,而是關乎拉美藝術家創作偏愛的形式及內容指涉。這里不得不提到在拉美大陸土生土長的興起于20世紀50年代的魔幻現實主義。它使得一片在政治經濟上因長期殖民壓迫而落后于世界的大陸經歷了一場“文學爆炸”而走在世界文化前沿。讀過加西亞馬爾克斯《百年孤獨》的讀者不會對此感到陌生,“主體模糊”催生的內心獨白、意識流動在幻想中完成了對現實的拆解。談到魔幻現實主義,馬爾克斯是人們公認的首選代表,但其實科塔薩爾的創作同樣具有魔幻現實主義風格,又或稱之虛無的現實主義。如前所說,科塔薩爾的作品充滿了重復、變位、交匯、合一,時間與空間可以被混雜和跨越。例如短篇小說集《秘密武器》中《追求者》一篇,主人公約翰尼曾拒絕對自己的薩克斯演奏進行錄音,他反復強調道:“這是我明天正在演出的曲目”。這里時間的秩序被完全打亂,敘事無需在現實時空中進行,魔幻卻為表現現實之真。所有的超自然、神秘、恐怖、怪誕,雖確實源起于土著印第安人的神靈崇拜與巫術傳說,我們卻不應單純視之為傳統民間文化習俗的延續與異化呈現。在現代語境下,自我與他者、真實與幻想的混淆才是孕育光怪陸離的魔幻成分的根基;而這種對孤獨與荒誕的魔幻化詮釋,其實標志著拉美文學與文化覺醒的開始。如此而言,我們是否應期許一場“音樂爆炸”的到來?
在世代累積的文化記憶場中,集體記憶與個體記憶交織,以圖鞏固集體的主體同一性,使集體獲得掌控文化存貯與傳播的權力與義務。對“集體性”這一詞匯的敏感使人們意識到拉美大陸對外來者(游客)展現出的邊緣化傾向,以及外來者(游客)對拉美大陸形成的異國想象。以筆者在墨西哥的凝視視角所生成的拉美異國想象為經驗基礎,我對拉美國家凝視的印象和想象是極其鮮活、深刻的,因為它完全符合外來者根據認知經驗和社會集體想象物而幻想形成的心理期待,即與先驗的拉美形象相契合,這或許是個體潛意識在發揮作用。與外來者(游客)的社會集體想象相對應的,是內部者(本土人)的“集體無意識”。榮格的集體無意識理論作為一種群體心理現象,在科塔薩爾文學作品中被推及到民族、人類的高度。民族的遷徙、口頭的傳頌、和無意識的積淀是一種社會性遺傳,在這一層面上,民族音樂體現了其遺傳的方式。約翰·布萊金認為,音樂證實了已經存在于社會和文化中的東西,音樂形成的方式與主體人在不同文化環境下形成的社會經驗密切相關。在集體無意識的語境中,或許可以說民間音樂是在“有意識”地表現無意識的本能,同時、表現了拉美文化的邊緣化趨向。
三、互文性:拉美音樂與文學互為鏡像的機制
從互文性視角探討音樂與文學的聯系,首先需要明確互文性的應用范圍。“互文性”又稱“文本間性”或“互文本性”,首由法國思想家克里斯蒂娃提出,在文學領域可被理解為文本彼此之間像一面鏡子,每一種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轉化,使得文學作品乃至文學現象之間能夠相互關聯、相互指涉并互做解釋。顯然,這種對互涉性尋找的本質特征并非只存在于文學研究領域。互文性理論從誕生之日起,就包含著拓寬語境的開放性潛力,像拉動一張充滿彈性的可延伸的網,完全能夠將應用范圍擴展到諸多文化視域中,進行多學科、多領域的對話。一切語境無論是政治的、歷史的,或社會的、心理的都變成了互文本,這樣互文性就顯現出既擴展了傳統文論的研究方法,又依舊包容著傳統文論的研究內容。
音樂與文學在互文性的關照下,同樣具有互為鏡像的表征。拉美民間音樂/文學指涉極廣,它經歷了不同時代背景和歷史發展時期,由原住民印第安人文化、作為殖民者的歐洲白人文化、殖民統治中被販賣到新大陸的非洲黑人文化交織而成。那么,音樂從何種角度、以什么方式與文學相關聯,顯然應該選取個案研究來加以認識,例如可以將南美民族民間音樂與阿根廷籍旅歐作家胡奧利·科塔薩爾(他同時也極富音樂涵養)的短篇小說作為切入口,二者皆經典,皆具力量。王爾德曾說:生活模仿藝術,生活實際上是鏡子,而藝術卻是現實。這里必須強調一個重要要素,即科塔薩爾的小說靈感皆源于生活經驗而非思想經驗,對生活經驗的萃取使其作品源于現實、卻超越現實。與之相似的是南美音樂——以阿根廷民族音樂為例——按類型可劃分為源自印加文化的印第安傳統音樂、從北方到安第斯山區,直至中部及潘帕斯大草原的廣闊地帶所流行的克里奧約音樂、以及享譽世界的探戈音樂。雖然原生性與移民性同存,但不可否認的是其音樂創作靈感皆源起于生活經驗。
至于內在結構相似性,需要談及科塔薩爾對自己文學創作的一個比喻標準,因為這一標準同樣適用于一些民族民間音樂作品。他認為一個好的短篇小說就像一個星球,有嚴格無誤的運行周期、善始善終、并且自成封閉體系。這體現在他的短篇小說集《動物寓言集》、《秘密武器》、《萬火歸一》中,每一部短篇都具有嚴密的運行章法,敘述流暢,首尾圓融;盡管某些小說具有開放性結局的特質,卻并非真正意義上的“開放”結尾,他作品的形式和結構都是封閉的。
從Music Online: The Garland Encyclopedia of World Music網站上Vol. 2: South America, Mexico, Central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udio CD一章中,可以找到拉美音樂的范例(如阿根廷探戈),其中的大多數樂曲能夠成為一個像科塔薩爾短篇小說那樣的星球。無論是以三聲、四聲和五聲為調式結構基礎、音域狹窄、樂句短小、曲調多為下行、演唱中還夾有假聲的印第安傳統音樂,還是音域不寬、節奏多為3/4拍、6/8拍,主曲調和伴奏之間的節奏交錯疊置的克里奧約音樂,抑或作為舞會舞蹈的探戈,它們都有運行周期、樂句發展有跡可循,獨立且封閉。更不用說探戈音樂后經阿斯托爾·皮亞佐拉發展為登上世界舞臺的、為現代聽眾所熟知的音樂體裁。
總之,圍繞拉丁美洲文化多元化、邊緣化及互文性關鍵詞的探討,旨在建構民間音樂與文學交互分析與對話的可能。文學研究以書面文本為主體,民族音樂學則偏重田野調查的資料;而民族音樂學發展到今天,在實踐過程中,理論分析也應得到強化。通過建構音樂與文學對話的機制,希望能夠拓寬民族音樂學理論分析的視野——記譜的譜面呈現使人們得知民族音樂之然,互文性的跨學科分析使我們更好地得知民族音樂之所以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