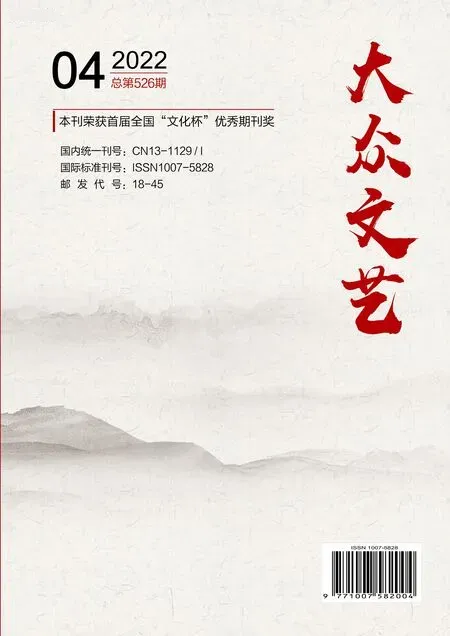論“聽和則聰”
楊 瀚 (陜西咸陽中學 712000)
“聽和則聰”語出《國語·周語下》單穆公對周景王進行勸諫時所表達的論樂思想。此語蘊含的價值一直以來并未受到學界應有的重視。蔡仲德曾在其論文《中國音樂美學的若干問題(上)》中說:“儒道兩家音樂美學思想有共同的源頭,都由孔子前萌芽狀態的音樂美學思想發展而來。”1“聽和則聰”正是出于這樣一個關鍵時期的思想,韓鍾恩在《中國音樂美學理念與相應范疇并及歷史轉型》2一文中,結合蔡仲德著《中國音樂美學史資料譯注》將“聽和則聰”列為先秦重要美學理念之列。蔡仲德今譯之為:“聽和樂就耳聰。”3“聽和則聰”是貫穿單穆公論樂思想,通達其所言“樂之至也”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此“聽和則聰”的角度為切入點,可以成為討論早期論樂思想的一條進路,值得重新審視其中思想內涵。
原文摘錄如下:
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度量衡于是乎生,小大器用于是乎出,故圣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震,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能思慮純固。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內聲,聲味生氣。氣在口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視聽不和,而有震眩,則味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慝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而有離民之器二焉,國其危哉!4
這段話出自《國語·周語下》周景王二十三年(公元前522年)。在此之前的周景王二十一年,景王欲鑄大錢,也受到單穆公的反對,單穆公從鑄造大錢“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5的角度向周景王進行了勸諫,最終結果是“王弗聽,卒鑄大錢”。兩年后的周景王二十三年,景王欲“鑄無射,而為之大林”6。此次單穆公從音樂和為政的角度向周景王進行了勸諫,景王不聽,又問于伶州鳩,雖然再次被反對,結果依然是“王不聽,卒鑄大鍾。”文段末尾記載“二十五年,王崩,鍾不和。”將周景王三年既崩與鐘之和并言,以表達《國語》作者的態度。這段記載突出了春秋末期周天子為政中的問題,即不能準確把握施政要點,致使人民負擔加重,國政偏失的問題。事實上,《國語·晉語八》記載早在晉平公(公元前547年)之時,就有:“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衰矣!’”7平公對新聲的喜愛,致使師曠擔心平公為政的能力衰退,這種現象是當時不少為人臣者所擔心的問題。本文欲以發掘的,便是單穆公這樣的背景下,向周景王勸諫的論述中所用到的“聽和則聰”理念內涵。欲意于此,首先需要闡明文中“聽和則聰”的文本含義。
一、釋“聽和則聰”字義及句式結構
“聽”的字形,與我們常見的聽不同,并非簡單地繁簡之別,更多的是語義的差異。本文論述中用“聽”字而非“聽”字,因為“聽”和“聽”兩字,在古代所代表的意義并不相同,現在“聽”代“聽”的用法,為今簡化后形成。
《說文》訓“聽”為“笑貌也,從口”,段玉裁注:“《史記·司馬相如·上林賦》:亾是公聽然而笑。”8訓“聽”為“聆也,從耳?”,段玉裁注“聽”為:“凡目所及者云視,如視朝、視事是也。凡目不能徧而耳所及者云聽,如聽天下、聽事是也。”又訓聆為“聽也,從耳”,段玉裁注“聆”為:“聆者,聽之知微者也。”9由字面義便可知《說文》以“聽聆”二字互訓之旨。又訓“?”為:“外得於人內得於己也”,段玉裁注之為:“”內得於己,謂身心所自得也。外得於人,謂惠澤使人得之也。”10由此可見“聽”、“聽”二字在古代之不同。“聽”為形容一種樣貌,而“聽”不但是形容用耳聽聲,更需分辨所聽之聲于入微,而使人內外皆有所得的一種能力。
其次是文本中,單穆公所言“聽和則聰”在:“夫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之后。《國語集解》注“樞機”為“發動也。心有所欲,耳目為之發動。”11點明了聽字與耳、與心有關,即耳之所聽必關乎于心。“聽和則聰”、“聰則言聽”結構工整,顯然有其中的理路,對于“聽”在文本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待后文論之。
結合以上兩點可以發現,單穆公所言中之“聽”,需是將“目不能偏見而耳所及者”與心連接,以心知其“微者”,再由此作用于外,以至于“外得於人內得於己”。這就要求“耳所及者”,心必須可以知其微,若心不足以知“耳所及者”之微,則不能稱之為“聽”。這將“聽”置于了一個很高的位置。
“和”的字形,根據鐘華《“和”的探源》12中的有關研究,“和”字在先秦以三種寫法為主,寫作楷書的字形為“和”、“龢”、“盉”三種。《說文》中訓三者之義分別為“相應也”13、“調也”14、“調味也”15,段玉裁在《說文解字注》中注“盉”時言:“調音曰龢,調味曰盉。今則和行而龢、盉皆廢矣。”可見在早期,形容音樂和諧時所用的“龢”就是“聽和則聰”中的“龢”。例如《左傳·襄公十一年》載:“如樂之龢,無所不諧。”16便是用“龢”來形容樂的和諧。段玉裁又注“龢”時言:“經傳多假和為龢。”17可知“和”與“龢”在古時通假。另《爾雅·釋樂》有載:“大笙謂之巢,小笙謂之和。”因此,和也是小笙的另一種稱呼。
《說文》訓“聰”為:“察也。從耳,悤聲。”段玉裁注之為:“察者,覈也。聰、察以雙聲為訓。”18可見“聰”有通過耳朵明達所察事物核心之意。關于先秦之“聰”的含義,亦有相應記載,《尚書·洪范》所載“敬用五事”中有載“聽曰聰”、“聰作謀”19;《管子·宙合篇》有載:“耳司聽,聽必順聞,聞審謂之聰。”20;《莊子·外物》有載:“耳徹為聰。”21由此三例可見,“聰”與“聽”有著密切的關系,結合單穆公所論文本“聽和則聰”、“聰則言聽”及上文釋“聽”為要求人可以以心知“耳所及者”之微。則可釋“聰”要求人能以所聽而“謀”、而“聞審”、而“耳徹”,故相對于“聽”之耳至心的關系,可釋“聰”為心至耳的關系,即“聰”是針對能察“耳所及者”之微的心而言的,若不能察其微,則不能稱之為“聰”。換言之,“聰”是一種心可以洞察事物之微的境界。
“聽和則聰”的句式結構分析可列舉如《國語·周語下》伶州鳩論樂:“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貴之。”22因為“平和”所以能“久”;因為“久固”所以能“純”;因為“純明”所以能“終”;因為能“終復”所以能“樂”。這樣排比遞進中,AB則C的句式與“聽和則聰”句式用法一致。均為A+B形成一個限定的整體將會造成C的結果,而單獨的A與B都不能導致C。類似的例子還有《論語·雍也》載:“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23可知,AB則C其實是因果關系,因為A+B的構成,所以將導致C的結果。將AB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則之前與則之后其實是因果關系,即因為前者的呈現,所以將導致后者的結果。例如《國語·楚語上》所載:“若周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匱。”24
由此可知“聽和則聰”的句式中,是因為“聽和”這個行為,所以將會導致“聰”的結果,“聽和”與“聰”是因果性轉換的。
二、釋“聽和則聰”
結合“聽和則聰”所出原文和上文所釋“聽”、“和”、“聰”,以及則的句式結構便可繼續討論單穆公所聽之“和”的意義指向。單穆公論之為:“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可見后文“聽和則聰”中的“聽和”意義指向,也就是“察和”的意義指向,其關鍵就在于“清濁”這對范疇之上,而“清濁”的思想可用《左傳·昭公二十年》記載晏子所言引證:
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大小、長短、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25
這段文字首先說明,先王“和五聲”是為了“平其心”、“成其政”。根據文中“以相成也”與“以向濟也”兩方面論述,可用之“以平其心”的音樂應該具備之條件,即可以符合“以相成”的諸多特點,又可以滿足“以相濟”的諸多條件要求,方可謂之“和五聲”。君子聽這樣的音樂,是為了“平其心”,“平其心”是為了“德和”的最終追求。在晏嬰的言論中列舉的“清濁”等十對范疇中,清濁這對范疇的思想內容相對抽象,可以看做是將后九對范疇綜合起來而言的。理由為其后九對范疇以現在音樂概念解釋則:“大小”關乎音量;“長短”關乎音符時值;“疾徐”關乎音節節奏;“哀樂”關乎情感;“剛柔”關乎音色;“遲速”關乎速度;“高下”關于音域;“出入”關乎空間感;“周疏”關乎氣韻。十對范疇,是以一定的相對立、對偶的元素為統一的。伴隨著音樂的運行產生于人的意義世界,并在意義世界中對音樂進行了一定的抽象和提升,均可列于“清濁”這對范疇之內。(十對范疇所關乎不止于此,其相互間也有重疊和交錯,現取其重點以論之。)從這點出發,則若一樂中具備“以相濟”的諸多元素,并能處于“清濁”范圍之間,致使君子能聽徹其中之和的音樂,即稱之為“和”。而超過“清濁”之和范圍的音樂,則君子不能“察和”,便是不“和”的音樂,這顯然是單穆公所反對的音樂,故言“今王作鍾也,聽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于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聽和則聰”所聽之“和”便處于這樣的范圍內而言的。
另一方面,單穆公提出“和”,是為了勸諫周景王不要耗費民財而鑄造“無益于樂”的鐘,單穆公勸諫周景王鑄鐘的理由是:“聽之弗及,比之不度”的鐘,會致使演奏時“鍾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是“無益于樂”反而耗費民財的,并不能達到作為君王應該追求的“樂之至也”。其中“聽之弗及”、“比之不度”指向為其前言之“耳之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因為不能滿足“耳之察和”,故稱周景王所追求的鍾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于樂”。這其中“知和”和“出節”的思想可以用《左傳·昭公元年》醫和的論述引證:
“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以后,不容彈矣。于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26
醫和認為君子應該遠離的音樂,是“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以至于沒有節制的音樂。所謂“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便是樂所承載的內容,不能使人心通達平和,反而以“慆心”為目標,使人沉浸于“慆心”之欲中,忘記了“先王之樂”是為了“以節百事”的目的,如此一來也就不能達到“平和”的目標。
與“聽和則聰”時代相近且類似的記載還有如《國語·楚語上》中:“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27也是將“聰”與“德”通過“聽”建立一種路線,以最終達于為“德”的目的,這與“聽和則聰”后“聰則言德”,并“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乃至于“成事不貳,樂之至也。”的思想是相近的。
至此,便可以綜合以上所論來闡釋“聽和則聰”了。它的意思是將以耳為媒介,在“清濁”范疇之內的“和”的音樂及其理念,通過“聽”的方式通達與心,并由心洞察分辨之于至微,復可作用于外的過程,稱之為“聽和則聰”。
三、“聽和則聰”與“樂之至也”
明白了“聽和則聰”在原文中的意思,我們再回到原文“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不過以觀目······政成生殖,樂之至也。”中的兩條并立的邏輯路徑上:
樂——聽耳——心——聽和——聰——言聽——思慮純固——言德于民——成事不二——樂(le)之至也
美——觀目——心——視正——明——德昭——思慮純固——明以時動——政成生殖——樂(le)之至也
其中“聽和則聰”與“視正則明”處于并立共行的狀態,“聽和則聰”由“樂不過以聽耳”對應而來,“視正則明”由“美不過以觀目”對應而來,都經過了“心之樞機”,并且共同推導至“思慮純固”,再復分為“成事不二”與“政成生殖”并最終達到“樂之至也”。“成事不二”依照文本中意思是:“口出”之言便可成“憲令”,使人民聽之無不盡心力行“從之不倦”,故而能使施政之人達到“樂之至也”。本文討論的“聽和則聰”思想對應的便是第一條路徑。
“聽和則聰”這條理路的起點是音樂之樂,但推導至“言德于民”、“成事不二”時,由聽樂欣賞已經到達了為政施政層面,單純的音樂之樂已經不能完全滿足邏輯意義的闡釋,若將之升華禮樂之樂來理解則更能符合文意,而文本對于“成事不二,樂之至也”的論述所言的:“以言德于民,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不濟,求無不獲,然則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也潛在的指向了這一層面的樂。因此“聽和則聰”正是處于使從聽音樂之樂,升華為作用于為政施政的禮樂之樂的關鍵一步,若不能“聽和則聰”,則“夫樂不過以聽耳”是無法通達至“成事不二,樂之至也”的。
四、總結
綜上所述,本文對春秋末期單穆公論樂思想中的關鍵理念——“聽和則聰”,進行了從字意到文本之意的梳理,再討論了“聽和則聰”在單穆公論樂的理路中的關鍵性地位,及其作用。“聽和則聰”思想,在后來相近時代的儒道兩家理論中也均有不同程度的呈現,如與道家典籍《文子·道德》中的“學問不精,聽道不深”28段論述相通,兩者均有表明人要對事物有深入了解,就必須對事物之微有深入洞察的要求;儒家典籍《五行》中的“五行皆形于內而時行之,謂之君子”29段也有類似體現,即皆要求人應該將好的理念作用于內心,而不是流于表面。
對于目前音樂美學、音樂史學研究來講,“聽和則聰”由于其蘊含思想在早期樂論理路中的關鍵地位,應該得到其相應價值的重視,它不但是一種認識,更是一種方法,是準確把握和研究音樂思想,不可或缺的重要理念。
注釋:
1.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的若干問題(上)》.中央音樂學院學報,1994年8月.
2.韓鍾恩.《聲音經驗的先驗表述》.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12年,第79頁.
3.蔡仲德.《中國音樂美學史資料譯注》.人民音樂出版社,2004年,第21頁.
4.徐元浩.《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年,第108-110頁.
5.同上,第105-107頁.
6.同上,第105-107頁.
7.同上,第423頁.
8.[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鳳凰出版社,2015,第100頁.
9.上同,第1028頁.
10.上同,第876頁.
11.徐元浩.《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年,第108-110頁.
12.鐘華.《“和”的探源》,世界文學評論,2007年10月,轉引自賈世敬博士論文《先秦典籍與〈黃帝內經〉“和”范疇研究》,北京中醫藥大學,2011年5月.
13.[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鳳凰出版社2015,第100頁.
14.[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鳳凰出版社2015,第152頁.
15.上同,第375頁.
16.[戰國]左丘明,[西晉]杜預集解《左傳》,轉引自劉鑫《唐前“樂象”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82頁.17.[清]阮元 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2009,第5659頁.
18.[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鳳凰出版社,2015,第1028頁.
19.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中華書局,2005,第1155頁.
20.黎翔鳳.《管子校注》,中華書局,2005,第230頁.
21.[清]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2012,第931頁.
22.徐元浩.《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年,第123頁.
23.[清]阮元 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2009,第5384頁.
24.徐元浩.《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年,第495頁.
25.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中華書局,2009,第1577-1578頁.
26.同上,第1351頁.
27.徐元浩.《國語集解》,中華書局,2002年,第493頁.
28.王利器.《文子疏義》,中華書局,2000,第218頁.
29.陳來.《竹簡〈五行〉篇講稿》,三聯書店,2012,第9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