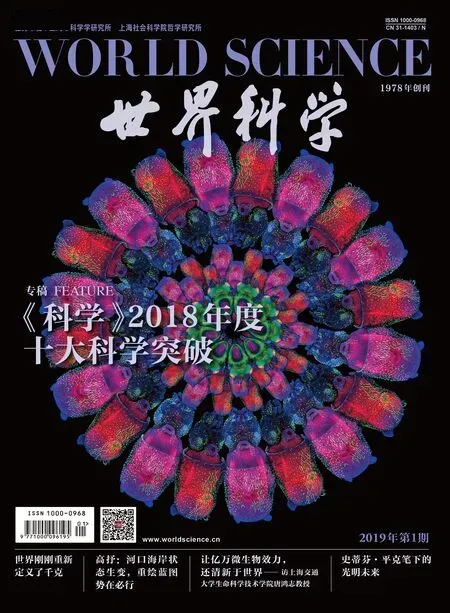科學滿意度調查
編譯 許林玉
許多理科生和初級研究人員一直渴望進入學術界,這可能是好幾代人的夢想。但是,《自然》雜志兩年一次面向全球科學界開展的薪資和工作滿意度調查揭示了一個重要事實:除了進行學術研究外,科學家還有大量其他的就業選擇,其中一些選擇無論是在情感上或是經濟上可能都更具價值。

《自然》的本次調查由倫敦一家研究咨詢公司遷移學習(Shift Learning)在2018年6月至7月期間開展,獲得了6 413名主動參與調查的讀者的反饋。(本科學歷以下受訪者的回復被篩選出來,最后只剩下4 334個樣本。)近40%的受訪者居住在北美,35%生活在歐洲,16%生活在亞洲,還有一部分研究人員來自澳大利亞、非洲和南美洲。
該調查的內容涵蓋了薪資水平、工作滿意度、工作與生活之間的平衡、是否遭遇歧視、心理健康以及其他一些關于科學職業生涯的關鍵問題。調查結果以及通過對一些受訪者的后續訪談表明,研究人員在科學領域的經歷不盡相同,有的已經功成名就,有的還在奮力前行。
超過2/3(68%)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對自己的職業生涯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這一比例與2016年的調查基本持平。不過,我們不能保證這些數據仍將保持穩定。37%的受訪者表示,在過去一年中,他們的滿意度有所下降;只有32%的受訪者表示情況有所改善。
就業部門的反饋也不盡相同。這表明,在廣闊的科學道路上,研究人員的態度千差萬別。就職于非營利組織的受訪者容易對自己的工作感到滿意(73%),其次是產業界(71%)、政府部門(68%)和學術界(67%)。加拿大溫哥華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和博士后研究系主任蘇珊·波特(Susan Porter)總結說:“這證明了一個事實,即在學術界之外也存在非常有成就感的高薪工作。”此外,自2016年調查以來,工作滿意度數據已有了一些變化,之前學術界科學家的工作滿意度(65%)略高于產業界(63%)。兩項調查呈現出來的差異表明,受訪者的工作滿意度已略微向企業傾斜。
其他調查也顯示,研究人員的工作滿意度處于較高水平,其中包括英屬哥倫比亞大學今年早些時候對博士研究生進行的調查和2016年非營利科學事業倡導組織Vitae對歐洲研究人員進行的一項調查。但是,Vitae負責人珍妮特·梅特卡夫(Janet Metcalfe)警告說,工作滿意度并非總是意味著工作環境令人滿意。研究人員對研究工作充滿熱情,因此他們的工作滿意度會很高,但他們仍然可能要承受較大的壓力和糟糕的身體狀況。
薪資水平
有關薪資的問題揭示出各領域之間更深的鴻溝。有59%的產業界受訪者表示對薪酬感到滿意,而相比之下,學術界、非營利組織和政府部門分別只有40%、41%和49%的受訪者對自己獲得的報酬感到滿意。總體而言,43%的受訪者說他們對自己的薪酬很滿意。報告稱最近加過工資的受訪者勉強超過50%,但這顯然不足以消除所有的失望情緒。

薩姆·普羅斯金(Sam Proskin)是加拿大卡爾加里瑟伯工程公司的一名高級巖土工程師,他對自己的薪水和職業選擇感到滿意。20世紀90年代中期,他獲得加拿大埃德蒙頓阿爾伯塔大學的巖土工程博士學位,當時他希望能在學術界找到一份工作。他對美國和加拿大的學術領域進行了研究,發現機會甚少,而且壓力極大、競爭激烈,于是決定從事咨詢工作,覺得這更適合施展自己的才華并實現自己的抱負。
如今,普洛斯金的工作是為其他正在憧憬未來的年輕工程師和地質工作者提供建議。他鼓勵他們保持開放的選擇,避免“要么進行學術研究,要么一無所有”的心態。他說:“也許現在是時候改變這種想法了。應有模式應該是,除非你非常具有學術潛能,否則就應該進入產業界。”
馬里亞娜·帕切科·布蘭科(Mariana Pacheo Blanco)是捷克維斯泰克生物技術和生物醫學學術研究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員,她對自己在學術領域的工作感到滿意。但她也有怨氣——對獲得資助經費的機會感到失望。布蘭科說:“我在德國待了5年,那里提供的科研經費非常充足。德國和捷克之間的差距可謂天壤之別。”布蘭科原籍墨西哥,在德國明斯特大學獲得了博士學位。
作為一名日子過得拮據的博士后,她代表了另一條可能比產業界與學術界之間相差更大的鴻溝:貧富之間的差距。只有5%的受訪者稱自己的年薪超過15萬美元,而近30%的受訪者稱自己的年薪在5萬至8萬美元之間,近25%的受訪者稱自己的年薪在3萬至5萬美元之間。還有11%的受訪者稱自己的年收入在1.5萬至3萬美元之間,12%的受訪者收入甚至沒有那么高。
在薪酬方面,職務職稱也十分重要。盡管收入低于1.5萬美元的教授、經理和研究負責人只有少數幾人,但收入區間的末端仍以教師為主。大約50%的教師受訪者表示,他們的收入低于3萬美元;近30%的研究人員的收入也處于中等水平。收入位于最頂層的大多是全職教授、經理和研究負責人。
與2016年的薪資調查一樣,地理因素被證明是薪資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在亞洲,近40%的受訪者稱年收入不足1.5萬美元,而在北美,這一比例為2%。在收入最高的地區,北美和大洋洲有11%的受訪者收入超過15萬美元,遠遠領先于其他地區。歐洲仍處于“水深火熱”之中,略高于20%的歐洲受訪者稱年收入低于3萬美元,而北美只有5%的受訪者稱年收入低于3萬美元,這一結果與2016年的調查結果持平。
此次調查還反映了收入方面的性別差異,尤其是在從事這一職業多年的科學家中。在那些說自己處于職業生涯晚期的受訪者中,33%的男性年收入超過11萬美元,但只有23%的女性達到這一水平。在處于初入職場階段、職業生涯早期和職業生涯中期的受訪者中,收入等級在性別之間的分配較均勻。此外,女性也比男性更有可能對自己的薪酬感到不滿(分別為59%和53%)。
結果表明,“您對您的薪水滿意嗎?”這一問題的答案是相對而言的。超過20%年收入15萬美元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對自己的薪水不滿意;而27%年收入為1.5萬至3萬美元的受訪者稱對自己的報酬感到滿意,這可能是因為該收入范圍達到了他們的預期,并且可以應對生活成本問題。
印度班加羅爾國際信息技術學院的計算機科學家施里沙·拉奧(Shrisha Rao)表示:“我很幸運能在一家很看重我的機構工作。我的收入并不比美國人多,但對于我的國家和我的職業來說已經算高了。”他的收入并沒有達到很高的水平,但他對自己的薪水和工作感到滿意。
職業路徑
然而,不出所料,學術工作仍然備受青睞:近3/4(70%)的受訪者表示,這一直是他們攻讀博士學位的主要目標,這與接受《自然》雜志2017年研究生調查的學生的愿望一致。從事非霍奇金淋巴瘤研究的布蘭科對自己的工作非常滿意,主要是因為她覺得自己的課題很吸引人。她說:“我在研究癌癥,這讓科學變得更加令人興奮,這項工作無論在哪里都是熱門課題。”她對自己的導師、癌癥生物學家翁德雷吉·哈夫拉內克(Ondrej Havranek)更是贊譽有加。哈夫拉內克對時間要求不嚴,也樂于提供建議,不會要求團隊長時間工作。她說:“如果我想在下午5點下班,就可以在下午5點下班。他尊重我的私生活,這對學術界的一些人來說可能是個奢望。”
2005年,拉奧獲得愛荷華大學的博士學位。他從接受科學培訓的早期開始就把目光投向了學術界。作為一家研究云計算和資源利用的技術機構的教授,他覺得他的計劃獲得了回報。他表示:“我獲得了學術自由,沒有人會定期告訴我該做什么。不過,如果有更多的資源,我和同事們會更開心。在科學方面,印度的表現不如人意,這是一個殘酷的事實。”
滿意度

無論科學家在哪里工作,在一天中找到足夠的時間來平衡事業和個人生活都是一大挑戰。盡管大多數受訪者認為自己做到了工作與生活的平衡,但這仍然是體現產業界工作優于學術界工作的另外一個方面:79%的產業界受訪者表示,他們在這一方面對自己的職業感到滿意,而感到滿意的學術界受訪者比例為68%。
工作滿意度涉及多個層面。當被要求指出對滿意度最重要的因素時,受訪者將興趣放在第一位。在實際滿意度方面(被認為最重要的事情能夠成為現實的理想情況),這一因素也排在第一位。盡管如此,科學家工作滿意度的其他方面也拖了后腿。參與調查的人普遍對自己無法對影響自身、工作保障、職業發展機會和成就獲得認可的決定施加影響而感到不滿,而他們認為所有這些都是將一份工作變得有價值的重要因素。
幸福感
受訪者也坦率地表示,他們的工作對自己的精神健康有消極影響。16%的受訪者認為,他們曾經或者正在接受抑郁或焦慮方面的幫助;17%的受訪者說他們沒有得到幫助,但愿意接受幫助;3%的受訪者尋求過幫助,但尚未得到幫助。這些反應與科學界普遍存在的“不安”模式相一致。在《自然》雜志2017年開展的研究生調查中,1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曾因學習直接導致的焦慮或抑郁而尋求幫助。

當然,歧視和騷擾問題仍然是科學領域普遍存在的頑疾,它們也會損害研究人員的工作滿意度或完成工作的能力。超過1/4(28%)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在目前的工作中發現了這類問題;超過1/5(21%)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曾親身經歷過這類問題。在那些說他們目睹或經歷過某種歧視的人中,將近一半(47%)的受訪者說他們經歷過最常見的歧視——性別歧視。曾親身經歷性別歧視的受訪者中,有91%是女性。與年齡(23%)或種族(22%)相關的歧視也相對普遍。
大約有一半受訪者認為,他們的工作單位在促進多元化方面已經做得足夠好。在產業界工作的受訪者(58%)比在學術界工作的受訪者(50%)更有可能認為,他們所在的機構是問題的關鍵。漢娜·墨菲(Hannah Murfet)是英國劍橋微軟研究院的一名質量合規經理,她對雇主的評價很高。她介紹說:“我現在工作的單位非常注重多樣性和包容性。”
墨菲提倡女性進入科學領域工作,她幫助建立了“下一代網絡”——一個致力于幫助年輕研究人員了解合規和質量控制相關工作的團體。合規和質量控制是一個越來越受歡迎的職業選擇,許多科學家幾乎都是出于偶然而踏足其中。她說:“如果更多的人考慮從事這份工作就太好了。”最重要的是,她希望鼓勵年輕人對各種選擇保持開放的心態。她解釋說:“如果你對產業感興趣,那就找個機會進入該行業,它能幫你實現自己的夢想。你不必一直做一名實驗室科學家,你還可以從事市場、銷售或合規領域的工作。
近60%的受訪者對自己的未來工作前景持積極態度,這一比例與2016年的調查相比變化不大,但這種樂觀情緒的分布并不均勻。如果科學家有一份全職工作,而且年齡在40歲以下,并且還是男性,他們的前景會更被看好。認為自己前景不容樂觀的受訪者占25%,他們更有可能是女性,而且簽的是臨時合同。另一個悲觀論調是,超過一半(51%)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的就業前景比前幾代人糟糕。盡管如此,仍有整整7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會建議學生從事科研工作,這一比例明顯高于2016年調查的61%。
美國德克薩斯科學博物館唐·哈林頓發現中心的執行董事艾倫·潘(Aaron Pan)就是這些科學支持者之一。在獲得古植物學博士學位后,潘開始在德克薩斯州達拉斯的南衛理公會大學做博士后,并計劃繼續從事學術工作,直到另一個選擇出現。后來,他通過申請成為德克薩斯福特沃斯科學與歷史博物館的館長,職業軌跡因此發生改變。他說:“我想自己在不同的道路上都會很快樂。我在這里仍然可以從事研究工作,但這是我想做的研究,不需要為了獲得終身職位而發表論文。”
無論是在學術界、產業界、非營利組織還是政府機構,有很多地方可以從事科研工作,也有很多途徑成為一名科學家。《自然》的調查強調了選擇的多樣性,也指出了研究人員在規劃職業道路時應該牢記的問題。從薪資水平到工作滿意度,也許可以順風順水,但也有可能事與愿違。好消息是,對于大多數人來說,科學永遠充滿樂趣,這足以讓一個人堅持下去。
資料來源Na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