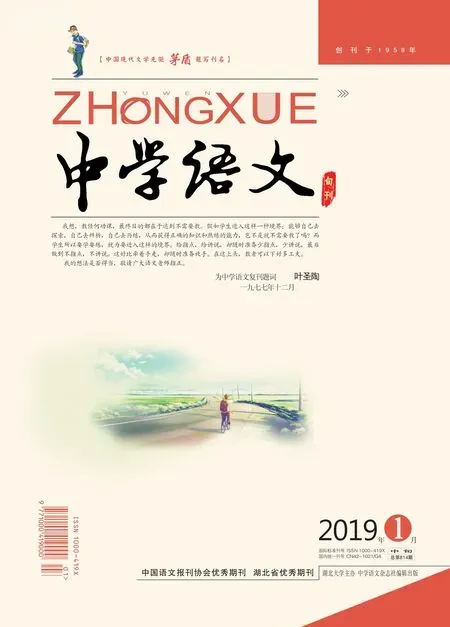是沉默,還是話語
——阿多尼斯《你毫無選擇》賞析
錢曉國
[作者通聯:湖北安陸市安陸二中]
“怎么?于是你摧毀地球的臉∕為他刻上另外一張臉。∕怎么?于是你毫無選擇∕除了火焰之徑,∕和拒絕的訓斥,∕當地球不再是∕一座斷頭臺或一個上帝。∕今天我有我的語言∕我已經摧毀了我的王國,∕摧毀了我的王座,我們的宮殿和柱廊。∕同時,我在我的肺上孕育,∕在尋求中漫游,∕把我的雨滴教給海,承認它們∕我的火與香爐,∕并寫下來到我唇邊的∕時間。∕今天我有我的語言,∕我的國境,我的土地和擦不掉的記號,∕我有我的人民,∕他們以無常養育我∕并在我的廢墟和∕翅膀上尋找光。”
(阿多尼斯《你毫無選擇》)
阿多尼斯,敘利亞著名詩人,在《毫無選擇》這首詩里,他一如既往地延續了他對這個世界深入骨髓地感受、審視與愛戀,盡心盡意地倡導人的自由和尊嚴,以及國家和民族的解放。大詩人之所以為大詩人,正是因為這種情懷、擔當和責任意識。詩歌自誕生之日起,從來都不是一種單純 “為詩歌詩歌”的純粹的語言藝術,詩歌除了表面的“能指”,還有其“所指”的意義。詩歌拒絕矯揉造作的無病呻吟,當然也拒絕將詩歌窄化為單薄的語言游戲。
“怎么?于是你摧毀地球的臉∕為他刻上另一張臉”,“地球的臉”是怎樣的?“另一張臉”又如何?在語詞的表象上是看不出來的,但從“摧毀”的徹底和“刻上”的堅決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地球正在“你”的手中進行著翻天覆地的變化。至于用什么手段來“摧毀”和“刻上”,接下來詩人說“怎么?于是你毫無選擇∕除了火焰之徑,∕和拒絕的訓斥,∕當地球不再是∕一座斷頭臺或一個上帝”在其隱晦的文字表達里,可以窺視的是這個手段就是“火焰之徑”和“拒絕的訓斥”,以熊熊燃燒的烈焰去摧毀象征著獨裁暴力統治的“斷頭臺”,以拒絕和訓斥的鮮明而決絕的態度和舊世界道別。在“你”的心中,地球的另一張臉應該是尊嚴和自由之地,而“一個上帝”所帶來的只能是思想上的禁錮。
這里不可忽略的還有一點,那就是潛在的人物的對峙。“你”是外顯的主體,直接表露個人的態度、情感和意志。而在兩個“怎么?”里,還隱藏著一個與“你”在語言和意義層面呈對峙關系的發問主體。這個主體可以是普羅大眾,代表世俗人心的頑固或覺醒;也可以是另外的一個“你”,以表面的分離對峙表現出意義的多樣性、復雜性和深邃性,否定舊秩序、舊世界從來不是平坦的通途,也從來不缺乏血與肉的洗禮。從這個意義上來講,“你”的分離,隨其變革意志的愈發堅定,必定會趨向融合。其后的詩句也正說明了這一點,從“今天我有我的語言”一句開始,“發問主體”消失了,“你”也消失了,統統代之以第一人稱的“我”。內在可能分列的人格、思想和意志,全都得以嶄釘截鐵地彰顯,詩人熱烈地宣稱“我已經摧毀了我的王國,摧毀了我的王座,我的宮殿和柱廊”。推倒是為了重建,摧毀是為了新生。于是,詩人說“同時,我在我的肺上孕育”,這是光明和希望的開始。其實,無論是“你”還是“我”,都不是哪個單獨的生命個體,而是融鑄了輝煌與沒落、封閉與開放的敘利亞民族。面對世界浩蕩的文明發展史,敘利亞自然不能置身其外,不管是內在的還是外在的因素,都讓敘利亞的政治局勢激流涌動。詩人阿多尼斯本著一腔愛國之心將強烈的熱情投注于敘利亞的變革與新生上。整個國家與民族都化身為一個鮮活的“我”,從呼吸中開始煥發新生。
“在尋求中漫游,∕把我的雨滴教給海,承認它們∕我的火與香爐,∕并寫下來到我唇邊的∕時間。”摧毀朽腐與專制相對而言,比較容易;但新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是“在尋求中漫游”。“把我的雨滴教給海”,無數的“雨滴”成就大海的蒼茫與遼闊,無數的個體匯聚成改天換地的無窮力量。變革固然要徹底,但徹底并不是完全地否定,變革之余最重要的是思索與反省。“我的火與香爐”里是燃燒過往的灰燼,是埋葬舊時代、舊制度的的灰燼,見證曾經的浮華與墮落,最終的價值就是供人憑吊與反思。“承認它們”需要智慧,更需要胸襟與勇氣。以往可鑒,未來可期。阿多尼斯以委婉而熱情地筆調寫下變革到來的“時間”,這“時間”由“我”親口說出來并記載于歷史的冊頁上。“時間”單獨成行,可見其歷史性的意義和無與倫比的分量。
“今天我有我的語言”,詩人反復高歌,全新的“我”、全新的敘利亞顯現于世人面前。這是一個嶄新的國度,也是一個嶄新的民族。這里有“我的國境、我的土地、和擦不掉的記號”,當然更重要的是“我有我的人民”。 “國境”與“土地”,構成有形的國家分界,這是國家在廣度上的伸展,而“擦不掉的記號”象征著古老的阿拉伯民族磨難重重的歷史記憶,則是國家于民族精神深度上的縱深。當然,敘利亞民族歷史上雖遭重重劫難,卻仍能如鳳凰在涅槃中重生,離不開偉大的敘利亞人民。對此,阿多尼斯作為一個民族詩人,充滿民族自豪感。“他們以無常養育我∕并在我的廢墟和∕翅膀上尋找光”。“無常”是國家和民族的無常,作為世界古老文明的發源地之一,曾歷經羅馬帝國、阿拉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等大國統治,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又由法國委任統治;1944年獨立,1963年由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執政至今;2011年開始,敘利亞又爆發了政府與反對派曠日持久的沖突,而今沖突仍未息止,敘利亞的明天在哪里?“無常”的命運從另一個方面鑄就敘利亞人民的堅韌品性,他們鍥而不舍地在 “廢墟和翅膀上尋找光”,“廢墟”重塑著敘利亞的根基,“翅膀”承載著民族復興之光。
詩傳情,詩言志,詩要有更偉大的使命,就如著名詩人楊煉所言:“新詩不能滿足于像浪漫主義詩人那樣抒發感情,而應體現全面、嶄新的文化觀,表達對人生、社會的全新認識。詩歌也不能滿足于像現實主義詩人那樣反映現實,而應該啟迪讀者,如火焰一樣為他們照亮新的天際。”阿多尼斯既非單純的浪漫主義詩人,亦非純粹的現實主義詩人,或許我們可以換個說法,他用浪漫主義的詩歌語言,藝術化地反映出一個民族復雜而深邃的社會現實和歷史印記。
阿多尼斯是偉大的,他有足夠的理由獲得世界人民的崇敬與愛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