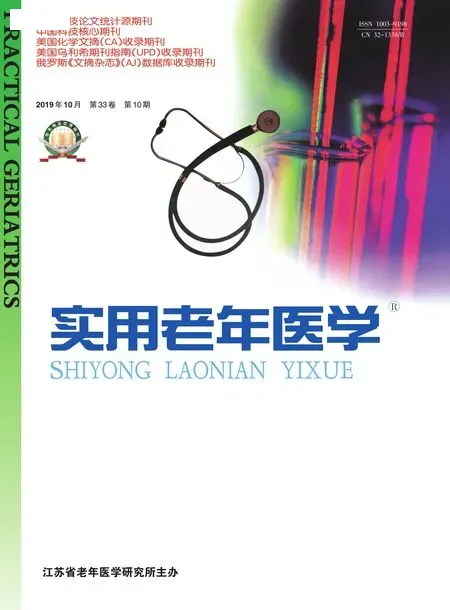老年人非軀體疾病所致軀體癥狀的特點分析
精神科里的軀體癥狀,是指病人沒有具體的軀體疾病,卻能感到切實的軀體不適。這類病人往往長期奔跑于綜合醫院的各個科室,做了大量的檢查,試圖能找出自己軀體不適的病因,但最終都是無功而返,且這類人往往顯得固執,十分“執著”的不斷尋找著。這類人通常還比較急躁、焦慮、難纏,以至于最終成為讓醫生看到就“頭大”的病人,其執迷不悟的“逛醫”行為,不光造成了巨大的醫療資源的浪費,也給很多科室的臨床醫生帶來了不必要的額外的工作負擔。但這部分本屬于精神科的病人卻很少就診于精神科,甚至其它科室的臨床醫生,也很少會想到將這部分人引導去精神科。王濤等[1]曾對5000多例以軀體癥狀為首發就診于消化科但最終確診為抑郁癥的病人進行調查,發現這些病人中只有很少(5.3%)的病人直接就診于精神心理門診,并且只有7.2%的病人被其他臨床科室的醫生識別了,大部分的病人都被不恰當地診斷和不恰當地治療。
這類人群中,老年人又常常是更為突出的一個群體。與年輕人比較,老年人身體機能下降,性格相對定型,適應能力下降,孤立、孤獨、患病、失業、遇到哀傷事件等,使得老年人成為容易出現情緒障礙的高危人群[2]。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老年抑郁癥病人占整個老年人口數的7%~10%,且發病率隨著年齡的上升而增長[3]。國內報道社區大于65歲老年人中重度抑郁患病率約為5%[4],其中,大于50%的老年抑郁病人突出表現為軀體化癥狀,但常被臨床醫生忽視或當作軀體疾病在綜合醫院往返診治[5]。那么,老年病人中的軀體癥狀,又有哪些特點呢?
1 老年軀體癥狀的臨床特點
軀體癥狀可見于精神科的多種疾病,常見的如抑郁癥、焦慮癥、軀體形式障礙、分離轉換障礙等。各個疾病的軀體癥狀,依據各疾病的特點,又稍有不同,如抑郁癥主要表現為乏力、疼痛、胃腸道不適等,而焦慮癥往往出現心悸胸悶、出汗、四肢震顫等,軀體形式障礙的軀體癥狀常多種多樣[6]。趙安全等[7]對老年抑郁癥的癥狀進行調查,發現老年抑郁癥病人的精神和心理癥狀不明顯,而是軀體癥狀比較突出。姜小琴等[8]還發現,老年抑郁癥病人,其焦慮癥狀的表現比非老年病人更突出,常合并認知障礙、激越、疑病。趙亞軍等[9]對社區老年焦慮病人進行了分析,發現老年焦慮病人的軀體癥狀多種多樣,主要為肌肉酸痛、運動不安以及氣短。Zijlema等[10]對老年抑郁癥病人進行了軀體癥狀的問卷調查,結果共統計了40項軀體化癥狀,其中70%為頭痛,65%為惡心或腹部不適,58%為氣短或呼吸困難,55%為頭暈,55%為背痛,且提示軀體癥狀越多,存在心境障礙的概率就越高,這些軀體化癥狀常不典型,十分容易漏診、誤診。趙貴淳等[11]對老年抑郁病人軀體癥狀的調查顯示,出現最多的癥狀依次為胃腸道癥狀(91%),頭暈頭痛(65%),心血管癥狀(58%),并且所調查的病人中,或多或少都伴有這樣那樣的軀體癥狀,且這些軀體癥狀常殘留至康復期,康復期殘留軀體癥狀的程度與病人的焦慮程度有關,而與抑郁程度、認知程度及社會功能水平沒有明顯的關系。
2 老年軀體疾病與軀體癥狀的相互影響
與青年人相比,老年病人還有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本身就常合并多種軀體疾病。老年人抵抗力下降,各器官功能減弱,易受多種慢性疾病的困擾,屬于健康最脆弱的群體。長期慢性病的困擾,易使老年人產生悲觀失望的情緒,存在較多的心理問題,常導致心理疾病與軀體疾病共病,使得軀體疾病的癥狀變得更加復雜,軀體癥狀常常擴大化,增加診斷難度,過多的癥狀常導致過度的治療,從而又增加了病人的疾病負擔,損傷病人的社會功能,甚至影響腦的認知情況,最終又降低病人的生活質量,使其心理問題進一步惡化[12]。孫菲等[13]研究軀體疾病對老年抑郁癥病人的影響,發現共病軀體疾病的老年抑郁癥病人,其抑郁的恢復比無軀體疾病的老年抑郁癥病人要差。
另一方面,共病軀體疾病,也使得精神障礙的臨床表現變得難以捉摸,如長期治療的精神障礙的老年病人,出現病情的變化,可能是精神疾病本身的病情變化,也可能是軀體疾病所導致的精神障礙。張會蓮等[14]對148例軀體疾病所致精神障礙的病例進行分析,發現軀體疾病所致的精神障礙臨床表現錯綜復雜,不典型的情緒障礙多見,或者一些心肺臟器受損時常出現意識障礙,對于一些突發的或不典型的精神癥狀,要多結合病史、查體及輔助檢查,不能輕易診斷為精神疾病。趙輝等[15]曾對護理院內出現的46例精神障礙病人進行分析報道,老年病人出現了焦慮失眠、多疑及軀體癥狀,本以為是焦慮癥,結果逐漸出現了幻覺及妄想,最終確診為軀體疾病所致的精神障礙。可見,重視老年病人軀體疾病可能導致的精神障礙尤為重要。同時,在一些慢性疾病的慢性進程中,也會伴隨逐步進展的精神癥狀,如陳曉等[16]對95例軀體疾病伴發精神障礙的老年病人的回顧分析顯示,這些病人患有心血管系統、呼吸系統、內分泌系統等不同程度的慢性疾病,在這些疾病的進展變化中,病人分別出現了人格的變化、智能障礙以及情緒變化等。總之,老年病人軀體疾病與精神疾病共病情況多見,軀體癥狀多變,需提高警惕,注意鑒別。
3 老年人心理特點與軀體癥狀的關系
老年病人不光其繁多的軀體疾病與軀體癥狀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其特有的心理特點,也是導致其軀體癥狀比青年人更常見的重大因素。與青年人相比,老年人的社會角色往往進入了轉型期,從原先的主要崗位離開或退休,經濟能力也可能下降,容易造成失落與孤獨,機體能力下降,軀體病變多,容易恐懼和悲觀,同時記憶力、思維能力下降,失眠等,容易造成老年人的情緒控制力下降及性格固執[17]。這時,家庭的支持,對老人尤其重要。陳長香等[18]研究指出,家庭支持差的老年人,其軀體和心理的健康情況,都要比家庭支持好的人差。
李昌俊等[19]曾總結,造成軀體化癥狀最突出的人格因素主要為述情障礙,缺乏安全感的依戀類型,以及神經癥與消極特質。其中抒情障礙,又可分為情感性述情障礙和認知型述情障礙,認知型述情障礙與軀體癥狀的關系最為密切。認知型述情障礙是指病人能體驗到情緒的變化,但不能將這些情緒表達出來。Waller等[20]將有軀體癥狀的病人與其他病人比較,發現述情障礙與軀體癥狀高度相關,且述情障礙對軀體癥狀有直接預測作用。老年人社會角色變化,認知功能下降,特別在我國過去的文化背景下,情緒的表達被視為可恥,因而老年人的述情障礙情況較青年人嚴重。其次,不安全感的依戀類型也易導致軀體癥狀,我國為家庭聚集型社會,但目前空巢老人多,或者家庭關系緊張,加上老年人軀體癥狀多,老年人自身的恐懼感,使老年人在人際關系上缺乏安全感,易緊張、焦慮。Schmidt等[21]將此類成人不安全感依戀類型大致分為焦慮不信任型和焦慮怕失去型,并對1997例德國受試者進行調查,發現焦慮不信任型易出現疲勞、心血管和胃腸道癥狀,而焦慮怕失去型易出現疼痛、皮膚及腹部癥狀。只有安全依戀型的人,才能靈活地處理人際關系,既接受別人的關愛,又給予別人愛,而那些不安全依賴型的人,人際關系總是恐懼的、僵化的,總認為自己得不到愛,特別在壓力來襲時,這種尋求關愛的行為會加劇,可以表現為對醫生訴說著各種各樣五花八門的癥狀,四處求醫。此外,神經質與消極情緒的特質,也是導致軀體癥狀的高危因素。神經質與消極情緒特質本質上一致,都是指具有一種體驗負性情緒體驗的傾向。研究表明,軀體化癥狀病人的消極情緒體驗更明顯。Fukuda等[22]對軀體化癥狀者與正常受試者做性格分析比較,發現軀體化癥狀者的神經質素質明顯要高。Aronson等[23]曾對64例健康大學生進行研究,發現消極情緒特質與癥狀自評量表SCL-90中的軀體化因子顯著相關。老年人性格易固執、緊張、焦慮,負性情緒體驗敏感,會進一步影響老年人的認知過程,使其易以悲觀的認知模式不斷的喚起對軀體癥狀的感知覺,甚至使一些正常的感知覺理解為疼痛或病理性,導致各種各樣的軀體癥狀。
4 老年病人軀體癥狀的病理機制
軀體癥狀的病理機制涉及多因素,同時涵蓋個體的易感性和環境的相互作用,涉及神經遞質、炎癥系統、腦環路等多個環節。同時老年病人又有自己的特點,其軀體共病多,認知功能下降,睡眠障礙等問題與軀體癥狀相互作用,可加重軀體癥狀。神經生化方面,5-羥色胺和去甲腎上腺素參與了從中樞到周圍神經系統多個層面的痛覺調整,其功能失調可導致多個系統的痛覺的傳入脫抑制,使大腦可以感覺到擴大的痛覺信號。一些慢性應激導致的慢性疼痛,可以導致糖皮質激素介導的抑制性連接下調,從而增強疼痛敏感性,加劇疼痛癥狀及情緒障礙[24]。神經環路方面,抑郁癥的情感癥狀和軀體癥狀存在差異,參與情感癥狀的腦區相對局限,如腹內側前額葉皮質、眶額葉皮質和杏仁核[25]。而額葉、前扣帶回、基底區及邊緣系統構成的廣泛皮質-皮質下通路參與軀體癥狀[26],例如基底前腦參與睡眠調節,下丘腦與伏隔核參與食欲、動機的調節,紋狀體、小腦、脊髓等參與運動的調節。
5 小結
我國已步入老齡化社會,隨著年齡的增長,生活方式、社會角色變化及各器官功能的不斷衰退,老年人出現復雜而不典型的軀體癥狀增多,社會功能及生活質量均受到影響,熟悉和掌握老年人軀體癥狀的特點,能提高我們對老年病人軀體癥狀背后的心理疾病的識別能力,而對老年軀體癥狀病人的關心、交流,也能讓我們在面對老年人繁多的軀體和心理疾病共病時做出更準確的診斷和更恰當的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