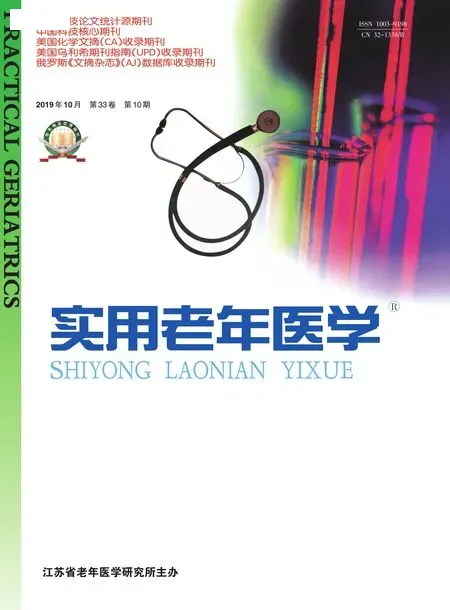知“心”懂“身”,從心身醫學角度理解軀體癥狀
在傳統的生物醫學思維中,軀體癥狀總是有相應的病理基礎,因此軀體癥狀就是各種軀體病理改變的線索,并指引臨床醫生啟動診斷及治療的流程。但是在具體臨床中,往往有這樣一些病人,有大量的軀體癥狀主訴,但是經過針對這些癥狀進行詳細的體格檢查或輔助檢查,其檢查結果卻無明顯異常或僅有微小的異常,往往“訴不對癥”。在傳統醫學模式中,這要么導致了疑難雜癥的產生,要么對病人來一句“你沒病”草草了事,導致臨床診療進入到一個困境中,耗費大量的醫療資源。隨著心身醫學的發展,對于臨床軀體癥狀,采用心身醫學理論框架進行理解,能讓臨床醫生更好地理解軀體癥狀,并進行合理的處理。
1 軀體癥狀的“心”和“身”
心身醫學(psychosomatic medicine) 是探討心與身之間的相互關系在健康的保持及疾病發生、發展和康復中作用的一門學科。它強調心(精神、心理、社會引起的情緒因素) 與身(軀體的結構與生理功能) 之間相互關聯、相互依賴、相輔相承、相互影響,互為因果[1]。心身醫學對于軀體癥狀的理解遵循了“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以最常見的軀體癥狀“疼痛”為例,2016年國際疼痛學會(IASP)官方雜志《疼痛》發表了關于疼痛的新定義:“疼痛是一種與組織損傷或潛在組織損傷相關的感覺、情感、認知和社會維度的痛苦體驗”[2]。從該定義我們可以發現:首先,疼痛是一種痛苦的主觀體驗,因此成為了一種軀體癥狀;其次,疼痛的發生是和組織損傷或潛在組織損傷相關,疼痛作為一種軀體癥狀并不是純生物源性的;第三,疼痛這種主觀體驗的產生又與感覺、情緒、認知和社會等精神-心理、社會因素相關。因此從心身醫學的角度來理解軀體癥狀,我們認為軀體癥狀應該存在兩種成分:一種是“身”的成分,這一成分也可以理解為生物學成分,如由物理、化學、生物因素導致身體組織的損傷直接導致的軀體癥狀;而另外一種應該是“心”的成分,這部分的軀體癥狀主要和精神、心理、社會因素有關,又稱為軀體化癥狀,也常常被醫生稱為非特異癥狀、功能性癥狀、神經官能癥等。Lipowski[3]將軀體化定義為,一種體驗和陳述軀體不適或軀體癥狀的傾向,但無相應的軀體疾病的證據,病人通常將軀體不適歸咎于軀體疾病,而求助于臨床各科室。這一部分癥狀,往往無法用生物醫學的病理結構改變和病理生理異常給予合理的解釋,所以又被稱為“醫學無法解釋的癥狀”(medically unexplained symptoms,MUS)[4]。
2 軀體癥狀“心”的解讀
孫學禮等[5]從心身醫學的角度對于軀體癥狀提出了5個定義,指出軀體癥狀是軀體對于外界環境的述求,是為緩解病人內心的沖突,是一種負性情緒的直接表現,同時軀體癥狀可能是一種學習模仿的結果,也和個體的認知和社會特征有關。根據這5個定義,提出軀體癥狀的意義不僅是提示軀體疾病,同時也可以作為提示精神疾病、心理異常、個體特征的證據。
“述情障礙(Alexithymia)”是心身疾病病人的一個核心特征[6]。述情障礙理論認為人類表達“述求”的主要方式是情感和言語,但述情障礙者在情緒體驗的自我感受和言語表達方面存在嚴重缺陷,最后只能用某一器官功能變化來表達“述求”,從而導致了心理問題軀體化。克萊曼通過對臺灣地區的研究發現,中國人受傳統文化的影響,習慣于壓制內心的苦痛情感。他認為,在中國人的概念里,相比較于心理問題,身體問題才是被普遍接受的。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的傳統文化觀念決定了中國人群中軀體癥狀“心”的成分可能更多。
個體的認知系統也和軀體癥狀的產生有關。這類病人的認知特點主要表現為異常的、放大的知覺模式,對健康和身體功能的強迫性推論,以及傾向于將身體知覺誤解為嚴重生理疾病的信號等[7]。當身體出現模糊的不適信號時,這種不適感覺和不合理的認知歪曲形成心身交互作用,病理焦慮、生理喚醒與軀體癥狀的惡化形成一個惡性循環,導致軀體癥狀發生并持續地發展。
軀體癥狀和社會文化因素有關。很多軀體癥狀的持續存在是有其社會特性的,個體通過癥狀的存在免除某種責任和義務,尋求別人注意和同情,避免被指責和批評等。值得關注的是,個體并非有意偽裝(不同于裝病),但卻在無意識中持續保持并達到“繼發性獲益”。這個時候軀體癥狀成為病人對付心理、社會各方面困難處境及滿足自身需要的一種應對方式。
3 “心”和“身”的融合
任何一位病人哪怕確實存在有某種軀體疾病,他的軀體癥狀都應該包含了“心”和“身”的成分,只不過這兩種成分占的比重不同而已。近年來,人們越來越意識到,沒有一種疾病的軀體癥狀是單純“身”的成分、也不會是單純“心”的成分。對于心身疾病的研究發現,心身疾病是心理因素和生物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是目前的越來越多的研究也提示了即使不是心身疾病的軀體疾病,心理社會因素也會對其臨床癥狀表現有影響,并最終影響疾病的預后。在精神科自1980年沿用至今的“軀體形式障礙”這一診斷強調了“醫學無法解釋癥狀”作為核心的排除條件,似乎存在一種單純軀體癥狀“心”成分的疾病存在,但在精神障礙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中,取消了“軀體形式障礙”這一診斷分類,代之以“軀體癥狀障礙”。這一診斷刪去“醫學無法解釋的癥狀”作為軀體形式障礙中一條核心的條件,認為軀體癥狀障礙的診斷需要對病人心理和行為的評估與其醫學狀況進行共同判斷[8]。新診斷標準認為軀體癥狀障礙和醫學狀況并不矛盾,它也可能出現在患有心臟病、癌癥等醫學疾病的人身上,就像抑郁癥會出現在很多嚴重疾病病人身上一樣。也就是說即使是軀體癥狀障礙,病人的軀體癥狀“心”的成分和“身”的成分是完全可以共存的。
綜上所述,從心身醫學的角度理解病人的軀體癥狀就需要應用“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全面理解病人,我們不但要懂得軀體癥狀“身”的成分,同時更應該知道軀體癥狀“心”的存在,知“心”懂“身”可以使臨床醫生打破原有診療模式中的僵化思路,從而更好地認識和診療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