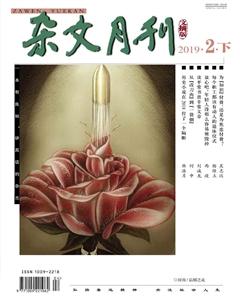緣何抽薪不止沸?
朱林興
教育部多次重申,在職教師不得兼職課外補課機構,違者嚴懲乃至開除公職,并寫進了中央關于規范課外培訓機構發展的意見。不少人都拍手稱道,認為是“釜底抽薪”之舉,是解決課外補課市場干擾業務教育秩序,減輕學生負擔過重的治本之道。
這幾年課外補課市場紅紅火火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所謂的“學霸老師”,而在職老師是構成這支“學霸老師”隊伍的主體。從這個意義上說,禁止在職老師兼職補課機構,確實是釜底抽薪,沒有了在職教師兼職,補課機構就成了無本之木,難以正常運轉,二十多年來形成的這一社會頑疾便可根治。
前些天,教育司長還在重申這一禁令。據說,這幾個月來課外補課機構被撤消了不少。但據我觀察,課外補課市場熱度依然不減。在我所在居住區的三公里范圍內,原來補課機構都還在,最近又增加了不少新的,我家門口的兩家小超市已“城頭變換大王旗”,改換了門庭,加盟于補課市場,就是明證。
這就奇怪了。既然在職教師不得兼職于補課機構而補課市場依然紅火,那么,就產生了一個問題:補課市場的師資是怎么解決的呢?筆者疑竇叢生。根據筆者的調查,逐漸得知其中奧秘。有一家設于某商場的補課機構,開辦十多年來,專職教師始終只有2人(合伙開辦人)。禁令下達后,專職教師沒有增加,生意則依然紅火。我問它的一個推銷員,上課的教師來自何方。他初避而不談,后來經過我旁敲側擊,多次和他試探性的交談,才找到了答案:在禁令頒布前,他們就地聘用所在區、鎮學校的在職教師。之后,他們就主要聘用外區學校的在職教師,這樣,學生及家長不知老師底細,補課機構和教師都相安無事。所以,就本質而言,釜底并未抽薪,僅是由“外來薪”取代了“當地薪”而已,結果自然是抽薪不止沸。目前這一方式已具普遍性。
在我看來,課外補課熱是個社會頑癥,它的存在和發展抹殺了基礎教育的基本屬性,異化教育目的,侵蝕教育秩序,加劇社會浮躁,乃至催化基礎教育產業化。砸碎課外補課機構這“釜”是解決問題的最省事之法。當然,嚴禁在職教師兼職補課機構,也不失為釜底抽薪之法。那么,問題出在哪里呢?
這使我想起了去年起由政府主導的城市拆違工作。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起,本市為滿足外來人口居住、經商以及部分居民住房緊張等需要,違章搭建遍地開花于城內,城郊結合部更甚。今天,違章建筑的存在嚴重有礙城市觀瞻、用地率和控制城市規模,必須拆除。然而,迎神易,送神難。拆違成了令人頭疼的棘手問題,這是因為它存在時間長,且有些還是經有司批準的,涉及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然而,自去年年初至今拆違工作僅短短一年多時間,就取得基本性勝利,拆違2400多萬平方米。總結其成功經驗,可用“到位”兩字概括,即領導重視到位,黨政一把手負全責;目標明確,立軍令狀,分工清晰,任務落實到位;對可能出現的阻力、困難和風險事先計劃周全,應對預案完備等。此事給人之啟迪是,世上很少有不能解決的難題,關鍵是看你真心想、半心想或無心想解決問題。
與此一對照,就不難發現整治課外補課機構之所以釜底抽薪難止沸,關鍵就在于缺乏拆違工作所體現的那種“到位”精神。
如何整治課外補課機構,中央文件有明文規定,但是如何落地則少見具體措施。以嚴禁在職教師兼職于補課機構為例,事先如何以預防為主,加強對在職教師的教育,事中如何加強監督檢查、地區間如何形成合力構建監督網,事后如何嚴肅查處違規行為等環節上,缺乏周密的制度安排和具體辦法。似乎禁令一定,有司數次重申,就能威懾八方,補課機構臣服,誰也不敢逆流而上,從此,天下太平。這無異于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