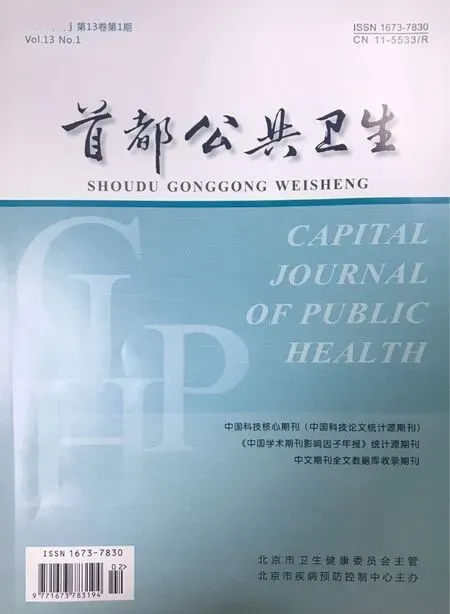互聯網+艾滋病防治技術應用與挑戰
吳尊友
互聯網,包括網頁和社交軟件,已經深入到人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國,每60 s,就會在互聯網上產生約265萬張火車票訂單,出現347 萬次百度搜索,9.5萬條微博發送,7.3萬筆支付寶交易[1]。全球用戶量最多的前十名社交軟件,每月活躍用戶均超過3億人,其中臉書 (Facebook) 每月活躍用戶達到16億。全球前十名社交軟件中有三個隸屬中國,其中QQ 每月用戶8.5億人 (用戶數排名第三),微信6.8億人(用戶數排名第四),百度貼吧3億人(用戶數并列排名第十)[1]。互聯網技術的發展和廣泛應用,深刻地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包括交友方式,以及伴隨交友引發的性行為方式。社交軟件不僅為人們購買日常生活用品提供了交易平臺,同時,也為性交易、毒品交易等提供了交流平臺。因此,社交軟件也必將成為艾滋病防治新的重要平臺。
1 互聯網及社交軟件
目前,社會上各種社交軟件多如牛毛,在百度搜索頁面,輸入“安卓交友App”,則顯示 3 431個不同種類的交友軟件,包括QQ、微信、陌陌等。敲入“同志App”,則顯示有84個男同交友軟件,包括 Jack ‘d App (接客帝)、BoyAhoy、Blued 等。各種社交軟件是為了滿足不同用戶的需求而設計,并在應用中不斷改進、完善。注冊社交軟件新用戶,一般都需要手機號碼或電子郵箱認證。通常,一個手機號或郵箱地址,只能在同一個社交軟件上注冊一次,但可以在多個不同的社交軟件上注冊。同一個社交軟件平臺上的不同用戶之間交流,有些社交軟件,首次交流的雙方需要事先確認并獲得對方認可后才能交流,比如QQ、微信。有些社交軟件則不需要其他用戶確認,比如微博、陌陌等。
用戶根據使用目的選擇一個或多個社交軟件。目前,微信的功能相對比較全面,除了與人聯系外,還可以用來支付多種購買活動,如支付出租車費、訂購火車票、飛機票等。我國最新的一項研究顯示,52%的學生同性戀使用男同專用交友軟件,使用目的包括:73.6%是為了交友、55.3%尋找伙伴、23%是找性伴[1]。尋找性伴應用最廣泛的社交軟件可能要算陌陌,用戶在陌陌社交平臺上認識附近的“陌生人”,達成意向后,雙方采用第二種聯系方式,如交換手機號碼或微信號碼,再進一步協商。不可否認,新社交軟件的出現,為那些有特殊性需求的人,提供了新的聯系平臺。
2 艾滋病流行特征與互聯網用戶
目前,全球有3 690萬艾滋病感染者,70%發生在非洲次撒哈拉地區,92%的感染者是經性途徑傳播,每天大約有4 500人感染艾滋病,約37%的感染者年齡在15~24歲之間[2]。2017年,我國報告艾滋病感染者13.5萬人,其中95%是經性途徑傳播。從感染者年齡分布來看,占比最高的是25~29歲青年,其次是20~24歲組和30~34歲組,即性最活躍年齡組感染人數最多[3]。青年人既是互聯網和社交軟件的主要使用者,同樣是艾滋病流行的主要受害者。因此,互聯網及社交軟件,可以作為載體平臺,為艾滋病預防和治療提供重要支持。
3 互聯網+艾滋病防治技術應用
互聯網及社交軟件可以用來傳播艾滋病預防信息,包括文字信息、視頻信息、圖片、聲音信息;也可以用其GPS定位功能,標識艾滋病檢測點和治療點的地理位置,供用戶使用;還可以用來作為求詢者與服務提供者之間的互動工具;可以用來預約診療服務,以及用于病人的隨訪管理服務等。
3.1開展流行病研究 Ren 等[4]利用男同社交軟件,開展用戶既往自我檢測后求醫行為情況調查,調查篩選了2.2萬用戶,對其中2 383位曾經做過艾滋病自我檢測的調查對象,進一步了解自我檢測結果及求醫行為。研究發現,只有15.9%的人在自我檢測后有求醫行為,而且,有求醫行為的主要是自我檢測陰性者,而那些自我檢測呈現陽性反應或不明確者反而沒有求醫行為。為了解高危人群流動情況,Mi 等[5]用互聯網登錄信息,比較用戶注冊地與最常見登錄地差異,分析79萬男同用戶的流動情況,發現其中約1/3處于長期流動狀態,廣東、上海、北京、天津和浙江的流動比例高,西南的男同主要向東部沿海流動。
3.2促進艾滋病檢測 Young 等[6]利用臉書進行隨機化干預實驗研究,將研究對象分為16組,采用隨機化分組方式,8組分配到臉書同伴干預組,并同時每天傳送艾滋病檢測信息,8組分配到對照組,無同伴引導,只參加在線健康社區活動。兩組均隨訪12周,觀察參與艾滋病檢測情況。研究表明,干預組12周后檢測比例為17%,而對照組的檢測比例為7% (aOR=2.61, 95%CI: 1.55-4.38)。Ybarra 等[7]以14~18歲青少年同性戀或雙性戀為研究對象,五周時間,每周發5~10條短信,第6周加強一次信息,隨訪3個月,看檢測情況。結果發現,干預組艾滋病檢測比例(55%)顯著高于對照組(28%, aOR=3.42,P=0.001)。
3.3改變危險性行為干預 Ybarra 等[7]的上述研究還同時觀察了短信息干預對性行為的研究。研究發現,干預組無安全套危險行為顯著下降(RR=0.39,P=0.04)。Mimiaga 等[8]以男性性工作者為研究對象,觀察手機傳送的減少危險咨詢以及個性化的文字信息或語音信息,在基線、隨訪3個月、6個月三個時點觀察危險性行為的情況。研究發現,無安全套的危險性行為比例,干預組和對照組都是7.7%,在隨訪3個月時分別是1.4%和4.9%(P=0.0003),在隨訪6個月時分別是0.2%和2.8%(P<0.0001),干預組顯著好于對照組。
3.4促進治療 感染者在診斷發現后,往往還沒有來得及接受治療,就脫失了。為了減少脫失,Mehta等[9]用每周一次短信提醒、連續4周的干預活動,觀察干預組與常規工作對照組診斷后脫失情況。研究發現,干預組診斷后的脫失比例比常規工作組減少了80%(aRR=0.2, 95%CI: 0.1-0.5)。抗病毒治療的依從性是影響治療效果的重要因素。Lester 等[10]用隨機化分組方式,對參加抗病毒治療的病人進行短信息干預,與常規治療組作為對照比較,發現短信息干預組不依從比例減少19% (RR=0.81, 95%CI: 0.69-0.94;P=0.006),病毒失敗率減少16% (RR=0.84, 95%CI: 0.71-0.99;P=0.04)。
另一項對全球85個臨床實驗研究進行薈萃分析,包括1.6萬名研究對象,發現短信息干預與常規對照組比較,無論是全球(OR=1.48, 95%CI:1.00-2.16)還是中低收入國家(OR=1.49, 95%CI:1.04-2.09),治療依從性均提高約50%[11]。
4 挑戰
4.1對互聯網與艾滋病流行關系的認識 有些人質疑互聯網及社交軟件廣泛應用為用戶之間的聯系提供了方便的同時,促進了性交易和艾滋病經性途徑傳播。實際上,我國艾滋病的流行發生于社交軟件出現和發展之前。我國艾滋病經性途徑傳播上升,在2006年就已經出現,并出現逐年緩慢上升。而社交軟件的出現和應用,僅僅才幾年時間。非洲國家社交軟件并不普遍,卻出現了世界上最為嚴重的艾滋病流行。再看看社交軟件最發達的美國,其艾滋病感染率近十年穩中有降,也沒有出現伴隨互聯網及社交軟件的廣泛應用而增加。
我國正處在一個快速發展的時代,在過去10年超過很多發達國家,一躍成為全球經濟總量第二的國家。我們不會因此質疑經濟發展造成了艾滋病快速上升。在過去的10年里,我國的小汽車產量和銷售量逐年增加,我們也不會因此質疑轎車的快速發展,促進了我國艾滋病傳播。互聯網及社交軟件是時代發展的產物,我們應該積極抓住機會,利用好這一寶貴平臺,開展更加積極的艾滋病防治活動。
4.2互聯網覆蓋面廣,短時間可接觸大量用戶,但效果難以保證 互聯網及社交軟件具有跨越時間和地域的優勢,可以在短時間內完成大量用戶的調查或信息發送。但由于這類活動都是人-機互動,研究人員無法控制,一方面,調查之類的活動應答率非常低,另一方面也無法研判其真實性。同時,調查或預防干預內容,宜短不宜長。
4.3互聯網及交友軟件用于艾滋病防治亟待加強 當前全國疾病控制機構、醫療衛生機構艾滋病防治人員對互聯網及社交軟件用于艾滋病防治的迫切性、重要性還認識不足,對于艾滋病防治的多個重點目標人群使用的常見社交軟件不了解、不熟悉。有必要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一支熟練運用互聯網及社交軟件用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專業隊伍,沒有一支強大的掌握現代網絡新技術的專業人員隊伍,將無法打贏控制艾滋病流行這場戰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