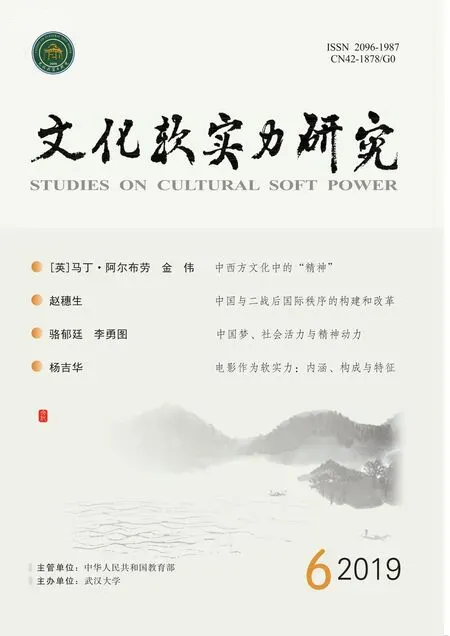奢侈品視角下“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生成與市場(chǎng)化運(yùn)作研究
俞鈺凡 尹可昕 彭桂芳
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作為中華民族最為獨(dú)特、最為豐富的財(cái)富,面臨傳承后繼無(wú)人、傳統(tǒng)手工技藝費(fèi)時(shí)費(fèi)力效率低、經(jīng)濟(jì)效益低等困境。如何進(jìn)一步推動(dòng)非遺的傳承和發(fā)展是國(guó)家和民族所關(guān)心的重要問(wèn)題。相比之下,與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類文化產(chǎn)品(以下簡(jiǎn)稱“非遺”類藝術(shù)品)具有相同特征的奢侈品卻能不斷地?zé)òl(fā)活力,發(fā)揚(yáng)傳統(tǒng)技藝的同時(shí)帶動(dòng)整個(gè)產(chǎn)業(yè)的發(fā)展,其中有值得“非遺”類藝術(shù)品借鑒的地方。
關(guān)于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研究從2011年開(kāi)始逐年增加,研究主要集中在相關(guān)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介紹,具體某一類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保護(hù)、設(shè)計(jì),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產(chǎn)業(yè)化以及傳播策略等(1)許磊、張蓉:《云錦、宋錦非遺文化保護(hù)傳承現(xiàn)狀及途徑研究》,《山東紡織經(jīng)濟(jì)》2018年第1期。。也有實(shí)證研究傳統(tǒng)工藝美術(shù)類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利用模式(2)劉鑫:《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經(jīng)濟(jì)價(jià)值及其合理利用模式》,《學(xué)習(xí)與實(shí)踐》2017年第1期。。然而,奢侈品視角下研究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研究還不多見(jiàn),其中肖瑋指出中國(guó)奢侈品牌的推廣需要解構(gòu)、創(chuàng)新、組合物質(zhì)性的消費(fèi)品與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概念,有機(jī)融合商業(yè)元素與文化元素,通過(guò)規(guī)模化運(yùn)作提升行業(yè)競(jìng)爭(zhēng)力,實(shí)現(xiàn)文化傳承下的產(chǎn)業(yè)復(fù)興。(3)肖瑋:《消費(fèi)時(shí)代的奢侈品和中國(guó)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關(guān)系論》,《學(xué)術(shù)界》2010年第7期。
以往的研究雖然頻繁提到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市場(chǎng)化,然而目前的問(wèn)題是如何進(jìn)行市場(chǎng)化運(yùn)作。有一些奢侈品品牌(譬如GUCCI)逐漸將中國(guó)文化元素納入其中,然而出發(fā)點(diǎn)是奢侈品品牌的運(yùn)營(yíng)。奢侈品與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相關(guān)的學(xué)術(shù)研究也主要是圍繞奢侈品進(jìn)行的。因此,本研究擬從奢侈品的視角,提出“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構(gòu)念,并深入分析其內(nèi)涵和類型,“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特征與生成機(jī)制;進(jìn)而剖析“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市場(chǎng)化過(guò)程中遇到的困境;最終給出運(yùn)作的策略研究。
一、“非遺”類藝術(shù)品構(gòu)念的內(nèi)涵及類型
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法》,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傳并視為其文化遺產(chǎn)組成部分的各種傳統(tǒng)文化表現(xiàn)形式,以及與傳統(tǒng)文化表現(xiàn)形式相關(guān)的實(shí)物和場(chǎng)所,包括:傳統(tǒng)口頭文學(xué)以及作為其載體的語(yǔ)言;傳統(tǒng)美術(shù)、(梅花篆字)書(shū)法、音樂(lè)、舞蹈、戲劇、曲藝和雜技;傳統(tǒng)技藝、醫(yī)藥和歷法;傳統(tǒng)禮儀、節(jié)慶等民俗等;傳統(tǒng)體育和游藝以及其他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高凌、張夢(mèng)霞在《消費(fèi)者非遺產(chǎn)品購(gòu)買意愿影響因素及作用機(jī)制》一文中將非遺產(chǎn)品界定如下:非遺產(chǎn)品是指以造型和技藝為手段,運(yùn)用非遺傳統(tǒng)技術(shù)制造的適合當(dāng)代生活方式的產(chǎn)品(4)高凌、張夢(mèng)霞:《消費(fèi)者非遺產(chǎn)品購(gòu)買意愿影響因素及作用機(jī)制》,《經(jīng)濟(jì)與管理研究》2018年第1期。。從語(yǔ)文修辭的角度來(lái)看,這個(gè)定義不夠嚴(yán)謹(jǐn)。“非遺”是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簡(jiǎn)稱,那么“非遺產(chǎn)品”就是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產(chǎn)品的簡(jiǎn)稱,這種表達(dá)方式顯然是不合規(guī)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指各種以非物質(zhì)形態(tài)存在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guān)、世代相承的傳統(tǒng)文化表現(xiàn)形式。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是以人為本的活態(tài)文化遺產(chǎn),它強(qiáng)調(diào)的是以人為核心的技藝、經(jīng)驗(yàn)、精神,其特點(diǎn)是活態(tài)流變。在對(duì)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活態(tài)化傳承式的開(kāi)發(fā)過(guò)程中,利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在文化藝術(shù)上的獨(dú)特優(yōu)勢(shì),生產(chǎn)出特色的文化藝術(shù)品,使傳統(tǒng)文化內(nèi)涵能夠以獨(dú)特的產(chǎn)品形式呈現(xiàn)出來(lái)。對(duì)于這類承載非遺藝術(shù)的獨(dú)特的產(chǎn)品形式,本研究給予“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稱呼。但是必須明確的一點(diǎn)是,并非所有的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都能以產(chǎn)品為載體進(jìn)行市場(chǎng)化。因此,本研究提出的“非遺”類藝術(shù)品指的是利用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在文化藝術(shù)上的特色,運(yùn)用非遺元素(主要是形象與技藝)制造的,反映傳統(tǒng)文化內(nèi)涵的適合當(dāng)代生活方式的藝術(shù)品。“非遺”類藝術(shù)品包括非遺原創(chuàng)藝術(shù)品、非遺衍生品、非遺授權(quán)產(chǎn)品、非遺復(fù)制品和非遺私人訂制品。實(shí)際上,這一定義規(guī)定了其“奢侈”的屬性來(lái)源,即其中飽含的“非遺藝術(shù)”和“工匠精神”。
“奢侈”來(lái)源于拉丁語(yǔ)“Luxury”,原意是指“極強(qiáng)的繁殖力、感染力、傳播力和延展力”。傳統(tǒng)的觀點(diǎn)站在二元論上認(rèn)為,奢侈和必需是對(duì)立的。如《劍橋辭典》將奢侈定義為“由貴重和美麗的擁有物、環(huán)境或美食,或其他令人愉悅、昂貴但沒(méi)必要的東西,所帶來(lái)的巨大舒適感與超感官的享受”。而奢侈品主要指人們生存與發(fā)展需要范圍以外的,具有獨(dú)特性、珍奇性及稀缺性的消費(fèi)品。(5)高興佑、向長(zhǎng)福:《從凡勃倫效應(yīng)談奢侈品的營(yíng)銷策略》,《商業(yè)時(shí)代》2010年第11期。Nueno和Quelch把奢侈品品牌定義為“功能比價(jià)格的比率低,而無(wú)形的和情境化效用比價(jià)格的比率卻高的品牌”。(6)Nueno,J. L.,Quelch,J. A.:The Mass Marketing of Luxury,Business Horizons,1998,41(6):61-68.但是,現(xiàn)有奢侈品和奢侈品品牌研究跳出了從非必需品的角度對(duì)它們進(jìn)行定義,認(rèn)為站在消費(fèi)者的立場(chǎng)上,奢侈品和奢侈品品牌滿足的是消費(fèi)者的生理和心理需要。(7)Vigneron,F(xiàn).,Johnson,L. W.:Measuring Perceptions of Brand Luxury,Journal of Brand Management,2004,11(6):484-506.(8)Hudders,L.,Pandelaere,M.,Vyncke,P.:Consumer Meaning Mak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ket Research,2013,55(3):391-412.彭傳新認(rèn)為,奢侈品只是代表了人性發(fā)展的需要。(9)彭傳新:《奢侈品品牌文化研究》,《中國(guó)軟科學(xué)》2010年第2期。從符號(hào)學(xué)意義上,奢侈品除了任何功能效用外,主要通過(guò)使用產(chǎn)品或顯示一個(gè)特定的品牌給產(chǎn)品擁有者帶來(lái)尊重感。(10)Kapferer,J. N.:Why are We Seduced by Luxury Brands? Journal of Brand Management,1998,6(1):44-49.奢侈品是“消費(fèi)得起的享受和質(zhì)優(yōu)價(jià)高的主流商品”,其“有形”的功能性價(jià)值遠(yuǎn)遠(yuǎn)低于自身價(jià)格,強(qiáng)調(diào)的是很高的“無(wú)形”內(nèi)在價(jià)值(11)Nueno,J. L.,Quelch,J. A.:The Mass Marketing of Luxury,Business Horizons,1998,41(6):61-68.。克里斯托弗·貝里在《奢侈的概念:概念及歷史的探究》一書(shū)中指出:奢侈品不僅是精美和品質(zhì)的代名詞,也是享樂(lè)的象征,使人產(chǎn)生愉悅感,但具有可替代性。(12)克里斯托弗·貝里著,江紅譯:《奢侈的概念:概念及歷史的探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周云在《奢侈品品牌管理》中提出,“奢侈品是指消費(fèi)者對(duì)某件特定商品預(yù)期會(huì)給自己帶來(lái)的體驗(yàn)價(jià)值遠(yuǎn)遠(yuǎn)高于該商品具有的使用價(jià)值的一類特殊商品”。(13)周云:《奢侈品品牌管理》,對(duì)外經(jīng)貿(mào)大學(xué)出版社2010年版。從藝術(shù)學(xué)角度來(lái)說(shuō),雷白慕認(rèn)為奢侈品將虛無(wú)縹緲的美學(xué)現(xiàn)象變成了實(shí)物,提出了“奢侈品是藝術(shù)與商業(yè)結(jié)合的產(chǎn)物”的觀點(diǎn)。(14)雷白慕:《淺談藝術(shù)品與奢侈品》,魯迅美術(shù)學(xué)院碩士學(xué)位論文,2015年。總的來(lái)說(shuō),奢侈品是一種高溢價(jià)且優(yōu)質(zhì),具有獨(dú)特性和稀缺性的商品。
根據(jù)以上有關(guān)“奢侈”與奢侈品牌的概念分析中,我們其實(shí)不難得出,奢侈與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之間的強(qiáng)關(guān)聯(lián)。“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對(duì)應(yīng)“奢侈”的觀點(diǎn),非遺是一種獨(dú)特的藝術(shù),根植于大眾的生活之中,匯聚了集體的智慧,具有極強(qiáng)的繁殖力、感染力、傳播力和延展力。然而,對(duì)于當(dāng)代生活而言,“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和必需是對(duì)立的。同時(shí),“非遺”的傳承與保護(hù)對(duì)其“原真性”要求甚高,市場(chǎng)在將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與市場(chǎng)對(duì)接的時(shí)候,有消解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原真性的負(fù)面作用。因此,“非遺”類文化產(chǎn)品的開(kāi)發(fā)需要在非遺的原真性與市場(chǎng)之間取得平衡,“非遺”類藝術(shù)品是非遺藝術(shù)與商業(yè)結(jié)合的具有獨(dú)特性和稀缺性的奢侈商品。
美術(shù)界一直有一個(gè)似是而非的觀點(diǎn),即把原創(chuàng)性看作構(gòu)成藝術(shù)品的唯一要素,而將仿作或復(fù)制品看作“準(zhǔn)藝術(shù)品”。但是,“非遺”類藝術(shù)品在生產(chǎn)性保護(hù)與傳承過(guò)程中,是不是只有非遺傳承人制作的才能稱為“原創(chuàng)”呢?顯然,這一觀點(diǎn)是有悖于市場(chǎng)認(rèn)知的。既然,“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奢侈屬性來(lái)源規(guī)定為“非遺藝術(shù)”與“工匠精神”,又強(qiáng)調(diào)其與當(dāng)代生活的適應(yīng)性。那么,據(jù)此結(jié)合起來(lái)對(duì)“非遺”類藝術(shù)品進(jìn)行類別劃分如下:一類代表中國(guó)工藝美術(shù)和傳統(tǒng)手工藝類的器具類“非遺”藝術(shù)品,譬如宜興紫砂壺、景德鎮(zhèn)手工瓷、徽墨等;另一類擁有特殊民族文化和極盡優(yōu)雅的手工技能的穿戴類“非遺”藝術(shù)品,譬如苗繡絲巾、緙絲制品等。不管是哪一類的藝術(shù)品,都是孜孜不倦地追求藝術(shù)上的美,用細(xì)節(jié)成就完美的典范。
二、“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特征及其產(chǎn)品品牌的生成機(jī)制
前面已經(jīng)對(duì)“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內(nèi)涵和類型進(jìn)行了清晰的界定,本研究接下來(lái)所提到的“非遺”類藝術(shù)品就特指器具類和穿戴類的藝術(shù)產(chǎn)品。
(一)“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特征
“非遺”類藝術(shù)品完美地繼承了奢侈品的一般特性,在以下幾個(gè)方面的表現(xiàn)則尤為突出:
1.悠久的歷史以及文化內(nèi)涵
奢侈品具有的特征可以歸納為:極佳的品質(zhì)、昂貴的價(jià)格、稀缺性、美學(xué)價(jià)值和傳承歷史。(15)Dubois,B.,Laurent,G.,Czellar,S.:Consumer Rapport to Luxury:Analyzing Complex and Ambivalent Attitudes,Jouy-en-Josas:Groupe HEC,2001.奢侈品只有經(jīng)過(guò)時(shí)間的沉淀和文化的滋潤(rùn)才能成為經(jīng)典的代表。戴世富通過(guò)對(duì)奢侈品的研究發(fā)現(xiàn),奢侈品依靠它特有的文化歷史和技藝的傳承區(qū)別于普通商品。(16)戴世富:《奢侈品牌是怎樣煉成的?》,《管理與財(cái)富》2005年第7期。奢侈品大多有悠久的歷史且包含傳奇色彩的品牌故事,這種蘊(yùn)含在奢侈品中的歷史文化是奢侈品的核心所在。因此,文化成了區(qū)分大眾商品與奢侈品的關(guān)鍵。對(duì)于奢侈品來(lái)說(shuō),不同的奢侈品品牌具有不同的設(shè)計(jì)風(fēng)格和發(fā)展歷史,它的起源深受起源地文化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說(shuō),奢侈品是時(shí)代和地域文化的產(chǎn)物。伴隨著文藝復(fù)興運(yùn)動(dòng)和工業(yè)革命,歐洲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得到了快速的發(fā)展,一些資產(chǎn)階級(jí)新貴想要躋身上流社會(huì),需要通過(guò)消費(fèi)奢侈品來(lái)提升自身的地位和形象,所以歐洲成為了奢侈品和奢侈文化的搖籃。
Hermans和Kempen曾指出文化產(chǎn)品來(lái)源于某種特定文化的潛在價(jià)值和信仰的表達(dá)。(17)Hermans,H. J. M.,Kempen,H. J. G.:Moving Cultures:The Perilous Problems of Cultural Dichotomies in a Globalizing Society,American Psychologist,1998,53(53):1111-1120.文化產(chǎn)品制作過(guò)程中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內(nèi)容和價(jià)值觀念。從經(jīng)濟(jì)學(xué)角度分析,文化產(chǎn)品中包含的文化和藝術(shù)價(jià)值使其價(jià)格超越其邊際成本。(18)張夢(mèng)霞:《奢侈品消費(fèi)動(dòng)機(jī)解構(gòu)的實(shí)證研究》,《中國(guó)零售研究》2010年第1期。從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的角度分析,文化產(chǎn)品的核心競(jìng)爭(zhēng)就是內(nèi)容競(jìng)爭(zhēng)。(19)雷興長(zhǎng):《中國(guó)文化產(chǎn)品走向世界的內(nèi)容競(jìng)爭(zhēng)戰(zhàn)略研究》,《科學(xué)經(jīng)濟(jì)社會(huì)》2012年第3期。文化產(chǎn)品作為文化和精神的載體,蘊(yùn)含著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非遺是各民族世代相承的傳統(tǒng)文化的表現(xiàn)形式,它承載著歷史的記憶,是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chǎn)物,具有鮮明的時(shí)代特征。通過(guò)“非遺”類藝術(shù)品可以了解過(guò)去的社會(huì)發(fā)展水平,人們的生活方式等,所以“非遺”類藝術(shù)品具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內(nèi)涵。譬如,中國(guó)傳統(tǒng)的絲制工藝品——錦,不同時(shí)代有不同的代表,如宋錦、云錦等。宋錦始于宋代末年,根據(jù)產(chǎn)品的不同可用于不同地方,如重錦只用于宮殿的陳設(shè),細(xì)錦因?yàn)楹癖∵m中被廣泛用于服飾的設(shè)計(jì),而云錦從元代開(kāi)始一直是皇家服飾專供。由此可見(jiàn),同奢侈品一樣,“非遺”類藝術(shù)品具有悠久的歷史和豐富的文化內(nèi)涵。
2.象征意義重大
象征性是指消費(fèi)者購(gòu)買的產(chǎn)品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了消費(fèi)者的品位和地位。奢侈品是奢侈的具體化表現(xiàn)和實(shí)物化。從社會(huì)學(xué)層面出發(fā),奢侈品展現(xiàn)了擁有者的社會(huì)地位,表達(dá)了個(gè)人的品位,是高端品質(zhì)生活的表現(xiàn)。Vickers和Renand曾從實(shí)用主義、經(jīng)驗(yàn)主義和象征三個(gè)維度分析奢侈品,并提出奢侈品的根本就是它是使用者身份和地位的象征。(20)Vickers,J. S.,Renand,F(xiàn).:The Marketing of Luxury Goods:An Exploratory Study—Three Conceptual Dimensions,Marketing Review,2003,3(4):459-478.奢侈品本身代表的就是美好的事物,是功能產(chǎn)品之上的藝術(shù)品,它既是純粹的物品,也是高品位的象征。O’cass和McEwen在研究中發(fā)現(xiàn)消費(fèi)者購(gòu)買的奢侈品往往會(huì)與他們的社會(huì)地位相匹配,借此展示個(gè)人榮譽(yù)和社會(huì)威望。(21)O’cass,A.,McEwen,H.:Exploring Consumer Status and Conspicuous Consumption,Journal of Consumer Behaviour:An International Research Review,2004,4(1):25-39.Danziger通過(guò)分析購(gòu)買奢侈品的消費(fèi)意愿將消費(fèi)者分為隔絕型消費(fèi)者、蝴蝶型消費(fèi)者、奢侈品喜好者與名位追求型消費(fèi)者等四種類型,其中追求名利型就是將奢侈品作為展現(xiàn)自身地位和威望的工具。(22)Danziger,P.:Let Them Eat Cake:Marketing Luxury to the Masses—as well as the Classes,Dearborn Trade Publishing,2004.可以說(shuō),奢侈品消費(fèi)的重要?jiǎng)訖C(jī)之一就是為了通過(guò)奢侈品消費(fèi)獲得相應(yīng)的社會(huì)地位和群體榮譽(yù)。(23)盧長(zhǎng)寶、秦琪霞、林穎瑩:《奢侈品消費(fèi)特性構(gòu)成維度的理論模型》,《管理評(píng)論》2013年第5期。
在文化產(chǎn)品的研究中,國(guó)內(nèi)學(xué)者趙淼認(rèn)為文化產(chǎn)品能夠幫助消費(fèi)者建立集體認(rèn)同感,消費(fèi)者購(gòu)買文化產(chǎn)品的一個(gè)重要原因是文化產(chǎn)品所代表的符號(hào)能強(qiáng)化他們自身的形象和社會(huì)地位。(24)趙淼:《淺談提升我國(guó)文化產(chǎn)品競(jìng)爭(zhēng)力》,《黑龍江對(duì)外經(jīng)貿(mào)》2008年第7期。文化產(chǎn)品的特征可分為一般特征和特殊屬性,其中一般特征中就包含象征性(25)臧秀清、游濤:《文化產(chǎn)品:特征與屬性的再認(rèn)識(shí)》,《探索》2011年第5期。,消費(fèi)者在購(gòu)買文化產(chǎn)品時(shí),看重的并非文化產(chǎn)品的實(shí)物而是其符號(hào)意義,消費(fèi)者可以通過(guò)符號(hào)互動(dòng)對(duì)文化產(chǎn)品象征價(jià)值進(jìn)行重構(gòu)。何佳潔在研究文化產(chǎn)品的社會(huì)效益時(shí)發(fā)現(xiàn),文化產(chǎn)品能引導(dǎo)人的身份認(rèn)同,形成自我意識(shí)。(26)何佳潔:《淺談文化產(chǎn)品的社會(huì)效益》,《商》2015年第11期。所以,“非遺”類藝術(shù)品不但可以表達(dá)消費(fèi)者的品位和喜好,而且能幫助他們建立認(rèn)同感,強(qiáng)化自身形象。以南京絨花為例,它是以蠶絲染色成絨,用鋼絲勾條制成的傳統(tǒng)手工藝品。絨花始于唐朝,是中華富貴文化的代表,被唐代列為皇室貢品。因?yàn)橹C音“榮華”,符合中國(guó)祥瑞文化,得到了貴婦們的喜愛(ài)。
根據(jù)上述可以獲知,消費(fèi)者消費(fèi)“非遺”類藝術(shù)品時(sh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幫助消費(fèi)者展現(xiàn)其消費(fèi)品位、凸顯社會(huì)地位,而消費(fèi)者的偏愛(ài)也反過(guò)來(lái)促進(jìn)和宣傳了“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象征性價(jià)值。在消費(fèi)過(guò)程中,“非遺”類藝術(shù)品和奢侈品的實(shí)物價(jià)值被消耗,但它們的象征性價(jià)值在社會(huì)互動(dòng)中被完整保留,甚至不斷放大。
3.強(qiáng)調(diào)手工制作
在產(chǎn)品制造上,奢侈品使用高質(zhì)量的材料,用精致的工藝制成。這種技藝通常是獨(dú)一無(wú)二的,以傳統(tǒng)而獨(dú)特的工藝著稱。在機(jī)器化大生產(chǎn)時(shí)代,手工制品可以提升消費(fèi)者的感知能力,提升創(chuàng)造力。(27)肖瑋:《消費(fèi)時(shí)代的奢侈品和中國(guó)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關(guān)系論》,《學(xué)術(shù)界》2010年第7期。奢侈品在制作和銷售過(guò)程中都追求細(xì)節(jié)的完美,推崇一針一線的手工制作精神。以香奈兒為例,它陸續(xù)斬獲法國(guó)歷史上最悠久和最負(fù)盛名的八大手工坊,其中由Lesage刺繡坊制作的Coromandel連身裙花費(fèi)了刺繡工人2000個(gè)小時(shí)才完成。與機(jī)器批量生產(chǎn)相比,這些手工藝人們的情感投入和創(chuàng)作顯得更加可貴。
同樣,無(wú)論“器具類”還是“穿戴類”的“非遺”類藝術(shù)品,均是技藝擁有者純手工制作而成。如以緙絲織造技藝為例,它是中國(guó)傳統(tǒng)絲綢藝術(shù)品的精華。緙絲一般需要經(jīng)過(guò)16道工序,擁有結(jié)、摜、勾、繞、盤梭、戧等眾多技法。2010年世博會(huì)期間為各位元首定制的緙絲旗袍是將6根上等白蠶絲擰成一根作為材料,經(jīng)過(guò)落經(jīng)線、牽經(jīng)線等16道工序,使用了近百種面料顏色。每一件旗袍都是各具特色、獨(dú)一無(wú)二的精品。精心、細(xì)致、謹(jǐn)慎和精確的手工制作表達(dá)了對(duì)消費(fèi)者的尊重,傳達(dá)了“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態(tài)度。堅(jiān)持手工制作,使得時(shí)間成本非常高,做出來(lái)的作品價(jià)格自然就比較高,并且產(chǎn)量有限。因此,只有把具有傳統(tǒng)技藝的產(chǎn)品做成奢侈品才能提升市場(chǎng)價(jià)值。
4.非必需性
Dubois等提出的關(guān)于奢侈品的幾大主要特征中包含了非必需性。(28)Dubois,B.,Laurent,G.,Czellar,S.:Consumer Rapport to Luxury:Analyzing Complex and Ambivalent Attitudes,Jouy-en-Josas:Groupe HEC,2001.Vickers和Renand認(rèn)為,奢侈品具有高價(jià)格、高品質(zhì),但并不是生活所必需的產(chǎn)品和服務(wù)。(29)Vickers,J. S.,Renand,F(xiàn).:The Marketing of Luxury Goods:An Exploratory Study—Three Conceptual Dimensions,Marketing Review,2003,3(4):459-478.文化產(chǎn)品同樣也不屬于生活必需品之列,具有非必需性的特征(30)孫日瑤、宋憲華:《以樂(lè)為本:文化產(chǎn)品消費(fèi)屬性的規(guī)范研究》,《中國(guó)文化產(chǎn)業(yè)評(píng)論》2014年第1期。。社會(huì)的發(fā)展和人們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而“非遺”的傳承與保護(hù)困難重重,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在于“非遺”與現(xiàn)代生活方式是有距離的,對(duì)非遺文化的體驗(yàn)是非必需的。從經(jīng)濟(jì)學(xué)角度來(lái)看,奢侈品和文化產(chǎn)品的需求彈性都較大。《消費(fèi)經(jīng)濟(jì)學(xué)大辭典》認(rèn)為,奢侈品是需求彈性大于1的商品,即人們對(duì)該商品的需求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加。周志太認(rèn)為,人們對(duì)于文化產(chǎn)品需求取決于收入水平和個(gè)人品位。(31)周志太:《文化需求是文化產(chǎn)品重疊需求的本質(zhì)——以中日貿(mào)易的實(shí)證為例》,《現(xiàn)代經(jīng)濟(jì)探討》2011年第12期。也就是說(shuō),當(dāng)其他條件不變時(shí),收入的增加會(huì)帶來(lái)奢侈品和文化產(chǎn)品需求量的增加。但當(dāng)經(jīng)濟(jì)蕭條時(shí),人們通常會(huì)優(yōu)先選擇增加生活必需品的購(gòu)買量,而減少甚至取消奢侈品或文化產(chǎn)品的購(gòu)買。事實(shí)上,奢侈品行業(yè)和非遺文化項(xiàng)目可以說(shuō)比其他行業(yè)更易被消費(fèi)者的向下消費(fèi)影響。
(二)“非遺”類藝術(shù)品品牌的生成機(jī)制
通過(guò)和奢侈品進(jìn)行比較,可以清晰地得知,“非遺”類藝術(shù)品天然地具有和奢侈品一樣的基因。可以認(rèn)為,“非遺”類藝術(shù)品走奢侈品路線是其內(nèi)在基因和外在市場(chǎng)共同的決定。學(xué)術(shù)界一致認(rèn)為,“生產(chǎn)性”對(duì)于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傳承與保護(hù)具有重要的價(jià)值與意義。可見(jiàn),從“文化生產(chǎn)”的角度探討“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生成機(jī)制是可行的,具體見(jiàn)圖1。

圖1 “非遺”類藝術(shù)品品牌的生成機(jī)制
第一是產(chǎn)品化。長(zhǎng)期以來(lái),談到非遺文化產(chǎn)品都是強(qiáng)調(diào)它的藝術(shù)性,它的傳承,它的文化符號(hào)承載的一些文化價(jià)值。但對(duì)于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而言,利潤(rùn)才是大部分的動(dòng)力和初衷。產(chǎn)品化圍繞著把非物質(zhì)文化的表現(xiàn)形式轉(zhuǎn)變?yōu)楫a(chǎn)品展開(kāi)。不論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還是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最初的創(chuàng)作本身都是產(chǎn)生于當(dāng)時(shí)那個(gè)時(shí)代或者在那個(gè)朝代有實(shí)用性的,是滿足一些需求的。現(xiàn)在對(duì)其保護(hù)開(kāi)發(fā),繞不過(guò)去的就是局限性,所有非遺的東西基本上不是現(xiàn)代社會(huì)生活所需要的,有一些實(shí)現(xiàn)產(chǎn)品化很難,但不等于就不能產(chǎn)品化。
第二是商品化。把產(chǎn)品轉(zhuǎn)變?yōu)樯唐肥鞘裁匆馑迹繌淖罨镜膶哟蝸?lái)說(shuō),即生產(chǎn)物品不知為了使用,還為了交換。商品被購(gòu)買,意味著私有、排他的所有權(quán),而非集體使用。對(duì)于“非遺”類藝術(shù)品而言,更為關(guān)鍵的是“如何評(píng)價(jià)商品化”。文化商品化的發(fā)展進(jìn)程是漫長(zhǎng)而又不平坦的。雖然,商品化導(dǎo)致了物品的極大繁榮,但與此相關(guān)也產(chǎn)生了許多問(wèn)題。很多學(xué)者視商品化為矛盾的、破壞性的。文化商品化與文化產(chǎn)業(yè)化交織在一起。文化產(chǎn)業(yè)化強(qiáng)化和擴(kuò)展了文化商品化。從生產(chǎn)層面來(lái)說(shuō),文化商品化是高度復(fù)雜的,不同階段有不同的形式。譬如,印刷文本的商品化,由實(shí)物發(fā)展到有版權(quán)保護(hù)的作品。商品化的圖書(shū)發(fā)展極為豐沛,版權(quán)不但鞏固了文化商品的所有權(quán),也促進(jìn)了這種繁榮。從消費(fèi)層面來(lái)看,文化商品化滿足了消費(fèi)者日益提升的精神文明需求。
磷肥實(shí)現(xiàn)自給有余,使農(nóng)民用上了價(jià)格穩(wěn)定、物美價(jià)廉的國(guó)產(chǎn)肥。我國(guó)磷復(fù)肥工業(yè)憑借資源與地域優(yōu)勢(shì),迅速將產(chǎn)能和產(chǎn)品覆蓋到南亞、東南亞市場(chǎng),既有效緩解了企業(yè)連續(xù)生產(chǎn)、季節(jié)銷售的矛盾,又提升了行業(yè)的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力。
第三是恒定性、活態(tài)性。做文化產(chǎn)業(yè)不能回避這樣一個(gè)重要前提:創(chuàng)造需求才是最好的保護(hù)與傳承。這也是非遺開(kāi)發(fā)一直在探討的基本點(diǎn)。在市場(chǎng)方面,一味地迎合市場(chǎng)或者一味地創(chuàng)新會(huì)使“非遺”藝術(shù)品陷入孤立,不利于“非遺”藝術(shù)品的發(fā)展和傳承。讓消費(fèi)者了解“非遺”藝術(shù)品,了解產(chǎn)品背后的創(chuàng)作理念是首要的。因此,非遺文化的開(kāi)發(fā),就必須保持非遺產(chǎn)品傳承過(guò)程中的恒定性和活態(tài)性。恒定性是要把技藝一招一式、原汁原味地傳承下去,活態(tài)性則是在傳承的過(guò)程中學(xué)會(huì)創(chuàng)新,創(chuàng)作別開(kāi)生面的產(chǎn)品并保證其原真的“奢侈”品性。
第四是品牌化。當(dāng)“非遺”藝術(shù)品沒(méi)有品牌的情況下,它可能僅僅被視為商品,此時(shí)價(jià)格是消費(fèi)者考慮的因素。“非遺”類藝術(shù)品品牌化,不但代表了該商品所表達(dá)的象征意義,還能喚醒其背后蘊(yùn)含的文化的聯(lián)想和期望,從而制造一定程度的獨(dú)特偏好。“非遺”類藝術(shù)品自然地?fù)碛杏凭玫臍v史,獨(dú)特的品牌故事有助于消費(fèi)者視該品牌為典范,加深消費(fèi)者對(duì)品牌的好感。
三、“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市場(chǎng)化分析
“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市場(chǎng)化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創(chuàng)意及其傳承都與特定的場(chǎng)域不可分割。從社會(huì)意義上說(shuō),與特定的社會(huì)空間及其歷史時(shí)期密不可分。(32)孫日瑤、宋憲華:《以樂(lè)為本:文化產(chǎn)品消費(fèi)屬性的規(guī)范研究》,《中國(guó)文化產(chǎn)業(yè)評(píng)論》2014年第1期。然而,關(guān)于市場(chǎng)化行為或經(jīng)濟(jì)行為的效率理論則主要基于商品本身,沒(méi)有考慮特定的時(shí)間或空間配置。所以,對(duì)于“非遺”藝術(shù)品而言,市場(chǎng)是無(wú)法充分發(fā)揮其調(diào)節(jié)作用的。與此同時(shí),傳統(tǒng)的分析方法一直強(qiáng)調(diào),“非遺”藝術(shù)品的創(chuàng)作者是審美創(chuàng)新的主要來(lái)源,分析的時(shí)候主要側(cè)重于其心理過(guò)程。但是對(duì)原創(chuàng)性的過(guò)度強(qiáng)調(diào),排除了社會(huì)因素(大眾媒體興起,生活方式的改變等)和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對(duì)“非遺”藝術(shù)品的影響,“非遺”藝術(shù)品的創(chuàng)作過(guò)程并不會(huì)發(fā)生在真空中。因此,聚焦于創(chuàng)作者個(gè)人因素的分析必然要結(jié)合一系列的關(guān)聯(lián)要素,譬如創(chuàng)作、生產(chǎn)、銷售和消費(fèi)等。“非遺”藝術(shù)品在市場(chǎng)中的流通主要是為了傳播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技藝和正確的價(jià)值觀,市場(chǎng)流通也是“非遺”藝術(shù)品實(shí)現(xiàn)自身價(jià)值的重要渠道。因此,想要保護(hù)、傳承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有必要借鑒奢侈品的市場(chǎng)化策略。
(一)文化消費(fèi)的特性
文化消費(fèi)是消費(fèi)者為滿足自身的精神文化需求所購(gòu)買或消費(fèi)文化產(chǎn)品的過(guò)程。在這個(gè)過(guò)程中文化產(chǎn)品作為中介,承載和傳播消費(fèi)者所追求的精神需求。根據(jù)現(xiàn)階段的研究,學(xué)術(shù)界將文化消費(fèi)分為基本型、發(fā)展型和享受型三類,但無(wú)論是哪一類的文化消費(fèi)都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黏性”特征。在日常生活中,物質(zhì)消費(fèi)主要是購(gòu)買生活必需品(剛性消費(fèi));文化消費(fèi)具有彈性消費(fèi)的特點(diǎn),主要是購(gòu)買非生活必需品。當(dāng)人類的物質(zhì)需求得到滿足進(jìn)而追求精神需求時(shí),所產(chǎn)生的文化消費(fèi)會(huì)展現(xiàn)出“黏性”特點(diǎn)。黏性主要表現(xiàn)在兩個(gè)方面,一是習(xí)慣性消費(fèi),二是附加型消費(fèi)。當(dāng)消費(fèi)者對(duì)某類文化產(chǎn)品比較喜愛(ài)時(shí),會(huì)持續(xù)消費(fèi)同類型文化產(chǎn)品,以不斷滿足自身的文化需求,這就產(chǎn)生了我們常說(shuō)的“游戲迷”“球迷”“影迷”等群體。此外,文化產(chǎn)品非獨(dú)立的個(gè)體,不同文化產(chǎn)品之間都可以產(chǎn)生關(guān)聯(lián),例如一部賣座的電影引起市場(chǎng)轟動(dòng)后,生產(chǎn)者可以圍繞電影IP生產(chǎn)玩偶、書(shū)籍、服裝等周邊產(chǎn)品,引導(dǎo)消費(fèi)者的附加消費(fèi)。文化消費(fèi)的“黏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推動(dòng)了文化產(chǎn)品生產(chǎn)和開(kāi)發(fā)的持續(xù)性,需要生產(chǎn)者和開(kāi)發(fā)者有效利用和正確引導(dǎo)。
第二,差異性。消費(fèi)者根據(jù)不同需求產(chǎn)生的文化消費(fèi)具有多樣化的特點(diǎn),人在精神活動(dòng)中產(chǎn)生的文化需求也因人而異。一方面,生活在不同地區(qū)的人由于氣候、海拔、歷史等客觀環(huán)境的不同,產(chǎn)生的文化需求具有地域差異,尤其是在幅員遼闊的中國(guó),56個(gè)民族由于其歷史和生活環(huán)境不同,產(chǎn)生了不同的文化習(xí)俗、語(yǔ)言和文字,文化消費(fèi)需求自然也存在著差異性。另一方面,不同的消費(fèi)者具有不同的教育背景、生活環(huán)境、社會(huì)地位等,他們的文化欣賞能力也會(huì)存在差異,需要不同的文化產(chǎn)品滿足他們自身的需求。但文化消費(fèi)的差異性中也存在著同一性,具有相同文化消費(fèi)需求的人,有極大可能擁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環(huán)境。文化消費(fèi)作為一種社會(huì)傾向其產(chǎn)生原因極其復(fù)雜,因此在研究文化產(chǎn)品市場(chǎng)化時(shí),要從各方面充分考慮到文化消費(fèi)的差異化。
第三,外部性。外部性是經(jīng)濟(jì)學(xué)用語(yǔ),是指經(jīng)濟(jì)活動(dòng)對(duì)社會(huì)和社會(huì)群體產(chǎn)生的積極或消極的影響。文化產(chǎn)品中往往蘊(yùn)含著大量?jī)?yōu)秀思想文化和精神內(nèi)涵,具有一定的思想啟迪和精神引導(dǎo)的作用。文化消費(fèi)是文化產(chǎn)品發(fā)揮其效用價(jià)值的過(guò)程,考慮到文化產(chǎn)品的社會(huì)效益,當(dāng)消費(fèi)者享受健康、積極的文化產(chǎn)品和服務(wù)時(shí),正確的文化和價(jià)值觀得以傳播,能夠引導(dǎo)人的行為,促進(jìn)社會(huì)和諧,這是文化產(chǎn)品的正外部性。當(dāng)消費(fèi)者享受消極、低俗的文化產(chǎn)品和服務(wù)時(shí),消費(fèi)者無(wú)法從文化產(chǎn)品中獲得正確的思想啟蒙和精神指導(dǎo),不利于人的全面發(fā)展和社會(huì)進(jìn)步,這是文化產(chǎn)品的負(fù)外部性。因此,無(wú)論文化消費(fèi)還是文化生產(chǎn)都不能完全依靠市場(chǎng)調(diào)節(jié),需要政府發(fā)揮其職能和社會(huì)群體一起進(jìn)行經(jīng)濟(jì)干預(yù)和思想引導(dǎo)。
第四,傳統(tǒng)性。非遺文化具有悠久的歷史傳承,這給予了非遺文化產(chǎn)品非凡的生命力。因?yàn)閭鹘y(tǒng)確實(shí)有種特別的力量,讓人順從,使人臣服。正因?yàn)橛辛诉@種力量,非遺文化產(chǎn)品才得以延續(xù)。它附著在歷史記憶中,體現(xiàn)在現(xiàn)實(shí)生活中,物化在各類用品中,無(wú)時(shí)無(wú)刻不在影響著人們的生活。如果說(shuō)非遺文化的歷史就是一部生活史,那么非遺文化產(chǎn)品就是這部生活史的一條主線。非遺文化產(chǎn)品的奢侈特性,與貧富無(wú)關(guān),只與傳統(tǒng)息息相關(guān)。
(二)“非遺”類藝術(shù)品市場(chǎng)化面臨的困境
1.生產(chǎn)性保護(hù)與市場(chǎng)需求之間的矛盾
2012年文化部正式提出非遺的“生產(chǎn)性保護(hù)”概念,明確了“堅(jiān)持把社會(huì)效益放在首位,社會(huì)效益和經(jīng)濟(jì)效益有機(jī)統(tǒng)一原則”。與非遺越來(lái)越受到重視和關(guān)注同時(shí)出現(xiàn)在大眾視野中的是越來(lái)越多的非遺項(xiàng)目后繼無(wú)人,前途堪憂。一方面是“生產(chǎn)性保護(hù)”要求,另一方面是非遺傳承的尷尬現(xiàn)狀,如何在這兩者之間尋求一種平衡,這是一個(gè)值得深入探討的問(wèn)題。
此外,對(duì)非遺的不合理利用和非遺的產(chǎn)業(yè)化擔(dān)憂也一直存在。有學(xué)者認(rèn)為非遺的產(chǎn)業(yè)化將會(huì)因?yàn)樽非蠼?jīng)濟(jì)效益而損害非遺的文化價(jià)值,偏離了對(duì)非遺保護(hù)的初衷。如馮驥才指出:“產(chǎn)業(yè)的主要目的是盈利。追求利潤(rùn)最大化,往往就會(huì)傷害了藝術(shù)的原真性”。(33)馮驥才:《文化遺產(chǎn)不能一股腦產(chǎn)業(yè)化》,《人民日?qǐng)?bào)》2011年8月12日。劉錫誠(chéng)提出,“凡是以犧牲傳統(tǒng)技藝及其文化蘊(yùn)涵為代價(jià)的所謂產(chǎn)業(yè)化,是不可取的,是我們所堅(jiān)決反對(duì)的”。(34)劉錫誠(chéng):《“非遺”產(chǎn)業(yè)化:一個(gè)備受爭(zhēng)議的問(wèn)題》,《河南教育學(xué)院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10年第4期。因?yàn)樵谑袌?chǎng)經(jīng)濟(jì)中,市場(chǎng)需求決定了商品的生產(chǎn),生產(chǎn)者始終以經(jīng)濟(jì)利益最大化為商品生產(chǎn)的目標(biāo)。但非遺文化產(chǎn)品是一種精神產(chǎn)品,是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具有公共屬性。“非遺”類藝術(shù)品中蘊(yùn)含著獨(dú)特的精神價(jià)值,其重要性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其使用價(jià)值,它將對(duì)社會(huì)的穩(wěn)定發(fā)展產(chǎn)生積極的推動(dòng)作用。如果任由市場(chǎng)需求決定“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生產(chǎn),可能會(huì)導(dǎo)致低俗文化的肆意傳播,其負(fù)外部性會(huì)影響消費(fèi)者的文化觀念。因此,“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生產(chǎn)需要考慮到其產(chǎn)生的社會(huì)效益是否符合正確的價(jià)值觀。要以精神文明建設(shè)的要求為生產(chǎn)導(dǎo)向,不能完全由市場(chǎng)需求主導(dǎo)。文化產(chǎn)品生產(chǎn)者不能盲目追求經(jīng)濟(jì)利益的最大化,而應(yīng)該將社會(huì)效益放首位。
2.“非遺”類藝術(shù)品品牌意識(shí)缺乏
“非遺”類藝術(shù)品大多是以流傳至今的品類名稱命名,如蘇繡、宋錦、絨花等,沒(méi)有發(fā)展特定的品牌。而品牌對(duì)于產(chǎn)品來(lái)說(shuō)是一種品質(zhì)與地位的象征,是企業(yè)產(chǎn)品和企業(yè)形象的直接反映,也是消費(fèi)者對(duì)企業(yè)和產(chǎn)品的一種感知。市場(chǎng)中存在的產(chǎn)品形式多樣,但相同類型的產(chǎn)品要想在面對(duì)消費(fèi)者時(shí)脫穎而出,品牌效應(yīng)必不可少。目前,我國(guó)“非遺”類藝術(shù)品品牌意識(shí)薄弱主要表現(xiàn)在以下兩個(gè)方面:
其一,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保護(hù)意識(shí)薄弱。“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核心在于凝結(jié)在其產(chǎn)品上的智力因素,因此,著作權(quán)、商標(biāo)權(quán)、專利權(quán)等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是文化產(chǎn)品市場(chǎng)化道路上的護(hù)身符。但我國(guó)文化產(chǎn)品的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未得到充分的重視和保護(hù),一旦某個(gè)文化產(chǎn)品引起購(gòu)買潮流,稍后就會(huì)出現(xiàn)大量成本低廉的仿造品。產(chǎn)品的文化內(nèi)涵被破壞,文化價(jià)值降低,山寨產(chǎn)品的肆意流通容易導(dǎo)致市場(chǎng)混亂,引起惡意的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富有創(chuàng)新力的文化企業(yè)由于無(wú)法降低產(chǎn)品成本在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中處于劣勢(shì),嚴(yán)重阻礙了“非遺”類藝術(shù)品品牌的發(fā)展。
其二,品牌建設(shè)能力不足。非遺傳承人雖然擁有著制作工藝,但缺乏專業(yè)的產(chǎn)品運(yùn)營(yíng)和品牌經(jīng)營(yíng)的知識(shí)和技能。品牌包含品牌名稱、商品質(zhì)量、歷史文化等多方面內(nèi)容,并非簡(jiǎn)單的企業(yè)注冊(cè)名。現(xiàn)階段我國(guó)的文化市場(chǎng)中能稱之為文化品牌的少之又少,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品牌建設(shè)能力不足,導(dǎo)致無(wú)法精準(zhǔn)傳遞產(chǎn)品的文化價(jià)值并產(chǎn)生良好的社會(huì)效益,文化產(chǎn)品在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中缺少辨識(shí)度與核心競(jìng)爭(zhēng)力。
3.“非遺”類藝術(shù)品產(chǎn)業(yè)鏈不完整
非遺文化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應(yīng)該是一個(gè)系統(tǒng)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的過(guò)程,包括創(chuàng)意開(kāi)發(fā)、產(chǎn)品制造、市場(chǎng)營(yíng)銷和衍生產(chǎn)品的開(kāi)發(fā)等環(huán)節(jié),其中創(chuàng)意開(kāi)發(fā)是文化產(chǎn)品生產(chǎn)中最具有價(jià)值、最核心的一個(gè)環(huán)節(jié)。衍生產(chǎn)品的開(kāi)發(fā)是文化產(chǎn)業(yè)鏈擴(kuò)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文化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jì)效益溢出效應(yīng)顯現(xiàn)的基礎(chǔ)環(huán)節(jié)。日本動(dòng)漫業(yè)具有非常完整的文化產(chǎn)業(yè)鏈,整個(gè)產(chǎn)業(yè)鏈中各個(gè)環(huán)節(jié)協(xié)同發(fā)展,充分開(kāi)發(fā)和利用動(dòng)漫產(chǎn)品及其周邊價(jià)值,帶動(dòng)制造業(yè)、影視業(yè)和旅游業(yè)的發(fā)展,產(chǎn)業(yè)關(guān)聯(lián)效應(yīng)十分顯著。
目前,我國(guó)“非遺”類藝術(shù)品生產(chǎn)大多采取零散作業(yè)的方式,產(chǎn)業(yè)鏈不完善。譬如,苗繡歷史悠久,其產(chǎn)品(譬如絲巾)在海外享有一定的聲譽(yù)和市場(chǎng),常常代表國(guó)家非遺文化項(xiàng)目參加國(guó)際交流,其精美的繡工令觀者贊嘆不已。然其文化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也都是零散作業(yè)再回購(gòu),采取訂單式生產(chǎn),對(duì)苗繡文化的市場(chǎng)認(rèn)識(shí)非常有限。另外,產(chǎn)業(yè)鏈上的環(huán)節(jié)發(fā)展非常不均衡,缺乏創(chuàng)新開(kāi)發(fā)能力。很多非遺文化產(chǎn)品過(guò)分強(qiáng)調(diào)手工制作和傳承人自身的演繹,卻不關(guān)注市場(chǎng)需求的變化和非遺文化本身的創(chuàng)新性開(kāi)發(fā)。再者,“非遺”類藝術(shù)品生產(chǎn)企業(yè)之間缺少商業(yè)合作和技術(shù)交流,只關(guān)心自家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缺少全局觀。如此,產(chǎn)業(yè)鏈的不完整和發(fā)展不均衡,大大降低了“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市場(chǎng)需求適應(yīng)能力和持續(xù)性創(chuàng)新能力。
4.“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傳播方式單一
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場(chǎng)域指的是一種文化樣式或者一種久遠(yuǎn)傳承的文化活動(dòng)所無(wú)法剝離的環(huán)境、場(chǎng)所,某種特定的、定期的文化儀式及其參與的人群的行為和規(guī)程。(35)王亮:《媒介視域: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研究的新思路》,《編輯之友》2015年第6期。非遺最早是通過(guò)傳承人親身傳播和實(shí)物傳播來(lái)實(shí)現(xiàn)信息的傳遞,其中親身傳播是歷史最久遠(yuǎn)的傳播方式。非遺類目中的各類戲劇、傳統(tǒng)舞蹈、游藝與雜技等曾經(jīng)都通過(guò)親身演繹的方式來(lái)傳播。(36)王詩(shī)文、陳亮:《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傳播特點(diǎn)及策略研究》,《淮南師范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15年第1期。除此之外,博物館是非遺實(shí)物傳播最多的場(chǎng)域。隨著新媒體的發(fā)展,整個(gè)社會(huì)構(gòu)成了一個(gè)龐大的信息網(wǎng)絡(luò)。 2006年我國(guó)設(shè)立了文化遺產(chǎn)日之后,國(guó)家和人們對(duì)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重視和保護(hù)程度逐步提高,傳播的非遺信息量逐年增多。傳播這些信息的渠道主要是以報(bào)紙、廣播、電視和雜志等組成的傳統(tǒng)媒體。傳統(tǒng)媒體接觸率隨被訪者年齡提升而提升,而新興媒體在青少年中的接觸率更高。15~24歲人群中,僅有50.8%的每天都會(huì)在家里接觸電視,隨著被訪者年齡的提升,55歲及以上人群中,每天在家里接觸電視的人數(shù)占比達(dá)到了96.5%(37)數(shù)據(jù)來(lái)源:CSM媒介研究12城市基礎(chǔ)研究。。而事實(shí)上,青年群體才是未來(lái)的文化消費(fèi)主力,所以眾多的奢侈品牌開(kāi)始啟用年輕一代的代言人,如吳亦凡、竇靖童、迪麗熱巴等。誠(chéng)然,相對(duì)單一的“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傳播方式可以增強(qiáng)“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神秘感。但是,和“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未來(lái)的主流消費(fèi)人群的絕對(duì)區(qū)隔不利于消費(fèi)者的成功消費(fèi)。
四、“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市場(chǎng)化運(yùn)作
合理開(kāi)發(fā)“非遺”類藝術(shù)品對(duì)于該類產(chǎn)品藝術(shù)性的生產(chǎn)性保護(hù)是目前急需解決的問(wèn)題。傳承人缺乏市場(chǎng)意識(shí),對(duì)產(chǎn)品的市場(chǎng)需求認(rèn)識(shí)不足,導(dǎo)致生產(chǎn)不可持續(xù)。沒(méi)有取得一定的經(jīng)濟(jì)和社會(huì)效益,反過(guò)來(lái)導(dǎo)致非遺傳承人傳承和保護(hù)的動(dòng)力不足。所以,文化生產(chǎn)的核心問(wèn)題是商業(yè)與創(chuàng)意之間的關(guān)系問(wèn)題,或者說(shuō)是盈利動(dòng)力與生產(chǎn)激勵(lì)之間關(guān)系的問(wèn)題。解決這個(gè)問(wèn)題的關(guān)鍵在于市場(chǎng)化運(yùn)作。考慮到非遺文化產(chǎn)品具有與奢侈品相同的特點(diǎn),借助奢侈品牌的市場(chǎng)化運(yùn)營(yíng),可以為非遺文化產(chǎn)品的市場(chǎng)化提出以下四項(xiàng)策略:
(一)產(chǎn)品策略
企業(yè)通過(guò)生產(chǎn)和開(kāi)發(fā)滿足市場(chǎng)需求的產(chǎn)品以幫助企業(yè)開(kāi)拓市場(chǎng),實(shí)現(xiàn)企業(yè)快速發(fā)展的產(chǎn)品生產(chǎn)方案就是產(chǎn)品策略。產(chǎn)品策略包括產(chǎn)品類型、質(zhì)量、設(shè)計(jì)等多個(gè)方面,直接影響著“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銷售和用戶體驗(yàn)。具體到“非遺”類藝術(shù)品,則應(yīng)特別強(qiáng)調(diào)以下三點(diǎn):
1.高品質(zhì)
高品質(zhì)是保證品牌在激烈的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中始終立于不敗之地的關(guān)鍵。奢侈品大多對(duì)品牌產(chǎn)品的生產(chǎn)工藝、原材料、步驟都具有嚴(yán)格的要求,即使是在工業(yè)生產(chǎn)發(fā)達(dá)的今天,仍然有純手工定制的奢侈品產(chǎn)品,這些對(duì)于質(zhì)量的高要求維持著奢侈品的高端定位,對(duì)于“非遺”類藝術(shù)品來(lái)說(shuō)也是一樣。“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定價(jià)要明顯高于其他相同功能的普通產(chǎn)品,除去文化價(jià)值,高品質(zhì)也是吸引高端消費(fèi)的一大要素。所以,非遺文化產(chǎn)品的設(shè)計(jì)師和制作者應(yīng)該從心理上尊崇手工制作,必須追求品質(zhì),講究細(xì)節(jié),提高“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力。
2.創(chuàng)新設(shè)計(jì)
“非遺”類藝術(shù)品在市場(chǎng)競(jìng)爭(zhēng)中并不是以量取勝,這要求商品質(zhì)量提高的同時(shí),商品設(shè)計(jì)更新速度也需加快。“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開(kāi)發(fā),需在把技藝原汁原味傳承下去的同時(shí),在過(guò)程中學(xué)會(huì)創(chuàng)新、學(xué)會(huì)適應(yīng)市場(chǎng),但不是毫無(wú)底線地往娛樂(lè)大眾方向發(fā)展。以蘇繡為例,在明代它吸收了顧繡“以畫入繡”的風(fēng)格,清末時(shí)期引入了西洋繪畫技巧創(chuàng)立了“仿真繡”,讓寫意的傳統(tǒng)蘇繡變得寫實(shí)和逼真,此后一直走在不斷創(chuàng)新不斷成長(zhǎng)的道路上。(38)雷虎:《蘇繡:風(fēng)景為何這邊獨(dú)好?》,《文化月刊》2013年第1期。“非遺”類藝術(shù)品針對(duì)的消費(fèi)市場(chǎng)更為廣闊和年輕化,消費(fèi)者擁有許多個(gè)性化的追求,為了滿足消費(fèi)者日新月異的消費(fèi)需求,非遺文化產(chǎn)品需要不斷地進(jìn)行產(chǎn)品創(chuàng)新。
3.保護(hù)性開(kāi)發(fā)
非遺的“生產(chǎn)性保護(hù)”,有學(xué)者提出構(gòu)建“非營(yíng)利性 + 營(yíng)利性”雙軌制利用模式,以“非營(yíng)利性”利用維持有效傳承,以“營(yíng)利性”利用推進(jìn)非遺文化元素產(chǎn)業(yè)化。(39)劉鑫:《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的經(jīng)濟(jì)價(jià)值及其合理利用模式》,《學(xué)習(xí)與實(shí)踐》2017年第1期。其中“非營(yíng)利性”即非遺核心技藝產(chǎn)品(主要針對(duì)非遺核心技藝產(chǎn)品),它是利用非遺的核心技藝生產(chǎn)出來(lái)的產(chǎn)品,含有完整的非遺文化價(jià)值;而“營(yíng)利性”即非遺衍生產(chǎn)品沒(méi)有非遺核心技藝,而是利用非遺相關(guān)文化元素開(kāi)發(fā)出的衍生產(chǎn)品(對(duì)傳統(tǒng)美術(shù)、傳統(tǒng)技藝和傳統(tǒng)醫(yī)藥類非遺適用)。這種模式和奢侈品化運(yùn)作“非遺”類藝術(shù)品是不矛盾的,本研究提出的“非遺”類藝術(shù)品強(qiáng)調(diào)的是產(chǎn)品中包含的“非遺藝術(shù)”與“工匠精神”,這就是對(duì)非遺文化最好的保護(hù)性利用。
(二)價(jià)格策略
價(jià)格定位是指定價(jià)方在通過(guò)成本核算和市場(chǎng)調(diào)研后,根據(jù)產(chǎn)品定位和市場(chǎng)需求的基本情況決定產(chǎn)品的定價(jià)和價(jià)格調(diào)整方案的過(guò)程。以下將會(huì)參照奢侈品的市場(chǎng)運(yùn)行準(zhǔn)則提出文化產(chǎn)品的價(jià)格定位方案,整個(gè)定價(jià)方案包括商品的基本定價(jià)、促銷定價(jià)兩部分。
1.基本定價(jià)
奢侈品的定價(jià)準(zhǔn)則與一般商品不同,一般商品的價(jià)格受市場(chǎng)需求的影響,定價(jià)方為零售商,奢侈品的價(jià)格受市場(chǎng)定位的影響,由制造商決定。在消費(fèi)者眼中,高價(jià)似乎就是奢侈品的代名詞,象征一定的社會(huì)身份和地位。“非遺”類藝術(shù)品所蘊(yùn)含的文化內(nèi)涵、地位象征才是商品真正的價(jià)值所在。因此,“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基本定價(jià)應(yīng)該由制造者來(lái)決定,需要考慮凝結(jié)在商品中的藝術(shù)價(jià)值、文化價(jià)值和符號(hào)價(jià)值等價(jià)值因素。
2.不促銷
一般商品在促銷時(shí)通過(guò)降價(jià)來(lái)刺激消費(fèi)需求,奢侈品除外。消費(fèi)者在購(gòu)買“非遺”類藝術(shù)品時(shí),消費(fèi)的不僅是商品的使用價(jià)值,更是商品的象征體系。“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消費(fèi)不僅是一種行為更是一種文化體驗(yàn),表達(dá)、體現(xiàn)或隱含了某種意義、價(jià)值或規(guī)范。這種消費(fèi)不再是一種簡(jiǎn)單的適用價(jià)值的自然屬性得到實(shí)現(xiàn)的過(guò)程,它承載著消費(fèi)主體對(duì)非遺文化進(jìn)行評(píng)價(jià)、認(rèn)同而做出的姿態(tài),是生活方式的一個(gè)組成模式。每一種“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價(jià)值,都取決于它的地位。“物以稀為貴”,“非遺”類藝術(shù)品與普通消費(fèi)者之間需要建立起的一種“距離感”而獲得適當(dāng)?shù)摹吧衩馗小薄R虼耍瑸榱司S護(hù)這種“距離感”,“非遺”類藝術(shù)品需要維護(hù)獨(dú)特的市場(chǎng)定位和象征性價(jià)值,而不是廣而告之降低售價(jià)來(lái)刺激消費(fèi)。
(三)品牌策略
品牌效應(yīng)是指生產(chǎn)產(chǎn)品或提供服務(wù)的企業(yè)的形象對(duì)消費(fèi)者購(gòu)買意向或消費(fèi)評(píng)價(jià)的影響。一般來(lái)說(shuō),消費(fèi)者對(duì)于產(chǎn)品品牌的認(rèn)知度會(huì)影響消費(fèi)者對(duì)于該品牌商品和服務(wù)的評(píng)價(jià),進(jìn)而影響消費(fèi)者的消費(fèi)行為和購(gòu)買意向。對(duì)于“非遺”類藝術(shù)品來(lái)說(shuō),可以通過(guò)打造全新品牌價(jià)值或者與強(qiáng)勢(shì)品牌合作增強(qiáng)來(lái)品牌效應(yīng)。
1.打造品牌
打造品牌是提升產(chǎn)品市場(chǎng)地位的第一步。如“上久楷”宋錦品牌,它以保護(hù)和傳承世界非遺宋錦為己任,注重“文化、創(chuàng)新、時(shí)尚”為核心價(jià)值觀,憑借絲綢傳統(tǒng)文化和研發(fā)、創(chuàng)新實(shí)力,實(shí)力亮劍國(guó)際舞臺(tái)。不僅多次作為國(guó)禮饋贈(zèng)給各國(guó)政要(如G20峰會(huì)),還通過(guò)亮相米蘭時(shí)裝周、米蘭世博會(huì)等國(guó)際舞臺(tái)贏得了國(guó)際的尊重與贊許。對(duì)于“非遺”類藝術(shù)品而言,品牌是其與眾不同的產(chǎn)品價(jià)值的集中體現(xiàn),也是引導(dǎo)消費(fèi)者購(gòu)買的動(dòng)力。文化企業(yè)需充分挖掘非遺文化的潛在價(jià)值,提煉出獨(dú)特的文化元素與文化框架,并選擇合適的品類載體(器具類或服飾類),設(shè)計(jì)文化場(chǎng)景,進(jìn)行合適的奢侈品牌定位。同時(shí),圍繞主要品類開(kāi)發(fā)周邊產(chǎn)品,打造完整的產(chǎn)業(yè)鏈。甚至,還可以將多種非遺文化融入進(jìn)產(chǎn)品之中,增強(qiáng)其文化包容性。譬如,上久楷品牌在G20峰會(huì)國(guó)禮設(shè)計(jì)中,就將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技術(shù)宋錦、新緙絲、杭羅和蘇繡完美結(jié)合在一起。
2.與強(qiáng)勢(shì)品牌合作
這種模式即通過(guò)和國(guó)際大品牌合作的方式來(lái)實(shí)現(xiàn)共贏,在獲得經(jīng)濟(jì)效益的同時(shí),可以不斷擴(kuò)大文化產(chǎn)品的影響力。在積聚實(shí)力之后,可以打造自身品牌,不再依托強(qiáng)勢(shì)品牌。如愛(ài)馬仕品牌創(chuàng)立的當(dāng)代時(shí)尚生活品牌“上下”,它致力于傳承中國(guó)精湛的手工藝,通過(guò)創(chuàng)新使其可以重返當(dāng)代生活。而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瓷胎竹編代表性傳承人通過(guò)和世界頂級(jí)的奢侈品公司合作,獲得經(jīng)濟(jì)效益的同時(shí),通過(guò)不斷創(chuàng)新設(shè)計(jì)出了立體、斜編、鏤空等多種編織技法使非遺得以傳承和發(fā)展,而為奢侈品牌公司的產(chǎn)品提供竹編技術(shù),并沒(méi)有違背“生產(chǎn)性保護(hù)”原則,且核心技藝仍留在傳承人手中。
(四)傳播策略
長(zhǎng)期以來(lái),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給人留下了古老、傳統(tǒng)、不時(shí)尚的印象。“非遺”類藝術(shù)品要融入現(xiàn)代人的生活,滿足目標(biāo)群體的某種需求。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信息交互效率大大提升的當(dāng)代社會(huì),多渠道傳播是提升品牌知名度的重要方式。但是,“非遺”類藝術(shù)品傳播的目的不是廣而告之,它們必須與普通大眾保持一定的距離感,同時(shí)又要準(zhǔn)確地送達(dá)其目標(biāo)消費(fèi)群體。因此,“非遺”類藝術(shù)品在傳播時(shí)除了選擇合適的傳播渠道,傳播內(nèi)容也要進(jìn)行“拆分”。品牌的文化內(nèi)涵和生活方式一定要在合適的渠道中進(jìn)行廣泛的深入的宣傳,這部分內(nèi)容的傳播重點(diǎn)是要講述屬于自己的真實(shí)的歷史文化故事和品牌故事,這樣一來(lái)就創(chuàng)建了情感卷入,建立了一個(gè)吸引人的身份以及消費(fèi)體驗(yàn)的幻想空間。其次,品牌的場(chǎng)域傳播要懂得如何設(shè)置必要的障礙來(lái)保持消費(fèi)者的欲望,因?yàn)楸揪碗y得。除了金錢障礙,還有其自身天然就具有的文化障礙,消費(fèi)者不光是用得起,還要懂得如何欣賞產(chǎn)品和消費(fèi)。設(shè)置時(shí)間障礙(搜索時(shí)間、等待時(shí)間和渴望時(shí)間)也是有必要的。因?yàn)椋胺沁z”類藝術(shù)品的傳播不是為了銷售,是要建立其排他性的地位。
五、結(jié)論
隨著文化產(chǎn)業(yè)的快速發(fā)展,市場(chǎng)中文化產(chǎn)品種類豐富,文化產(chǎn)品的市場(chǎng)化趨勢(shì)不可逆轉(zhuǎn)。為了非遺更好的保護(hù)與傳承,“非遺”類藝術(shù)品不能回避市場(chǎng)化這個(gè)重要問(wèn)題。但“非遺”類藝術(shù)品作為非一般勞動(dòng)產(chǎn)品,如果采取普通商品的市場(chǎng)化運(yùn)作方式,必然會(huì)導(dǎo)致一系列問(wèn)題。考慮到非遺文化產(chǎn)品與奢侈品具有許多相同點(diǎn),本研究從奢侈品的視角挖掘“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市場(chǎng)化策略。非遺文化產(chǎn)品關(guān)鍵在于奢侈品定位的確立,通過(guò)完善創(chuàng)新與利用機(jī)制,打造優(yōu)質(zhì)的文化產(chǎn)品,這意味著必須深刻了解它能夠?qū)嵺`的天性和自發(fā)性。目前,“非遺”類藝術(shù)品營(yíng)銷沒(méi)有起作用的原因是因?yàn)橐催\(yùn)用日常消費(fèi)品同樣的營(yíng)銷思維,要么根本就不進(jìn)行市場(chǎng)化運(yùn)營(yíng)。“非遺”類藝術(shù)品包含了獨(dú)特的“非遺”與“工匠精神”,“非遺”類藝術(shù)品必須是感官的全方位的體驗(yàn)。因此,不能簡(jiǎn)單地給產(chǎn)品定價(jià),要運(yùn)用奢侈品定價(jià)的策略和獨(dú)特的傳播策略。對(duì)于改變心態(tài),價(jià)格是一個(gè)決定性的因素。在傳播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和正確的價(jià)值觀的同時(shí),不但維護(hù)“非遺”類藝術(shù)品的市場(chǎng)地位,還促進(jìn)了非物質(zhì)化文遺產(chǎn)的保護(hù)和傳承。
- 文化軟實(shí)力研究的其它文章
- 2019年總目錄
- 中華思想文化術(shù)語(yǔ)(連載二十一)
- 新時(shí)代的中國(guó)鄉(xiāng)村文化振興
——新時(shí)代下中國(guó)鄉(xiāng)村文化振興國(guó)際學(xué)術(shù)會(huì)議暨2019年特色文化產(chǎn)業(yè)論壇綜述 - 奮力推進(jìn)新時(shí)代黨的建設(shè)偉大工程
——“學(xué)習(xí)貫徹習(xí)近平總書(shū)記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70周年大會(huì)上重要講話精神暨中國(guó)共產(chǎn)黨的建設(shè)”理論研討會(huì)綜述 - 電影作為軟實(shí)力:內(nèi)涵、構(gòu)成與特征
- 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國(guó)際傳播路徑探析
——基于唐宋文化對(duì)外傳播方式的歷史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