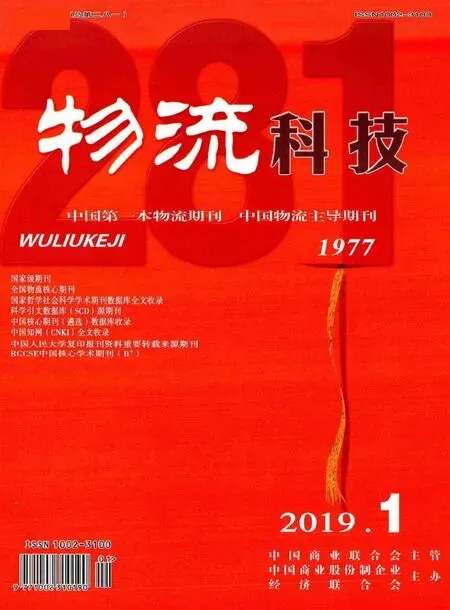供應鏈視角下東部煤礦生產企業跨區轉移的溢出效應研究
杜沈悅,李存芳 (江蘇師范大學 商學院,江蘇 徐州 221116)
0 引言
我國煤炭資源儲量已呈現出明顯的東少西多現象,山西省煤炭儲量最多,內蒙古次之,東部地區的煤炭資源已十分稀有(見圖1)。東部地區的現有煤炭資源存儲量已無法承載東部煤礦生產企業的高負荷生產,東部地區的煤礦生產企業面對煤炭資源即將耗竭的現實問題,不得不采取企業轉移措施。據資料統計,許多東部煤礦生產企業已轉移到煤炭資源豐富的中西部省份[1],例如江蘇省的徐州礦務集團、山東省的兗州礦務集團等大型煤礦生產企業在山西、內蒙古等地投資項目,新建企業,繼續進行生產經營活動。

圖1 2016年全國煤炭基礎儲量
東部地區的煤礦生產企業轉入東道地進行生產經營活動,成為東道地煤炭供應鏈網絡中不可缺失的節點企業。東部煤礦生產企業與中西部本土煤礦生產企業相比,擁有明顯的技術優勢,其生產的煤炭產品質量比供應鏈網絡中其他本土煤礦生產企業生產的煤炭產品質量更高,這些煤炭產品對于后續生產工藝流程的要求也更加嚴格。位于煤礦生產企業下游的企業,一方面為了使自身的生產工藝流程滿足煤礦生產企業提供的原材料的生產要求,會重新設計生產設備,改進生產模式,優化生產技術,提高生產能力,從而獲得更大的經濟效應;另一方面,煤礦生產企業供應的高質量產品,會直接提高其下游本土企業的生產效率,增加經濟效益。這樣,東部轉入的煤礦生產企業便對其下游企業產生了溢出效應。
關于供應鏈企業間的溢出效應問題,學者們集中研究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其上下游企業的溢出效應。許和連等(2007)對我國工業行業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企業通過從上游本土企業購買產品,與上游本土企業建立聯系,進而對上游本土企業產生了溢出效應[2]。Lileeva(2010)、Xu和Sheng(2012)研究均發現,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下游東道國本土企業產生了正向的溢出效應[3-4]。Fernandes和Paunov(2012)對智利的研究發現,生產性外商服務企業對其下游的制造業企業產生了溢出效應[5]。鐘昌標(2006)、Jabbour和Mucchielli(2007)、Du等(2012) 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研究證明,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其上下游東道國本土企業均產生了正向的溢出效應[6-8]。Gorodnichenko et al.(2015)研究發現,外商投資企業為了使得供應鏈上下游企業間的合作更加順利,將技術和管理方法等傳授給上下游企業,從而對其上下游企業產生了溢出效應[9]。徐宏毅等(2016)通過對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的面板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發現,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對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的上游企業的溢出效應,大于其對生產性服務業下游企業的溢出效應[10]。以上學者們的研究結論均表明,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會對其上下游企業產生了溢出效應。我國學者關愛萍和李輝(2013)研究發現,我國國內區際間產業轉移存在行業間的技術溢出效應[11]。
關于我國國內跨區投資企業對上下游本土企業溢出效應的研究還較少,尤其缺乏在供應鏈視角下對東部煤礦生產企業跨區轉移溢出效應的研究。煤礦生產企業處于煤炭供應鏈的上游,主要與其下游企業產生關聯,所以本文探究東部煤礦生產企業轉移對東道地下游本土企業的溢出效應,以期為東道地煤炭供應鏈節點企業間的協同發展提供有益參考。
1 研究方法
參考已有的研究,以C-D生產函數為基礎,建立東部地區的煤礦生產企業跨區域投資內生化的技術進步模型,用來檢驗東部地區的煤礦生產企業轉入東道地后對本土企業的溢出效應。
C-D生產函數如下:

其中,i表示煤炭行業,t表示時間;Y表示產出;K表示資本投入;L表示勞動力投入;α、β表示彈性系數;A表示技術進步,衡量全要素生產率。假設煤礦生產企業跨區域投資是影響東道地全要素生產率的因素之一,建立如下模型:

式(2)中,S表示煤礦生產企業跨區投資額占東道地煤炭行業總投資額的比;B表示影響技術進步的其他因素;λ表示彈性系數,反映煤礦生產企業對煤炭行業本土企業溢出效應的溢出效果;Findlay(1978)指出,如果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在東道國所占投資份額比較大,那么發生技術溢出效應的可能性就越大,可以假設,煤礦生產企業在東道地的投資份額越大,其對東道地本土企業產生溢出效應的可能性就越大。
將式 (2) 代入式 (1) 中,得:

對式(3)兩邊同時取對數,得:

利用近似估計:當z很小時,log( 1+z)≈z,對表達式(4) 中的ln( 1+ λSit)做近似估計,則表達式(4) 可以寫成:

式(5)度量的是煤礦生產企業對煤炭行業內的其他本土企業的溢出效應,而其對下游m行業企業的溢出效應指標的設定參考薛漫天和趙曙東(2008)[12]、蔣樟生(2017)[13]的做法,具體如下:

式(6)中的θim表示煤礦生產企業向其下游m行業的企業供應的產品占煤炭行業企業總產出的比重。
則檢驗煤礦生產企業轉入東道地后對其下游本土企業的溢出效應的模型如下:

2 實證分析
本文將東部地區轉入的煤礦生產企業作為研究對象,與煤礦生產企業聯系最緊密的企業是電力、熱力生產與供應企業,煤礦生產企業對原煤進行開采、洗選、加工,將煤炭產品供應給其下游的電力、熱力生產與供應企業(下文簡稱:電熱力企業)。在東部煤礦生產企業轉入內蒙古之前,電熱力企業使用本土煤礦生產企業的低質量煤炭,煤的發熱量低,電熱力企業為了維持機組負荷必須投入助燃油,而助燃油價格很高,這將嚴重影響電熱力企業的經濟效益;低質量、可磨性差的煤炭會磨損設備,增加設備維護費用,影響電熱力企業機組的經濟性。東部轉入的煤礦生產企業擁有絕對的技術優勢,其生產出的煤炭產品比本土煤礦生產企業生產出的煤炭產品品質更高,電熱力企業從東部轉入的煤礦生產企業采購煤炭作為生產原料,一方面,電熱力企業為了使自身的生產設備及工藝流程滿足高質量煤炭的生產要求,會重新設計生產設備,優化生產技術,提高生產能力,從而獲得更大的經濟效益;另一方面,高質量煤炭會直接提高電熱力企業的生產效率,增加電熱力企業的產值。因此,本文實證檢驗東部煤礦生產企業轉入內蒙古之后對其下游本土電熱力企業的溢出效應,探究這種溢出效應是否存在?若存在溢出效應,溢出效應的強度如何?
2.1 數據來源
我國煤炭經濟在2002年之前處于低迷時期,從2002年出現回溫,因此選取2002~2015年的數據。又因為內蒙古是煤礦生產企業轉入數量較多的地區,且煤炭資源儲量豐富,開采潛力較大,未來可能會吸引更多的東部煤礦生產企業前來投資開發。綜上,考慮數據的代表性,本文選取內蒙古2002~2015年的時間序列數據進行實證分析。數據選自《中國工業統計年鑒》、《內蒙古統計年鑒》。
產出Y,選取內蒙古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2002~2015年的工業總產值數據,并調整為2002年的不變價格;資本投入K,選取內蒙古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2002~2015年的固定資產凈值年平均余額數據,并調整為2002年的不變價格;勞動力投入L,選取內蒙古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2002~2015年年平均從業人員數量數據;Fmt由Fmt=θimSit計算得到,其中,θim來源于《中國投入產出表2012》中《直接消耗系數表》,取投入為煤炭采選產品與產出為電力、熱力生產和供應業的交叉欄中的數據,即θim=0.1818;Sit為煤礦生產企業跨區投資額占內蒙古煤炭業總投資額的比,分別選取內蒙古煤炭業2002~2015年的法人資本與實收資本的數據,并調整為2002年的不變價格。溢出效應指標的具體計算結果見表1。

表1 溢出效應指標的計算結果
2.2 結果分析
運用EViews8軟件對模型(1~7) 進行最小二乘(OLS) 回歸,回歸結果見表2。
表2的回歸結果度量了電熱力企業的資本投入,電熱力企業的勞動力投入,東部煤礦生產企業對電熱力企業的溢出效應三方面因素,對電熱力企業的工業總產值的影響。從表2的回歸結果看,可決系數R2為0.987,說明回歸方程總體的擬合度很好;F統計量為261.391,說明模型總體在0.0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D.W值為2.649,說明不存在序列相關。
變量資本投入K的回歸系數等于0.604,在0.0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表明電熱力企業的資本平均多投入1%,電熱力企業的工業總產值便增長0.604%。變量勞動力投入的L的回歸系數等于1.202,在0.0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表明電熱力企業的勞動力平均多投入1%,電熱力企業的工業總產值便增長1.202%。變量東部煤礦生產企業對電熱力企業的溢出效應F的回歸系數等于0.260,在0.05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表明溢出效應平均增強1%,電熱力企業的工業總產值便增長0.260%,說明東部煤礦生產企業轉入到內蒙古之后,對下游電熱力企業產生了明顯的正向溢出效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當地電熱力企業產值的增加,使當地電熱力企業的獲得更多的收益。

表2 模型(1~7) 的OLS回歸結果
溢出效應變量的回歸系數小于資本投入變量的回歸系數,且溢出效應變量的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水平也低于資本投入變量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水平。溢出效應變量的回歸系數小于勞動力投入變量的回歸系數,且溢出效應變量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水平也低于資本投入變量回歸系數的顯著性水平。說明煤礦生產企業對電熱力企業產生的溢出效應,雖然對電熱力企業總產值的增長有一定貢獻,但是仍沒有資本與勞動力投入對總產值增長的貢獻大。究其原因,東部煤礦生產企業轉入內蒙古之后,憑借先進的生產技術,生產出高質量的煤炭產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下游電熱力企業更新生產設備,使生產設備與高質量煤種的后序生產要求相匹配,從而提高燃煤效率,增加產值。然而,電熱力企業的機組更新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完成,因此當前時期的溢出效應對產值增加的間接作用,沒有資本和勞動力投入對產值增加的直接作用效果顯著。
3 結論與啟示
基于供應鏈視角,實證檢驗了東部煤礦生產企業轉入內蒙古之后對其下游本土電熱力企業的溢出效應,得出如下結論與啟示:
(1)東部煤礦生產企業轉移后,對下游東道地本土電熱力企業產生了正向溢出效應。東部煤礦生產企業轉入到內蒙古,生產出品質更好的煤炭產品,一方面,機組老舊的電熱力企業采購這些高質量的煤炭,需要按照這種煤質設計生產設備,重新整合機組,從而提高生產效率,增加企業產值;另一方面,擁有新型機組的電熱力企業采購這些高質量的煤炭直接投入到生產中,可以減少原本使用低質量煤炭時耗費的助燃油費用、設備維護費用,從而直接增加電熱力企業的經濟效益。
(2)增加東部煤礦生產企業跨區投資額,有利于增強東部煤礦生產企業對下游東道地本土電熱力企業的正向溢出效應。加大轉移投資,提升轉移企業的煤炭開采、洗選、加工技術,生產出更加優質的煤炭產品,進一步促使東道地本土的電熱力企業的技術進步,逐步推動東道地本土電熱力企業的產值增長,增強正向外溢效應。
(3)加快電熱力企業設備更新的速度,有利于促進東部煤礦生產企業對下游東道地本土電熱力企業正向溢出效應的有效發揮。電熱力企業按照煤質設計生產設備與機組,煤質提高,會促進設備更新,提高技術水平。設備更新項目的完成無法一蹴而就,但是通過督促項目進程,縮短項目完成時間,可以使正向溢出效應盡早發揮作用。
綜上,東部煤礦生產企業轉移后,對下游東道地本土企業產生正向溢出效應,提高下游本土企業的收益,使本土企業更加依賴東部煤礦生產企業生產的高質量煤炭,為東部煤礦生產企業創造源源不斷的產品需求,穩固兩方企業間的供需關系,促進煤炭供應鏈上下游企業間的協同發展。因此,中西部煤炭資源豐富地區的政府應出臺相應的招商政策,采取措施積極地引入東部煤礦生產企業,從而提高本土電熱力企業的經濟效益,實現當地煤炭供應鏈整體收益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