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和他的江湖論劍
明月

三千多年前,當古埃及為法老王拉美西斯二世慶賀九十歲壽辰的時候,因為從未見過如此長壽之人,所以他的臣民都相信這位號稱太陽神之子的老法老王真的會得以永生,所以一年后當法老王死去之時,整個埃及都沉浸在一片悲傷之中。時代遷轉,我們當然不相信永生的神話,但是,當真正得知金庸先生離我們而去時,難言的無盡悲傷久久難以忘懷,我們終于成為了那些遺落的埃及臣民。

就像許多偉大的事業,起源都只是一個巧合。1955年,時任《新晚報》副刊編輯的金庸,接到總編輯羅孚的邀約,讓他寫一篇武俠連載。你說一個副刊編輯,怎么就被要求去寫武俠呢?說來也巧,羅孚心中的第一人選并非金庸,而是他的同事陳文統,也就是剛剛因為寫過《龍虎斗京華》而火得一塌糊涂的梁羽生。只不過,當時的梁羽生因故無法答應,所以便推薦了和自己坐同一個辦公桌的查良鏞,《書劍恩仇錄》便應運而生,金庸這個名字也開始步入江湖。
后來我們也知道了,金庸武俠自此一發而不可收,席卷了整個華人社會,做到了有華人的地方便有金庸武俠。如今,金庸過世可謂是備極哀榮,我們這樣普通讀者的紀念文章可以刷爆朋友圈,微博上演藝界、財經界等各界人士都由衷哀悼。社會各界人士,此時此刻為了一個人,集結在一起。這一切看起來順理成章,理所當然。可是在生前,金庸所在的江湖決不能說是風平浪靜。
初出江湖,便遇見史詩級“大反派”
1959年12月8日,胡適在臺北世界新聞學校發表主題為《新聞記者的修養》演講,在演講上他說:“記者要多看偵探小說,我們中國文學的唯一的缺點,就是沒有翻譯的最好的偵探小說。現在有許多報紙都刊武俠小說,許多人也看武俠小說,其實武俠小說實在是最下流的。偵探小說是提倡科學精神的,沒有一篇偵探小說,不是用一種科學的方法去求證一件事實的真相的。”
時年三十五歲的金庸,年輕氣盛,并沒有因為對方是文學界的前輩,文化界的大佬,而不敢出劍。怒之所生,一往無前。


12月10日,他在《明報》發表社評《最下流之胡適之》,稱翻閱胡適從前文章,發現胡適一直以詆毀中國文化為己任,數十年來一如既往,胡適妄稱《水滸》是“誨盜之作,粗暴下流”,而京戲的內容無聊,毫無價值,中國人懶惰骯臟,不可救藥。進而諷刺胡適,既認中國人如此混賬,“胡適之博士胡適之乎……何以又適臺灣也?原來在胡博士眼中,臺灣非中國地也,乃美國地也。胡適之適臺灣,非履中土,乃處于我祖宗老爺美國之偉大土地也。于是美國人送我的朋友胡適之以博士銜,有骨氣之中國人卻稱之為‘最下流之胡適之焉!”
金庸這一段以筆為劍,憤然出鞘,頗似少室山激斗慕容復的段譽。滿腔的憤怒,化作劍氣層出不窮,雖無章法,一味胡攪蠻纏地猛打,卻仍是看得人十分痛快。
武俠小說,作為一種文學形式,仍是脫胎于中國舊小說的傳統。作為新文化運動的領導者,提倡新文學、新文體,在政治文化上傾向于歐美西化的胡適,說出“武俠小說實在是最下流的”,倒也是十分符合他的文化邏輯。只不過,后來據胡適學生唐德剛回憶,胡適是不看金庸小說的,倒是他的妻子江冬秀十分喜愛金庸小說,時常混放在胡適的書架上。
響徹江湖,卻有劍客從北來
1999年,王朔在中國青年報發表《我看金庸》,此文一出,一石激起千層浪。在文章中,王朔將金庸與四大天王、瓊瑤和成龍電影,一起并稱為“四大俗”:
這些年來,四大天王,成龍電影,瓊瑤電視劇和金庸小說,可說是四大俗。并不是我不俗,只是不是這么個俗法。我們有過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時期文學,搖滾,北京電影學院的幾代師生和北京電視藝術中心的十年。創作現在都萎縮了,在流行趣味上可說是全盤淪陷。這個問題出在哪兒,我不知道。也許在中國舊的、天真的、自我神話的東西就是比別的什么都有生命力。
語言之酸辣,打擊面之廣,便是那個嬉笑怒罵的王朔。不過,與胡適那一次不同,王朔顯然是有備而來,在文章中,王朔談及了自己閱讀金庸小說的體驗,并從寫作手法和文學理念上,對金庸武俠進行了批駁:


……我得說這金庸師傅做的飯以我的口味論都算是沒熟,而且選料不新鮮,什么什么都透著一股子擱壞了哈喇味兒。除了他,我沒見一個人敢這么跟自己對付的,上一本怎么,下一本還這么寫,想必是用了心,寫小說能犯的臭全犯到了。什么速度感,就是無一句不是現成的套話,三言兩語就開打,用密集的動作性場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說文字通通作廢,只起一個臨摹畫面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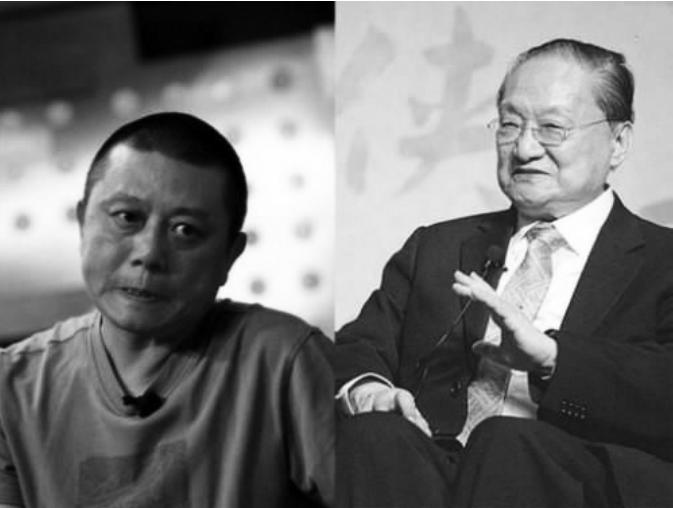
說起王朔,可能年紀較輕的讀者,只是聽聞其名,但并不怎么熟悉。但是王朔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卻是一位注定可以留下大名的作家。作為嚴肅作家中的一員,王朔卻以其辛辣的筆調,獨特的底層反精英視角,市場化的寫作,留下了諸如《頑主》《動物兇猛》《我是你爸爸》等一大批經典的文學作品。在1988年,王朔的四部作品在這一年被同時搬上銀幕,文學界、電影界、評論界不約而同地稱1988年為“王朔年”。
就是這樣一位市場化,以反知識分子立場聞名,偏向大眾文藝的作家,王朔也對金庸武俠亮劍。其實,從文學立場上來看,兩人頗有共同點,都是反高雅,都是反對傳統“文以載道”的知識分子精英立場,傾向大眾化、市場化。
不過寫這篇文章的動機,王朔說得很清楚,在他的認知中,自己雖然也“俗”,但是金庸的武俠小說實在是俗得過分。
此時的金庸已經是七十五歲的古稀老人,與上一次論戰不同。兩人地位已經反轉,金庸這一次是文學前輩,而王朔則是文壇正當紅的作家。這一次金庸的回復顯得理性而又克制,當然仍舊不掩筆下的鋒芒:
王朔先生一文以及由此引起的其他批評意見,予我教益甚多。我誠懇接受下列指教:情節巧合太多;有些內容過于離奇,不很合情理;有些描寫或發展落入套子;人物的對話不夠生活化,有些太過文言腔調;人物性格前后太過統一,缺乏變化或發展;對固有文化和舊的傳統有過多美化及留戀;現代化的人文精神頗嫌不足;有些情節與人物出于迎合讀者的動機,藝術性不夠。這些缺點,在我以后的作品中(如果有勇氣再寫的話)希望能夠避免,但如避得太多,小說就不好看了,如何做到雅俗共賞,是我終生向往之的目標,然而這需要極大的才能,恐非我菲材所及。這是今后要好好思索的事。這里誠意感謝各位批評者的幫助。

至于王先生說我的文字太老式,不夠新潮前衛,不夠洋化歐化,這一項我絕對不改,那是我所堅持的,是經過大量刻苦鍛煉而長期用功操練出來的風格。
而王朔所言的“四大俗”。
“四大俗”之稱,聞之深自慚愧。香港歌星四大天王、成龍先生、瓊瑤女士,我都認識,不意居然與之并列。不稱之為“四大寇”或“四大毒”,王朔先生已是筆下留情。
這一次,用金庸自己話說的“猛烈攻擊”,金庸先生頗有《笑傲江湖》中沖虛道長武當山腳下試陣令狐沖的那種風度,一圈圈耀目的刀光劍影之中,仍保持著沖和的氣度。就這樣用武當太極式的方式回應。這一次論劍,攻得辛辣,守得完美,堪稱是二十世紀末最有影響力的一次文人論戰了。
這次論戰,金庸先生一改對胡適的狂追猛打式的反擊,采用了正面回應。一則是,王朔所言雖然辛辣,但仍是有理有據,有自己的文學觀點,相較胡適一句不著頭腦的“下流文學”,總歸是本著討論的態度。仍是是文學討論,是以,金庸先生對批評有所揚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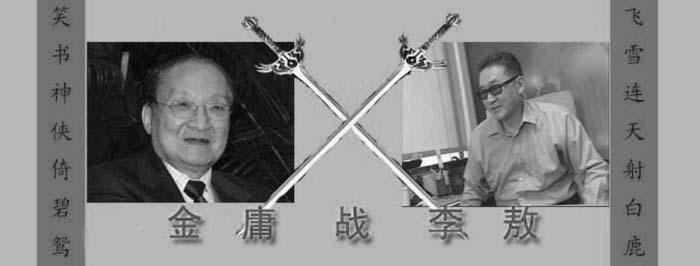
不虞之譽,求全之毀
說到金庸的論劍,還有一個小插曲。這不過這一次完全算不上論劍,這一次金庸先生的表現,倒不如說更像是靜靜看著對手磨刀。磨刀人不出所料,仍舊是一位鼎鼎大名的文化學者。這一次,金庸先生對手的名字是李敖。
1981年,李敖在《“三毛式偽善”和“金庸式偽善”》一文之中,表達了自己對于武俠小說和金庸人格上的一些看法。李敖式的文字和邏輯,讓金庸和金庸小說又一次站在了風口浪尖:
接著談到他寫的武俠,我說胡適之說武俠小說“下流”,我有同感。我是不看武俠的,以我所受的理智訓練、認知訓練、文學訓練、中學訓練,我是無法接受這種荒謬的內容的,雖然我知道你在這方面有著空前的大成績,并且發了財。金庸的風度極好,他對我的話,不以為忤。他很謙虛的解釋他的觀點。他特別提到他兒子死后,他精研佛學,他已是很虔誠的佛教徒了。我說:“佛經里講‘七法財、‘七圣財、‘七德財,雖然‘報恩經、‘未曾有因緣經、‘寶積經‘長阿含經、‘中阿含經等等所說的有點出入,但大體上,無不以舍棄財產為要件。所謂‘舍離一切,而無染著,所謂‘隨求給施,無所吝惜。你有這么多的財產在身邊,你說你是虔誠的佛教徒,你怎么解釋你的財產呢?”金庸聽了我的話,有點窘,他答復不出來。為什么?因為金庸所謂信佛,其實是一種“選擇法”,凡是對他有利的,他就信;對他不利的,他就佯裝不見,其性質,與善男信女并無不同,自私的成分大于一切,你絕不能認真。他是偽善的,這種偽善,自成一家,可叫做“金庸式偽善”。
李敖的這一次批評主要有兩個論點:1.武俠小說“下流”;2.金庸是人格偽善的佛教徒。關于武俠小說的論斷,李敖繼承了胡適的看法。兩人都是不看武俠小說,而且以自我經驗出發,認為武俠小說這種文體是“下流”的。關于人格偽善的說法,更是體現出了李敖文字中淵博的學識和獨特的角度,是李敖式一貫的辛辣文風。
金庸這一次,并沒有像二十年前那樣勃然大怒,也沒有像十年后那樣云淡風輕。這一次,他選擇了沉默。有人說,李敖罵金庸二十多年,金庸為什么一直不回應?我想這是很好理解的,自己一生所追求的事業和心血,被人無端指責,怒極之下,冷漠才是常態。私德的問題則更好理解了,一個人不必也不能在社會的放大鏡中,證明自己的品德。這是無益也是愚蠢的偽命題。所以,這一次論戰,金庸先生選擇了少林掃地僧的隱忍和豁達,只不過這一次的“掃地僧”在全書完結之時,也未能登場罷了。
在金庸先生離世的現在,縱觀大眾對于金庸小說乃至武俠小說的評價,我們發現一個很吊詭的問題。正統文學界和許多文化大佬、巨擘對金庸小說嗤之以鼻,相反,其他社會各個階層,上至政商精英,下至普通讀者,都對金庸武俠小說有極高的評價。為什么,文學界不接受金庸,不接受武俠呢?


金庸在《金庸作品集序》中,隱晦地提到了原因:
中國人的文藝觀,長期以來是“文以載道”,那和中世紀歐洲黑暗時代的文藝思想一致的,用“善與不善”的標準來衡量文藝……他們不相信文藝所表現的是感情,認為文字的唯一功能只是為政治或社會價值服務。

而金庸先生關于自己寫武俠小說的動機也說得很清楚:
我以小說作為賺錢與謀生的工具,談不上有什么崇高的社會目標,即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沒有懷抱興邦報國之志……不過我寫的興高采烈,頗有發揮想象、驅策群俠于筆底之樂。
因此,就可以解釋胡適和李敖所說的“下流”。在金庸那里,文學只是美與丑的范疇,而“下流”明顯是“善于不善”的道德標準了。
即便金庸提出“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這樣宏偉的教化主題,學術界對于金庸小說仍是保持著懷疑和旁觀的態度。或多,只是娛樂的消遣文學。所以,我們可以斷言,文學界駁斥金庸小說,倒不如說是駁斥整個武俠小說。只不過,金庸是武俠文學中的一座高山,自然而然,成為首要攻擊的目標。
不過,金庸先生通過自己的文字,征服了無數的讀者。這一點,讓傳統的文藝界不能裝聾作啞。胡適說“許多人在看”,王朔說“比別的什么都有生命力”,而桀驁如李敖,也會說“空前大的成績”。相較傳統文學的日益萎縮,甚至90年代就有純文學作家說“文學已死”,而武俠為代表的通俗文學,卻在網絡的大時代中愈發獲得生機。這種時代轉變,正是以金庸等為代表的作家苦心孤詣的成果。他用自己的才智和影響力,倒逼文學界承認武俠等通俗文學的正式地位。

在一次次的論爭中,金庸小說擺脫了一百年前“鴛蝴派”被絞殺的命運,帶領眾多通俗文學登上雅堂。北大出現了嚴家炎、陳平原、孔慶東等正面論述武俠小說的文學批評家,甚至也出現了金庸小說入選語文教材的盛況。
毫不夸張地說,正是金庸、古龍、梁羽生等武俠作家,將通俗文學這一派“魔教”重新又帶回了中原武林,獲得了各大“名門正派”的理解和接納。
如今,在通俗文學這一個門類中,武俠文學這門分支也開始沒落。面對網絡上此起彼伏的新興勢力,武俠文學實在顯得有些寒酸。金庸離世,我們還沒有爬上巨人的肩膀之時,巨人就已經倒下了,形勢越發嚴峻。但是,這些都是留給有志氣的武俠作者們要去面臨的困境。如今,不妨讓我們先花點時間,用先生自己寫的墓志銘來憑吊這位巨人。
這里躺著一個人,在20世紀、21世紀,他寫過幾十部武俠小說,這些小說為幾億人喜歡。
今古傳奇·武俠版2019年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