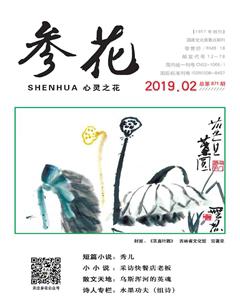故鄉的陰雨天
在北方住得久了,深受氣候干燥與污染的困擾;長期的過敏性鼻炎,讓我痛苦不堪。煩惱之中,不禁懷念起遠在江漢平原的故鄉的陰雨天來。
有朋友問:我們一直都不喜歡陰雨天,陰雨天會讓人感到迷茫,你為什么懷念故鄉的陰雨天咧?所謂境由心生,人見人殊。在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記憶中,故鄉的陰雨天不僅濕潤可人,她還是春季的甘霖時節,是夏日的休憩借口,是秋天的收獲享受,更是冬上的悠閑郊游時分。
戊戌初冬,到華中公干之余,順便回老家看看。車出喧鬧、灰蒙的江城,沿漢宜高速,經漢川駛往我的家鄉天門市。剛進平原水鄉地帶,天空中竟下起了蒙蒙細雨。望著路邊飛馳而過的黛色水鄉村莊,我下意識地搖下車窗,盡情地呼吸空氣中久違的清新氣息,一任飄進車內的小雨,沾濕我的額頭與臉龐。
一路的旅途勞累,一路的景致親切,一路的秋冬雨霧滋潤,讓我昏昏欲睡。慢慢地,我進入故鄉陰雨天半夢半醒的追憶之中……
春天的故鄉,不用說諺語中的“春雨貴如油”了,我感觸最深的,是昌黎先生的名句“天街小雨潤如酥”,一個“酥”字,寫活了故鄉春季陰天小雨的神情特色:她如甘霖一般悄無聲息地浸潤干涸的農田,讓土壤松軟如發糕,讓枯葉化為珍貴的肥料,喚醒冬眠的種子,滋養大地萬物。一如詩圣老杜的名句,“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這時的陰雨天,家鄉的人們或蜷縮在溫暖的被窩,美美地享受清晨的自然醒;或慵懶地來一個回籠覺,完全不用去理會什么雞鳴狗叫、什么“一年之計在于春”。春天的種子,早就播種好了。
我記得總喜歡操心的父親,那個時候往往會披上亮紙(塑料)外衣,戴上斗笠,穿上長筒套靴,點一根自家種、自家曬、自家卷的“土雪茄”旱煙,背起雙手,悠閑地踱到田間看一看,到地頭轉一轉。“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正是此時的真實寫照。
夏季的陰雨天,是勤勞的父老鄉親難得的閑暇與休憩日子。家鄉人多地少,再肥沃的“啞巴兒子”土地,也難以養活一天天增加的人口。面朝黃土背朝天的鄉人,一到酷熱的夏天,既要趕農時,又要趕一場又一場沒完沒了的運動,艱辛備至。這時,忽然一片烏云壓來,夾帶一陣沁人心脾的涼風,隨后就是滾滾的瓢潑大雨劈頭蓋臉地砸下來,農人們于是爭先恐后地往大樹底下跑,往生產隊的倉庫跑,往家里跑,總之哪個地方能躲就往哪個地方跑。
是蒼天的陰雨,讓善良的農人得到了暫時的解放;是自然的饋贈,讓鄉民難得地喘息與休憩。那個時候,大家在心中默默祈禱:下吧,下吧,好懂事的雨,下得越長越好。
江漢平原的秋天,農作物種類并不太多,大麥、小麥已經在夏天收割完畢。剩下的,只有棉花,少許的水稻、黃豆,還有已經葉枯藤干的紅苕。隨著天氣的逐漸轉涼,些許的陰雨會加快農人們收割晚稻的步伐,也會催促人們采摘棉花、收割黃豆的節奏。地里的紅苕,似乎并不擔心秋雨的浸濕,反而會偷偷地躲在土里長個兒。經了秋霜的紅苕,生吃起來會更加清甜、香脆,真正地津津有味。當然也有個別的苕,經了秋霜,還是會腐爛。農人們每當挖到這種倒霉的破爛玩藝兒,會用鄉語罵一句:“真是他姆媽的一個‘苕!”
間斷的秋季陰雨天里,農人們會一天到晚待在家里,掰一筐又一筐趁晴天從地里搶摘回來的棉花桃,三三兩兩地開著不著邊際的葷話玩笑;還會在傍晚時分,用劈柴生上一個燉缽爐子,將白菜、蘿卜和少許臘肉一股腦兒地放進一個土火鍋里,一家人或是叫上幫忙掰棉花桃的鄰居、親友,一起圍坐,抿幾口小酒,大筷子地夾起飄香的簡樸菜肴,開開心心地享受這秋天的陰雨時節。
好一幅“圍爐夜話”的場景啊,秋天的陰雨,帶給農人的是年景將成的釋然,好不好就這樣了;帶給鄉民們的是身體的調整,勞累了大半年了,也該稍微歇歇了。
故鄉的陰雨天,在冬天則是走家串戶的小聚與娛樂契機。我至今記得一到冬天,身為剃頭匠的遠房辛未大伯,往往用衣兜懷揣一個火烙子,踩著一雙今天已不多見的木屐子,踏著咯吱咯吱的冰凍泥地,扯著嗓子到家門口對我父親喊一聲:“水牛,你來不來剃頭的吶?”是的,到了冬季的陰雨天,農人們才有足夠的時間拾掇一下自己,理個發,刮個臉。我還記得在這個時節,同族的千金婆招呼姐妹們打牌的爽朗笑聲,更忘不了她一笑起來就露出的幾顆大金牙。
打牌,是一種延續了幾百年的民間娛樂。我記得故鄉的牌,有用桐油糊面的紙質“幺字牌”,麻將那時好像并不多,是后來才多起來的。這種“幺字牌”與麻將的“條、餅、萬”中的一二三……到九的數字設置,似乎完全一樣。在那個物質匱乏的年代,聰慧的鄉人置不起整副的麻將,于是用這種“幺字牌”替代。也許還有那個年代嚴格禁賭的原因?麻將目標太大,聲音太響,不好應對治保主任等“鬼打架們”的突襲。鄉民們對有限娛樂生活的管制十分無奈,也有幾分機敏。
冬天的陰雨天是冷凊的,但鄉人們猶能苦中作樂;冬天的陰雨是綿長的,但春天已經不遠。
晃蕩之中,車身一震,停了下來,友人告訴我:“天門到了。”我一下完全醒了過來,索性打開車門,不顧友人喊我帶上雨傘的提醒,一頭扎進家鄉初冬的綿綿陰雨之中……
作者簡介:曾冰之,原名曾令濤,清華大學博士后,某國家智庫研究員。有多種學術論文、散文及專著發表、出版。本文由“鴻漸風”微信公眾號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