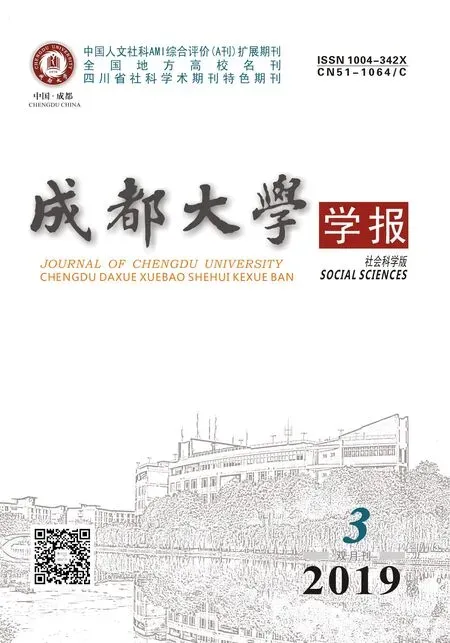對日本思想范疇界定的思考*
——以《講座 日本思想》為例
宋媛媛
(廣東省外語藝術職業學院 廣東 廣州 510640)
一、前言
我國的日本思想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19世紀50年代后期,經過一百多年的發展,中國學者對日本思想的研究已在各個層面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縱觀現有的日本思想研究成果,有關日本思想史、日本思想流派以及日本思想家的思想著作方面的研究較多,學者們對日本思想的研究仍然以意識形態的研究為主。然而,思想并不僅僅是意識形態上的思想,它還應包括人們對時間、空間以及日常生活等各個領域的看法、想法和記憶。
到底何謂思想呢?《現代漢語大詞典》將思想定義為:(1)想念,懷念。(2)思維的條理脈絡。(3)念頭,想法。(4)思想意識。(5)客觀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識中經過思維活動而產生的結果或形成的觀點。《辭海》則將思想解釋為:(1)思維活動的結果,屬于理性認識,一般也稱“觀念"。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一切根據和符合于客觀事實的思想是正確的思想,它對客觀事物的發展起促進作用;反之則是錯誤的思想,它對客觀事物的發展起阻礙作用。(2)想法、念頭。(3)進行思維活動。
《現代漢語大詞典》和《辭海》都側重于從意識形態上去界定思想,強調思維的條理性和思想的客觀、理性,仿佛非理性的認識就不是思想了。“關于思想的定義,《現代漢語大詞典》和《辭海》的諸種解釋,總體而言,偏重于思想的外延解釋,而對于其內涵,尤其作為支撐起思想家存在的思想內涵的解釋,則未免顯得單薄”[1]。如若我們只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去研究思想, 則容易將思想拘囿于哲學的范疇中。事實上,“在日本,‘哲學’包括的范圍被限定得很窄,而它所包括不了的廣闊領域就用‘思想’一詞了”[2]。
《漢英大詞典》中,“思想”一詞被譯為“thought”(思想、想法)、“thinking”(思考、見解)、“idea”(主意、觀念)、“ideology”(思想意識、意識形態)、“anamnesis”(尤指對前世生活的記憶,思想)等等。
《日本大百科全書》則從廣義上將“思想”定義為,因思考而在精神中所產生的一切現象,并將它由高到低劃分為以下四個階段:(1)具有明確體系的理論、學說。(2)人們的世界觀、人生觀。(3)人們對日常生活的處事態度、看法、想法。(4)人們理性地反思以前的生活和行為模式等。
在此,思想不僅僅被定義為具有明確體系的理論學說,人們對人生、社會以及日常生活的處事態度、看法和想法,以及對前世生活的記憶、回憶等也包含其中。在日本學界,之所以不單單從理性意識或是理論學說的角度定義思想,有其特殊的歷史緣由。早在1900年(明治33年),著名的思想家中江兆民(1847—1901年)曾斷言“ 我們日本自古至今無哲學”[3]31。雖然中江兆民先生提出此觀點有其歷史背景,但影響深遠。至今日本學界仍普遍認為日本在近代(明治維新)以前并沒有哲學,只有思想。因此,“在日本,討論傳統思想時,通常不用‘哲學’一語,而是使用‘思想’”[4]。
可見在日本,思想的歷史早于哲學,范疇也廣于哲學。研究日本思想,就不能將其限定于某種特定的思想領域,而應更大范圍地去解讀和理解隱藏于普通民眾中的思想,彈性地擴充思想這一概念。日本著名的歷史學家安丸良夫(1934—2016)歷來重視研究民眾思想史的重要性。他認為,“只有民眾才是歷史發展的主體”[5]。日本著名歷史學家鹿野政直(1931—)也呼吁日本思想界應注意對民眾思想的研究。他認為,“思想史的認識對象不僅應是有序形態的秩序意識(即思想家的思想),還應擴大到無序形態的日常生活意識,還應以行動為對象。”[6]也就是說意識形態(思想家的思想)與生活意識(民眾的精神實態)是不一樣的,研究思想,不僅要研究意識形態上的思想,還應將研究的視野擴大至日本普通民眾,去觀察他們在日常生活中所呈現出的原始想法、一般知識和信仰。
本文試以日本著名歷史學者相良亨、尾藤正英和秋山虔所編寫的《講座 日本思想》一書為中軸,概述對日本思想范疇界定的思考,嘗試以一種新的視角詮釋“日本思想”這一概念。
二、《講座 日本思想》成書背景
1983年10月至1984年3月,東京大學出版會陸續出版了由相良亨、尾藤正英和秋山虔編寫的系列叢書——《講座 日本思想》。該書不但編入了三位編寫者的文章,還匯集了安丸良夫、子安宣邦、宮田登等來自一橋大學、大阪大學、筑波大學等大學知名學者的著作。《講座 日本思想》出版后,受到了學界的關注。1986年4月該書進行了第8次印刷。
20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發展,一躍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經濟大國,在國際上嶄露頭角,凸顯出一定的經濟影響力。日本政府開始思考日本作為一個世界經濟大國所應發揮的作用。然而日本在經濟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卻沒能讓日本國民產生強烈的國家歸屬感。日本國民對自我身份的認識也極其模糊。日本社會學者,原京都大學教授大澤真幸在《戰后日本的思想空間》中曾寫道:“自己當然能說日語,擁有日本國籍,也蒙受這個國家法律和安全的恩惠,但這些都是非常偶然的事情——對于自己自身的身份認識而言是怎樣都可以的事情——就是這樣一種感覺占主流的時代。1970年代、19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也是如此”[7]8。日本人在七、八十年代對自我身份的認同感低,或許與其因戰敗的壓抑所產生的自我否定的情緒有一定的關系。此外,當時日本經濟和政治發展的不對等關系也是導致日本國民對自我認同感低的原因之一。首相中曾根康弘在1985年發表的著名演講似乎也印證了這一點。他在1985年7月27日發表了“重新認識和確立日本的主體性”,提倡進行“戰后政治總決算”的講演[8]390。其演講的目的不僅是期望改變當時日本在政治和經濟發展上的不平衡問題,也是為了讓國民盡快走出戰敗的心理陰影。為更好地確立日本國的主體性,他提倡創立一種反映日本主體性的“日本學”[8]390,引導國民重新審視日本原有的獨特的文化,增強國民對國家以及自身身份的認同感。“在日本的思想脈絡中,八十年代末期后是日本人開始認識到作為日本人在世界中具有重要意義的一個時期”[7]8。
在政治上追求身份轉變的日本,在思想研究上自然而然地表現出追求一切能反映日本主體性的思想。因此,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講座 日本思想》的出版,可謂正合時宜。正如本書的編者在刊行詞中所說:“本講座集中展示當時學界所取得的日本思想研究成果,目的是以客觀的態度審視日本思想并將其扎根于日本土壤之中”[9]。
《講座 日本思想》由自然、知性、秩序、時間、美五卷組成,該書打破了以往學者將思想按流派、階層或是按時代來劃分的常規手法,而是以自然、知性、秩序、時間、美這五大主題將思想分門別類,考察隱藏于各種思想底層中日本人特有的思考方式和感知方法,以此來凸顯日本思想的獨特性。
三、日本思想的范疇
《講座 日本思想》中所選的思想素材和思想對象,既包含有思想家著作中的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元素,又涵蓋了普通民眾樸素的思想觀念。編者通過“自然”“知性”“秩序”“時間”“美”這五大主題巧妙地把這些內容目別匯分,借以達到從整體上捕捉日本思想的基本特質的目的。
(一)自然
在自然主題一卷中,“自然”一詞被特別注音為“おのずから”,而非人們常讀的“しぜん”,旨在強調自然即“自然而然”、“自動地、天然地”,是客觀的存在。正因為它客觀存在,所以一切福禍皆為自然。這不僅顯示出日本人樸素的自然觀,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日本人心中深藏著人與自然共生,并將所有的現實(幸福的或是不幸的)都視為自然的肯定態度。
日本人對自然的感知與理解樸素且細膩。在該卷古代人的心情一節中,作者提到“古代律令制時代,施行死刑的季節被定于非樹木繁茂期”,“除了謀反、謀大逆、叛變、弒主等罪外,立春至秋分之間不施行死刑”[10]4的內容。這與中國古代的“秋后問斬”同理。春夏為萬物生長繁茂之時,秋冬為樹木枯萎凋謝之期,人的生命也如同大自然中草木一般,傷其身但不能傷其魂。“日本古代雖無中國一般有陰陽二氣推動自然發展的理論認識,但同樣具有的游離魂思想,以及將人作為自然的一部分,視人的生命過程如同植物的生命循環等,這些足以表明中國的(秋令)行刑思想完全被日本接受。枯死后回歸泥土,時光輪回時生命得以復蘇,若以此想法為前提,季節便成為結束生命的關鍵。這樣的想法不僅根植于日本古代人心中,也同樣深藏于現代日本人的精神深處。”[11]6這種樸素的自然觀里雖然滲透著佛教的思想,卻又不同于中國傳統的自然觀,更有別于西方對自然的理解。
西方的“自然”多強調人與自然的分離,日本人則重視人與自然的融合。這種以自然為中心,與自然融合的思想反映在日本建筑、藝術、文學及人們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如日本的庭院以展現原生的、無人工雕琢的自然景觀為美;日本的花道以呈現花木原有的姿態為美;日本的和歌和俳句多詠唱大自然的美麗景色,每首俳句必定嵌入適時的季語等,這些無不傳達著日本人重視“自然而然”,珍惜人與自然的和諧之美。日本民眾的生活智慧也正好說明日本人骨子里所信奉的尊重自身與自然的和諧,肯定一切“自然之物”的思想。
(二)知性
《日漢雙解大辭典》中,將“知性”定義為“知性,即理智,智慧。思考、理解、判斷事物的能力,人的智能;也指將通過感覺得到的素材加以整理,統一后形成新知識的心理能力”。《日漢大辭典》中“知性”被定義為“智力。思考能力。分析與判斷事物的能力;(哲學)理智。從事知識性活動的性質和能力。”簡而言之,知性不是知識,知性是指對知識進行分析、判斷、整理和運用的能力。
若論日本人知性活動的歷史,學界通常會提及日本接受佛教、儒學或是洋學等外來文化和知識的過程。歷史表明,日本人很好地運用了這些外來知識,并結合本土文化創造出自身獨特的文明。一方面它展現出日本人卓越的知識理解和運用能力,另一方面也表露出日本缺乏獨創性的、理論性的哲學思想。
對外來文化的認知和運用,反映出日本人就事而論式的、經驗主義般的知性特點。“較之抽象性、概念性的思考,日本人將重心更多地放在具體的、實踐性的思考上,這樣的思考模式在日本人知性活動中占了主流。”[12]如“近世儒學中的朱子學到伊藤仁齋、荻生徂徠的古學的發展動向中,均充分展現出(他們)摒棄原理性的內容,追求與道德、政治有關的實踐性智慧的志向”[12]。又如幕府末期日本文人志士在接受西洋學問時,多注重西洋學問之“術”,而非“理”。足見日本人在吸收外來文化時,所展現出的知性特點。
正如尾藤正英所說,“日本人并非僅僅停留于簡單地掌握這些外來文化,而是在接受外來文化初始,就選擇性地或是改變性地接受外來文化,并長期地在各種各樣獨創性的思考基礎上推動外來文化‘日本化’,成功地使外來文化適用于日本傳統的社會組織和精神土壤之中,這就是日本接受外來文化歷史中的顯著特色。這種接受方式,可以說表現出日本人極高的認知能力。”[13]由此亦可窺見出日本人凡事尋求融合的思想。
(三)秩序
“秩序是普遍的現象,在自然界中有秩序,人類社會也有秩序。由于社會是由人組成,是由人們的行為推動發展的,因此,社會秩序又可以看成是在社會進程運轉中人們的行為在某種程度的一致性、連續性和確定性。”[14]
秩序包括自然界的秩序和人類社會的秩序。人類社會秩序很大程度上受到人們長期以來的習俗和風俗影響。對于日本而言,沉淀于其社會構造之中的習俗、風俗以及宗教信仰等曾對日本的社會秩序構成起著關鍵作用。眾所周知,在日本權力社會構造中,天皇曾處于權力的頂峰。雖然如今的天皇已被視為一種象征,并無實際的政治權力,但天皇本身所具有的宗教般的傳統權威在民間的影響力卻不容忽略。天皇“處于義禮秩序中的中心位置,當然這種義禮秩序不僅是出于某種政治意圖而形成的,它背后的宗教性背景也是不可忽視的”[15]。
“日本人默認(天皇)具有某種權威并讓其存續至今,恐怕也是源自日本群體底層的某種內在的訴求。”[16]民間對于天皇傳統權威的推崇,也反映出日本社會長期以來形成的宗教信仰和習俗對于社會秩序的某種訴求。
隨著社會生活的進步,人們逐漸意識到單靠宗教信仰和習俗已無法有效維持和發展人類社會的秩序,人類社會的秩序還需靠外在秩序的“法”和內在秩序的“道德”來約束。
在此卷中,天皇象征著神界,法意識象征著外部秩序,道理觀象征著內部秩序。揭示日本人以怎樣的姿態去接受日本的社會秩序,顯現出日本民眾特殊的思想特質。
(四)時間
“從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角度講,時間是物質運動的一種存在方式,它表現了物質運動的持續性。……但是,在民俗學、文化學的角度上講,時間又是具體的、多樣的。每個人在不同的情景下對時間的感覺不同,每個民族對時間的感覺也不盡相同”[17]。對于日本人而言,時間意味著無始無終,永恒反復。宮田登在《歷書思想》中曾說:“新年與去年一樣,時間是反復的。生活的形式、四季的變化、農作物的收割以及豐收祭祀,都周期性地回到了原初。”[18]5時間永恒反復,每年從初春至寒冬,仿佛沒有變化一般。因此,年初由天皇唱誦的祝詞便成為了喚醒百姓對于時間的最初意識的關鍵。
此卷開篇以探討祝詞、天皇、時間之間的關系為切入口,既承接上卷解釋了天皇在民間具有宗教般的傳統權威的原因,又強調了時間對于個人和國家社會形成的重要性。“時間對于個人而言,是生與死之場,對于社會和國家而言,時間是歷史形成之場。”[19]
透過時間,不僅可以窺視出日本人對于歷史以及個體生死觀的態度,對我們研究時間與宗教、信仰、思想、歷史之間的諸多關聯也有著重大的意義。“考察日本思想的時候,發現時間意識所具有的重要性中存在更大的意義。其一,圍繞國家歷史的思考被視為是形成日本思想的基磐;其二,特別是近世以后,個人生死觀中多與國家的歷史有著密切的聯系。”[20]正如作者所言,日本人“對歷史、時間的意識,在更深之處,支撐著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思想”[19]。
(五)美
美與日本人的生存方式有著密切關聯。日本的文學、藝術、建筑、乃至人們日常的生活中無不滲透著美的意識。日本人對于美的意識也凸顯出日本人特有的文化與精神性格。到底何為美呢?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對美的性質作了著名的論斷。他認為“美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21]78,也就是說人的本質決定了美的性質。某種程度上來看,人與物的美與不美也視人類所付諸于它的情感而定。如自然的一草一木只是客觀的存在,因人類的情感投射于它,一草一木便有了美。同樣,人的情感也因所處的自然環境不同而迥異。日本人之所以如此強調誠、雅、幽玄、粹等美學境界,也源自于日本所處的四面環海的島國環境。狹長的地理自然環境造就了日本人對萬事萬物擁有著不同尋常的細膩情感。在時間的沉淀中,日本人對美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思考,這些思考和理解形成了日本人對美的意識。“美的思考即所謂美意識,是指人們的審美心理、審美情感以及判斷美的基準和思考。”[22]日本人逐步將自己對美的感受和意識提煉成“誠”“雅”“幽玄”“物哀”“粹”“空寂”“閑寂”“余情”“無常”“虛實”“枯淡”“素樸”等術語。這些術語被廣泛地運用于文學作品、藝術作品、建筑設計以及百姓的日常生活形態中,可謂直觸日本美學的核心。
此卷不僅闡述了“雅”“幽玄”“風雅之誠”“粹”等象征美意識的詞的時代背景和精神內涵,也梳理了美在日本不同歷史時期的表現形態。日本人不僅在藝術上追求誠、雅致與空寂,在生活中也追求簡單、素樸、真實。這樣的美意識至今影響著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生存方式。
四、結語
“自然”“知性”“秩序”“時間”“美”這五大主題看似與思想無關,實則集中反映了日本人獨特的世界觀、人生觀,以及日本人對日常生活的原始想法和一般認知。自然、知性、秩序、時間、美既是思想的內涵,也是文化記憶的重要元素。在此書中,自然意味著原生、無常、和諧,知性代表著認知、即物、改變,秩序意味著主從、義理、規范,時間代表著歷史、信仰、生死,美意味著誠、雅致、幽玄。
“自然”“知性”“秩序”“時間”“美”這五個主題也并非毫無關系,而是彼此關聯,互為支撐。如自然中提到人們對原始的、古樸式時間的感知,知性中提及日本人獨特的自然觀和美意識對于其知性活動的影響,秩序中談到天皇在日本國民心中的權威與宗教影響,時間中論及天皇在日本國民對四季時節產生意識的過程中所起到的影響,美中又論述自然環境、時間與日本傳統美意識形成之間的密切聯系。由此可見編者將“自然”“知性”“秩序”“時間”“美”列為思想范疇的良苦用心。
該書無意將思想拘泥于某種特定的思想領域,而是通過豐富思想的內涵來擴大對隱藏于普通民眾中思想的解讀。其目的仍然是想通過廣泛且深入地挖掘日本思想的源頭,來確立日本思想的獨立性,以此來抵抗西方思想的沖擊,增強國民對國家以及自我身份的認同感。可以說,這樣的研究視野不僅拓寬了我們對思想界定的范疇,也為我們研究日本思想提供了新的探索空間和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