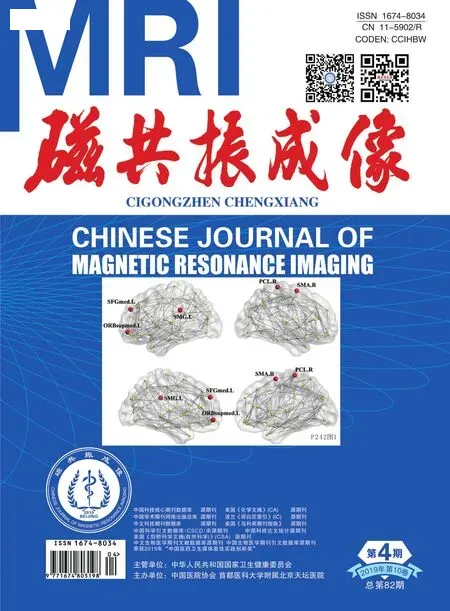Gd-EOB-DTPA MRI在監測肝硬化結節多步態癌變早期中的應用進展
額·圖婭,歐陽漢
肝細胞肝癌(hepatocellular carcinoma,HCC)是肝臟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中國則提供全球每年一半以上的新發病例[1]。由慢性乙型和(或)丙型肝炎等高危因素所致的硬化肝中,由再生結節(regenerative nodule,RN)發展為低級退變結節(low grade dysplastic nodule, LGDN),再演變為高級退變結節(high grade dysplastic nodule,HGDN),而后癌變為早期肝癌(earl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E-HCC)乃至進展期肝癌,這連續過程符合約80% HCC的多步態演變。DN (尤其是HGDN)及E-HCC是這一過程的關鍵步驟,也是臨床早診早治的重要環節[2]。長久以來,二者的精準診斷及鑒別診斷無論是在影像方面還是病理方面都是研究熱點及難點之一。基于大多數DN及E-HCC的血供變化尚不足以使其在常規細胞外對比劑的影像方法上表現具有特征性,因此利用常規影像方法對二者的檢出及診斷并不理想[3]。近年來,釓塞酸二鈉(gadolinium ethoxybenzyl diethylene triamine pentaacetic acid,Gd-EOB-DTPA)因其能額外提供肝細胞功能方面的信息,并與MRI其他序列聯合應用獲得更多有效信息,在DN及E-HCC的檢出及預測轉歸方面體現出重要價值,進而有利于提高患者預后及生存率。
1 Gd-EOB-DTPA的應用原理
Gd-EOB-DTPA是一種磁共振肝臟雙相對比劑,靜脈注射后經過肝血竇毛細血管分布于細胞外間隙,從而提供血流動力學信息;肝細胞通過其血竇面細胞膜上的有機陰離子轉運多肽1B3(organic anion transporting polypeptide,OATP1B3)將其攝取,而后經位于膽管面的多重耐藥相關蛋白2(multidrug resistant protein,MRP2)將比例高達50%的對比劑排泄到膽管內,剩余50%則經腎臟排泄,以此提供肝細胞功能方面的信息。這種雙重清除途徑在肝或腎功能受損時可以相互代償,因而具有更高的安全性[4]。Gd-EOB-DTPA因其獨特優勢,對于小病灶的診斷效能優于多排增強CT及其他MRI對比劑[5-6]。對于E-HCC或小肝癌(small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S-HCC)甚至是DN亦具有較高的發現率與確診率。如Kim等[7]研究顯示,Gd-EOBDTPA MRI較多排增強CT能夠顯著提高對E-HCC及HGDN的檢出率;Renzulli等[8]報道Gd-EOB-DTPA MRI聯合擴散加權成像(diffusion weighted imaging,DWI)可有效鑒別HGDN及E-HCC。
2 Gd-EOB-DTPA對肝硬化相關結節診斷的應用評價
對于DN (最主要是HGDN)及E-HCC的病理診斷標準,現已達成一定的國際共識[9-10]。DN常發生于硬化肝中,直徑通常在1~1.5 cm,邊界多清晰,無纖維包膜。根據鏡下細胞及組織結構異型性分為LGDN及HGDN。LGDN常表現為以大細胞改變為主的結節,幾乎無其他明顯異常;HGDN則以小細胞改變為主,細胞異型性增加,細胞密度增加,呈膨脹性生長,伴有不規則的細小梁狀結構,假腺管結構形成,伴有脂肪變性,間質內有孤立性動脈,肝血竇出現毛細血管化。后者因其具有極高的惡性轉化潛能被列為癌前病變,且會以“結節內結節”形式出現局灶癌變。在病理上,E-HCC是基于其生物學行為定義的,即癌組織缺乏纖維組織包裹,邊界模糊,通常呈高分化狀態,幾乎無微血管浸潤,稱為早期S-HCC或模糊結節型HCC。S-HCC則強調腫瘤體積,通常認為S-HCC為<2 cm的病灶。需說明的是,并非所有的S-HCC均為E-HCC,部分S-HCC分化程度減低,有纖維包膜包裹而邊界清晰,可伴有門靜脈浸潤及肝內微小轉移灶,故而被稱為進展期S-HCC或明確結節型S-HCC。上述HGDN的病理特征亦可表現于E-HCC,致使二者鑒別診斷頗為困難,二者鑒別要點在于是否出現間質浸潤,即腫瘤細胞侵犯匯管區、纖維間隔等結構[9-13]。
肝硬化相關結節在多步態演變過程中,在細胞內部物質成分、功能及血供方面都會發生一系列的復雜變化,其中一些變化可由MRI的不同序列予以識別,用于結節的鑒別診斷及其轉歸評價。
2.1 癌變過程中肝硬化相關結節物質成分的變化及其影像表現
DN及E-HCC在常規MRI上信號多變,這可能與MR場強、參數設置、序列選擇、圖像質量等有關。
典型無鐵質沉積的DN多呈T1WI高信號而E-HCC則多為等信號,多數學者認為高信號可能為銅或脂肪沉積所致。在非脂肪肝中,部分DN (尤其是HGDN)細胞內常含有豐富的脂肪,利用T1WI雙回波技術可提高檢出率。E-HCC相較于DN來說,脂肪變性更多見,且會隨著腫瘤體積增大而逐漸減少。有學者將其歸因于血供不足導致缺血缺氧,而在進一步去分化過程中,隨著血流進一步豐富而消失。LGDN多呈T2WI等信號,HGDN多表現為稍高信號,而E-HCC多為高信號[3-4,12,14]。
若病灶含鐵質沉積時,含鐵物質常導致局部磁場不均勻產生質子失相位,最終使得結節表現為T2WI低信號,尤其是T2*WI能更好地反映鐵的沉積。當含鐵結節在T2WI上信號升高時需警惕HCC的可能,因硬化結節癌變過程中會逐漸失鐵。應用較T2*WI更敏感的磁敏感加權成像(susceptibility weighted imaging,SWI)來檢測肝硬化結節內鐵含量變化從而鑒別癌前結節及HCC成為近年來的研究熱點之一[15-16],但SWI亦受到如脂肪肝背景等多種因素影響而干擾診斷。若將其與Gd-EOB-DTPA聯合應用與此領域,互相彌補不足并獲得更多診斷信息將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
肝硬化結節惡變過程中,細胞密度會逐漸增加,得以通過DWI而檢測。諸多研究報道聯合DWI與Gd-EOB-DTPA MRI在鑒別肝硬化結節中具有重要意義。Inchingolo等[17]報道聯合DWI高信號及肝膽期(hepatobiliary phase,HBP)低信號特征,其敏感性、特異性及準確性在HCCs組與DNs組、HCCs+HGDNs組與LGDNs組分別為100%、57.1%、84.21%和96.77%、100%、97.37%。Renzulli等[8]研究亦表明大部分HGDN及E-HCC呈HBP低信號,可根據DWI是否為高信號鑒別二者。Hwang等[18]報道表觀擴散系數(apparent diffusion coefficient,ADC)值在乏血供HCC與DN之間無明顯差異,但可通過高b值DWI進行鑒別。Zhu等[19]應用體素內不相干運動成像(intravoxel incoherent motion DWI,IVIM-DWI)研究發現D值(diffusion coefficient,D)及ADC值對高分化HCC有更高的診斷效能。Gd-EOB-DTPA MRI聯合IVIM-DWI在有效評價癌變結節的功能和代謝水平方面具有較高的臨床價值,但國內外對此相關臨床研究報道還較少。這可能是由DWI及其衍生技術本身的局限性所致,如DWI易受運動偽影干擾或部分容積效應明顯,目前各機構DWI掃描技術的多樣性,勾畫ADC方式的不統一及DWI衍生的定量參數界值的不確定性等。
2.2 癌變過程中肝硬化相關結節血流變化及其影像表現
在DN逐步去分化發展為HCC的過程中,血管形成途徑被激活,誘導腫瘤新生血管形式,即無膽管或門脈伴行的獨立小動脈,稱為非配對或非成組小動脈,同時也會逐步出現肝竇毛細血管化[9]。
在至少3期的多期Gd-EOB-DTPA MRI上,LGDN強化特征常同周圍正常肝實質相仿,這是因其血流絕大部分仍由門靜脈供應所致。雖然HGDN及E-HCC新生腫瘤血管都在逐步增加,但形成尚不完全,肝竇毛細血管化稀少。在大多數情況下,二者動脈期與周圍肝實質相比常呈等/低強化,亦稱為動脈期乏血供強化模式[2-3]。諸多研究結果亦證實這點,88.2%~96.7%的HGDN和71.4%~86.6%的E-HCC呈乏血供強化模式[7,20]。可見,仍有少部分HGDN及E-HCC會表現為動脈期強化,這種不同的動脈期強化模式,亦說明二者的血供變化呈動態演變,且常有重疊,僅憑借常規動脈期難以互相鑒別。
Channual等[21]研究結果顯示,通過比較不同增強時相結節與周圍肝組織的信號強度比值,可獲取LGDN、HGDN與HCC的相關定量信息并進行鑒別診斷,但仍是易于鑒別LGDN與HGDN+HCC,而不同分化HCC組內仍有較多重疊。覃夏麗等[22]研究顯示,應用Gd-EOB-DTPA增強T1 mapping鑒別DN及不同分化程度的HCC,DN的T1值及T1增加率均低于不同分化HCC。由于腫瘤新生血管結構紊亂扭曲,基底膜欠連續,導致滲透性增加,Gd-EOB-DTPA在病灶中的分布及代謝不同于正常組織。基于此病理基礎,Gd-EOBDTPA經過后處理可獲得一系列藥代動力學參數(Ktrans、Vp、Kep),以此來反映病灶微血管密度(microvessel density,MVD)的狀態。Kitao等[23]報道Ktrans與Ki-67增生及HCC分級顯著相關,Vp和Kep與腫瘤微血管浸潤有關。IVIM亦可通過灌注參數D*及f值來反映肝臟局灶性病變的血流灌注信息[24]。
上述基于Gd-EOB-DTPA自身或聯合IVIM-DWI多模態定量參數,可通過反映病灶內部血液動力學改變來檢測結節是否癌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潛在的腫瘤細胞特征,為評估肝硬化相關結節早期惡變及預后提供了可能性。Gd-EOB-DTPA劑量較低、濃度稍低,且硬化結節癌變早期血供并不豐富等原因可能致使此項技術在肝癌早期病變中應用較少,但因其為非創技術并提供豐富的診斷信息在此領域仍具有發展潛力和應用前景,有待于進一步挖掘。需注意的是,Gd-EOB-DTPA更易出現呼吸偽影,從而影響動脈晚期圖像,對于診斷亦造成一定困難。應用動脈多期增強技術以弱化這種偽影,且基于此項新技術更易最大程度地區分并捕捉到個體化的最佳動脈晚期以便于肝硬化相關結節的診斷及鑒別診斷[25]。
2.3 癌變過程中肝硬化相關結節細胞功能變化及其影像表現
2.3.1 乏血供肝膽期低信號的肝硬化相關結節及隨訪
肝細胞膜OATP1B3表達量會隨著肝硬化結節演變而逐漸減少乃至缺失,MRP2表達量維持正常或增加,從而導致70%~82.4%的HGDN及76.2%~86%的E-HCC表現為HBP低信號。同時,二者多數情況下在Gd-EOB-DTPA MRI上呈乏血供強化模式,從而被稱為乏血供肝膽期低信號結節(hypovascular hypointense nodule,HHN)[7,26]。需補充的是,并非所有HHN都為HGDN及E-HCC,部分不典型HCC亦可表現為此征象。諸多研究將此種征象歸因于結節OATP1B3表達量下調表現早于血流改變。隨著時間的推進,部分HHN會轉化為富血供HCC,因而具有高風險性。一項薈萃分析報道HHN混合總體轉化率為28.2%,1年、2年、3年混合累積發生率為18.3%、25.2%、30.3%[27]。不少研究報道以下信息與HHN進展為富血供HCC有關:(1)初始大小直徑≥9 mm[27];(2)T1WI呈高信號或體積倍增時間短[28-29];(3) T2WI呈高信號或DWI呈高信號[30-31];(4)包含脂質成分[30];(5)伴有HCC治療史[31]。Chou等[32]也報道,在隨訪過程中若結節T1WI信號較前減低、T2WI信號較前增高,并檢測到動脈期強化,這些可能作為結節惡性轉變的征象。除此之外,Toyoda等[33]及Lee等[34]研究表明,在肝癌行手術切除及消融治療之前并存HHN是其治療后復發的獨立預測子。綜上所述,早期發現高危患者HHN并謹慎隨訪,重點觀察其不同序列MRI信號及強化改變在預測腫瘤生物學行為和確定治療方案中尤為重要。
2.3.2 乏血供肝膽期等或高信號的肝硬化相關結節及隨訪
部分HGDN及4%的E-HCC也會表現為HBP等或高信號[26],這有可能與OATP1B3發生突變有關。研究顯示,當OATP1B3高表達,此時HBP的信號則取決于MRP的表達量。MRP2并不會固定在肝細胞膜上,當細胞處于氧化應激狀態時,MPR2會從膜上回縮至胞內;Gd-EOB-DTPA也可能通過MRR3排泄,肝細胞功能正常時其處于低表達狀態,當處于膽汁淤積等病理狀態時會表達上調[35-36]。研究顯示,當腫瘤細胞MRP3為高表達時(這可能是因為膽管的缺失導致MRP2并不起作用或者表達量下降),因其排泄率低于OATP1B3的攝取率,而呈HBP等或高信號,且更多見于中分化HCC[37-38]。Tsuboyama等[39]研究表明,當腫瘤細胞MRP2為低表達或腫瘤細胞內假腺體膜上MRP2為高表達,則呈HBP高信號。Sano等[40]報道肝膽期高信號的結節預后較好。與其相反,Matsuda等[41]報道這類結節有惡變為富血供肝癌的可能性。顯然,目前研究資料對此尚有爭議,仍需大樣本研究進一步驗證。
3 小結與展望
DN及E-HCC常因其體積小且內部成分不均勻,在病理上進行精確活檢并鑒別診斷存在一定困難。但二者又有進一步惡性轉化的高風險性,因此,影像手段在預測其惡變及預后方面顯得尤為重要。隨著Gd-EOB-DTPA的廣泛應用,亦發現其一定的不足,如易產生動脈期運動偽影;無真正的平衡期,部分結節可能因為假性廓清而被過度診斷;其藥物濃度相對較低,可能導致結節動脈期呈假性未強化模式。但因
其高敏感性檢出越來越多的高風險肝硬化相關結節,尤其是HHN (主要為HGDN及E-HCC)。如前所述,這二者在病理及影像表現上均有諸多重疊,僅憑單純的某征象難以精準診斷。但二者在演變的動態過程中,會逐步發生一系列復雜的除血流動力學以外的改變,如脂肪變性、鐵含量、細胞密度等的變化,并構成如T1WI雙回波技術、SWI、DWI、IVIM-DWI等多模態MRI的病理基礎。但不同序列均有各自的優勢與不足,將其有效的與Gd-EOB-DTPA MRI聯合應用,不僅在高風險肝硬化相關結節的診斷及鑒別診斷方面,而且在預測這些結節進一步惡變及預后方面均具有較大的潛力和臨床價值,這些仍需進一步的系統研究和探索。
利益沖突: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