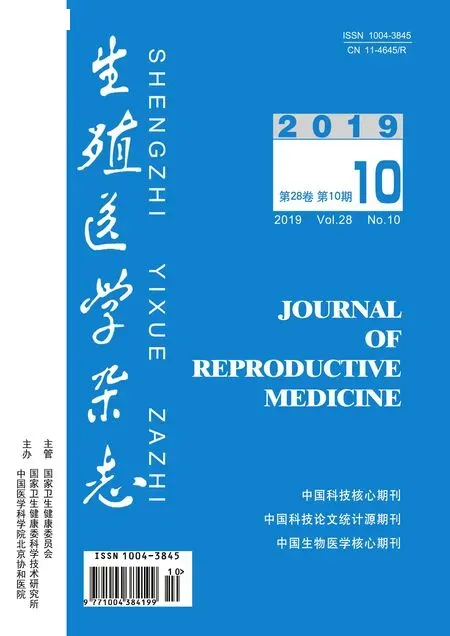圍絕經期抑郁癥研究進展
徐冠英
(德州市婦女兒童醫院婦科,德州 253000)
女性抑郁癥發生率是男性的兩倍,抑郁癥女性20%以上會出現健康殘損,女性激素水平波動期其發生率增加,圍絕經期更易患抑郁癥[1],且比圍絕經前癥狀更嚴重[2]。早期識別危險因素并盡早預防、早期篩查圍絕經期抑郁癥并有效治療其癥狀,將有效減少圍絕經期抑郁癥對婦女健康的影響。現將國外圍絕經期抑郁癥研究進展綜述如下。
一、流行病學
中年女性尤其是圍絕經期女性抑郁癥發生率上升,70%發生在圍絕經期[3],老年婦女中抑郁癥發生率與男性的差距變小。圍絕經期女性出現抑郁癥狀的比例在15%~50%[1],是絕經前女性的3倍多,15%~30%的圍絕經期女性會發展為抑郁癥。圍絕經期抑郁癥狀的發生率因國家/地區而異,西班牙為40%,土耳其為25%,美國費城為50%,墨西哥為52%[4]。國內圍絕經期抑郁癥狀的發生率,臺灣為31.0%~38.7%,北京為24%,上海為13.1%,廣東為21.1%[4]。
重度抑郁癥是一種慢性、嚴重損害性疾病,是導致婦女健康相關殘損的第二大病因,終生患病率在全世界范圍內為3%~17%(美國為16%~17%;歐洲為13%)[5]。女性首次發病的風險在生育期間最高,圍絕經期發生風險明顯增加[3]。在少數女性中,更嚴重的抑郁癥狀可能會在絕經后2~3年內持續,然后才會下降[6]。
二、病因學及危險因素
圍絕經期是一個社會、心理、生物因素交互作用明顯的時期。抑郁癥不是癥狀的集合,而是行為、知覺、認知和神經生物學特征的一種功能失調、重組、綜合的集合[7]。有研究發現,圍絕經期抑郁癥與下列因素相關聯:人口、社會經濟特征(失業、低學歷、黑人或西班牙裔);健康相關因素(較高的體重指數、吸煙、慢性疾病造成的健康不良);心理社會因素(低社會支持、焦慮史、多重生活壓力源)等[3]。Colvin等[8]提出,抑郁家族史在中年女性抑郁癥發展中有重要作用,抑郁癥家族史預示著中年婦女有嚴重抑郁癥狀,不依賴于圍絕經期的轉變和其他時變的協變量。
抑郁癥可能與單胺類神經遞質系統相關的基因有關,如5-羥色胺受體(5HTR2A c.102C>T,5HTR1B c.861G>C,5HTR2C c.68G>C)、色氨酸羥化酶(TPH1218C>A,TPH2 c.1077G>A)[9]。有研究表明,單胺氧化酶A(MAOA)、5,10-亞甲基四氫葉酸還原酶(MTHFR)、雌激素受體1(ESR1)、鄰苯二酚-O-甲基轉移酶(COMT)參與抑郁癥的發病,且COMT多態與嚴重抑郁癥和雙相抑郁有關[10]。研究表明,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BDNF)對海馬神經元的功能產生影響,增加海馬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磷酸酶-1(MKP-1)的表達[11],抑郁癥狀嚴重程度與女性血清MKP-1水平升高及圍絕經期婦女睪酮(T)水平降低有關聯[12-13]。
圍絕經期抑郁癥狀與性激素水平之間沒有直接關系,但與性激素水平波動有關[14]。數據顯示,雌二醇的波動是絕經過渡期間發生亞臨床、顯性抑郁發作的危險因素[15]。一些邊緣腦區對卵巢性激素敏感。具體來說,杏仁核、下丘腦、海馬和腦干高表達雌二醇和孕酮激素受體[16]。卵巢類固醇激素也可以影響從中縫背和中縫提取的5-羥色胺神經傳遞,這反過來可以調節抑郁癥相關的腦功能特征[17]。因此,卵巢類固醇激素的波動可能會有效地影響與抑郁癥相關的區域的腦功能,包括它們的功能連接性[18]。一些研究也表明,根據絕經年齡和生育期長度評估,長期接觸內源性雌激素的風險越大,抑郁癥的風險就越低[14,19]。一項對南美洲10個中心中年女性抑郁癥狀及相關因素的報告提出,抑郁癥與種族(非裔哥倫比亞人)、潮熱嚴重程度、激素治療使用、久坐生活方式、絕經、亞健康狀態和低教育程度有關,這些因素會加重抑郁癥狀[2]。高頻次的性交、健康的性伴侶會減輕抑郁癥狀。一項澳大利亞婦女健康縱向研究證明,停止和開始使用激素治療會增加抑郁癥狀,即目前激素治療使用者的抑郁癥狀更高,停止激素治療可能會引起情緒紊亂[20]。一項隨機對照試驗數據表明,停止雌激素可能會在有病史的婦女中引發反復抑郁癥[21]。圍絕經期抑郁癥是長期和短期風險因素復合暴露的結果。絕經狀態、代謝狀況和局部腦活動在圍絕經期存在一定關系,這導致圍絕經期抑郁的風險增加[22-24]。
三、臨床影響
相對于無抑郁癥圍絕經期女性,圍絕經期抑郁癥患者的生活質量、社會支持、適應能力和健康狀況明顯下降[25]。圍絕經期抑郁癥發病率增加,預示著全因死亡和心血管死亡的增加。
抑郁癥狀造成的功能損害較抑郁障礙小,但降低生活質量,增加社會衛生服務的使用,也可能增加身體健康問題的風險和負擔,包括心血管疾病、糖尿病、代謝綜合征和慢性疼痛[20]。
四、診斷標準
抑郁癥的診斷除抑郁癥狀外,還要有癥狀持續時間和/或嚴重程度[3]。
“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簡稱DSM),是一種普遍適用于精神疾病診斷的診斷工具。DSM-5于2013年發布[26]。抑郁癥的嚴重程度可以用漢密爾頓抑郁量表 (HRSD)和貝克抑郁量表(BDI)來評估,這兩種標準量表在世界各地的試驗中都使用過。格林更年期量表(GS) 是以圍絕經期癥狀評估為核心,用于醫學、心理、社會學或流行病學不同類型研究。三個獨立的子量表測量血管舒縮癥狀、軀體癥狀、心理癥狀和一個與性功能相關的表現。心理癥狀可以進一步細分以衡量焦慮和抑郁[27]。
五、治療
雌激素在抑郁癥患者中的抗抑郁作用結果不一致[28-29]。在2010年關于絕經相關激素補充治療(MHT)的科學聲明中,內分泌學會的結論是,B級證據支持雌二醇對圍絕經期婦女的抗抑郁作用,但不支持絕經后婦女的抗抑郁作用[30]。近期一項關于雌激素治療圍絕經期抑郁癥狀的系統評價及Meta分析提出,雌激素治療圍絕經期抑郁癥狀沒有明顯作用[31]。因此,抗抑郁藥仍然是圍絕經期和絕經后婦女重度抑郁癥的一線治療方法[32]。先前的研究認為,與絕經前或年輕女性相比,選擇性5-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SSRIs)對更年期婦女或老年婦女重度抑郁癥的療效較差。目前的研究表明,5-羥色胺-去甲腎上腺素再攝取抑制劑(SNRI)能夠有效地治療圍絕經期相關癥狀和圍絕經期的重度抑郁癥[28,33]。現有數據支持新病例或首次治療時使用SSRIs和SNRIs[3]。
盡管圍絕經期抑郁癥患者有多種治療方案可供選擇,但抗抑郁藥物治療的低應答率和緩解率表明抗抑郁藥在圍絕經期女性的使用受到某些因素的影響。先前研究認為,抗抑郁藥物的藥動學和藥效學在男性和女性患者之間可能有所不同,而且治療反應可能因性別而異。近期研究發現治療效果在性別上無差異[34]。先前有研究表明對某些抗抑郁藥的反應因更年期狀態而不同,而近期研究發現治療效果并不因更年期狀態不同而有異[34]。
Toffol等[35]關于激素治療圍絕經期抑郁的綜述對不同MHT方案、激素制劑及成分、抗抑郁藥和/或MHT對治療圍絕經期抑郁癥效果進行評價分析提出,沒有確鑿數據表明雌/孕激素治療有助于緩解圍絕經期抑郁,不同孕激素制劑、劑量、服用時間對緩解圍絕經期抑郁效果不一。因此使用雌/孕激素治療時要關注抑郁癥狀的緩解或加重情況[35]。目前研究中雌二醇治療圍絕經期抑郁癥的最適劑量是不確定的,但更高的劑量,每天50~100 μg透皮雌二醇或1~2 mg口服雌二醇可能更有效[31]。抗抑郁癥的治療用藥時要考慮藥物的有效性、耐藥性、副作用、緩解圍絕經期癥狀[5],以及與其他藥物的反應等[36]。
綜述所述,圍絕經期是一個社會、心理、生物因素交互作用明顯的時期,圍絕經期女性抑郁癥發生率上升且達到峰值。圍絕經期抑郁癥受多種因素影響。發病機理可能與神經遞質系統相關的基因有關,也可能與腦源性神經營養因子有關,還可能與性激素波動有關,目前仍處于研究中。格林更年期量表可以測量血管舒縮癥狀、軀體癥狀、心理癥狀以及性功能相關的表現,心理癥狀還可以進一步細分以衡量焦慮和抑郁,比較適合圍絕經期女性的評估。雌激素治療和雌/孕激素治療圍絕經期抑郁的結論不一,抗抑郁藥仍然是圍絕經期和絕經后婦女重度抑郁癥的一線治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