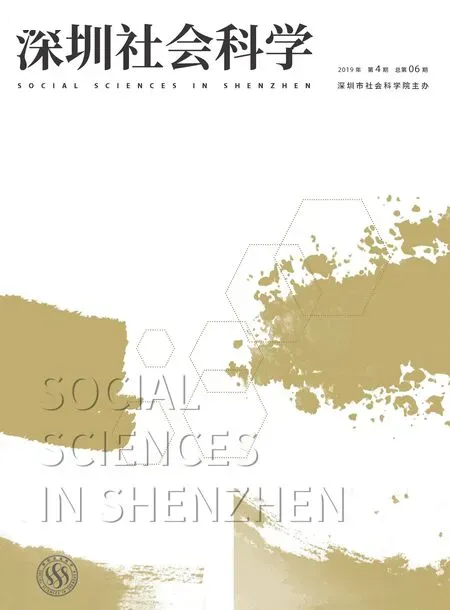龍興之物:人參與明末清初的遼東變局
李中躍
近些年來,學界逐漸重視醫藥社會史的研究,但直到目前并未較為系統全面地闡述藥物與社會之間的復雜關系。研究人參社會史可以對此有所突破,為之后醫藥社會史的研究提供較好的案例。元代中醫溫補思想出現后,人參愈加受到人們的重視,對醫學和社會的影響也逐漸增多①[清]薩英額主編:《吉林外紀》卷七,臺北文海出版社,1984年,第15頁。叢佩遠:《東北三寶經濟簡史》,農業出版社,1989年,第6~13頁。蔣竹山:《人參帝國》,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26~36頁。。而在明末清初大裂變之際,遼東人參則扮演了非常重要的歷史角色。如果說東北是滿族的“龍興之地”,則人參就是滿族的“龍興之物”。
人參與明末清初遼東社會的關系非常復雜,很長時間內沒有被完全理清,尤其是人參在后金戰勝明朝過程中的作用沒有被系統研究。有關人參對后金的經濟作用已有較多論述,認為人參促進了女真族經濟繁榮,是后金重要的經濟支柱②代表論著參見叢佩遠:《東北三寶經濟簡史》,《人參篇》第三、四章。袁清:《清入關前的經濟潛力》,《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佟永功:《清代盛京參務活動述略》,《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美]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陳蘇鎮、薄小瑩譯,新星出版社,2013年,第31頁。郭頌:《論朝鮮與清朝的人參貿易》,延邊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此為平允之論,但也未論述全面。有關人參的政治影響,已有論著指出人參爭奪是后金與明朝、朝鮮民族矛盾激化的重要誘因①宮喜臣、駱云和、段鳳琴:《明清時期的東北采參業》,《人參研究》,1990年第4期。趙郁楠:《清代東北參務管理考述》,中央民族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于磊:《論清代前期東北參務管理體制的演變及影響》,遼寧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8年。蔣竹山:《人參帝國》,第52~58頁。。學人已注意到“人參之爭”的后果,但對各方如何處理參爭則論述不多,乃至“人參合作”的歷史被較少研究。更不多見清初人參對清朝及朝鮮的文化與生態等影響的論述。以往論述認識到了人參對遼東的單一或局部影響,但并沒有看到人參的社會性影響,且不少局部影響仍有待深化研究。本文主要著眼于清入關前期,從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生態等方面理清人參在明清之際遼東變局中所起到的多樣作用,以期說明人參的社會性影響,深化醫藥社會史研究。
一、人參經濟與金興明衰
遼東人參對建州女真人的經濟崛起有重要作用。明代中后期,受溫補思想以及享樂之風②秦玉龍:《溫補源流初探》,《天津中醫藥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俞宜年等:《明代溫補學派用藥特色探析》,《福建中醫學院學報》,1996年第1期。王明強等主編:《中國中醫文化傳播史》,中國中藥出版社,2015年,第220~238頁,第292~310頁。金元明時期,醫家治病非常重視人參的功用。、遼東豐富的人參資源③李洵、薛虹:《清代全史》第1卷,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7頁。[清]阿桂等修纂:《欽定盛京通志(二)》卷一百七《物產二》,鳳凰出版社等,2009年,第586頁。清人將人參位列東北藥材之首,倍加隆寵。、女真南遷④曹樹基:《中國移民史》第五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42~443頁。閻崇年:《清朝開國史》上卷,中華書局,2014年,第33~51頁。、靠近市場廣闊的京津等因素的影響,建州女真人的采參業迎來了歷史黃金期。人參便成為建州女真崛起壯大的重要依托,也推動了建州女真其他行業的進步。
(一)采參業刺激了建州女真的人口增長
建州女真的人口增長,主要靠自然生育、和平移民、戰爭劫掠,而戰爭劫掠對其人口的短期增長影響尤為顯著⑤李健才:《明代東北》,遼寧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1~172頁。。那么采參業與三者有何關系?在滿族早期歷史中,采參是一種群體行動,包含識路、辨別、采挖等角色,須用較多人手。既然社會需參量擴大,那么產參量須隨之擴大才能適應形勢。女真家庭或家族欲得更多參利,就須有更多的勞動力,才能保證大規模采挖、爭參、自衛。在這種歷史背景下,采參業的擴大再生產和女真族的繁殖生育成正比例關系,刺激了其自我繁殖和劫掠他族人口。
在女真吸引和劫掠他族人的過程中,人參扮演了重要的誘拐角色和攻略借口。人參的高利潤,是部分漢人移民遼東和誘使明朝、朝鮮的窮人越境偷參的重要經濟動因⑥[日]稻葉君山:《清朝全史》上冊,但燾譯訂,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第51~52頁。從佩遠:《東北三寶經濟簡史》,第51~58頁。。正面來看,這是漢人等在爭奪女真利源,但另路思考,這是外族人主動為遼東采參業增加人手。為人參主動移民或逃亡到此定居的外族人,會演變成女真勢力下的人口⑦曹樹基:《中國移民史》第5卷,第268~283頁,第401~404頁。朱誠如主編:《遼寧通史》第二卷,遼寧民族出版社,2009年,第65~66頁,第192~193頁。。不定居失手的外人,被女真人逮住或撫化,“為奴使喚”“砍木負米”或者“入山采人參”等,也會變成女真轄下的人口①鄭天挺主編:《清史》上編,天津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38頁。。而女真人為捍衛參利,對成功越境偷參的人常采取報復措施。有勢力的女真貴族,常將怒火引向邊境漢人,攻殺的目的除了報仇雪恨,更在于攫取更大利益如人口財物土地。努爾哈赤將明朝人“越境偷參”列入“七大恨”中,以此發動戰爭,不斷攻城略人,使女真人轄下的漢族人口大為增加,女真人也因此得到漢族先進的技術和文化②《清太祖高皇帝實錄》第五卷,中華書局,1986年影印本,第69~70頁。有關清對明戰爭的人口俘略,可參見朱誠如:《遼寧通史》第二卷,第193~202頁。。反觀明朝,漢人因參利尤其是相關的邊境戰爭而被囚掠,造成了大量的人口流失,對遼東乃至明朝的衰弱產生了重要影響。人參誘略使女真人口增加,實力增強,而明朝人口減少,實力下降,二者是有密切關系的。這或許是人參贈給明末清初女真人意想不到的“人口福利”。
(二)人參貿易與女真經濟結構的改善
人參市場的擴大和繁榮,使人參業成為熱門行業,對有關輔助行業起到推動作用,改善了女真社會舊的經濟結構。
1.人參業的完善。人參需求量和價格的上漲,對遼東人參的運輸、保存、售賣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進了技術革新。在以努爾哈赤為首的女真人中,吸取漢族經驗和市場教訓,創造了儲存人參的“蒸曬法”,“獲利倍增”③《清太祖高皇帝實錄》,第47頁。。在售賣過程中,“干參”逐漸取代“鮮參”,革新了售貨方式和人參市場格局,使明清之際人參市場基本演變成“干參”市場,增強了女真人在人參市場博弈中的主動權④宮喜臣等:《明清時代的東北采參業》,《人參研究》,1990年第4期。。大量干參的出現,必然對倉庫的濕度和通風提出要求,這對女真人改進倉庫具有推動作用⑤賀飛:《清入關前糧倉研究》,渤海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5年。。此外為價格著想,女真人也逐步加工“紅參”,促使了遼東人參加工技術的進步⑥王鐵生主編:《中國人參》,遼寧科學技術出版社,2001年,第27頁。。
2.種植業的進步。女真早期的經濟結構以采獵為主,與中原農業經濟相比,經濟結構缺陷太多⑦[明]王崇之:《陳言邊務事》,見[明]黃訓編:《名臣經濟錄》卷四十,《文津閣四庫全書》第152冊,第312頁。。人參業的發展,增加了建州女真的人口,為其種植業發展提供了人力條件。因人參被誘掠的漢人,也為女真族種植業帶來先進的技術條件。發展種植業也需要種子、耕牛和農具。而人參貿易的興盛,為種植業購買種子、耕牛和農具提供了便利⑧戴逸、李文海主編:《清通鑒》1,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9頁。。這有利于后金加速封建化,逐步向農耕經濟過渡,為后金崛起提供了堅實的經濟基礎⑨鄭天挺:《清史》上卷,第57~62頁。李洵、薛虹著:《清代全史》第一卷,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0~43頁。。
3.手工業的進步。刨釆人參,需要特制的鐵工如“索羅木棍”“快當刀子”等⑩林仲凡:《明清時代我國東北各地人參的開采和經營》,《中國農史》,1988年第4期。。人參的蒸曬,需要鐵盆鐵鍋和炭火。人參數量和價格的增加,對采挖技術、炭火數量和冶煉技術及鐵鍋盆數量等提出了要求,有利于推動建州女真大規模炒鐵活動及冶鐵術的提高?曹文奇、楊秀:《女真人與鐵器》,《滿族研究》2002年第2期。李鴻彬:《明代女真族鐵業發展簡況》,《民族研究》1984年第5期。。售賣前需要對人參加工、裝飾,對推進木工技術和加工參的多樣化具有幫助?王鐵生主編:《中國人參》,第27頁,第475~476頁。。人參保藏需通風干燥,也有助于改良后金倉庫。
4.商業的盤活興盛。受溫補思想的影響,人參在明朝受到熱捧,是公開市場和走私市場的緊俏貨。人參成為后金打開和立足東北亞經濟貿易圈的關鍵商品之一。在明朝封禁馬市進行經濟制裁的時候,后金便利用人參的獨特價值,通過武力、走私、賄賂、轉賣等手段,重新撬開大明市場,得以暗地繼續維持①如明末女真人就曾利用毛文龍的皮島黑市,繼續對明人參貿易,可參見[明]文秉:《烈皇小識》,見于浩輯:《明清史料叢書八種》1,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第42頁。或參見后文。。而在明金、朝金、蒙金的商貿中,人參是女真以貨易貨和貨幣交換的關鍵要素之一。大量的人參貿易為女真換取金銀貨幣提供了機會。金銀的增加可為女真族的整體商貿注入活力,帶動其他物品的貿易。這不僅給后金帶來了大量貨幣,對穩定后金社會也有重要作用。
但對明朝來說,后金的人參貿易對明朝財政消極作用明顯。人參屬于名貴藥品,價格不菲。后金對明朝的人參傾銷,造成了明朝的白銀外流,削弱了明朝的經濟實力,不利于本國的商品貿易和經濟穩定。而買參的群體,多為達官貴族等社會剝削者。這些剝削者最終還是要將買參的錢轉嫁到貧苦大眾身上,加劇了官民對立和腐敗衰亡。
(三)滿清壟斷經濟的最早出現
古代王朝中,統治者常壟斷某種生活必需品,借機謀取厚利,如鹽、酒。清代壟斷經濟模式,最初卻與人參有關,確實獨具特色,開啟了清代專賣制度的先河。滿清貴族實行界限分明的八旗分山制,將采參權和售賣權緊緊抓在自己手中,形成了滿清入關前獨具特色的人參壟斷經濟,為籌集軍費提供了便利②戴逸、李文海主編:《清通鑒》2,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28頁。宋抵、王秀華編著:《清代東北參務》,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3~4頁。。在滿清貴族的規劃下,人參壟斷經濟孕育了早期滿族社會牢固的經濟鏈。八旗貴族處于上游,對人參的采賣和利益享有支配權,是參利最大者。八旗官兵和參務官員,位于中上游,保護和沾潤參利。參商、參把頭等則處于中下游,賺取人參差價。刨夫、車夫等采運的低層人員,則處于經濟鏈的下游。人參壟斷經濟幾乎是滿清社會的縮影,與滿清貴族甚至下層參民的利益息息相關。觸動這條經濟鏈,就意味著與滿清社會打交道,甚至為敵。
人參壟斷經濟是特殊歷史下的戰時產物,對清朝入關后的壟斷經濟有一定影響。入關后,人參壟斷經濟不僅沒有減弱,反而進一步加強,出現了制度化,對清代中后期的參務管理體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礎③佟永功:《清代盛京參務活動述略》,《清史研究》2000年第1期。王宏志:《洪承疇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第255~258頁。不少滿族權貴,入關不久就急不可耐地催迫人參傾銷。。人參壟斷經濟的暴利啟發了滿漢權貴對其他重要物資的專賣。如吳三桂在巴蜀開行的連附壟斷經濟,就是受到了遼東人參專賣的影響。他降清進軍西南后,“以遼地產參,利盡四海,而連附獨出巴蜀,因嚴私采之禁,設官監之官收其值而鬻于市,犯者至死。”④佚名:《吳耿尚孔四王合傳》,見于浩輯:《明清史料叢書八種》1,第550頁。連附乃黃連和附子的合稱。其中附子用于回陽救逆,時為巴蜀著名特產。不過人參壟斷經濟的出現,也是滿族官民對立的重要標志。貴族和百姓在參利上的矛盾,雖暫時被明清大矛盾遮掩,但并沒有消失了,“私采”一直存在,反映了統治者的封閉和貪婪⑤宋抵、王秀華編著:《清代東北參務》,第37~41頁。李博:《清代順治至嘉慶時期東北私參活動》,《史學月刊》,2011年第9期。。
(四)人參財富的來源和規模
人參經濟對女真如此重要,受到后金權貴的高度重視。擴大參利,是后金增加財富的重要手段。擴大參利的兩個必要條件便是增加參量和提高參價。首先為盡可能地增加人參持有量,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都非常重視統治區內部的人參采掘。后金內部有計劃地開發人參資源,劃分參區,增加采挖人員數量和擴大采挖區,否則后金對明朝進行大規模人參貿易是不可能的。但是東北人參并非女真獨有,別族也會采挖一部分人參。那么另一個增加人參數量的重要措施便是通過戰爭強占參山和掠奪人參。其次關注人參市價,對明則趁機增價,對弱小部落則“勒買參斤”,賤買貴賣,積極進行價格競爭,盡可能維持和擴大參利①《清通鑒》1,第85~87頁。。隨著實力的增強,有些女真人甚至在馬市上“強鬻枯參,倍勒高價”,非常蠻橫②[明]楊道寶:《海建二酋逾期違貢疏》,見[明]陳子龍選輯:《明經世文編》卷四五三,中華書局,第4977~4982頁。。
史載努爾哈赤在馬市上“歲以貂參互市,得金錢十余萬”,可見后金攫取了大量參利。人參貿易,確實促進了女真社會“國富民殷”③北平故宮博物院編:《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卷一,1932年,鉛印本,第8頁。。
二、人參政治與權勢轉移
人參經濟的重要性,使后金參務已經越過醫藥和經濟的傳統界限,深深嵌入到后金的政治生活中,讓明清參務變得復雜化。有關人參的爭執分合成為牽動遼東政局演變的重要紅線。
(一)人參之爭與明金的內政外交
饋贈人參是官場交往中的厚禮,而抄查權貴的藏參則是政治斗爭的重要手段。對于明朝來說,人參對明朝政治的腐敗和內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遼東官員為了巴結上級,遮過顯功,常向權勢太監或高官賄賂人參—“參賄”。但是要想“參賄”,須有足量夠品的人參方可。將官想要獲得足量夠品的人參,免不了勒逼官民士兵挖參貢參,或者欺行霸市,成為“參霸”甚至“參渣”,惡化遼東官民與民族關系。萬歷時期的不少遼東邊官為攫取參利,“減價強鬻參,毆打市夷幾斃”,導致馬市人參貿易凋零,激起民族仇恨④[明]張學顏:《貢夷怨望乞賜議處疏》,見《明經世文編》第5冊,卷363,第3906~3908頁。。最典型的是遼東稅監高淮,借置辦參貂之名,“無一城堡不到,無一村屯不被騷擾”,敲骨吸髓,引起遼東軍民的極大憤怒⑤[明]何爾健著,何茲全、郭良玉編校:《按遼御檔疏稿》,中州書畫社,1982年,第60、72頁,第70~71頁,第83~84頁。。高淮放縱下屬隨意敲詐,僅在廣寧一處就至少榨取人參18斤,而其他各處則難以統計⑥[明]何爾健著,何茲全、郭良玉編校:《按遼御檔疏稿》,中州書畫社,1982年,第60、72頁,第70~71頁,第83~84頁。。對將官兵,高淮則“頤指氣使,陽騙陰索,欲千則千,欲百則百,參貂黃白,任意攫取,稍不如意……揪采凌辱”⑦[明]何爾健著,何茲全、郭良玉編校:《按遼御檔疏稿》,中州書畫社,1982年,第60、72頁,第70~71頁,第83~84頁。。盡管高受到多人彈劾,但在萬歷庇護下逍遙法外。這令遼東軍民倍感心寒,以致很多視故土不如夷地,逃到女真地區避難安生⑧[明]何爾健著,何茲全、郭良玉編校:《按遼御檔疏稿》,第12~16頁。[清]張廷玉等編纂:《明史》卷三〇五《宦官二·陳增傳附高淮傳》,臺灣商務印書館百衲本,第3362~3364頁。。高淮轉移了遼東軍民的斗爭焦點,為努爾哈赤的休養生息和壯大實力提供了幫助,客觀上成為大明朝的內賊和后金的好朋友。再如崇禎時期黨爭仍在,打擊政敵的重要手段就是指責對方接受“參賄”。權臣周延儒招權納賄,曾被揭發受賄重達十兩的“清河參”⑨[明]文秉撰:《烈皇小識》,于浩輯:《明清史料叢書八種》1,第208頁。。袁崇煥斬殺毛文龍的“九當斬”理由更是與人參密切相關。⑩袁崇煥:《島帥正法謹席藁待罪仰聽圣裁疏》,見[明]袁崇煥著,楊寶霖輯校:《袁崇煥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93~197頁。袁指責毛文龍制定了苛重的“參役”。毛勒逼投靠難民到危險的“夷地”挖參貢參,每天只給其“米一碗”,導致“皮島白骨如山”,然后將上好人參賄賂朝中太監或權臣,還勒逼登州守將等“不曰受我參貂若干,則曰受我商人領狀若干”,讓其得以炫功掩過,顛倒黑白①[清]吳騫輯,賈乃謙校:《東江遺事》,浙江古籍出本社,1985年,第175頁。。再者毛文龍在明朝危難之際,勒逼朝鮮獻參,在皮島馬市私自購買敵國女真的人參,大肆向內地高價轉賣,發國難財,弱親肥己資敵②從佩遠:《東北三寶經濟簡史》,第60~63頁。[美]袁清:《請入關前的經濟潛力》,《清史研究》,1996年第1期。。滿清貴族中也有不少“參霸”,但遠不及毛文龍之無恥。毛文龍可稱得上明末遼東獨特的“參渣”。袁崇煥殺毛文龍對明朝邊防造成消極影響,也造成了皮島人參貿易的萎縮,卻解放了因“參役”而受盡折磨的難民。
對后金來講,人參是轉移內部矛盾和增強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人參已經被視作女真族的民族物產,是女真族共同的記憶,為女真族形成“人參政治”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明朝人和朝鮮人越境偷參,在后金權貴別有用心的挑唆下,極易演化成女真族的共同仇恨。而滿清權貴便利用這種民族“參恨”,掩蓋內部的不平等,將內部矛盾轉嫁到外部。他們一則用“參恨”增強了民族凝聚力和戰斗力,成為征明伐朝的重要借口;二則以代言人的形象申復“參恨”,利于籠絡人心,集中權力;三則可借口防范越界偷參,堂而皇之地將參山收歸“公有”,將采參權集中在權貴手中,假公濟私。“參恨”對明清之際的滿清權貴可謂是一石三鳥的法寶。
在雙邊關系中,明人越界采參、壓低參價是激化民族矛盾的重要導火索。這是已成為學界的基本看法。不過仔細分析,人參激化明金民族矛盾的事實多見于后金中前期③宋抵、王秀華編著:《清代東北參物》,第143~144頁。。但在后期,明朝在遼東步步敗退,其人口和勢力已經大不如前。明朝遼東漢人在戰爭的威脅下,強橫早已不在,對女真避之唯恐不及,逃亡甚多,人數銳減,再去越界偷參或壓低參價的可能性已大降④當時遼東巡按熊廷弼歷數后金戰爭劫掠大量人口,曾悲觀夸張地說:“遼左今日之患,莫大于無人。”參見[明]熊廷弼:《懲前規后修舉本務疏》,收于[明]程開祜輯:《籌遼碩畫》,商務印書館(上海),1937年,第52~53頁。熊論盡管言過其實,但是遼東明朝人因戰亂而人口銳減是不爭的事實。。但后期后金仍不斷指責明人越界偷參,煞有其事。其實到皇太極時期這個由頭已經實少虛多,不過是一種戰爭借口而已。客觀講,明朝人在滿清人參經濟的壯大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女真人應當感謝漢族才對。后金是人參的主要生產輸出國,而明朝是人參的主要消費輸入國。沒有生產就沒有消費,但是沒有消費的生產注定是長不了的。沒有漢族溫補思想、廣大的消費市場等,女真人參經濟是很難發展起來的。在后金龐大的人參經濟中,漢人越境偷參造成的損失是微小的,女真權貴才是真正的獲利者。后金的狡猾之處,在于將舊賬翻出來當事實借口,煽動一般女真的民族仇恨,以增強伐明的氣勢和力量。而明朝內外失火風聲鶴唳,很難針鋒相對地進行斗爭,在輿論戰上處于下風。
在處理參爭中,明清做法差異較大。明朝中后期對待“參爭”事件上,除對參爭人命較多關注外,對越境偷參案件不重視,管理松懈,充耳不聞。而后金則對“參爭”的大小事件均密切關注,大做手腳,對內則大作反明宣傳,對外則反復叫冤。在人參的政治博弈中,衰弱的明朝愈加被動。崛起的后金積極主動,終成明清人參政治的主導者。
(二)人參分合與朝金關系的轉化
朝鮮位于后金的戰略后方,與明朝關系融洽,在初期助明抗金⑤《清通鑒》2,第477~478頁。。后金無法用和平手段將朝鮮拉攏到自己的陣營中。為了防止朝鮮助明,尤其擔心兩面夾擊勢態的出現,后金需要動用武力改變朝金舊關系。而朝金的人參之爭,為后金發動征朝戰爭和改變朝金關系提供了口實,使金朝關系從最初的“平等之國”,退為“兄弟之國”,最終跌至“君臣之分”。兩國的人參政策隨著國家地位的變化發生了重大改變。
后金崛起初期,實力較弱,在明朝眼中的地位遠不如朝鮮重要。在朝金關系中,明朝常壓金護朝。明朝在處理轟動一時的“渭源參案”便是最明顯的例子①《清通鑒》1,第47~49頁,第349~351頁。。朝鮮在其中的態度是比較微妙的。一方面,朝鮮在明朝的支持下,不愿吃大虧,整軍備戰,以防不測②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六),中華書局,1980年,第2145頁。。另一方面,為了獲取明朝的更多支持,朝鮮賄賂明朝邊將,謊稱參案乃系民間私相斗毆,積極游說明朝錯先在金,自己總體上是正當的。但私底下朝鮮鑒于后金的壯大和自己的衰弱,非常擔心后金會借此報復,再致國內動蕩,所以朝鮮又派人對后金進行低姿態的賠禮道歉,置備布匹、高麗參、酒宴,希望消弭戰端③詳情可見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六),第2149~2187頁。。后金對于明朝的袒護和朝鮮的陰猾,自是上下氣憤,對朝鮮的低姿態道歉更是不買賬,但是自知理虧,且羽翼未豐,怕朝明兩面夾擊,不得不暫時退避三舍,最后從“人參之爭”被迫轉向“人參之和”。
但皇太極繼位后,對外奉行更加積極的擴張戰略,對朝鮮一改過去的隱忍姿態,屢次拿邊界參爭要挾朝鮮。衰弱的朝鮮對后金被迫隱忍退讓,主張“人參之和”,試圖將邊界參爭降到民間私事級別,希望小事化了④叢佩遠:《東北三寶經濟簡史》,第54~56頁。。但后金卻主動將邊界參爭升級為國家政治問題,將其統籌到戰略目的中。在金強朝弱的形式下,朝鮮的“民間參爭”處理模式,最終還是拗不過滿清的“國家參爭”處理模式。在后金挑起對朝戰爭的借口中,指責朝鮮人“越界偷參背盟”幾乎是必備的。而這個借口,與征明的“參恨”不一樣。征明“參恨”虛多實少,伐朝“參恨”實多虛少。后金常能將朝鮮“參賊”人贓并獲,讓朝鮮無可否認⑤張存武、葉泉宏主編:《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匯編:一六一九—一六四三》,國史館印行,2000年,第84~86頁,第127~129頁,131~133頁。以下簡稱該書為《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匯編》。。后金利用這個由頭,添油加醋,向朝鮮提出大堆條件,逼迫朝鮮臣服。
明清決裂后,清朝人參貿易萎縮,加劇了國內的饑荒動蕩⑥《清通鑒》1,第47~49頁,第349~351頁。。這迫使滿清不得不將貿易重心東移,擴大朝金貿易份額。在第一次朝金戰爭中,皇太極以武力暫時逼服朝鮮,使二者變為“兄弟之國”,趁機強令朝鮮開放更多邊市銷售人參。在西部人參貿易萎縮的情況下,皇太極用戰爭手段打開東部朝鮮市場,欲使后金人參經濟繼續運轉。但這并不容易。
人參在西部漢人區物以稀為貴,但在東部朝鮮區見多不怪。朝鮮也是傳統的產參大國,故遼參在朝鮮沒有貂皮暢銷⑦刁書仁:《明代女真與朝鮮的貿易》,《史學集刊》,2007年第5期。。朝鮮對邊境人參貿易的態度是雙重的。一方面,人參也是朝鮮內外貿易的重要產品,與后金的人參貿易存在競爭關系。為保護朝鮮的北部市場,朝鮮在朝金邊市故意壓低遼參的價格,抵制后金的人參貿易⑧《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匯編》,第127~129頁。雙方原定馬市參價16兩,朝鮮則云人參對其無用,壓至9兩,否則收回。。另一方面,朝鮮迫于后金的軍事壓力,也低價收購一部分遼參,但卻轉身高價賣給水深火熱中的明朝,賺取地區差價⑨《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匯編》,第167~170頁。后金指責朝鮮在皮島向明朝倒賣人參,“每斤參售價二十兩”,可從收購的遼參中凈賺一倍以上,不可不謂厚利。。朝鮮這種不光彩的行徑,是一種自保自私的表現。
因為以上原因,朝金的人參貿易并沒有打開局面,這是后金無法容忍的。后金通過反復偵查,曝光了朝鮮的小算盤,然后言辭激烈地批評朝鮮的陰猾偽善,諷刺朝鮮“既言人參無用,貴國年年出境,挑斗是非,不識掘此無用之人參何為也”,強令朝鮮提高參價,增加邊市數量①《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匯編》,第127~129頁。。朝鮮對此則是據理力爭,爭辯參價漲幅是市場規律,與朝鮮政府無關,對增加邊市也是不情愿,還多次以“兄弟之國”為名強調自己的“善良和平”,指責后金恃強凌弱、無理取鬧,言辭時而嚴厲,打起了口水仗②《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匯編》,第131~133頁,第171~173頁。朝對高價賣參之事,矢口否認。。對于朝鮮的“強詞奪理”和“種種不禮”,后金非常氣憤。于是后金在人參問題上再次老調重彈,以人贓并獲的形式反復指責朝鮮“越界背盟”,多方恫嚇③《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匯編》,第134~136頁,第166~167頁,第180~185頁。。但是朝鮮利用“兄弟之國”的名義,針鋒相對軟磨硬泡,不肯徹底屈服,且仍與明朝暗通曲款④《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匯編》,第167~173頁。。后金可能萬萬沒有想到作為“弟”的朝鮮這么難纏。征明戰略和長期的矛盾,最終令滿清對朝鮮“忍無可忍”,再次動兵,變“兄弟之國”為“君臣之分”。
第二次朝清戰爭,朝鮮慘敗投降,被迫接受清朝的全部要求,絕明臣清,成為清朝的藩屬國,實現了清朝的戰略訴求⑤[日]稻葉君山著,但燾譯訂:《清朝全史》上冊,第71~87頁。。二者變為“君臣之分”,使清朝在雙邊關系中徹底占有了主動權和最終決定權。之后,清朝主動將兩國“參爭”從國家政治矛盾降低到一般矛盾。盡管之后朝鮮“越境偷參”的現象依舊存在,但是君臣之分已定,清朝為了顏面對朝鮮的指責頻率大大下降,總體上淡化處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愿為蠅頭小利大動干戈,破壞“天朝上國”的形象,穩固雙邊關系。而朝鮮對清初兩國參爭的惡果心有余悸,對清朝的輕度指責不再力爭,反而主動配合抓捕境內的“參賊”,并將“參爭”的最終決定權拱手讓給清朝,展現出鮮明的合作姿態⑥《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匯編》,第327、329、337~340頁。。用朝鮮君臣自己的話說,這為了避免“邊釁”⑦[日]末松保和編輯:《李朝實錄·肅宗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4年,肅宗卷三八下,二十九年十一月丙午,第528~529頁。。兩國的參爭處理模式,最終合二為一,走到了一起。
在清朝中前期,為防朝鮮人越界偷參引起邊釁,朝鮮政府非常重視朝清邊界的監管,對北部人參采掘行為嚴加控制,總體上還是奉行“參禁令”,一段時間還實行更加嚴格的“南北參商禁斷”,企圖全面禁止采參和售賣⑧郭頌:《試論朝鮮與清朝的人參貿易》,延邊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6年。。這導致西北等采參重地的朝鮮人民“自我境禁采之后,生理斷絕……怨咨日深,散亡相繼”,而不少百姓出于生計,違令采參,導致李朝“參獄”累累,非常可憐,削弱了朝鮮對外人參貿易,加劇了西北地區的衰弱動蕩,更不利于朝鮮的經濟發展⑨《李朝實錄·肅宗實錄》卷三八下,十一月戊寅,第535頁。《李朝實錄·肅宗實錄》卷三八下,二十九年十一月丙午,第528~529頁。。清入關后朝鮮北部人參業的萎縮和地區的貧弱動蕩,是權勢地位倒置的不良產物。
三、人參物資與擴軍強兵
人參是滿清重要的軍用物資,是擴軍強兵的助手。女真族增強戰力,需要增加人口、糧食產量、戰馬和鐵器、布匹、金銀貨幣等。采參、參貿以及“參爭”為劫掠人口、促進種植業具有幫助。女真在明、蒙、朝邊境進行人參貿易,為換取好馬良牛和鐵器提供了條件,促進了女真社會的農耕發展。比如后金通過與蒙古的邊境貿易,就獲得了大量馬匹,尤其到了皇太極時期金蒙之間的人參、皮貨與牛馬貿易更盛以前①《清通鑒》2,第568~569頁,第329頁。。與朝鮮的邊境貿易,有效增加了女真的鐵器和布匹②《清通鑒》2,第568~569頁,第329頁。。這都為女真擴軍強兵積累下較好的基礎。
再據現代醫學研究,野生人參及相關參藥,對于保持和增強男性生殖能力,以及治療保健孕婦諸多疾病具有重要作用③孫國才:《人參的醫療保健功效》,《藥學情報通訊》1991年第2期。王鐵崖主編:《中國人參》第十四章。張紅梅:《人參與鹿茸配伍對腎陽虛大鼠生殖機能影響的實驗研究》,遼寧中醫藥學院碩士學位論文,2002年。遼東滿人常以人參和鹿茸作為基本藥料,進行醫療和保健,對于解決男性陽痿、增強精子成活率以及治療女性妊娠疾病等具有神奇療效。。這有利于滿族的自我繁殖和人口增加,為后金保持和增加青壯年兵力提供了醫療保障。
在努爾哈赤時期,后金的醫療知識和技術是比較落后的。被后金俘虜的朝鮮人李民寏曾對后金軍民的醫藥狀況做如下描述:“疾病則絕無醫藥針砭之術,只使巫覡禱祝,殺豬裂紙以為祈神,故豬紙為活人之物,其價極貴云。”④[朝]李民寏著,遼寧大學歷史系校注:《建州見聞錄》,中華書局,1987年,第44頁。當時的女真兵民“病輕服藥,而重跳神”,甚至連努爾哈赤與其子都曾利用跳神的方式醫療祈壽。⑤滕紹箴:《滿族醫學述略》,《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滿文老檔》第72冊,中華書局,1990年,第703~704頁。在這種情況下,人參是女真熟知的為數不多的藥材,是軍民極為重要的藥材。女真人長期販參,對人參的大體醫療作用自然清楚。早在明代女真人就已會用“人參水”等以人參為主的藥物來治病保健⑥王平魯:《薩滿教與滿族早期醫學的發展》,《滿族研究》,2002年第3期。。后人調查也發現近現代東北的高壽滿人有食用人參的習慣⑦于永敏:《滿族藥膳與食療經驗》,《滿族研究》,1992年第2期。。現代醫學研究證明人參對于失血、重傷、休克以及抗疲勞、增強免疫力等均有神奇療效。明末清初中國氣候處于小冰期,遼東更是干寒,利于傷寒、天花等傳染病的爆發⑧葛勝全等編著:《中國歷朝氣候變化》,科學出版社,2010年,第497~500頁。。這使得人參在氣候轉變過程中救治重癥病患的意義顯得尤為重大⑨王平魯:《薩滿教與滿族早期醫學的發展》,《滿族研究》,2002年第3期。。在應對清初天花瘟疫襲擊過程中,盡管人參不能根治該癥,但可以幫助滿人增強免疫力,延緩死亡時間爭取救治機會,減少死亡數量⑩梁其姿:《面對疾病》,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8~60頁。杜家驥:《清初天花對行政的影響及清王朝的應對措施》,《求是學刊》,2004年第6期。。再者八旗子弟馳騁沙場,所受戰傷不在少數,那么失血、殘肢、昏迷、休克等“戰爭病”對官兵是家常便飯。豐富的人參資源,便可以幫助戰傷的八旗士兵加速康復,甚至延長或拯救生命。
食用人參對于維持八旗權貴的身體健康、增強耐力具有幫助,有助于維系后金權力核心的穩定。清朝歷代皇帝都比較重視人參醫療,服食生人參以及相關參藥如參茸丸、龜齡集等,對延長壽命和個人統治年限具有較好幫助,而皇帝的長壽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政局的穩定?程志力等:《龜齡集與服食養生》,《中華中醫藥雜志》,2014年第6期。。在一個政權的崛起期間,最高統治者的良好健康和較長壽命,是非常重要的。作為開國者的努爾哈赤,早年起兵曾受過幾次嚴重的戰傷,失血不少,但最終卻康復了,且最終活了68歲,在清前期屬于高壽者。最嚴重的一次可能是萬歷十二年九月努爾哈赤攻打翁郭落城時,頭、脖子等處被射中,血涌如注,回營后流血不止,一夜數醒,幾至昏迷,直到次日未時流血方止。然而不出三四個月,努爾哈赤就“創愈”了,還親自帶兵成功復仇,降服射中自己的戰將,大有鐵木真降服哲別的心胸風范。①《清太祖高皇帝實錄》第31~34頁。趙爾巽等:《清史稿》卷一,《太祖本紀》,中華書局,1976年,第17頁。不過鐵木真是靠自己的運氣、體魄、忠誠部下和馬奶,才逃過哲別的死亡之箭②策·達木丁蘇隆編,謝再善譯:《蒙古秘史》,青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77~80頁。。努爾哈赤靠什么逃過死亡之箭呢?在醫藥知識和技術匱乏的時代,努爾哈赤能在短時間康復,暗示除了他身體基礎良好外,在休養期間也很可能吃了人參等速效藥。因為他青年時代就曾長期采參和賣參,活躍在遼東馬市,清楚人參的醫療奇效,在《清實錄》中每次論及人參時,經常流露對人參的深厚感情,以致建國后親自主持改良人參經濟和政策。故筆者推測:除了其本人身體素質良好及運氣外,努爾哈赤服用人參是其脫離生命危險、保養長壽的重要原因之一。反過來思考,如果當時女真沒有人參這一醫療特產,失血過多的努爾哈赤,在天寒地凍的東北地區,恢復得慢幾個月,甚至病死,那么中國歷史將要改寫了。
相比之下,明末清初滿清權貴乃至基層軍民以人參為主的醫療保健模式,雖看似簡單粗野,但要比明朝不少文人兵民甚至皇帝的煉丹醫療要健康得多③蓋建民:《明清道教醫學論析》,《宗教學研究》2000年第1期。張衛:《明清道教醫學研究》,中國中醫科學院重要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6年。。這或許也是清朝皇帝的平均壽命,要高于明朝皇帝的一大原因。而明朝中后期皇帝的早死,卻容易造成政局的動蕩,不利于平滿戰略的穩定。④史泠歌:《帝王的健康與政治》,河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附件1,2012年,第151~168頁。趙秀麗、馬建平:《明代皇帝政治作為的影響因素》,《理論月刊》,2010年第7期。
另外“參賄”也是后金腐化收買明朝遼東邊將,刺探軍情的重要手段。天啟六年十二月,皇太極就曾以人參、貂皮等物,“值亦千余金”,公開或私下賄賂遼東巡撫袁崇煥等人,不料袁崇煥不吃這一套,將“禮單”押在寧遠府庫,奏明朝廷“以待皇命”⑤天啟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夷目來寧情實疏》,見《袁崇煥集》,第82~85頁。。明末政治腐敗,貪污橫行,那些見得不光的“參賄”就不知道有多少了。再有值得一提的是,削平云貴的吳三桂及其幕僚,為了“使朝廷勿疑”,還特意令吳應熊在京大肆搜購遼參,一則為了自身侈享和轉賣牟利,二來更是為了裝出耽于享樂毫無野心的面目,麻痹清廷⑥滕紹遠:《三藩史略》(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第936~937頁。。
四、人參物種與文化生態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重要的社會存在,會對社會文化產生深刻的影響。
(一)人參對滿清文化及近現代東北文化的塑造產生了重要影響。
1.人參是滿族形成的共同經濟基礎之一。人參作為女真族獨特而重要的物產,增進了其內部凝聚力和民族認同感,為女真族的整合與滿族的形成提供了一定的心理基礎。
2.人參在滿清內政外交禮儀中扮演重要角色,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滿清政權的形象。在內政方面,皇帝常對重要大臣賞賜人參,籠絡人心,成為以后的常例。這種“參賞”幾乎伴隨滿清的始末,是清朝政治文化中頗具特色的地方。在外交中,滿清在與明朝、朝鮮、蒙古的交往中,為表和善之意,饋贈人參成為特殊的國禮,以致出現“參禮”,與朝鮮十分類似①《圣仁祖皇帝實錄(三)》,中華書局,1985年,第290頁。蔣竹山:《人參帝國》,第234~237頁。。不過由于入關后人參主要變成權貴富豪的內需以及產量的下降,這種“參禮”在順治朝后有所減弱。
3.儲賣人參逐漸演化成入關后滿清權貴的常見財富手段之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巨貪和珅,貪儲人參高達680余兩(估銀27萬兩),還開藥鋪賣人參②唐文基:《和珅傳》,東方出版社,2009年,第159~160頁。。從中也可以看出,“參賄”這種骯臟的賄賂手段,也被入關后的權貴“發揚光大”了。這種儲賣人參的經濟方式,一直保持到現在。我曾走訪一些東北滿族家庭,發現不少都還藏有野山參,要么保存起來當藝術品自我把玩,或者自我醫療,或者期待高價。
4.在民間,女真人創造了獨特有趣的人參風俗文化。在對人參根莖葉等的命名方面,滿族根據大小形狀季節等創造了復雜形象的稱呼,如稱根部為“棒槌”,或“根”“貨”,將肉紅粗大者稱為“紅根”,半紅半肉者稱為“糙重”,空皮者稱為“泡”;根據季節將初夏參曰“芽參”,開花參曰“朵子參”,秋霜參曰“黃草參”,將蒸煮參名為“罕參”以紀念努爾哈赤。入山采參又分為“放山”“相山”“搭老爺府”“排棍”“喊山”、拜祭等,挖到大參俗叫“大貨”,且要拜山神和老把頭。值得一提的是努爾哈赤挖參的傳說,后變成滿族院子立桿子祭祀的源頭。這都使人參深深嵌入到東北的民間宗教信仰文化中。③楊英杰:《清代滿族風俗史》,遼寧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94~298頁。滿清崛起后,“參貂升天”。對滿清崛起立下汗馬功勞的人參、貂皮等物產,在統治者的宣傳下,聲名更勝以前,從此無論東北三寶如何變化,人參始終穩居榜首,為近現代人參的聲譽奠定了基礎④[清]阿桂等修纂:《欽定盛京通志(二)》卷一百七《物產二》,第586頁。蔣竹山:《人參帝國》,第34~36頁,第174~175頁。[清]高士其:《扈從東巡日錄》下卷,遼沈書社,1985年,第7~8頁。。此外,東北從古至今都流傳著精彩動人的人參傳說,如“人參娃娃”“人參姑娘”“人參精”等,及清代許多人參詩詞,是近現代東北人參文學、曲藝以及旅游業等的歷史文化資源。明代以來滿族繼承和創造的人參文化,為近現代東北的人參知識文化發展奠定了基礎。近現代只要一提人參,大眾一般都會想起東北三寶的俗語:“東北三寶,人參貂皮烏拉草(或鹿茸角)”,進而馬上聯想到清朝、東北。清代以來,人參與清朝、東北逐漸演變成中國大眾的“捆綁記憶”。人參變成了東北的“名片”,在宣傳和發展東北中始終散發著活力。近代以來,每當外地人問起東北人家鄉特產或者東北人想家之時,有關人參的話題也會經常出現。可見人參已經深深嵌入到東北人民的鄉土意識和地方觀念之中了。
5.人參為近現代滿族醫學以及飲食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重要支撐。用參療養,是明代以來滿族醫藥文化的特色之處,尤其成為清宮醫藥的亮點⑤劉淑云、宋柏林編著:《中國滿族醫藥》,中國醫藥出版社,2015年,第110~123頁。。滿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中,創造了許多人參藥用方式 ,如“參丸”“參水”“參湯”“參雞”等,對滿族的食療文化產生重要影響,更為中國醫學增添光彩⑥于永敏:《滿族藥膳與食療經驗》,《滿族研究》,1992年第2期。。滿清入關后,打開了內地廣闊的人參市場,再也用不著強迫朝鮮買參,推動了東北人參藥業的迅速崛起,也附帶刺激了東北其他藥業的興盛比如鹿茸、虎骨、熊膽等等,為近現代東北中藥業的發展打下了基礎⑦唐廷猷:《中國藥業史》,中國醫藥科技出版社,2013年,第199~202頁,第299~301頁。。但另一方面,入關后的滿清權貴接受了溫補文化,變人參為權貴尤其是宮廷王府飲食醫療的必備品,對清代宮廷醫學及溫補派的形成具有重要影響,但卻對民間用藥風格卻造成了不良影響①劉淑云、宋柏林:《中國滿族醫藥》,第110~120頁。蔣竹山:《人參帝國》,第148~158頁。。為此,康熙帝曾幾度告誡滿漢權貴不要輕服人參等補藥,要養成良好的起居飲食習慣來養生,但是效果了了②《圣仁祖皇帝實錄(三)》,中華書局,1985年,第301~302頁。。而過度依賴人參等補品,也成為滿洲八旗身體素質整體衰退的一個原因③于永敏:《滿族藥膳與食療經驗》,《滿族研究》,1992年第2期。蔣竹山:《人參帝國》,第161~168頁。聞性真:《康熙的醫學與養生之道》,《故宮博物院院刊》,1981年第3期。。這也為清代中后期如徐大椿等醫學家革新醫學理論提供了社會條件,推動溫補派理論方法的完善④[清]徐大椿:《人參論》,參見徐大椿:《徐靈胎醫學全書》,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5年,第133頁。。
(二)人參采掘和近代東北生態退化的萌芽。
滿清帶給人參的是盛名、高價、多需,刺激了社會上下采參偷參的欲望,使人參的采挖量遠超以前。但是人參生長成型不易,再生速度慢⑤王鐵生主編:《中國人參》,第65頁。。清初以來的東北人參的開發方式又非可持續模式,而是粗放掠奪式,導致了野山參該物種的銳減。雖然清廷也認識到了危險,進行息山輪采,但效果微弱,并迫使采參區東移⑥宋抵、王秀華編著:《清代東北參務》,第45~47頁。。故清代入關后,東北野山參的生長繁育進入衰退期,數量漸減。
粗放的采參模式,也附帶惡化了東北生態。須知人參的生長環境要求很高,與周邊的生物有很強的共生關系⑦王鐵崖主編:《中國人參》,第48~52頁。方士福:《野山參鑒別經驗》,人民衛生出版社,2003年,第8~12頁。。人參生長區都是生態良園,對維系當地氣候、水文和黑土及其他物種的生存都具有益處。人參的存在,意味著該區物種繁茂,所謂“一榮俱榮”。但采參主要是在高溫多雨的夏秋季節進行,本身就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而粗放掠奪式的過度采挖,必然會大量破壞地表植被、土壤、水文以及其他物種,可謂“一損俱損”。該區植被、土層、水文以及其他物種的破壞,甚至消失,則會加劇黑土流失和不良氣候。明末以來東北水旱災害不斷,使人參采挖更易造成人參坡地水土流失⑧張士尊:《明代遼東自然災害考略》,《鞍山師范學院學報》,2001年第4期。魏剛、于春燕:《明代中后期遼東地區的水旱災害與饑荒》,《大連大學學報》,2011年第4期。。已有學者指出近代東北的黑土等水土流失,在晚清就已出現⑨衣保中:《近代以來東北平原黑土開發利用的生態代價》,《吉林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穆興民等:《東北3省人類活動與水土流失關系的演進》,《中國水土保持》,2009年第5期。。通過研究,筆者認為:近代東北的黑土等水土流失,早在明末清初就已經種下了禍根。反過來,當地生態環境的改變和破壞,延緩了生態恢復,自然也就不再利于人參的再生長,加速該區人參的銳減。這也是滿清政府封山育參效果了了的重要原因。而清代中前期東北野山參的銳減,一方面造成嘉慶以后“秧參”增多,使“辨參”環節在人參貿易過程中的地位愈加突出;另一方面,國內野山參的銳減和居高不下的市場,成為國內參藥功效下降、高麗參與西洋參趁機崛起的重要源頭,進而導致近代世界人參貿易格局發生轉變。⑩方士福:《野山參鑒別經驗》,第4~6頁。張存武:《清韓宗藩貿易1637~1894》,“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5年,第227~233頁。
余 論
明末清初人參對遼東社會的影響,并非局部的而是社會性的,與當時的歷史演變存在著非常復雜的關系。“文殊曰能活能殺,冷笑迷而不悟人”,①[清]薩英額撰:《吉林外紀》卷二,成文出版社影印版,1974年,第13~14頁。乾隆可能沒想到小小的人參,在明清遼東社會裂變中竟然也“能活能殺”,對經濟、政治、軍事、民族、文化和生態等社會諸多方面的演變起到了相當重要的影響。而造成諸多變局的核心原因則是人類對參利追逐的擴大化。遼東人參諸多復雜的社會作用,是明亡清興社會大變局的產物。明清社會大裂變是遼東人參生態和社會功用發生巨大變化的決定因素,而后者對該歷程起到了催化推進的作用,畢竟人參的社會功用及角色定位,是由人決定的。隨著社會矛盾的變化,清代中后期,人參的社會面目又隨之改變,并對社會歷史造成另樣影響。
醫藥史與社會史的相遇可以給我們提供新的視野。傳統醫藥史研究,多是就藥論藥,未能體現醫藥與社會之間廣闊的聯系。“醫藥社會史”則可在宏觀綜合的視角下,將醫藥置于歷史的背景下重新考慮,同時也加深微觀研究,突出醫藥演變過程中“人”的活力和重要性,充分揭示醫藥與人類社會的復雜聯系,開拓歷史研究的新領域。
類似于人參的重要藥材或藥物還有很多,比如四川附子、安徽祁術、西藏冬蟲夏草等,都曾對地方乃至全國的歷史文化產生重要影響,可惜至今也沒有多少人對這些藥物進行較為全面的研究。通過梳理史實,從中可以發現醫藥對人類社會的多元化影響,從而對地方和全國歷史發展產生新的認識。筆者相信,未來在“大醫藥史觀”的指導下,醫藥社會史研究會越走越寬,成為歷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單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