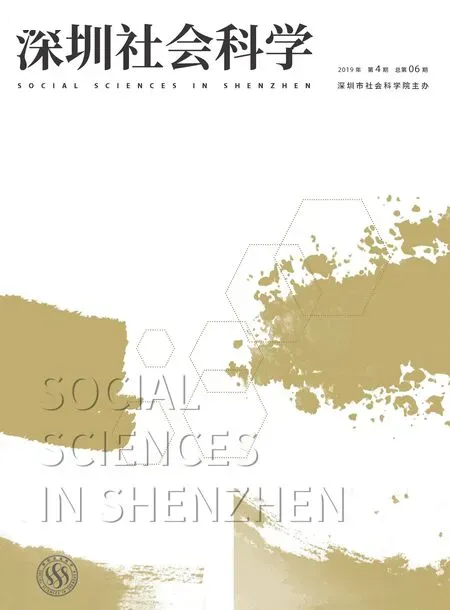回歸傳統與開啟新局:武德、貞觀時期的文壇*
劉 順
武德、貞觀時期在“四唐”框架中歸屬于初唐早期,此一時期定位,也多少決定了初唐早期文學在文學史中的過渡地位。無論視之為“沈宋”前期,導唐律之先路,抑或標顯其一二異乎梁陳周隋之特性,此時期文學之影響,相較于“貞觀故事”輝耀中古近世,實如寸燭之光。與此相應,在中古文學批評史的主流書寫中,武德、貞觀時期被視為儒家政教詩說的復興期。雖然,研究者大多能予政教之說以同情了解之態度,但無甚高之評價,似乎也是學界之通識。“思想與文學”之研究,乃古典文學研究的常規話題,只是歷時雖久,不免思路相因,易入窠臼。其偏重“外緣性”的研究思路,即關注“寫什么”的主題選擇與“為何而寫”的功能定位,長處在于可見“共性”,同時也易與“純文學”的評價尺度相調和。但難見“特性”,不能彰顯思想應時而變的內在特性,也難以真正將“長時段”的眼光植入文學研究,從而探究思想觀念的深層變革所引領的文學變動以及文學中的孤明先發所預示的思想新變,卻是其難以自我辯護的短板。而對思想核心觀念內在張力的忽視,讓貌似差異明顯甚或對立的觀點本可容納于同一框架的思想常識難以成為文學研究的基本自覺,也構成了思想與文學研究自我突破的另一瓶頸。武德、貞觀文學研究,百年來視角與結論多相因循,此種研究慣習當有以致之。在此研究傳統中,儒家政教詩說復興的必然及學說本身的特性,常常遮蔽于對“詩教”說的通性表述,而“文學”也隨之成為時代變革的旁觀者與詩教介入文學的印證者。“隋唐之際”本是政治史或思想史研究中“異彩紛呈”的歷史時段,而“文學”的沉寂,似乎又一次以其疏離于時代的異質性,印證著詩教理論壓制文學的舊說。但是,若研究者能適度關注唐初詩教說的時代特性,并將其研究視角延伸至詩教說如何影響文學或文學如何有效應和詩教說之問題時,唐初的文學觀照或許會獲得異于常識的新發現。
一、“文之將史”與天人之際:“文史”傳統的回歸
儒家政教詩說自現代學術建立以來,常橫遭批判,即有學人予以同情之理解,但于傳統中國國家權力運行的內在邏輯關注不足,所給予的解釋也不免流于態度之表達。儒家詩說對于詩文政治倫理功能的強調及其所流露之“道德共同體”的企望,根源于士人對于權力缺乏制度制衡之歷史事實的清醒。權力運用公共性的自覺與權力私化與頹廢的內在邏輯構成了傳統社會一難解謎題,所謂歷史周期律亦根源于此。儒家詩教說關注君子人格的養成,立基于政治生活之良窳多取決于為政者與社會精英道德水準的認識傳統。在現代學術建立以來與儒家詩教說構成一對反題的“純文學”說,雖非全為學人的歷史想象,但“純文學”只為歷史之異響別調的事實,卻遮蔽于此敘述洪流,“國家不幸詩家幸”之深沉喟嘆所逗露的豐富信息,也自隱而不彰①劉基《項伯高詩序》:“言在于心而發為聲,詩則其聲之成章也。故世有治亂,而聲有哀樂,相隨以變,皆出乎自然,非有能強之者。是故春禽之音悅以豫,秋蟲之音凄以切,物之無情者然也,而況于人哉!予少時讀少陵詩,頗怪其多憂愁怨抑之氣,而說者謂其遭時之亂,而以其怨恨悲愁發為言辭,烏得而和且樂也;然而聞見異情,猶未能盡喻焉。比五六年來,兵戈迭起,民物凋耗,傷心滿目,每一形言,則不自覺其凄愴憤惋,雖欲止之而不可,然后知少陵之發于性情,真不得已,而予所怪者,不異夏蟲之疑冰矣。”。以中古文學而言,魏晉以降,“文史”漸離為二,至梁陳之際,裴子野人稱“良史之才”,蕭綱譏之“了無篇什之美”,沈約為《宋書》以“(裴)松之已后無聞焉”,“文”重于“史”,已蔚為一時風氣②參見胡寶國《漢唐間史學的發展》第三章《文史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蕭綱“立身”與“為文”的兩歧表述,以“純文學”眼光視之,似乎最為合拍于“文學自覺”之成說,但后世對于中古文學的批評卻多聚焦于此一時段:“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察,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周氏并吞梁荊,此風扇于關右,狂簡斐然成俗,流宕忘返,無所取裁。”③《隋書》卷六十七。
南朝后期文學的污名化,自隋唐以降似已為定案,而現代已來所流行的多部文學史持舊說而不疑,也自有推波助瀾之效用。雖然,以“淫放”、“輕險”相責,不過儒家詩教之故技,然梁陳文學“漸乖典則”,在為南朝知識人興趣之焦點自玄學清談而文學提供佐證之外,亦可探見天人觀念變化的痕跡,此一點,學界殊少關注,故于儒家詩教之說,常見其同而不見其異。魏晉學術玄學盛而經學衰,有無本末之說為玄談核心話題,影響之下,漢儒天人之說遂呈衰勢,及釋教波瀾漸廣,天人之說另有新解,儒家兩面受敵,頗賴史家崇尚符瑞災異,存漢儒天人之說于一線:“于時玄者重名理,史人崇災異,災異固兩漢以來天道說也。玄者以虛無為天道,史家以災侯為天道以抗之。符瑞之志,各家尚焉。”①蒙文通:《經史抉原》,巴蜀書社,1995年版,第272~273頁。西晉之際,玄學已一時為盛,但詩文書寫,猶存天人合一、天人感應之遺意,時入東晉則有“新自然說”,天人感應影響消歇,然此時詩文言道談玄,關注天理人事諸“一般問題”,未離“天人之際”之基本框架②參見錢志熙:《魏晉詩歌藝術原論》第四章,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降及梁陳則刻畫細碎,面目迥異:“晉世風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歙習、舒徐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寫性情,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凌遲至于梁陳,淫艷、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③元稹:《元稹集·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周相錄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360頁。“天人之際”在儒學觀念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諸如性情、義利及群己等問題莫不植根于此。因而,文學對于儒學的跳脫最為根本處乃為天人觀念的別生新見。在今日文學史的主流敘事中,“宮體”乃梁陳“淫放”文學之典型,學界或釋之以佛教色空理論,釋家影響痕跡宛然。而儒家天人觀念在意識形態與精英文化中漸呈衰勢,亦合拍于儒佛地位在南朝后期的消長起落④參見普慧:《南朝佛教與文學》第六章,中華書局,2002年。。文史相離,文盛于史,提升了文學書寫的自由度,但由之所導致的對于文學“公共性”的悖離與個性趣味的強化,卻難與追求文學公共價值的認識傳統相調和,故而,當儒家天人觀念體系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重新復蘇之際,“人人有集”為士人取則的價值取向即難逃“何必要事文章”的挑戰⑤《梁書》卷三三《王筠傳》:“又與諸兒書論家世集云:‘史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世者也。'”南朝重視文集于此可見一斑。貞觀之時,太宗則有言曰:“朕若制事出令,有益于人者,史則書之,足為不朽。若事不師古,亂政害物,終貽后代笑,非所須也。只如梁武帝父子及陳后主、隋煬帝,亦大有文集,而所為多不法,宗社皆須臾傾覆。凡人主惟在德行,何必要事文章耶!”(《貞觀政要·論文史》)雖太宗發論聚焦帝王與王筠之說有異,但梁陳以來帝王多有文集正可見重文風習之影響,太宗之論,考之唐初文壇實況,殊有失實之處,但時代風習已生變改,卻非過為推論。。
武德五年十二月,李淵下詔修史:“思典序言,史官紀事,考論得失,盡究變通。所以裁成義類,懲惡勸善。自有魏室至于陳隋,莫不自命正朔,綿歷歲祀,各殊徽號,刪定禮儀,然而簡牘未編,紀傳咸缺,炎涼已積,謠俗正訛,余烈遺風,泯焉將墜,顧彼湮落,用深震悼,有懷撰次,實資良直。”⑥王溥:《唐會要》卷六十三,中華書局,1985年。楊隋短祚,南北分立數百年所遺留的地域、文化與種族諸問題猶存,唐初修史乃欲以文化正統自居,考定正朔,彌合帝國權力的法統與名號之爭,進而以話語模式與知識譜系的營造,凝聚情感,重建認同。帝國對過往的回眸,自不免對人物及事件的刪改與重組,以及價值的顛覆與重估,相比于存一代之信史,資史以為鑒,無疑更為符合唐初的修撰旨趣⑦《舊唐書·李大亮傳》載太宗贊荀悅《漢紀》“敘致既明,議論深博,極為治之體,盡君臣之義”,足見撰史典則所在。。漢唐間史學,南勝于北,而各有專擅。唐初史學,重視民生國計似北,留意史論似南,頗兼南北之長。武德、貞觀兩朝相繼,史學大興,士人有以“不得與修史”為憾者,天人之說重回唐初知識結構的核心位置⑧武德七年,歐陽詢編成類書《藝文類聚》,一百卷四十六部,修撰之初衷本為尋檢之便,但由其分類與排列,實可窺見知識界于知識及思想之分類與價值認定。在四十六部的類目編排中,天、歲時、地、州、郡、山、水與符命八部列于帝王部之先,與隋時虞世南編定《北堂書鈔》置天、歲時、地于類目之末差異明顯。《類聚》首舉“天部”,以叢聚儒家天說為要務,佛教之天說則見于“內典”部,輕重之義,一目了然。雖北周武帝之時,道教已編成類書《無上秘要》,置“天”為首,但道教的孤明先發,尚未能成為知識界的共識,直到七世紀早期,在意識形態的助推之下,天地與歲時所象征的時空結構在清整知識確立價值的智力運作中位置方始無可替代。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二卷:“如果我們以后兩個一百卷的宗教類書為對照分析文本,我們就可以看到,《藝文類聚》中的這些思路似乎并不只是體現著官方意識形態,實際上就連佛教與道教的類書也在靠近并采用這些思路。”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第603頁。。本已影響漸衰的天人感應之說,遂乘勢反彈:
竊以陛下承國開家,積德累功,世濟擬于高陽,纘緒盛于周武,載誕燭神光之異,儀形表玉勝之奇,白雀呈祥,丹書授歷,名合天淵,姓符桃李,君堯之國,靡不則天。星紀云周,奉時圖始,甲子之旦,不俟而脫。起兵西北,勢合乘乾,我本自東,位當出震,至八井深水之圖讖,堂堂桃李之謠歌,固已備在人謠,無德而稱者也。①裴寂:《勸進表》,董誥等編:《全唐文》卷一三二,中華書局,1990年。
中古之世,祥瑞符兆、讖緯謠諺與星象占卜乃社會生活頗具影響之技術與知識。中古權力合法性的自我論證,標示冢中枯骨與稱揚勘黎武功之外,常借助于此類知識的宣揚以彰顯歷命所在,并壓制“逐鹿中原”之言說模式的滋長。雖然,此類技術與知識的宣揚者,不必然是其服膺者。但流行既久的話語模式,在應和思想惰性的同時,也在提示一般知識層面對新思潮與舊傳統的鈍感與敏感。在國家與社會的互動中,無論標示高度的精英思想如何的理性與周密,形成于國家與社會互動中的意識形態卻無法不俯身傾聽看似重復而單調的底層生活。日常的一般知識與信仰在拉低時代知識水準的同時,也在固執地強調傳統的執拗與強大。祥瑞災異甚至被視為旁門左道的方技與幻術都可以底層社會的知識土壤中獲得生長與發育的空間,并由此影響意識形態的言說策略。在唐初的詩文書寫中,追求公共效應,特別是面對社會民眾傳播的檄文、教令、碑志、儀式歌辭以及刻意造作的謠讖與符瑞,均可見及對天象符瑞的頻繁言說。與此相應,稱揚大國光華,贊頌典章文物之美,以顯新朝之盛世赫赫,亦為相近之理路。而社會精英間的文化互動,則更容易展現天人觀念上的精英形態:
人君者位貴居尊,志移心溢,或淫恣情欲,壞亂天下。圣人假之神靈,作為鑒戒。夫以昭昭大明,照臨下土,忽而殲亡,俾晝作夜,其為怪異,莫斯之甚。故鳴之以擊鼓柝,射之以弓矢,庶人奔走以相從,嗇夫馳騁以告眾,降物辟寢以哀之,祝幣史辭以禮之,立貶食去樂之數,制入門廢朝之典,示之以罪己之宜,教之以修德之法,所以重天變,警人君也。天道深遠,有時而論,或亦人之禍爨,偶與相逢。故圣人得因其變常,假為勸誡。知達之士,識先圣之幽情,中下之主,信妖祥以自懼。②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春秋左傳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1242頁。
魏晉以來的學術發展,業已提升“天行有常”觀念在天人框架中的影響,故而,唐人雖依然重視“休咎之變”的觀察、記錄與解讀,但態度已頗為理性。圣人假天象以設教意在勸誡人君,與詩教欲培養君子人格之意圖實異曲同工。相較于漢儒對神道或信或疑,唐初儒者對于天象與人事之間的聯系,更注重于預防權力的私化與腐化及維持共同體之穩定的實際功效。天人關系在知識結構中位置的提升以及相關認識的理性化,讓天人關系的天平逐步傾向人事一端,而理論自身的包容性也在應對歷史變局中逐步提升,武德、貞觀時期文壇正處于此思想觀念的時代氛圍之中。因為對人事的關注,回眸歷史與經驗反思便成為常見的主題:
漢祖起豐沛,乘運以躍鱗。手奮三尺劍,西滅無道秦。
十月五星聚,七年四海濱。高抗威宇宙,貴有天下人。
憶昔與項王,契闊時未伸。鴻門既薄蝕,滎陽亦蒙塵。
蟣虱生介胄,將卒多苦辛。爪牙驅信越,腹心謀張陳。
赫赫西楚國,化為丘與榛。(王珪《詠漢高祖》貞觀十二年)
唐初修史,以取鑒求治、重建意識形態及彌合地域與族群分歧為主要目的,故而尤重“理亂興衰”的書寫與總結,對于史書的評價以“文”“事”“義”為要件,忽略“典章制度”在歷史流變中的穩壓作用。在歷史興亡的可解與不可解的諸因素中,唐初的知識精英更重視“人”對歷史的主導與創造。受此影響,唐初詠史詩常聚焦于君臣相合與君王德行在歷史興亡中的重要作用:
余以萬幾之暇,游息藝文,觀列代之皇王,考當時之行事,軒昊舜禹之上,信無間然矣!……予追蹤百王之末,馳心千載之下,慷慨懷古,想彼哲人,庶以堯舜之風,蕩秦漢之弊;用咸英之曲,變爛熳之音,求之人情,不為難矣!故觀文教于六經,閱武功于七德。①李世民:《唐太宗全集》,吳云、冀宇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頁。
人情不遠、人性古今相通是唐初精英層的基本共識,因為對于人性的認可以及對推己及人責任的標顯,“道德共同體”的藍圖遠景似乎只在“一克念”之間,彌漫文字間的理想情懷,為盛唐詩文中動人心魄的情感之美奠定了人性基礎。當安史之亂打破盛世圖景之時,人性的美好似乎已成為遙不可追的昨日夢境,而興起于律體中的詠史之作,也在“金陵王氣黯然收”的詠嘆中重現人力難為的黯然。
天人觀念的盛行影響了武德、貞觀文學的題材選擇,同樣也影響著此時期的“文”之定位。在唐初的論“文”話語中,以天文論人文可視為基本模式,無論是必也正名乎的合法性闡述,還是“壯夫不為”的功能性否棄,天人觀念均扮演了提供理論支撐的角色,天人話語的內在張力,包容了觀念間的差異與對立,但同時也極易掩蓋在基礎觀念層面的一致。故而,在特定的意義上,對于儒家文論的革新而言,天人觀念方是真正的判斷標尺。雖然在儒家的經典表述中,人文出于天文,有其無可置疑之價值,但“文”的多義性,卻使文學價值的確立依賴于“文”之意涵的界定。故唐初文學之觀念,遂有兩歧之表述,視文學為雕蟲者,詆其無益政教,論文論人尤多酷評②李百藥:《北齊書·文苑傳序》:“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宮,刑乎流俗,雜沾滯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梁時變雅,在夫篇什。莫非易俗所致,并為亡國之音。”;重文者,以文經天緯地、溝通上下,則有“大矣”之嘆③參見《隋書·文學傳序》。。李唐一代,古體近體之爭,風骨雅正與綺錯婉媚之辨,均不越此藩籬。而衡以初盛之際,“清流”文化漸勝之趨勢,以文有“體國經野”之用,乃當日之主流④參見陸揚:《唐代的清流文化—一個現象的概述》,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編:《田余慶先生九十華誕頌壽論文集》,中華書局,2014年,第545~68頁。:
而近代諂諛之臣,特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常冕服,章句翰墨為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升平,流蕩因循,敗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旂常冕服為人文,則秦漢魏晉,聲明文物,禮縟五帝,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亂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為人文,則陳后主、隋煬帝,雍容綺靡,洋溢編簡,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核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既如彼,較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天緯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治,則文之時義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小伎,廁雜其間乎。⑤呂溫:《人文化成論》,《全唐文》卷六二八。
呂溫之論,時已入中唐,但其對以章句翰墨、旂常冕服為人文之傳統的批判,卻恰恰佐證了與中唐儒者所認可之價值相偏離的文學傳統的存在。歐陽修在破簏中發現昌黎古文,似乎本可視為宋儒對中唐文學重構的隱喻,只是百年來的敘事傳統卻多少掩蓋了宋儒對中唐思想與文學圖景選擇性記憶的事實。古文運動的強大光芒,壓制了另一種書寫傳統及人才標準存在的印跡。呂溫的論述易在日常的接受習慣中,獲得情感的貼近與認同,但其話語中所逗露的信息,卻難以獲得應有的重視。武德、貞觀以降,文武參用之格局已難以維持,而以文晉身者于高層政治之影響則日益增長,新的人才觀念與選才標準也在逐步改變原有的社會認知,曾經流行于政治高層內省性的“文學”批判話語,在得到邊緣與草萊之呼應的同時,似乎在宮廷內部銷聲匿跡。雖然,以詔書與表狀箋啟諸應用文字之書寫為核心的政治文學尚未能與“唐詩”在文學史的章節安排爭一短長,但李唐之時,“文章”之盛,實有賴于朝野共同的鼓吹。
天人觀念的理性化以及由之而來的對于人事的關注,讓唐初的知識界對于過往的歷史遺產保留了應有的敬意,而在歷史的洪流中探究文運的興衰,也讓唐初的文論有了深沉的歷史感①《隋書·經籍志集部總論》:“其中原則兵亂積年,文章道盡。后魏文帝,頗效屬辭,未能變俗,例皆淳古。齊宅漳濱,辭人見起,高言累句,紛紜絡繹,清辭雅致,是所未聞。后周草創,干戈不戢,君臣戮力,專事經營,風流文雅,我則未暇。其后南平漢、沔,東定河朔。訖于有隋,四海一統,采荊南之杞樟,收會稽之箭竹,辭人才士,總萃京師。屬以高祖少文,煬帝多忌,當路執權,逮相擯壓。于是握靈蛇之珠,韞荊山之玉,轉死溝壑之內者,不可勝數,草澤怨刺,于是興焉。古者陳詩觀風,斯亦所以興乎盛衰者也。”李延壽《南史·文學傳序》以“金陵之數將終三百年”釋南朝文學之衰亂亦同此理路。。影響之下,唐初詩文之書寫,常以天象、人事并置之典型方式為冒頭,如“夫大德曰生,資兩儀以成化。大寶曰位,應五運以遞昌”之表述,為唐人常用之手法。雖文有冒頭,取資天象(理)、人事均非自李唐而始,然較之北周楊隋官方文學以古質相尚,李唐對于起句與應句之間象(理)與(人)事均衡感的著力,無疑會強化文學主題選擇上的“公共性”。而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天人觀念,則會進一步確定“公共性”的主題選擇,對于儒家倫理道德的服從。與此同時,天人觀念的流行以及天人感應在一般知識層面的傳播,也強化著唐初詩文在言說天人時對于均衡感的追求,如果說冒頭是唐文天人均衡化的有效方式,在唐時即已引發一定批評有雕飾之稱的近體,則通過屬對中對應對稱原則的強調、中間兩聯仰觀俯察的視角安排以及全詩事、景、情先后展開的結構配置以達成整體風的均衡②“應制詩所特有的儀式性、現場感容易使作品具有直觀的描述性,因此比其他部類的詩歌更容易形成秩序感。在展示宴飲、寓目、節日、慶典等有帝王參與的‘大場面'時,疊字,雙聲疊韻及對偶的大量使用,都可以產生秩序效果,而應制詩人要窮極應制場合的所見所聞,必須悉心安排詩歌結構的層次,注意‘時間圖案'與‘空間節奏'的結合,從而形成‘多樣統一性',在人的心理上產生充滿秩序感和節奏感的妝飾效果。”程建虎:《中古應制詩的雙重觀照》,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38頁。。雖然,此時期的近體尚屬于“沈宋前期”,情、景之間的拼貼痕跡明顯,但相比于成熟時期的近體,其差異已只是技法高低之別。直到中唐思想界再次聚焦天論,一種以新型天人觀念為支撐的文學樣態方始嶄露頭角③參見劉順:《中唐文儒的詩文新變》,《安徽師范大學學報》,2013年第6期。。
二、文質彬彬:大一統時代的文學
“文質”在中古思想與政治文化論述中出現的頻次并不亞于“天人”,雖然現代學術以來的文學研究慣于在文論的維度上理解和使用此組概念,但衡之于中古時期的思想事實,“文質”實是一組內涵復雜的多義概念,諸如種族、地域、階層之別,乃至個體之內在德行與外在行為展演均可納入此一概念結構中。作為文論之語辭的“文質”概念,無法獨立于連鎖糾纏、相互指引的意義鏈條。南北分立時期的自我認同與他者想象及大一統時期的遠景懸設,限制著唐初“文質”闡釋的意義空間并提示著文論話語乃時代政治之文化投影的角色定位,“文質論”在一般層面所預設的循環論的文學觀,也由之成為歷史循環論的另類表述。雖然,以“文質”衡文,相較江左文論之佳構迭出,實有簡化甚或退化之嫌,但此解讀模式作為李唐文論之基本框架的地位,卻尤難動搖①在“文質”框架中,初期的李唐無疑偏于“質”之一端,及李唐漸入盛世,大興禮樂,則有清流文化之興起,即由質而入文,禮樂辭章,一時為盛;而天寶年間,河洛儒者興起,倡文章中興,以古文相號召,延及安史亂后,有春秋學應時而起,制度義理,波瀾漸廣,由文返質又成一時風氣。。“文質論”的流行,也決定了魏征“文質彬彬”的經典表述在此內涵豐富的語義場中,如果僅以純文論話語視之,或許會錯失魏征此論所內在隱含的真實意圖②“文質”概念或以論人或以論政,然經董仲舒之改造,“任德教”為王道之“正”,或質或文則為王道之“偏”。以此,則王道之正,實含“文質彬彬”之意。參見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中華書局,2011年)第二章第三節。。相較于“天人之際”在題材選擇上更注重通性,“文質彬彬”的目標追求在應合通性的同時,更能體現題材的時代特性。文學應合或迎合官方意識乃詩教說之基本觀念,但文學如何應合以及在應合中文學又如何作用于官方意識依然是存有探究空間的話題。武德、貞觀時期的文學生長于“文質”話語的氛圍之中,也生長于李唐構建大一統帝國的理想實踐中,合拍于大一統之構想的“文質彬彬”表述,傳遞著“大一統”的歷史使命對于文學的期待。故而,考察此時期文學對大一統之可能性、目標設定、程序呈現與實踐樣態的關注與書寫,在為定位武德貞觀文學提供特定視角的同時,也可為文學如何應合官方意識提供參照樣板③唐初文學的題材選擇、價值定位與風格偏好,也因在此視野中重獲觀照。惟“風格”問題,前賢高論俱在,本文所論重在題材選擇之問題而兼及價值之定位,以嘗試細化儒家詩教之表述,并進而勾畫初唐大一統之理想與文學之關聯。參見王運熙《中古文論要義十講》(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與“文質”論相關之篇目。。
大師少有著述之志,常以宋、齊、梁、陳、魏、齊、周、隋南北分隔,南書謂北魏“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又各以其本國周悉,書別國并不能備,亦往往失實。常欲改正,將擬《吳越春秋》,編年以備南北。④李延壽:《北史》卷一〇〇《序傳》。
華夷之分,本有文野之別,故文質之說即可視作華夷之辨的另一表述。五胡亂華,晉室南渡,中古中國遂入南北分立之時期。三百余年間族群互動頻繁,政權亦多有更迭,以北方而言,其政權多融合胡漢而以胡族為主導;南方則僑姓漢人政權為主。南北或戰或和,然多以正統自居,揚“大一統”之義,南方以恢復中原之承諾為合法性表征,北方則以飲馬長江為本朝之遠圖。文化名份北虜南夷之口舌,不過是意識形態上正統之爭的特例而已。進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在漫長的政治實踐與身份轉化過程中,逐步確立了以魏承晉的五德歷運譜系⑤高閭:《五德議》(魏收:《魏書·禮志》):“計五德之說論,始自漢劉,一時之議,三家至別。……以為火德者,懸證赤帝斬蛇,棄秦之暴,越惡承善,不以世次為正也,故承周以為火德。……故以魏承秦,魏為土德,又五緯表驗,黃星曜彩,考氏定實,合德軒轅,承土祖末,事為著矣。又秦、趙及燕,雖非明圣,各上號赤縣,統有中土,郊天祭地,肆類咸秩,明刑制禮,不失舊章。奄岱逾河,境被淮漢。非若齷齪邊方,僭擬之屬,遠如孫權、劉備,近若劉裕、道成,事系蠻夷,非關中夏。”另可參見羅新《十六國北朝的五德歷運問題》,《中國史研究》,2004年第3期。,而偏居江南的漢族政權,卻越來越體現出地域化的特性⑥何德章:《論梁陳之際的江南土豪》,《中國史研究》,1991年第4期。,在“大一統”的歷史進程中漸落下風:
(韋)鼎仕梁,起家湘東王法曹參軍。入陳為太府卿。至德初,鼎盡質貨田宅,寄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問其故,答曰:“江東王氣盡于此矣。吾與而黨當葬長安。期運將及,故破產耳。”初,鼎之聘周也,常與高祖相遇,鼎謂高祖曰:“觀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監深遠,亦非群賢所逮也。不久當大貴,貴則天下一家,歲一周天,老夫當委質。公相不可言,愿深自愛。”及陳平,上馳召之,待之甚厚。①《隋書·韋鼎傳》。
北方的胡漢混血政權主導了大一統的歷史進程,但軍事征伐所帶來的自信,并未能彌補南北文化上的差距②煬帝之初,內史舍人竇威等撰《丹陽郡風俗》,以“吳為人為東夷”,煬帝震怒,敕令杖責并稱其為“天下之名都”。李昉《太平御覽》卷六〇二《文部》十八“著書”引《隋大業拾遺》。。北方政權的華夏化,雖然提升了北方中國的文明程度,但相較于南方的衣冠禮樂與典章文物,北方依然不脫質樸之貌。對于承隋而立的李唐而言,“文質彬彬”的理想,即首在于立根北朝,揚質抑文。此既合北方胡漢混血政權自我標榜之需,亦合于西魏北周政治文化之傳統。西魏北周政治文化的特點,以蘇綽六條詔書所倡導之“清心”、“教化”為典型,在承認族群與地域間政治、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之差異的基礎上,嘗試利用儒家的基本倫理整合社會,以形成價值共識。其擬周官古制,所推行之制度禮儀革新,不過用其名號以凝聚地域人心而已③谷川道雄《中國中世共同體》解釋六條詔書曰:“詔書就是這樣解釋治民之本在于為政者的心態。然而僅僅心態端正,仍不過是無形的狀態。還必須以行為示于民。所以不僅要‘治心',而且要‘治身'。為政者必須先為民之師表,故為政者須‘心清如水,形白如玉'。躬行仁義、孝悌、忠信、禮讓、廉平、簡約,繼之以不懈努力,加之以明察,訓導人民,是以民畏而敬之,則自然而然效法之。”(馬彪譯,中華書局,2004年,第220頁。)另可參見何德章《魏晉南北朝史叢稿》(商務印書館,2010年)第295頁之論述。。及楊隋承周,文帝雖“易周氏官儀,依漢魏之舊”④《隋書》卷一《高祖本紀》。,但在政治文化層面,隋文帝崇尚以孝治國并強制推行“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之“五教”,整合社會的思路,與北周可謂一脈相承。重視道德、任德教以化民,也由之成為唐初建設政治文化,構建共同體之首選: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為國之基,德歸于厚。自有隋失馭,政刻刑繁,上懷猜阻之心,下無和暢之志,遂使朋友游好、慶吊不通,鄉土聯官,請問斯絕,至有里門相接,致胡越之乖,患難在身,忘救恤之義,風俗玩弊,一至于此,化民以德,豈斯之謂。⑤李世民:《唐太宗全集·論崇篤實詔》。
共同體的構建與維系,依賴于以資源競爭為核心推力的邊界劃定與他者想象,同樣也依賴于群體內部的利益共享與情感認同。看似舊調重彈的德性標舉,強調為政者的道德自覺以及底層對國家的順應與服從,乃是為政者對于權力必然會產生私化與腐化之自利傾向的清醒。在權力結構具有先天缺陷且其監督效果受社會運行成本之約束的中古時期,權力運用的公共性以及降低社會摩擦成本的可能性更多地取決于時代的道德水準。故而,在關于共同體的理解或藍圖想象中,總隱含著作為其可能性之要件的人性預設。唐初之政治文化近資北魏、西周,而實遠紹兩漢,其內在之精神頗近于董仲舒的公羊學。董氏之“德教”主“以德善化民”,注重為政者的道德修養及其表率作用,以三皇五帝為典范,不同于“以禮義治民”以三王為典范的“德教”。唐初詩文書寫中頻繁出現的堯舜記憶以及太宗對君王德行的自覺,均可視作此政治理念的文學表達⑥參見劉順《構建共同體:唐初的堯舜記憶》,《西北師大學報》,2015年第1期。。對于人性的認可,為貞觀朝構建歡洽和樂、溫情脈脈的道德共同體的嘗試提供了可能⑦“朕以隋末亂離,毒被海內,率土百姓,零落殆盡,州里蕭條,十不存一,寤寐思之,心焉若疚。是以日昃忘食,未明求衣,曉夜孜孜,惟以安養為慮。每見水旱降災,霜雹失所,撫躬責己,自慚德薄。……比聞刺史以下及百姓等,并識朕懷,逐糧戶到,遞相安養,回還之日,各有贏糧,乃別賫布帛,以申贈遺。如此用意,嘉嘆良深。一則知水旱無常,彼此遞相拯贍,不慮兇年。二則知禮讓興行,輕財重義,四海士庶,皆為兄弟。變澆薄之風,敦仁慈之俗,政化如此,朕復何憂。”李世民:《唐太宗全集·勞鄧州刺史陳君賓詔》。,而大國光華的書寫與傳播則勾畫著共同體的理想藍圖:
時雍表昌運,日正葉靈符。德兼三代禮,功包四海圖。
逾沙紛在列,執玉儼相趨。清蹕暄輦道,張樂駭天衢。
拂蜺九旗映,儀鳳八音殊。佳氣浮仙掌,熏氣繞帝梧。
天文光七政,皇恩被九區。方陪瘞玉禮,珥筆岱山隅。
—岑文本《奉和正日臨朝》
四海一家的想象與標榜,在中古時期的政治語境中,關涉地方性政權自我正統化的正當性論證,同樣也是帝國時期懸設遠景,以證成性之承諾,贏獲社會認可的重要方式。四海一家、王化無外的頻繁表述,在強化帝國政治之基本理念的同時,也會深化社會對于時代的感受與想象,并進而影響時代文學的格局養成—一個過于強調分化與邊界的時代,無法培育滋生浪漫高華的文學。雖然,初唐文學典重有余而風神不足,但其所展現之氣象,卻昭示著政治文化對于文學的期待。自典午南渡至李唐肇建,華夏的動蕩分立已逾三百載,四海一家的想象實凝聚了南人、北人對于安定生活的共同期待,但是文質彬彬的遠景藍圖卻必須經由先質后文而文質彬彬的特定程序方有實現之可能。
唐初“任德教”,由質而文,董仲舒之影響痕跡宛然。而其構建共同體的理想程序,同樣可以在董氏的學說中尋得痕跡。董仲舒的公羊學有所謂“三世異治”之說,衰亂之世,“內其國而外諸夏”;升平世“內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董氏此說實建基于戰國以來秦漢帝國的版圖構建與華夷互動的歷史事實①參見邢義田:《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征意義》,見邢著《天下一家—皇帝、官僚與社會》,中華書局,2012年,84~134頁。,然考之李唐建國時所面臨之局勢與建國之過程,漢唐之間,差異無多。李唐皇室本屬關隴集團,其取天下亦為據關中以討山東。及李唐立國,取“據關中以馭天下”之策,以關中為本位,符合“內其國而外諸夏”之說。但“內諸夏”卻需有效彌合三百余年來的政治與思想文化乃至日常生活慣習之間的差異。淡化邊界,在南北向心的基礎上再建認同,對于李唐而言,則必須打破關隴本位,在國家與社會的互動中,尊重并順應社會對國家的期待:
時已平矣,功已成矣,然而刑典未措者何哉?良由謀猷之臣,不宏簡易之政;臺閣之吏,昧于經遠之道。執憲者以深刻為奉公,當官者以侵下為益國。……強本弱枝,自古常事,關河之外,徭役全少,帝京之輔,差科非一,江南河北,彌復優閑,須為差等,均其勞逸。今公主之室,封邑足以給資用,勛貴之家俸祿足以供器服,乃戚戚于儉約,汲汲于華侈,放息出舉,追求什一,公侯尚且求利,黎庶豈覺豈其非,錐刀是競,實由于此。②高馮:《上太宗封事》,《唐會要》卷五五。
共同體認同的構建,通常依賴于以祖源記憶為核心的類血緣情感的構造,故而族群融合的腳步總伴隨著特定“歷史知識”的傳播、變形與再造。但類血緣的情感認同須與資源共享的利益認同配套共組,方能行之久遠,而更以后者為其根本。資源共享既可存在于區域間的利益分配與均衡層面,同時也會具體化為上下階層間的共存格局。從地域性的集團領袖向大一統國家治理者身份的過渡,意味著其身份公共性的放大。帝國的認同度首先取決于國家對社會的順應③關于“社會”與“國家”的理解,參見牟發松《國家對社會的順應和社會的國家化—漢唐歷史變遷中的生活與國家關系及其變動的基本特征》,《社會科學》,2011年第7期。,以及由此展現出的官僚群體的道德性及超越地域與身份限制的官僚體系的開放性。雖然,在唐初高層官僚的組成中,關隴之比重遠超山東與江左,高祖、太宗于不同出身之官僚亦意有輕重,但“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時代卻已然到來。而作為社會運作成本的實際承擔者,底層的生存狀況與生存感受乃是帝國盛衰的風向標符。唐初詩文中流露的民本意識及對西漢文帝故事經典化,既是為政者對為政之難的清醒,在另一層面也可看出國家在順應社會的同時,強化著對于社會的整合:
氏族之盛,實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義。自有魏失御,齊氏云亡,市朝既遷,風俗陵替。燕趙右姓,多失衣冠之緒;齊梁舊族或乖德義之風。名雖著于州縣,身未免于貧賤。自號膏粱之胄,不敦匹敵之儀,問名惟在于竊貲,結縭必歸于富室。……自今以后,明加告示,使識嫁娶之序,合乎禮典,稱朕意焉。①李世民:《唐太宗全集》,第444頁。
社會與國家之間的互動不僅有眉目傳情的兩情相悅,也有橫眉冷對的遠離與抗拒。但因國家在符號與道德資本上的優勢,相較于對社會的順應,國家強制整合社會方是互動的主要模式。以道德的名義,崇尚“冠冕”,太宗試圖以政治的認同統合社會的認同取向。隋唐是世族政治的晚期,太宗《氏族志》的修訂,自是對歷史潮流的借勢,門閥政治的榮光黯淡,曾經以為標榜的“金縷玉衣”式的文學②參見林曉光:《王融與永明文學—南朝貴族及貴族文學的個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六章。,也將逐步讓位于“平民式”的文學,大型類書的修訂與流行詔示一個崇尚知識簡易化與實用化時代的來臨,個人的才氣縱橫更易贏得社會的關注與贊譽。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大一統時代的內在邏輯,恰恰是對古典型知識的趣味淡化。而核心文體由“賦”向“詩”的逐步過渡,也同步于時代文化趣味的轉換。都城詩自然而然地開始嘗試替代曾經以彰顯“上國光華”為主要功能的都城大賦:
二華連陌塞,九隴統金方。奧區稱富貴,重險擅雄強。
龍飛灞水上,鳳集岐山陽。神皋多瑞跡,列代有興王。
我后膺靈命,爰求宅茲土。宸居法太微,建國資天府。
玄風葉黎庶,德澤浸區宇。醒醉各相扶,謳歌從圣主。
南登少陵岸,還望帝城中。帝城何郁郁,佳氣乃蔥蔥。
金鳳凌綺觀,璇題敞蘭宮。復道東西合,交衢南北通。
萬國朝前殿,群公議宣室。鳴佩含早風,華蟬曜朝日。
柏梁宴初罷,千鐘歡未畢。端拱肅巖廊,思賢聽琴瑟。
逶迤萬雉列,隱軫千閭布。飛甍夾御溝,曲臺臨上路。
處處歌鐘鳴,喧闐車馬度。日落長楸間,含情兩相顧。
是月冬之季,陰寒晝不開。驚風四面集,飛雪千里回。
狐白登廊廟,牛衣出草萊。詎知韓長孺,無復重然灰。
—袁朗《和洗掾登城南坂望京邑》
共同的苦難記憶會強化共同體的情感凝聚,而輝煌歷程的參與感及圍繞其周邊的榮譽分享感同樣會增進共同體的向心力。在中古時期的都城書寫中,洛陽具有“洛州無影、天下之中”的崇高地位以及東漢以來長為政治中心的歷史傳統,故而唐初的都城詩賦,亦隱含著政權合法性的論證企圖。袁朗的長安詩有著明顯的都城大賦的痕跡,這座占盡天時、歷史悠長而光輝奪目的都市,炫耀著大唐應天順人的榮光。萬國來朝的京城凝聚著唐人的盛世想象,也迎來送往著異域的“他者”,太平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的理想,似乎就在眼前。
共同體的存在依賴內在的情感認同與資源平衡,但一條無法抹除的邊界是共同體存在的“確證”,唐初構建大一統帝國的實踐,必然地要遭遇對于“邊界”的認定以及對邊界之外的非我族群的認識與理解。“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于枝葉。擾其本根,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自陛下君臨區宇,深根固本,人逸兵強,九州殷富,四夷自服。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①李大亮:《請停招撫突厥疏》,《貞觀政要·安邊第六三》。李唐是一個大一統的時代,也是一個胡漢關系重新調整與定位的時代,曾經的他者已成為把臂言歡的兄弟,塞外的土地上似舊而新的族群以及更為遙遠之異域中的“化外之民”,才是唐人眼中的胡人。是“此疆彼界”,還是“王化無外”,唐初胡漢關系的處理,總繞不開基本策略的認定問題。雖然“王化無外”的目標在中古時代,過于理想,甚至空幻,其強制推行所帶來的成本危機,也在提醒著“此疆彼界”的合理與現實,但太宗“視天下如一家”的態度表達與政治實踐,卻在一個存在交通障礙的時代,營造出以漢文化為核心的高度“國際化”的前現代生活,“天下遠近大小若一”的太平盛世,也似乎即在眼前:
玄奘輒隨游至,舉其風土,雖未考方辨俗,信已越五逾三。含生之疇,咸被凱澤;能言之類,莫不稱功。越自天府,暨諸天竺,幽荒異俗,絕域殊邦,咸承正朔,俱沾聲教。②玄奘:《大唐西域記校注》,季羨林等校注,中華書局,2012年,第32頁。
無論“咸承正朔”以及“愿身死作中華鬼,來生得見五臺山”③《長安辭》,任半塘:《敦煌歌辭總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85頁。是歷史的寫實,還是宗教徒諂媚的虛構,胡漢關系都已成為組建唐人政治、宗教以及日常生活的重要元素。而作為唐代詩文書寫的主要題材之一,胡漢關系也是觀察李唐國運盛衰的晴雨表。歷經三百余年的動蕩,華夏民族又一次成為“天下”文明的引領者,貞觀文壇稱頌著偉大的時代,也在描繪著制禮作樂并最終達成“文質彬彬”的美麗遠景。
三、情志一也與興必取象:另啟新局的可能與途徑
武德、貞觀時期的文學,在唐人的接受史中居于邊緣,而在后世的命運依然。今日通行的文學史與批評史的章節安排,均可見出此時期文學的過渡特性。只是此種過渡特性,又通常會被視為南朝遺風,無論是古體溯源于陳子昂,還是近體歸美于沈宋,都無法為武德與貞觀文學安排一個恰當的過渡位置。即以技法層面而言,唐代前期流行的各類詩格,也大體出現于貞觀之后。今日尚存的武德、貞觀時期文獻,也似乎無法為“技法的自覺探究”提供支撐。而如若在“儒學與文學”互動觀照視角中,尋找可以支撐“過渡”標簽的解釋框架,此種“過渡”則依然需要回到觀念的層面。唐代是一個以“詩”為核心文類的時代,這既是后世批評傳統的疊加確認,也是文學與時代互動之內在邏輯的自然展開。故而在某種意義上,詩歌代表唐代文學所能抵達的高峰。后世論唐詩,或曰其“興象玲瓏”(《滄浪詩話》),或曰其“如旦晚脫筆硯者”④江盈科:《江盈科集·雪濤閣集·敝篋集引》,黃仁生校,岳麓書社,2008年。,或徑稱“唐詩以情勝,以自然意象勝”,相近的批評,提示唐詩成就的要點之一,即情與象。雖然,武德、貞觀時期的文學,在此兩點上并無特出的成就,但在觀念層面,“情”與“象”,卻屢被論及,故而,武德、貞觀文學對于有唐文學的影響實較詩格的技法研磨更為根本。
“情性”是儒學思想的另一對基礎概念,其具體的展現形態通常受制更為根本的“天人”觀念。先秦儒家雖在性之善惡問題上存有見解之差異,但大體認同,性自天出,“情”亦與生俱來而情中有欲①《禮記·禮運》:“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荀子集解·正名篇》:“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因“欲”之污名,“情”必須經一轉換,方能進入言詩與用詩之過程。
合樂,則工歌、笙入、間歌并作,而樂于是備矣。大用之于天下,小用之于一國,其于移風易俗,無自不可。況用之于鄉人乎?……工歌《鹿鳴》《四牡》《皇華》,所以寓君臣之教,則升歌三終也,笙入堂下,磬南北而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所以寓父子之教,則笙入三終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以寓上下之教,間歌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蘩》《采蘋》,所以寓夫婦之教,則合樂三終也。②馬端臨:《文獻通考·樂》引陳秧《樂書》。
中國早期之詩與舞、樂合而不分,服務于禮儀展演與教化之用。詩樂教化的目的本在于彌合紛爭,以營構有序而不失溫情的群體生活。人生而有欲,有欲而不知收斂則易生爭斗,故含欲之情,須經相應之過濾與節制方有公開展演之可能。《尚書·堯典》曰“詩言志”,后世以之為中國詩學開山綱領,然“志”亦為情之一種,或可稱之為情之理性化與公共化。同時,也因詩樂展演的儀式化,“志”之表現同樣須遵循合度的原則,此即所謂節之以禮。而儒家詩學對于鄭衛之音的拒斥,實因鄭衛之音,所傳遞之情感或過度私人化,或過度失中,不宜于公共場合的儀式展演,有悖詩教之用。《禮記·樂記》曰:“樂者樂也,人情所不能免也”,人生天地,感物生情,“夫物之代感人無窮,而人之好惡無節,則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滅天理而窮人欲者也。”情之流蕩,生無窮之欲,故先王之樂本于情性而能稽之度數,節之禮義。《毛詩序》雖倡以情言志,主志出于情,然情非志,以情言志即以志化情。而唐初政治文化多有取法的董仲舒之情性論中,董氏以“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陰陽也”③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凌曙注,中華書局,1975年。,“性”有善質而非善須待后天之教化方能為善。情雖亦因生而有,但“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故情乃惡之根源。時入魏晉,經學衰而玄學盛,圣人有情無情遂可討論,及陸機倡“詩緣情而綺靡”已欲與“詩言志”并轡通衢。故而,武德、貞觀之時,“情性”與“情志”的討論語境,較之天人、文質同樣復雜。唐初在此問題上所以引發后世學者之關注,要在“情志一也”理論的提出:
詩者,人志意之所之適也;雖有所適,擾未發口,蘊藏在心,謂之為志;發見于言,乃名為詩。言作詩者,所以舒心志憤懣,而卒成于歌泳,故《虞書》謂之“詩言志”也。包管萬慮,其名曰心;感物而動,乃呼為志。志之所適,外物感焉,言悅豫之志則和樂興而碩聲作,憂愁之志則哀傷起而怨刺生。《藝文志》云“哀樂之情感,歌詠之聲發”,此之謂也。正經與變,同名曰詩,以其俱是志之所之故也。④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6頁。
與陸機“詩緣情”之說出于士人之手為民間見解不同,孔穎達“情志一也”之說出自廟堂,由此可以推見“情”之位置在官方思想中的提升。儒家詩教中對于“情”的警惕與凈化,本源自于在缺乏制度約束時代,對共同體道德狀況的預期。故而,官方對于“情”的認可,其要因之一,實為律令體系的建設與完善及國家對社會整合能力的提升①“立法原理方面,在漢武帝史實獨尊儒術后,諸儒不斷鼓吹建立禮(德)主刑輔、失禮入刑的法則,初步實現于西晉泰始律、令,而確立于隋唐律、令。就這個意義而言,西晉至隋唐可說是先秦以來儒學在禮律方面最具體的實踐,并非如學界一般所說已經轉衰。”高明士:《律令法與天下法自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頁。。其要因之二,則為對“人情”乃教化與整合社會所以持久有效之基礎的認識。而“情”有風俗、情實之意,也可見出國家在整合社會時對于社會的順應。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太一之初。原始要終,體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資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漓,感陰陽而遷變,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喜怒哀樂之志,于是乎生;動靜愛惡之心,于是乎生。精粹者雖復凝然不動,浮躁者實亦無所不為,是以古先圣王,鑒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于德義。②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禮記正義序》,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頁。
人性本靜,感物而動,則為喜怒哀樂之志、動靜愛惡之心。性志乃一體一用,而此處“喜怒哀樂之志”實為喜怒哀樂之情,故“情志一也”,性情亦為體用,情在性中,性因情見。唐初“情性”常聯組出現,但因此體用關系,情為性之象,性之實際影響已遠不及情之重要③《晉書·文苑傳論贊》:“夫賞好生于情,剛柔本于性。情之所適,發乎詠歌,而感召無象,風律殊制。”《周書·王褒庚信傳論》:“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轉,銘誅與書論殊涂,而撮其指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為主,以文傳意。”。然而制度設計上的先天缺陷以及制度運行中的成本限制,讓對歷史興亡有敏銳感受的儒家士人,于為政者之道德猶念茲在茲:
并以中庸之才,懷可移之性,口存于仁義,心怵于嗜欲。仁義利物而道遠,嗜欲遂性而便身。便身不可久違,道遠難以固志。佞諂之論,承顏候色,因其所好,以悅導之,若下坂以走丸,譬順流而決壅。非夫感靈辰象,降生明德,孰能遺其所樂,而以百姓心為心哉?此所以成康,景千載而罕遇;癸、辛、幽、厲靡化而不有。毒被宗社,身嬰戮辱,為天下笑,可不痛哉!④姚思廉:《陳書·后主紀論》。
因為道德感的強勢在場,武德、貞觀時期的文學,其寫情者雖偶有涉及宮體之題材者,大體依然以表達極具公共性的情感為主,情與欲之間有著不可觸探的紅線。歷史興亡回眸中的感喟與時間長河中的物是人非是最常見的情感表達。對于“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發人意”⑤嚴羽:《滄浪詩話校釋·詩評》,郭紹虞校釋,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的有唐文學而言,唐初在情感觀念上的影響,最為重要的當不是對公共性的強調,而是對“真情”價值的認可:
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故神替有以知其趣也。設有言而非志,謂之矯情,情見于聲,矯亦可識。若夫取彼素絲,織為綺毅,或色美而材薄,或文惡而質良,唯善賈者別之。取彼歌謠,播為音樂,或辭是而意非,或言邪而志正,唯達樂者曉之。……若徒取辭賦,不達音聲,則身為榮、封之行,口出堯、舜之辭,不可得而知也。⑥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第7頁。
情由物感而生,真情生長于真實的生命經驗,可以關涉家國天下,亦可囿于個體與家庭,“真”之與否在于感受者的內心判斷而非社會標準的外在量準,故而,孔氏之論,在觀念層面為李唐文學開拓了極大的言說空間。然人生之情,無論“七情”,抑或“六情”,為生人之所共有,對于詩歌而言,在情之層面,“如何言說”較之“言說何物”更為根本,唐初儒學所倡“興必取象”之說,則在技法層面為李唐文學提示了路徑選擇。《周南·樛木》以“南有樛木,葛藟累之”起興,毛傳曰:“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南土之葛藟茂盛。”孔穎達疏傳云:“興必取象,以興后妃上下之盛,宜取木之盛者。木盛莫如南土,故言南地。”①李學勤主編:《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第41~42頁。五經孔疏,論興象者,在在多有,如“興取一象”“喻必取象”等,對于唐詩之影響功莫大焉。②鄧國光:《唐代詩論抉原:孔穎達詩學》(《唐代文學研究》第7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詩興、易象、譬喻于孔穎達說都是相通的。詩論史上‘興象'一詞,透過孔疏,可確定為譬喻的異名。這樣,‘興象'便可得到著實的診釋。盛唐殷璠的《河岳英靈集》標舉‘興象',作為診詩的稱衡,論者多以為遙接《文心》《詩評》之緒,究其實,孔疏興象論'相配,不出孔疏的范疇。即使流行于晚唐的詩格,也顯示了孔穎達的余影。”興必取象,講求情因象起,心物合一。王世懋論《黃鶴樓》、《鳳凰臺》之優劣曰:
崔郎中作《黃鶴樓》詩,青蓮短氣。后題《鳳凰臺》,古今目為勍敵,識者謂前六句不能當,結語深悲慷慨,差足勝耳。然余意更有不然,無論中二聯不能及,即結語亦大有辨。言詩須道比興賦,如“日暮鄉關”,興而賦也,“浮云”、“蔽日”比而賦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雖同,孰為當乎?“日暮鄉關”,“煙波江上”,本無指著,登臨者自生愁耳。故曰:“使人愁”,煙波使人愁,寧須使之?青蓮才情,標映萬載,寧以予言輕重?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竊以為此詩不逮,非一端也。如有罪我者,則不敢辭。③何文煥:《歷代詩話·藝圃擷余》,中華書局,2004年。
兩詩之優劣且不論,王氏所言比而賦與興而賦之別,正在情與物之是否融凝。盛唐之詩號“興象玲瓏”,即盛唐人之自評,亦以“興象”為標準之一。“興象”之說,為唐詩突破齊梁舊格之偏擅聲色物象,提示了路徑可能,此亦儒學于唐詩之一重要貢獻。興必取象重在意象之營構,但以全詩結構之整體而言,興必取象成功與否,既依賴于意象話語與推論話語之間的平衡,復決定于語義對等原則的處理④參見高友工、梅祖麟著,李世躍譯:《唐詩三論》,商務印書館,2013年。,而這對于近體具有主題雷同、內容單薄且格調偏淺俗輕靡之“南朝舊習”的武德、貞觀文壇來說⑤葛曉音:《先秦漢魏六朝詩歌體式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33頁。,責任似乎過于沉重,此一歷史難題的解決將是沈宋時代的使命⑥“沈宋時代”的命名參考了吳光興《八世紀詩風—探索唐詩史上的“沈宋的世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導言部分。。
唐初三十年的文學,無論是創作的成就,還是技法的研磨多難以在唐代文學史上留下令人矚目的印痕。但唐初君臣在構建大一統帝國過程中的政治文化建設的自覺,卻為李唐文學開一代之規模,其天人、文質以及情性、興象等觀念為唐文學或提供觀念支撐或提供路徑指引,影響可謂深遠。中唐時代的文學雖然展現出新的變化,但其內在理論卻并未悖立唐初的框架,甚至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在儒學影響持續的時代,以上的框架均有其重要之影響,而思想與文化的突破與轉型也應自此視角加以觀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