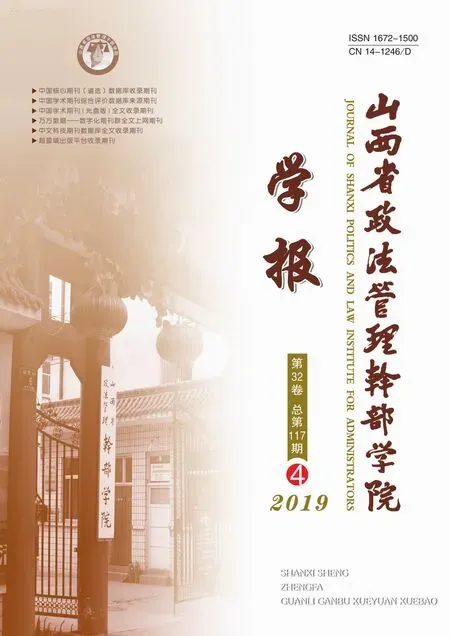刑事責任年齡制度問題與解決方案淺析
景沛梁
(華東政法大學 刑事司法學院,上海 201620)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十七條規定:“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犯罪,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因不滿十六周歲不予刑事處罰的,責令其家長或者監護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時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養。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刑事責任年齡是基于刑事責任能力的,其本質在于行為主體是否具備完全或部分辨認與控制自己的能力,而年齡作為最直觀的體現,其可以反映個體的生理、心理發展是否成熟,相應的就包括了是否有辨認與控制自己的能力,因而采用刑事責任年齡制度是大體上比較準確、比較快捷的認定主體刑事責任能力資格的方法。
一、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目前面臨的困境
刑事責任年齡設立的依據不僅僅是作為表象的年齡,更本質的應該是其背后的辨認與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同樣要受到生理發育、心理發展、受教育程度、生活環境、社會環境等多方面影響。自1979年刑法將刑事責任年齡相關規定確定下來之后,到現在四十年間沒有出現過變化。眾所周知,在這四十年間,我國無論是國情還是社會環境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新興傳播媒介崛起,互聯網迅速普及,智能手機、電腦被廣泛使用,義務教育全面落實。與之相應的,現代未成年人可接受的信息量大大增加,接收信息的速度大大加快,其對于社會、周圍環境的認知也在快速進步,因而其辨認與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相較于四十年前的同齡人要發展的更加全面。
從身體發育狀況來看,有資料顯示我國少年兒童的生理發育總體上比改革開放前普遍提高了一至兩年。[1]從心理發育狀況來看,青少年的叛逆期和成熟期都有所提前。皮亞杰學者證明了從12歲開始青少年出現抽象思維,可以對思維形式與內容予以區分,并開始運用邏輯推理、歸納的方法以及開始具備思考虛擬假設問題的能力。[2]從中可以看出,相較于幾十年前,我國青少年越來越早熟,生理與心理的發育越來越提前。
同時,義務教育已經得到普及。在十四周歲之前,未成年人已經完整接受了小學教育,在此期間或多或少的接受了關于違法犯罪的教育,其辨認與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得到了相應的提高。當今的未成年人不再是對于違法犯罪行為一無所知,不需要對其惡劣行為負責的“小孩子”。
綜上所述,現代的未成年人關于違法犯罪的認知得到了很大的進步,其辨認與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相較于以前的同齡人有了很大的提升,但刑事責任年齡依然未改變,這與其設立依據不匹配。刑事責任年齡制度沒能與時俱進,使得其陷入困境與尷尬。
二、我國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可行性
隨著犯罪低齡化趨勢越來越盛,未成年人犯罪問題日益凸顯,犯罪惡劣程度急劇上升,社會越來越關注未成年人犯罪問題,同時對于犯極其嚴重罪行而由于未滿十四周歲免予承擔刑事責任的情況表現出很大的不滿,對于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呼聲也越來越高,那么單純降低刑事責任年齡在我國是否可行呢?
首先,降低刑事責任年齡,與未成年人保護法的方針、原則相悖。在對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責任的指導思想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三條規定:“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可以看出,對于未成年人,我們堅持的是讓其能夠通過教育、感化、挽救的手段重新回歸社會,融入社會,最終使得其可以健康地成長,正常地生活,而不是僅僅為了懲罰而懲罰。單純降低刑事責任年齡顯然不符合這一原則。未成年人與成年人有許多不同之處,其對于自己的行為大多沒有清醒的認識,思想單純,難以控制自我,直接要求其對自己的行為負責,接受嚴厲的刑罰不僅不符合對未成年人的刑事政策的宗旨,也不利于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發展。同時,未成年人的認知方式、思維模式還未定型,世界觀價值觀還處于形成階段,其改變相對于成年犯罪人來說要容易很多,因此教育感化的作用也要大于單純懲罰。
其次,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主要依據即未成年人辨認與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標準難以界定。對于未成年人辨認與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判斷中主觀因素占很大比重,不能僅憑借人們的模糊感覺與自我認識、媒體輿論的導向就認為青少年這一能力有所提升。對于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設置,自古至今一直存在著爭議,規定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本質依據即未成年人的辨認與控制自己的能力很難有一個科學的、確切的標準,相應的最低刑事責任年齡也不應該輕易降低。
青少年尚處于人格成長與完善的過程中,在這一進程中,青少年對自我行為的思考往往是簡單的,與青少年自己的思考相比,社會風氣、學校教育、家庭影響往往對青少年行為的導向作用更大。換言之,青少年進行違法犯罪行為很可能是社會的影響,學校、家庭的教育出現了偏差,這時將最低刑事責任年齡降低,把對青少年進行懲罰作為遏制手段,無疑是在拋卻與故意忽視社會、學校、家庭自己的責任,而單純地讓未成年人去承擔本不應該由其擔負的社會責任,這本身就是逃避社會責任的表現。
三、英美法系的“惡意補足年齡”規則
惡意補足年齡規則是英美法系國家判斷未成年人刑事責任能力的方式之一。在英美法系國家,法律推定一定年齡段范圍內的未成年人不具有刑事責任能力,但該推定可以被推翻,如果控方舉證證明特定未成年人在實施嚴重不法行為時具備“惡意”,意識到行為的錯誤性且故意為之,則視其已達到刑事責任年齡,該未成年人需對其實施的嚴重不法行為承擔刑事責任。此即“惡意”補足“年齡”。[3]可以看出,在這一原則中,惡意是這一原則的核心內容,其使得關于刑事責任年齡的規定不那么刻板,而是多了一些靈活運用的意味。
那么這一為英美法系國家所青睞的規則優勢又在哪里?可以看到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就是將刑事責任年齡的“死規定”變得靈活起來,給予司法工作人員更多的裁決權,這樣一來就可以彌補刑事責任年齡可能單純看年齡而忽視本質的缺陷,從而使得青少年司法制度更加完善以及使得公眾更加信服。
四、現行刑事責任年齡問題的解決方案
既然單純降低刑事責任年齡的方案不可行,那么建議借鑒英美法系國家的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在我國建立相對的彈性入罪制度。彈性入罪制度,即參考惡意補足年齡規則,當未滿最低刑事責任年齡的未成年人犯了極其嚴重罪行,證明其有顯著的惡意時,可以推翻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制度,對其行為進行定罪。與之相應的,應該同時解決惡意的認定標準,確定惡意的手段。
首先,確定惡意的認定標準。惡意作為人的主觀想法的組成,本身難以界定,需要有明確的參考,那么與行為密切相關的應該是罪名及其法定刑了。因此可以將罪名及法定刑作為惡意的認定標準。犯罪構成要件中,主觀方面是必要構成要件之一,其中包含了犯罪人的惡意及其行為的惡性程度,法定刑的輕重更是直觀體現了相應罪行的嚴重程度。
其次,確定惡意的手段。即使可以通過罪名與法定刑作為惡意的認定標準,但罪名與法定刑本質上是客觀上的認定,作為主觀方面的惡意同時應該具有其他確定的手段。可以使用相關的調研報告與測試量表作為惡意的確定手段。第一類可以采用的報告即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未成年人社會調查報告是我國法律明確規定、司法實務部門廣泛認可的證據形式,其中包括未成年人的個人資料,受教育經歷、家庭環境、生活環境、歷史表現、犯罪情況等等一切與之相關的資料,這樣一份內容詳盡全面的報告可以充分客觀地體現出未成年人行為背后的動機、性格因素、環境影響等等,從中分析主觀上的惡意可以做到更加準確與科學。第二類可以采用的測試量表即針對犯罪心理結構的測量量表。目前應用較為廣泛的包括個性測量表與專門用于犯罪人的量表,個性測量量表包括明尼蘇達多項人格測驗量表(MMPI)、卡特爾16項個性因素量表(16PF)、以及艾森克個性問卷(EPQ);關于專門用于犯罪人的量表包括最早使用的1928年美國伯吉斯的假釋成敗預測研究以及目前我國上海市監獄1994年出版的《犯罪心理素質測定量表》。這些量表都是經過大量社會實踐制定出來的,因此可以通過這樣的心理測量方式作為確定惡意的手段。
可以看到,相較于單純降低最低刑事責任年齡可能會帶來的時間問題與影響,現在已經具備了建立相對彈性認罪制度的基本條件,建立這一制度不失為一種解決或者說減緩未成年人犯罪情況嚴重的好方法,但是要踐行這一方法,對我們的司法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是司法人員的職業素養。即使有調研報告與測試量表的幫助,但惡意的認定是主觀方面的,這對于從事認定工作的司法人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司法人員不能僅僅是對法條有所理解,更重要的是理解法條制定背后的法理知識,了解法理學、法哲學的基礎,對于法律的本質,設立的目的有更好的把握,才能結合法律對于相關的未成年人案件作出相應的裁決,而不能是僅僅根據法條內容而死板地斷定。
二是在惡意的認定中罪名的選擇,即要注意這一彈性制度的適用范圍。目前我國的刑事責任年齡制度中,已滿14周歲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只有在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時需要承擔刑事責任,這一制度作為14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入罪判斷依據,其適用范圍應該顯著小于或等于14—16周歲未成年人承擔刑事責任的罪名范圍,否則很有可能造成司法的濫用。
三是在裁決未成年人需要擔負刑事責任之后對其采取的刑罰問題。對于未成年人首先須有其專屬的監管場所,尤其是14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否則在學習模仿能力極強的年紀,很容易在獄中出現“交叉感染”的情況。同時相較于14—16周歲的未成年人,14周歲以下的未成年人很可能難以脫離監護人而獨自生活,需要監護人的長時間陪伴,因此在相應的制度上應當對其生活予以特別地照料。
五、結語
筆者所主張的是對于目前未成年人犯罪低齡化、暴力化、嚴重化的問題,單純降低刑事責任年齡是拋卻社會責任的表現,同時也會引發很多后繼性問題,因此可以考慮參照英美法系國家的惡意補足年齡規則,在我國建立相對彈性制度,希望可以通過國家機關的干預,更好地對未成年人進行教育、感化、挽救,從而使其健康成長,順利融入社會。與之相應的,在制度方面我們可以建立彈性制度并在適用過程中不斷改進與發展,同時也要配套相應的措施,提高司法人員的職業素養,明確制度適用范圍與方式,完善監管體系,為未成年人犯罪提供完美的解決方案,確保每一位未成年人都能健康成長,順利地步入社會進行正常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