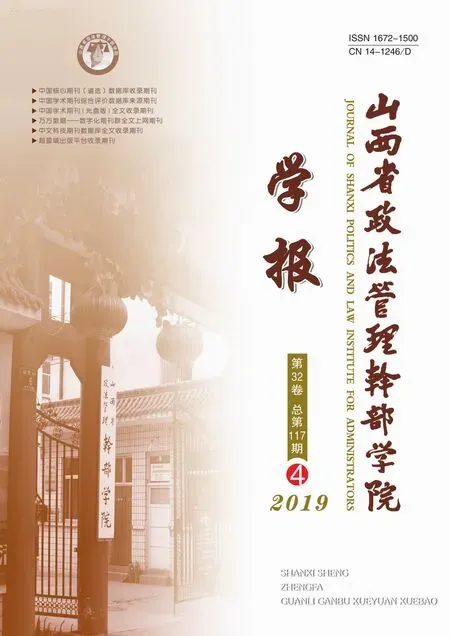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完善
何旻鈺
(江南大學 法學院,江蘇 無錫 214122)
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法律規定
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后,各部門法隨之進行了相應的完善,將保障人權的精神體現于立法中。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將排除非法證據確立為一項具體的程序規則。2012年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吸收了這兩個規定的相關內容,對非法證據排除的對象、訴訟階段、程序、證明責任及證明標準等作出具體規定。之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分別出臺了相應的司法解釋對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具體適用進行細化。由此,我國刑事訴訟中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體系得以大致確立。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刑法室編寫的《〈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條文說明、立法理由及相關規定》可知,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立法目的是“為從制度上進一步遏制刑訊逼供和其他非法收集證據的行為,維護司法公正和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利”。而實踐中,無論在制度實施或是目的貫徹方面都存在問題。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實際運用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運用需要經過申請、啟動、排除的環節,而現實生活中存在著不積極申請、申請后難啟動、即使啟動也沒什么效果等問題。
(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啟動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制度的啟動涉及兩方主體——法院和被告方,但雙方出于各自的原因在啟動上都不積極。從法院一方來看,首先,雖然理論上法院可以依職權啟動,立法卻并未詳細規定啟動程序,實質上使得制度無法實施。其次,因為程序一旦啟動會牽涉到調查等一系列環節,導致訴訟進程被拖延,法官考慮到審限等問題,迫于繁重的業務壓力,本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則,通常情況下不會主動提出,會采取一些諸如補正的方法將其合理化,這些都導致依職權啟動這一構想難以落實。
對于被告方而言,可以主動提出申請,由法院審查決定是否排除,但現實中往往會選擇不提出申請。首先,被告方主要關心定罪量刑方面的問題,擔心因提出排除非法證據而被認為認罪態度不好而選擇不提出。其次,雖然被告人對非法證據排除享有知情權,法院在送達起訴書副本和首次訊問被告時,都會告知被告有申請排除非法證據的權利以及具體如何申請,但在此背景下仍難得到合理運用。其一,被告方對如何運用不很清楚,往往與一般質證混淆,提出不正確的申請勢必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其二,被告方往往缺乏法律知識,其律師又不能對偵查機關的活動進行合理監督,難以保存證據,即使權利受到損害也不能提出有效證據佐證自己的主張。最后,長期以來司法機關與被告人之間存在相互不信任的對立關系,為防止非法證據排除制度被利用而成為拖延訴訟進程的工具,立法在啟動程序和舉證責任方面對其進行了嚴格的限制。在啟動程序方面過于嚴格,被告人申請后須經司法機關審查決定是否啟動非法證據排除的程序。在舉證規則方面對被告人有強人所難之嫌,《最高法院解釋》第九十六條的規定,當事人及其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申請人民法院排除以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的,應當提供涉嫌非法取證的人員、時間、地點、方式、內容等相關線索或者材料。畢竟人身都在偵查機關的控制之下,即使被刑訊逼供也難以保存證據。因為實踐中即使提出申請也不一定能被排除,即使排除也不一定對定罪量刑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實際效果不佳使得其積極性不高。
(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排除
從法院一方來看,首先,長期以來受實體正義重于程序正義的觀念影響,法官迫于壓力,為了不放過真正的犯罪人,不敢輕易將影響定罪量刑的證據排除。作為彌補措施,往往將其認定為瑕疵證據,令檢察院限期補正,但是這些證據根本上不能算作是瑕疵證據。因為《刑事訴訟法》和相關司法解釋規定,只有物證和書證存在瑕疵時才可以通過補正或合理解釋的方式重新賦予其證據能力,并非所有證據都可采用此方式補正。[1]其次,制度規定不合理,能被認定為需要排除的非法證據只是所有以非法方式獲取的證據中的一部分。比如,在所有非法證據中,突出對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而非法言詞證據只是非法獲取的證據的一小部分,即便取證方法違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規定,能否被確認為非法言詞證據,還要取決于其是否達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非法獲取的物證、書證認定為非法證據則通常須同時具備三方面條件:收集過程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不能補正或作出合理解釋,導致非法證據的范圍十分狹窄。
立法對非法證據范圍的規定過于狹窄,而對于瑕疵證據的補正則規定的過于寬泛,似乎有一種傾向于引導法院在審判時盡可能少認定為非法證據,而多認定為瑕疵證據通過補正的方法肯定其證明力,這與制度設計本身的目的并不相一致,不能達到立法目的。而且對于 “瑕疵證據”與 “非法證據”的界限、補正是否到位、解釋是否合理,法律賦予了司法機關幾乎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權。[2]這些都可能造成制度實施中對立法目的的偏移。實在不能補正時公訴方會在法官的配合下放棄該份證據,雖然存疑的證據未被采用,但也放過了偵查機關和公訴機關在獲取證據時可能存在的不合法行為,失去了制度設計時希望對其起到的監督作用,不利于其依法履行職責。即使被認定為非法證據排除后,結果也不盡如人意。據一份實證研究的統計數據來看,很多時候雖然非法證據被排除了,但并沒有對案件處理結果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因為并未規定排除重復供述,法官仍然可以通過采納其他重復供述對案件事實進行認定,和不排除沒有什么區別。
事實上,只有在排除后不影響案件的實際處理結果的情況下法官才會選擇排除,如果真的出現了足以影響定罪量刑的非法證據,則不會選擇走此程序。[3]對實體正義的過分強調使得法官不敢在非法證據排除上發揮太大的主觀能動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制度的有效實施。
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之完善
非法證據排除制度要在我國有效發揮作用,需要由上至下很多方面的調整。
首先,一個事物的發展需要各方面適宜的條件,包括經濟基礎、政治制度、文化影響、社會生活觀念等等,如果不加分析和改變地移植國外很可能達不到預期效果,非法證據排除制度也不例外。非法證據排除制度來源于英美法系,英美法系強調程序的重要性。他們認為雖然實體正義會受到主客觀因素的影響不能保證,但程序正義是能夠做到的,在有效保證程序正義的情況下才談得上實體正義。無程序正義即使實現了實體正義也只是偶然,沒有意義。但是在我國正好相反,無論是歷史原因、出于維護社會秩序的需要,還是人民樸素的正義觀影響,實體正義都重于程序正義。在偵查手段不夠發達時,出于維護社會秩序的需要,即使造成冤假錯案也要嚴打,這是一種價值取向上的問題。長久以來,我們一直有一種固有的觀念——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不值得尊重和保障。比如杭州保姆案一審判決后被告人上訴,絕大多數網友認為她罪大惡極,對她提出上訴感到不可思議。還有不少人質疑疑罪從無的合理性。此外,存在廣為詬病的司法行政化、地方化,這與英美法系有較大不同。英美法系的法院是司法機關,獨立性較強,而我國的法院更多的是作為審判機關,在經濟等方面不同程度受到地方政府的制約,不能做到完全獨立。偵查、公訴、審判三機關同為國家機關,雖然分工不同,但履行職務時存在密切的聯系,法院難免會傾向于將他們認為是“自己人”,而排斥被告人,將被告人視為對立面。這些問題由來已久,要想改變會牽涉諸多問題,需要漫長的過程。有學者認為,推動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完善與實施,除應建立起對規則的理性期待并合理調整規則的內容外,關鍵在于法意識形態的轉型及刑事司法權力的優化配置。[4]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披著個人權利保障外衣卻包裹著國家權力本位的規則,其解決需要社會性結構因素的調整。因此在我國,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發展的土壤還不夠完備,生搬硬套、強行推行是不行的。
其次,切實可行的制度是必不可少的,無論是制度本身還是配套制度。一項制度無論在設計時初衷如何,如果不切合實際,無法實際操作,不能達到其期望的效果。我國立法對非法證據排除制度的規定很粗糙,并且在非法證據的范圍、舉證責任的合理分配等方面,以及相應的配套制度,如法官的考核制度存在諸多不合理之處,需要逐步進行完善。法官考核制度中為實體正義服務的錯案追責制影響了程序的啟動和運行。排除非法證據未納入考核,該程序的運行必須等待公訴人提交證據,會耗費大量時間,影響考核,所以實踐中法官傾向于通過“做工作”的方式來勸解當事人不申請或撤銷排除非法證據申請,即便提出申請法官也只是酌情進行證據收集合法性的調查。[5]法官迫于制度壓力不能很好地發揮主觀能動性,制度上自相矛盾的規定影響了其實施效果。因此需要進一步明確非法證據的具體內容,制定合理的考核指標,以便于實際操作。有學者認為,既然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最終目的在于遏制違法取證,面向程序的事前預防性規則更有實效,因此建議將直接面向事實的事后制裁規則轉變為一種面向程序的事前預防規則。[6]實際上也是一種對現有規定的細化,將不符合規定的情形推定為存在以非法方法收集證據的情形。
在逐漸意識到制度適用困難的情況下,我國對結構設置和配套制度進行了一系列的調整。比如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又如,2015年1月20日召開的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作出的全面清理各類司法考核指標,堅決取消有罪判決率的改變。這些舉措都將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公檢法機關互相配合及偵查中心主義的體制與機制,弱化打擊犯罪的觀念性因素,從而為法院主動、敢于嚴格依法適用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撐環境。
最后,即使有了恰當合理的制度,任何新鮮事物都需要一定時間的適應和磨合,只有給予一定時間適應才能逐步被接受,這是一個長期發展的漫長過程。只要不斷進行符合實際的制度完善,相信假以時日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能在我國發揮應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