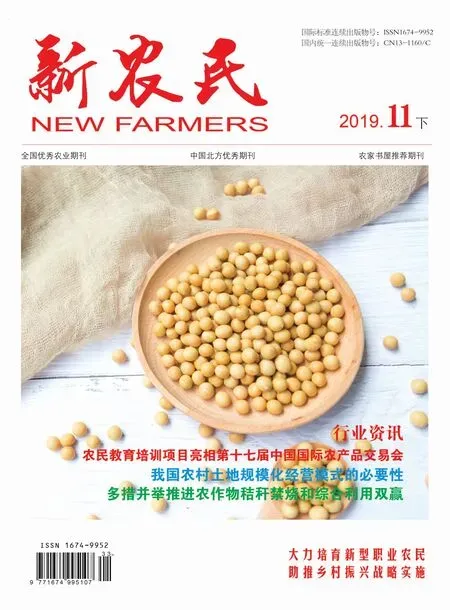梳理鄉村治理困境 健全鄉村治理體制
陳 麗
(柳江區委黨校,廣西 柳州 545001)
1 當前鄉村治理面臨的困境
1.1 基層黨組織建設令人擔憂,工作推進受阻嚴重
農村基層黨組織起著戰斗堡壘作用,它的日常工作是通過直接接觸村中的細小事,具有非規則化、瑣碎化的特點。一旦基層黨組織中的“軟弱渙散”缺陷出現,不利的后果隨之出現,它包括有組織覆蓋“空”、組織職能“虛”、組織監督制度不佳等。這樣不利后果帶來的直接影響是“村民的要求傳達不上去,上面的政策執行不下來”。鄉村基層黨組織是“人體末梢神經”,末端一旦不通暢,必導致上下執行受阻,基層組織功能無法實現,嚴重阻礙鄉村政治的健康發展。
此外,它還受制度自身不足的影響。基層村級組織面對著諸多對其發號施令的上一級部門,使得“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的局面出現。農村基層組織擔負著與它職責極不對稱的工作壓力,負面情緒與不利因素出現,導致基層組織內部建設無法順利推進,治理效果不佳。
1.2 鄉村治理主體外流嚴重,村民參與積極性低
鄉村的各類資源外流,特別是鄉村人力資源流向城市,農村大量年輕勞動力外出,鄉村“空心化”問題嚴重。村中大多留守的是老人、婦女和兒童“993861”人口組合留守在鄉村。《中國農村發展報告(2019)》中顯示外出農民工都是青壯年,占村人口比重高達40%以上,導致農村治理主體大概率留失。留守老人、婦女和兒童無法承擔鄉村治理的重任之外,他們甚至無法對鄉村治理公共事務做出貢獻,身心都無法參與治理。
1.3 傳統鄉村社會秩序發生變化
傳統鄉村社會秩序建立在互相信任基礎上,通過村中有威望的“鄉賢”“鄉紳”帶領下實現自我管理、自我控制,鄉村生產生活秩序得以維護。但隨著市場經濟發展特別是城鎮化推進,功利主義、個人主義價值觀沖擊著集體主義,打破“幫助互利”“交換團結”的互信關系,導致基層工作和公共建設難以推進。村民與鄉村之間的利益聯結越來越弱,村民參與治理的興趣不高,積極性低。
2 完善鄉村治理體制建設
2019年《關于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的指導意見》中強調,加強和改進鄉村治理要建立和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現代鄉村社會治理體制,抓基層黨組織,整頓軟弱渙散村黨組織,選好配強農村黨組織帶頭人,深化村民自治實踐,發揮農民在鄉村治理中的主體作用,傳承發展農村優秀傳統文化。以此總體要求作為指導,針對基層鄉村治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以下幾項完善措施。
2.1 基層組織建設“三治”結合,提升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力
“三治”結合指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的結合。它的方式采用多管齊下,三者高度融合共治,以解決基層組織建設中出現的復雜問題和錯綜關系,運用單一治理模式是達不到這樣的效果。“三治”結合更強調多要素之間的綜合影響,即自治利于實施,法治利于穩定,德治利于功效的立體成果,以實現鄉村社會快速發展,激發活力發揮基層黨組織陣地作用。
2.2 升級農村集體經濟,發揮經濟最佳紐帶作用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政治原理,用在鄉村治理過程中,可延伸為村經濟發展好壞決定了村治理的體系的完整與否。第一,通過經濟效益增長留住人。升級和壯大村集體經濟,形成長效發展機制,增長鄉村經濟效益。第二,通過吸收農村經濟型人才,發揮治理帶頭人作用。把土專家、田秀才、經濟能賢人聚集起來,發揮農村人才優勢,引導群眾發家致富。第三,發展村集體經濟解決農村集體經濟滯后性。構建集體經濟總量提升,分層次多方位擴展集體經濟合作方式,形成最優經濟創收以帶動鄉村治理建設。
2.3 增強村民集體利益認同感
在物質手段上通過收入增加,推動村集體認同感增加。除大力發展農業,實現“一村一品”的特色產業外,可結合發展農村一二三產業的融合,包括旅游觀光、農莊餐飲、農業住宿等,增加村民收入。在產業推動的下農村勞動力人口特別是青年骨干留下來參與鄉村治理建設,解決了治理主體缺陷問題。
2.4 創新鄉村管理方式
鄉村治理制度建設的創新是部署上的作用,在日常治理過程中,它主要體現在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的創新上。我區鄉村治理示范村中的戈茶屯,在制度創新上走在前列,在完善村民理事會制、村民議事代表制的基礎上,首創保潔員制度、水源清潔制度“—保兩治三清理機制”。此種創新方式既執行了制度,同時擴展村民自治管理內容,突出村民主體地位。村里無論大小事都可通過理事會方式解決,提高村民參與鄉村治理積極性;村民議事以戶代表為單位,有效補充村民參與村事的方式;保潔員制度和水源清潔制度的設置與實施,把生態環境建設與鄉村治理結合起來,突出人與社會、人與環境、社會與環境的有機關系。
2.5 引用多元主體治理體系,完善鄉村治理機制
第一,從行政管理到鄉村治理的轉變,強調在治理過程中采用多元主體的融合治理模式,它包括行政執行、意識交流、政治感染等過程中民主、參與、互動的結合;第二,多元主體中還強調個人最大效能的發揮,好人、能人、強人及精英的作用最大化。要讓他們記得住鄉愁的同時,想得起家鄉,用他們的影響力感染力給鄉村做貢獻。第三,活躍鄉村組織主體,包括農民合作社、民間組織、企業等,這些組織在資金上和技術上有巨大優勢,它們給鄉村建設助力不容小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