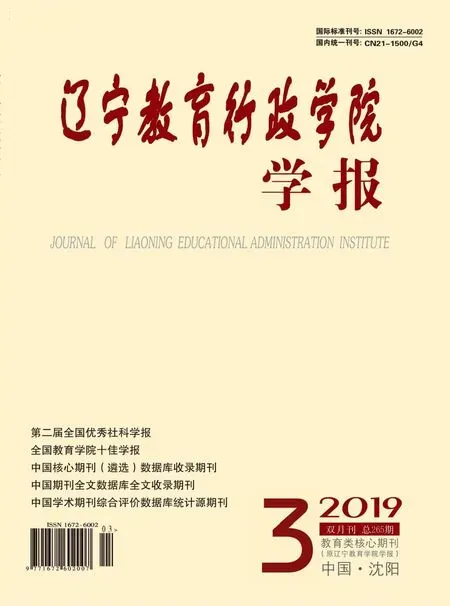從依附到自立:特殊教育立法的問題與前瞻
楊克瑞
南京特殊教育師范學院,江蘇 南京 210038
改革開放以來,國家日益加強對于特殊教育的頂層設計。特別是在2017年,《殘疾人教育條例(修訂稿)》正式頒布,《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計劃(2017—2020)》也發布實施。法規政策的雙輪驅動,助推中國特殊教育新的航程與未來。然而,在這些政策推動的背后,真正的“特殊教育法”,更加引發人們的期待。從深層次來說,中國特殊教育的未來發展,面臨著政策驅動與法律驅動之間的不同選擇,即國家如何面對有關特殊教育的政策與法律關系,這應當是未來中國特殊教育發展中進一步需要明確的基本戰略選擇。
一、特殊教育法制化的初步探索
從殘疾人教育到特殊教育,其概念的理解在理論上是有分歧的。可是在教育實踐中,“特殊教育”一詞更多的是被用于“特指”,即狹義的特殊教育,其內涵與殘疾人教育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此而言,作為殘疾人的特殊教育事業,世界各國大體上都是從民間慈善走向政府關懷、從政策引導走向法制建設的規范化路徑。中國特殊教育的法制化進程,基本上也經歷了相似的過程,法律體系逐漸完善,法制化水平逐步提升。[1](P80~83)從國家憲法層面到教育各系統的部門法,對于特殊教育問題都有一定的關注。然而,特殊教育法律體系化的背后,卻是“特殊教育法”單獨立法的滯后。特殊教育立法,更多的是借助或依托于相關法律而存在。這種依附狀態,又可以具體分為對憲法與教育基本法的依附、對教育部門法的依附,以及對殘疾人權益保護法的依附等不同形態。
(一)對憲法與教育基本法的依附
中國的特殊教育事業,最早是以西方傳教士的慈善活動為發端,依存于民間教育而開展,一直沒有形成國家層面的特殊教育政策與法規。這種局面直到新中國成立后才得到根本改變。1951年中央在《關于改革學制的決定》中正式明確:“各級人民政府應設立聾啞、盲目等特種學校,對生理上有缺陷的兒童、青年和成人施以教育。”這是中國政府首次將特殊教育列入國家的教育事業發展之中,對此后特殊教育的觀念確立,以及特殊教育事業的發展規劃,都奠定了重要的政策基礎。但是,建國初期的國家憲法,并沒有明確涉及有關殘疾人的特殊教育內容。
直至改革開放后的1982年,中國進行了新的《憲法》修訂。新《憲法》對于中國的政治前途以及人民的社會生活都產生了重要影響。其在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中的第四十五條明確指出:“國家和社會幫助安排盲、聾、啞和其他殘疾的公民的勞動、生活和教育。”這里將殘疾人的教育問題首次納入憲法,其在法理學上具有重要的意義。這是因為,對受教育權這一概念及其法律屬性,學術界是有爭議的。[2](P250)但是,作為本質上屬于“權利法案”的憲法,其內容也就成為了國家最為基本的“人權宣言”。正是從這種意義上,人們通常以憲法作為某項權利確立的基本標志。這樣,1982年《憲法》對于殘疾人教育問題的明確,同時也意味著殘疾人的受教育權,是作為一項“憲法權利”而存在的,在這一點上也就無可爭議,充分體現了當時的改革開放精神。
中國的改革開放也帶來教育的大發展,特殊教育事業從此進入了快車道。1979年國家開始試辦培智學校,特殊教育的對象從傳統的盲目與聾啞兩類發展到包括弱智兒童在內的三類群體。[3](P3~10)特別是隨著1984年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的成立,各項有關特殊教育的政策也開始加快出臺,《義務教育法》也于1986年頒布。1995年,作為教育基本法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正式頒布,其法案有兩處有關特殊教育的明確表述:前面總則的第十條提出:“國家扶持和發展殘疾人教育事業,”這就為特殊教育的發展確立了基本方向與宗旨;后面的具體內容方面,第三十八條在有關受教育者的內容中進而指出:“國家、社會、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應當根據殘疾人身心特性和需要實施教育,并為其提供幫助和便利。”這里也就可以看出,法案從前面的總則綱領到后面的具體內容,都已經明確關注到特殊教育這一特定的教育類型,從而明確了特殊教育在現代教育法律體系中的應有地位,在一定意義上體現了教育基本法的歷史進步性。
(二)對教育部門法的依附
改革開放后的80年代,中國教育走向規范化快速發展時期。特別是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的出臺,中國各項教育制度全面走向正規。該《決定》首次從宏觀政策層面上加強了對特殊教育的關注,其中明確要求“在實行九年制義務教育的同時,還要努力發展幼兒教育,發展盲、聾、啞、殘人和弱智兒童的特殊教育。”在此背景下,1986年國家頒布的《義務教育法》充分吸收了上述《決定》中的教育改革精神,進一步明確了各級政府在特殊教育事業發展中的責任。其中第九條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為盲、聾啞和弱智的兒童、少年舉辦特殊教育學校(班)。”這樣,發展特殊教育,就不再是一種教育理念與人道關懷,而是各級地方政府實實在在的責任。由于1986年國家頒布的《義務教育法》是中國首次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方式通過的第一部教育立法,其本身就是中國教育法制化進程的重要里程碑,有關特殊教育的立法規定,同樣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
此后,在1995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以及《高等教育法》與《職業教育法》等教育部門法中,特殊教育的內容都成為其中不可或缺的基本組成部分。如1996年國家頒布的《職業教育法》,其中涉及到特殊教育內容的,主要是其第十五條,即“殘疾人職業教育除由殘疾人教育機構實施外,各級各類職業學校和職業培訓機構及其他教育機構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接納殘疾學生。”這樣,至少從立法關懷的角度,特殊教育進入法制視野,已經成為了中國教育法制建設的基本特征。
(三)對社會部門法的依附
對包括教育權在內的殘疾人的權利保障,“二戰”后國際組織對此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并對各成員國產生了深刻的影響。1975年,聯合國發布了《殘疾人權利宣言》,該《宣言》第6條是有關教育權利保護的內容,其中提出殘疾人有權享受“……教育、職業培訓和康復、各種幫助、指導、就業和其他服務,以充分發展他們的能力和技能并加速他們參與社會生活或重新參與社會生活的過程”。[4](P121)國際組織的有關殘疾人權利宣言與公約,與中國后來改革開放的背景基本相適應。在教育部門加強特殊教育工作的同時,社會相關部門對于殘疾人的支持與關愛也在提升。1988年被認為是中國“殘疾人事業發展的最為重要的歷史節點”,[5](P92~99)這一年成立了“中國殘疾人聯合會”,其工作職責內容從民政系統正式獨立出來。第一次全國特殊教育工作會議也在這一年召開,之后所發布的《關于發展特殊教育的若干意見》,對中國特殊教育的發展更是影響深遠。
在“中國殘疾人聯合會”的積極努力下,1990年國家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這是新時期中國殘疾人權益保障的重大事件,其內容涵蓋了康復、醫療以及教育、就業等有關殘疾人基本權利保護的多個方面。其特別是將平等地接受教育作為一項重要的殘疾人權利,加以詳細的規定指導。法案以九條的突出內容分別對于殘疾人教育的基本原則、辦學方針與途徑,以及特殊教育機構建設及其保障措施等,都有著較為明確的規定。就內容的詳細與豐富而言,這是一部比教育系統的立法更加凸顯殘疾人教育權的重要法案,這也表明了教育對于殘疾人生活及成長所具有的非同尋常的意義。
在殘疾人權益保障逐漸得到社會支持的背景下,教育領域的立法也加強了對于特殊教育群體的關注。這就包括2005年國家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護法》,以及《未成年人保護法》。例如,《婦女權益保護法》第十八條規定:“政府、社會、學校應當采取有效措施,解決適齡女性兒童少年就學存在的實際困難,并創造條件,保證貧困、殘疾和流動人口中的適齡女性兒童少年完成義務教育。”《未成年人保護法》中更是在第三章中專門設有“學校保護”的內容,多條涉及殘疾兒童教育保護的法律。
這樣,從國家層面的憲法,到教育基本法以及部門法,再加上社會有關弱勢群體權益保護的各類法律,殘疾人特殊教育的問題已經受到社會各部門的高度重視,相關法律制度體系也日漸豐富與全面。當然,作為特殊教育立法的初步探索,其法律實施效果也是有待進一步完善的。
二、特殊教育的法制表象與真實
依法治教是依法治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未來教育發展的基本趨勢。在殘疾人權利日益得到保護、特殊教育立法日漸受到重視的教育發展背景下,特殊教育的依法治教水平如何呢?這恐怕是當今學術界感到棘手而難以回答的問題。從特殊教育的立法實踐來看,正如前面有關的內容梳理,其立法的表現形式日益豐富全面,所謂“特殊教育立法體系日漸完善”,[6](P18~21)但從實際運行效果來看,上述法律規定大多停留在法律的文本層面,很少被司法實踐所運用。原則性多、號召性強,司法實踐難以落實而成為一種所謂的“軟法”,[7](P47~52)這也就是人們對于特殊教育立法所經常進行的一種批評。顯然,法制不等于法治,二者雖然緊密相連,卻具有不同的含義:法制是法律制度的簡稱,指的是立法體系;法治則是依法治理的簡稱,是法律制度的司法實踐。簡而言之,法制是前提,但法治才是目的。就當前我國特殊教育的法治實踐來看,可將其存在問題總結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法制形式化,缺乏司法執行力。盡管當前中國特殊教育的立法取得了諸多進展,但上述法制化的內容,象征意義大于實際意義,很難在司法實踐中得到運用。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各級人民政府應當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權利,并采取措施保障家庭經濟困難的、殘疾的和流動人口中的未成年人等接受義務教育。”這里的“應當”是一種號召性指示,對于殘疾的未成年人如何采取措施來保障其接受義務教育,這些實質性內容還不足。同時,這里的立法規定,與《義務教育法》的有關規定基本一致,立法重復而缺乏司法價值。顯然這類規定并沒有增加新的法律內容,只是讓人感受到其相應的立法關懷而已,是一種宣示性條款、象征性存在。
其次,立法被動滯后,缺乏法制推動力。就有關特殊教育法律內容的規定,大多是特殊教育實踐活動的經驗總結,或者政策的提升,相對于特殊教育實踐的需求而言,明顯具有被動性與滯后性。這也就是說,現有的特殊教育立法,并沒有增進新的權利關系,只是將實踐中政策所支持的行為合法化,賦予了其相應的法律權威而已。其典型立法事例就是1998年頒布的《高等教育法》,其中第九條規定:“高等學校必須招收符合國家規定的錄取標準的殘疾學生入學,不得因其殘疾拒絕招收。”事實上,關于殘疾學生的公平錄取規定,早在1985年國家教育部、民政部等部門聯合下發的《關于做好高等學校招收殘疾青年和畢業分配工作的通知》中,就有了比較明確的要求,即“在全部考生德智條件相同的情況下,不應因殘疾而不予錄取”。由此看出,特殊教育法制建設的被動與滯后,是當前存在的突出問題。也正是因為其立法的被動與滯后,其法制的社會效果也被淡化,使人們不能感受到特殊教育法的存在。可以說,在特殊教育活動的實踐中,法制建設發揮的作用是有限的。
最后,立法具有依附性,司法監督不力。應當看到,現有特殊教育法制的建設,是建立在相關法律基礎上的,這雖然具有表現優勢,但同時也呈現出明顯的依附性特征。無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還是《殘疾人權益保障法》,其法案雖然體現了對于特殊教育問題的重視,但特殊教育本身顯然不是這些法案的核心內容,相關內容就無法進行充分展開,獨特的特殊教育理念也難以在這些法案中完全展現。正是由于其法制建設過程的依附性,就更加導致了司法監督困難,缺乏比較直接與專業的特殊教育司法監督。
三、教育行政法規與法治
從法制走向法治,除了人大立法之外,還有一類重要的法規文件,這就是國務院所頒布的有關行政法規。1994年《殘疾人教育條例》的頒布,是中國特殊教育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作為國家層面所頒布的專門性行政法規,其首次對于全國特殊教育學校及其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全面系統的規劃指導,成為各地推動特殊教育學校發展的重要政策依據。2017年對于該《條例》的新修訂,更是對新時期我國特殊教育工作的系統總結與發展提示,充分體現了特殊教育的新理念與新趨勢。“理念的變化與更新是《條例》修訂的關鍵,直接影響和決定了具體的制度設計和條文表述,也進一步明確了今后殘疾人教育事業發展的原則與方向”。[8](P3~6)
根據我國現行的教育法律體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是教育的基本法,這是由全國人大審議并通過,對教育發展的全局具有宏觀指導作用。此外,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也往往會頒布一些教育單行法,如《義務教育法》《教師法》等,用以調整特定教育領域的行為規范。而由國務院所制訂或頒布的教育行政法規,如《殘疾人教育條例》等,則處于教育法律體系中的第三層次。換句話說,條例是介于法律與政策之間的行政法規,這類法規在當今的司法界已經具有了特定內涵,即“國務院根據憲法和法律,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有關行使行政權力,履行行政職責的規范性文件。行政法規一般以條例、辦法、實施細則、規定等形式組成,其效力次于法律,高于部門規章和地方法規”。[9](P27)
國務院頒布的各類事業發展條例,在我國的法制化進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但相對于依法治教的現代法制化要求而言還是不夠的。根據我國《憲法》以及《立法法》等有關法律規定,國家立法權屬于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而國務院所頒布的各項行政法規,以及國家各部門所頒布的各項規章制度,是國務院及國家各部門根據憲法和法律,按照法定程序制定的有關行使行政權力,履行行政職責的規范性文件。在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化建設的特定階段,國務院及其國家各部門所頒布的各項行政法規或者規章制度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現實作用。但是,從學理分析的角度看,教育政策與教育法律的性質有所不同,即教育法律是由國家依照法定權限、程序制定和認可的,其“通常以規范性法律條文的形式出現,有其特殊的表達形式,對法律的適用條件和具體情況、具體行為規則、權利義務關系以及違法者應承擔的法律后果等要作出確切的表述。”[10](P21)相對而言,教育行政規章的制定程序則相對簡單,其表述形式也不完全是嚴格的法律條文格式,規定的內容往往具有原則性與號召性的特點。
四、特殊教育法制的自立與趨勢
中國特殊教育法制的發展,經歷了從無到有、從單一到多元的發展,成績無疑是顯著而具有歷史意義的。與此同時,被動與依附等法制初創的稚嫩特性,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歷史烙印。因此,許多人期盼著“特殊教育法”能夠早日問世。然而,從當前國家對于特殊教育的管理實踐來看,還是立足于《殘疾人教育條例》的修改。那么,在新修訂的《殘疾人教育條例》已經比較充分地吸收了當前特殊教育新理念的情況下,“特殊教育法”的法制建設是否還具有意義呢?這里雖然反映了有關問題的核心爭議,但就法律與政策的本質區別而言,依法治教是發展的必然,未來的“特殊教育法”也是大勢所趨。然而,這一歷史進程的實現,需要現代特殊教育觀念的進步,更需要現代法制理念的進步。
首先,特殊教育立法是教育法制化發展的趨勢。當前,我國教育的法制化已經走向正規,初步形成了以憲法中的公民教育權為基礎,以《教育法》以及各系統或部門法律為支撐的教育法律體系。特殊教育作為整個教育體系中的重要內容,其地位越來越受到政府和全社會的重視,相應的立法工作必然成為一種基本趨勢。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國內有學者早在2005年就呼吁特殊教育的立法問題。[11](P3~6)該提議已經過去十余年了,雖然“特殊教育法”的制訂之路可能還會很漫長,但從教育法制化的發展規律來看,其獨立立法是是未來發展的趨勢的。此外,教育“去行政化”改革,必然推動教育法制化的發展。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下放辦學自主權的教育體制改革就已經啟動。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又聯合下發了《關于深化教育體制機制改革的意見》,進一步改革教育行政管理模式,推動依法治教更是教育體制改革的中心工作。
其次,特殊教育立法體現的是現代法治思維。關于特殊教育立法的發展走向,當前學界基本上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一是沿著《殘疾人教育條例》的路徑完善;二是著手構建新的“特殊教育法”。可以說,《殘疾人教育條例》自1994年頒布以來,在推動特殊教育發展與規范特殊教育學校建設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其2017年的修訂,更是融入了融合教育、入學“零拒絕”以及殘疾人教育全覆蓋等國際理念,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其依然是我國特殊教育工作的“根本大法”;不過,殘疾人教育與特殊教育,畢竟是不同的概念,當前國際特殊教育的發展趨勢更強調全納教育的現代法治觀念。因此,未來的特殊教育立法,需要現代法治觀念。
再次,特殊教育立法的實質在于特殊教育政策的法律化。“教育政策的法律化是指一定的國家機關依據法定職能,按照法定程序將經過實踐檢驗,成熟,穩定,已長期調整社會關系的教育政策上升為國家法律的過程。”[12](P118)從世界特殊教育的發展經驗來看,政策往往是特殊教育改革的前奏曲,法制才是穩定發展的根本歸宿。以在這方面,中國的特殊教育政策已經形成了一系列的“發展意見”或“提升計劃”。因此,中國未來的特殊教育立法,應當將國家有關的政策內容通過立法的方式來推進。換句話說,未來的特殊教育立法,應當是《殘疾人教育條例》與《特殊教育提升計劃》有機結合,充分體現特殊教育立法的完整性與實踐性。
最后,加強立法的針對性,打造中國特色的特殊教育。從1989年我國第一次發布《關于發展特殊教育的若干意見》,到2001年、2009年的兩次“進一步”的《發展意見》,再到2014年《特殊教育提升計劃》以及2017年《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計劃》,國家對于特殊教育的重視日益加強,財政投入逐漸加大,初步奠定了中國特殊教育事業強盛的基礎。然而,“目前我國特殊教育立法仍停留在宏觀層面上,可操作性相對較弱,很多條款缺乏強制性以及具體法律責任和懲罰措施”。[13](P196~199)這是不少學者對于當下特殊教育法制現狀的意見。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人們對于教育工作本身習慣于理想化與說教化;另一方面就是我國對于文教事業的管理趨于行政化,法制化力度有待提升。因此,加強特殊教育立法的針對性,也需要從兩方面著手。一是,行政管理改革需要進一步放權,加大“放管服”改革力度,充分調動特殊教育的社會資源與市場機制,即《殘疾人權益保障法》所提倡的“鼓勵社會力量辦學、捐資助學”精神。二是,特殊教育立法要將國際人權要求與中國傳統的“仁愛”文化充分結合。在2006年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制定過程中,中國拿出的文案發揮了重要作用,充分彰顯了中國人權保障工作的自信。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更有著豐富的殘疾人關愛思想,如儒家的“仁者愛人”、墨家的“互助兼愛”思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