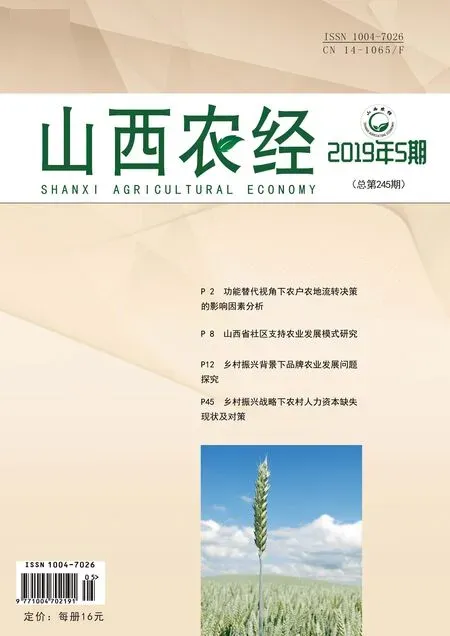論個人破產制度在我國的建構
(山東科技大學文法系 山東 泰安 271000)
近年來,超前消費、信用消費觀念盛行,一些人因貸款炒股、炒房及信用卡大額透支等造成個人資不抵債;個人市場投資因風險負債,超出個人負擔能力而陷入還債困境;地震、臺風、泥石流等自然災害發生,削弱了人們償還貸款的能力。上述情況造成部分自然人處于個人破產的邊緣。基于從繁重的債務負擔中解放“善良而不幸”的債務人并最大程度維護債權人利益的現實思考,開展我國個人破產制度相關研究,具有深遠的社會意義。
1 個人破產制度概述
個人破產制度,是指當自然人債務人的全部資產無法清償到期債務時,由法院依法宣告其破產,清算和分配債務人財產或免除其債務的法律制度,同時確定當事人在破產過程中和破產后的權利與義務。與專注于保護債權人利益的企業破產制度不同,個人破產制度明顯傾向于保護債務人的權益,旨在將“誠實而不幸”的債務人從無休止的債務清償深淵中解救出來。在平衡債權人和債務人利益的同時,以期債務人可以重新創造新的社會財富。
個人破產制度始于古羅馬時期,并在中世紀意大利與英國取得了很大發展。之后很多國家逐漸把個人破產制度納入破產法之中。今天,個人破產已成為現代破產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國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在理論界被稱為“半部破產法”,因其把破產主體范圍局限于企業法人,而把個人破產主體(如負債的自然人個人或消費者個人、合伙企業及其合伙人、個人獨資企業及其出資人以及其他依法設立的營利性組織和從事工商經營活動的自然人)排除在破產法大門外。相對于企業破產制度的完備,個人破產制度在我國長期處于法律真空的狀態,缺乏一套符合現代市場經濟需求的個人破產制度來解決現實存在的個人破產糾紛,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法律的局限性和滯后性[1]。
2 建構個人破產制度的必要性
2.1 維護私法公正,彰顯債權平等性
在中國現行企業破產法中,參與破產程序的主體僅限于企業法人,自然人不具備參與破產程序的主體資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擁有較多私人財產的個人投資者積極參與市場競爭,活躍于市場的各個領域,與企業法人同為市場競爭主體。當兩者面臨投資失敗的境況時,企業法人可以依托破產法中的制度(破產、重整以及和解)從繁重的債務負擔中脫身,獲得機會再次投資創造新價值。而同為市場競爭主體的個人,卻常常在債權人追討下走上了漫長的還債之路。
市場經濟在本質上屬于私法經濟,公平合理對待各類市場主體是其內在要求,而個人破產制度的缺失實質上未對作為市場競爭主體的自然人一視同仁,甚至帶有一定的歧視性,有違私法的公平正義。此外,在自然人無法償還債務時,債權人只能采用申請強制執行的方法來捍衛他們對債權的主張。但信息不對稱使得擁有信息絕對優勢的債權人率先申請強制執行,其債務通常可以獲得全部或大部分清償,對缺乏信息資源的部分債權人,其債權卻無法得到公平合理的清償,違背了債權平等性的要求[2]。
2.2 激勵企業家精神,維護社會秩序穩定
個人投資者在市場經濟的舞臺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為我國經濟增長貢獻了重要力量。建立個人破產制度是對企業家不慎作出錯誤投資或戰略決策造成損失進行補救的措施,為其提供基本生存空間,在性質上兼具社會保障功能。可以鼓勵個人投資者重新開始,整合現有社會資源,再創造新的社會財富。從這一點上講,個人破產制度利于激發企業家創新創業精神,實現個人投資者創造社會價值。此外,由于中國個人破產領域缺乏法律法規,當個人資產無法抵償債務且缺失還款能力時,常出現債權人想盡辦法追索債務,債務人驚慌失措四處逃債的局面。甚至有的債權人不惜以非法手段追索債務,債務人為償還債務鋌而走險,走向了犯罪路途。此類社會現象激化了社會矛盾,對社會秩序穩定產生了負面影響。
3 建構個人破產制度的可行性
3.1 社會信用體系建設完善及司法實踐經驗積累
有人認為社會信用體系成熟是確立個人破產制度的前提。這實則混淆了社會信用體系和個人破產制度發展的因果關系。個人破產法是企業破產法的基礎,早期商業活動孕育了個人破產,而后催生出后期成熟市場經濟中的企業破產,企業破產是個人破產的放大與延伸。只有樹立起個人的債權債務意識,才能建構起企業的債權債務責任意識,進而推進社會信用體系的完善和發展。個人破產制度的建立,也會迫使社會信用體系本身得到改善。
司法實踐中禁止被執行人進行高消費活動、公布被執行人失信記錄、強制其申報財產、限制其出境等措施出臺,把個人破產制度的影子投射進社會生活中,個人破產制度在社會生活中已經初具雛形。發達國家關于個人破產制度的法律規定,為我國提供了法律框架建構的借鑒。
3.2 中國個人破產制度建立已初步具備條件
我國社會經濟體制初步確立,體現為社會開放程度高、個人自由度大、私人財富擁有量增加。資源的有限性使市場競爭日益激烈,個人投資者希望在市場經濟中獲得一席之地,卻又懼于市場風險帶來難以承受債務負擔,使得社會剩余財富難以轉換為新的經濟動能,造成資源浪費。經濟體制改革,需要法律配套體系的規制。個人破產制度在我國推行滿足經濟發展的需求,對上述現象做出良好的制度回應。隨著中國金融體制改革,信用消費觀念普遍存在,打破了量入為出的傳統消費原則。超前消費等促進個人破產出現,為中國個人破產制度的發展提供了基礎條件。
4 我國個人破產制度的建構
人們普遍擔憂,如果輕易確立個人破產制度,會出現一些債務人事先惡意借貸肆意浪費,而后通過個人破產制度逃避債務的現象。但大多數國家的立法實踐表明,良好的制度建構將會很好地阻卻惡意破產案件發生。
4.1 完善我國現行破產法
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2月27日發布了“五五綱要”(2019—2023),提出研究和推動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為修訂中國企業破產法提供政策支持。良好制度的運行離不開法律規則指引,個人破產制度推行依托于破產法完善,在處理個人破產案件時才能具備法律依據。立法者在修改企業破產法過程中,可以考慮擴大現行企業破產法的適用主體范圍,將自然人主體納入企業破產法,使其真正成為實質意義上的“破產法”。此外,我國學者對個人破產制度進行的理論研究、發達國家制定的法律規范以及民事司法程序中企業破產制度實行所積累的司法經驗,都為完善我國破產法提供了幫助,我國建立個人破產制度的時機已相對成熟。
4.2 建立科學合理的債務人許可免責制度
破產免責制度指破產程序終結后,破產人在破產程序尚未清償的債務,在符合一定條件和范圍時,得以免除其繼續清償責任的制度。目前,除少數采取絕對豁免主義的國家外,大多數國家采用許可豁免。即在破產過程中,法官依法審查債務人的債務,只有符合特定條件的債務才能獲得豁免。中國個人破產制度仍處于起步階段,許可豁免制度更符合我國目前的社會形勢。法官負有對債務人進行審查監督的職責,以防止惡意破產逃避債務或損害債權人利益等現象的出現。
4.3 賦予債務人擁有自有財產的權利
自有財產概念源于個人破產制度,即由法律規定或法院酌情決定的,可由破產人自由管理、使用和處分,且不得查封和扣押并用于分配清償的財產。在英美法上,這部分財產稱為豁免財產。該制度能夠保障債務人最低限度生活,給予其重新開始的機會,適應市場經濟規律要求,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由于該制度一定程度上減損了債權人的利益,故對自有財產的范圍應進行嚴格限定,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權濫用使債權人利益遭受損失。
4.4 構建失權和復權相結合制度
在防止濫用個人破產制度方面,建立權利喪失制度發揮著重要作用。在破產程序完成后,失權制度的適用會導致破產人喪失某些民事權利及專業資格。從世界范圍內的司法實踐來看,相對于當然形式主義失權,裁判形成主義失權更有利于保護破產自然人的權利,并能起到良好的社會懲戒效果。復權制度與失權制度密切相關,即在權利喪失的基礎上恢復自然人的某些權利和專業資格的制度。同樣,復權制度的行使也需要司法權介入。加大對破產人資格的審查和監督,避免破產人利用復權制度惡意逃債的現象。
4.5 設立專門的破產法庭,保障個人破產案件審理
從各國司法實踐來看,個人破產案件是破產案件的主要來源,案件數量遠超企業破產。大多數國家都設立了專門的破產法庭對個人破產案件進行審理。在我國現有司法體制中,民事審判庭負責對破產案件進行審理。在我國建立個人破產制度后,隨著案件數量增加,民事審判庭案多人少的現象更加顯現,增加了司法審判負擔。因此,建立一個專門的破產法庭以提高審判效率顯得尤為重要。
破產案件的復雜性要求法官專業化,中國現有司法資源很難與現有社會需求相匹配。在審理破產案件時,設立專門法院更加科學合理,可以最大程度維持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利益平衡。目前,我國深圳、上海、北京等地已設立了破產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