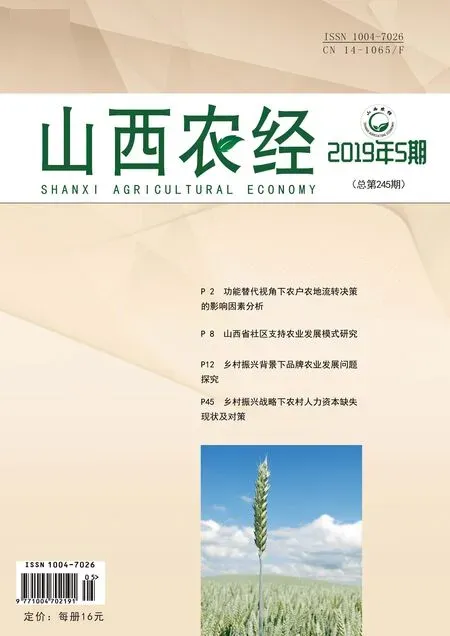中國鄉鎮定期集市的基本經濟邏輯分析
(河南大學經濟學院 河南 開封 475004)
1 集市概況
復旦大學歷史學教授樊樹志在其《明代集市類型與集期分析》一文中將中國的集市大致分為4種類型。第一種是不定期集市,這是最早的集市形態,沒有固定的交易日期、交易地點與場所,以物物交換為交易形式,是具有偶發性質的市場。第二種是定期集市,有固定的交易時間、固定的交易地點,主要的交易對象產自周邊地區,交易的參與人也來自臨近的村鎮。第三類是常市,也即現代成熟的市場形態,交易時間通常是全天候的,交易地點也是固定不變的。第四類是特殊集市,即大眾熟知的廟會與集會,這類集市的交易時間相對固定,通常為具有特殊民俗意義的時點。本文所討論的集市即為在廣大鄉村地區常見的定期集市。
2 布局之“集”
集市一詞大致可拆解為集與市兩層含義,因市而集,也由集而市。故“集”的因素也就顯得異常重要。由于有了聚集才能發揮規模經濟效益,才有了降低流通費用的可能。現代區域經濟學奠基人德國經濟地理學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 Walter)在其《南部德國的中心地原理》一書中指出:“幾乎所有的城市都在不同程度上,履行著商品集散中心和加工中心的職能”。不可否認現代農村的集市,并不是分散在各個村落,而更多的集中于鄉鎮等具有一定規模經濟效應的地區,由此一來,在交通條件相對優越的鄉鎮,周圍地區的村民可以不那么費力地將待交易的農業剩余輸至中心地,又由于中心地集市更大的市場規模,可以更為迅速地完成交易,在時間與空間上促進農業剩余的流通,一定程度上縮短了農業的生產周期。在克里斯塔勒之后,經濟學家Stine在繼承中心地理論的基礎之上,通過研究認為,小生產者的流動性取決于商品運輸銷售的最大范圍與最小范圍之間的相互關系。最大范圍是指商品銷售距離的最大范圍,而最小范圍則是商品銷售所獲得利潤的最小距離。當商品銷售的最大范圍大于等于獲得利潤的最小范圍時,生產者(商人)將該交點的空間上固定下來,即常市的形成。如果前者小于后者,商人將選擇流動。由此關系不難看出,在最小范圍與最大范圍的游離巨間,一種介于常市與流動交易之間的集市方式——定期集市應運而生。
3 制度之“集”
著名經濟學家林毅夫認為,制度安排可以分為正式的制度安排與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像家庭、企業、市場等都可被視為正式的制度安排,而如觀念、意識形態、習慣則可視為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但現實中的集市往往是由于周圍村民的習慣而逐步演化,從習慣性的非正式制度向正式性的制度逐漸過渡。制度的最終形成往往是復雜和難以預料的,正如美國著名經濟人類學家施堅雅(Skinner)曾預言,中國的鄉鎮集市伴隨著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將會在20世紀末不復存在。然而就實際情況而言,該預言無疑是失敗的,在商品經濟高度發達的今天,鄉鎮定期集市依舊是我國廣大農村地區,廣泛存在的市場交易形式,不但沒有消失,反而商業化程度愈加深厚,產品愈加豐富,文化內涵與文化傳播作用愈加強烈。
定期集市之所以“集”,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交易費用的存在。由于鄉村空間分布模式上的稀疏分散性,造就了農村地區人員物質流通的高成本,物質流通的成本往往集中表現在物價上,農民作為小生產者,有著天然的價格靈敏性。同時,作為單一性質的小生產者,其時間成本較低,在經濟活動上表現為人員流動的低成本,又由于在廣泛農村地區交通工具有著生產生活的雙重屬性,故在價格角度上表現為人員短距離流動的低邊際成本狀態。兩相對比就決定了在廣大農村地區是物的聚集和人的分散,這是定期集市因何而“集”的重要原因之一。
4 結束語
成本是影響區域經濟結構、區域經濟布局的基本原則。區域經濟學從數理角度合理論證了集市在空間上固定下來的原因。結合實際情況,在物質層面的另一維度,農村居民對價格反應的靈敏性也就構成了集市形成的必要條件。在實際生活中也就表現為物的集中而非人的集中,因此“因集而市”也就成為了鄉鎮定期集市運行的基本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