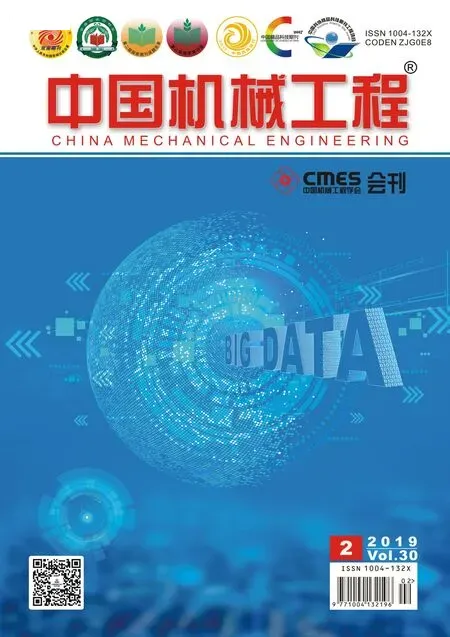驅動制造業從“互聯網+”走向“人工智能+”的大數據之道
姚錫凡 雷 毅 葛動元 葉 晶
1.華南理工大學機械與汽車工程學院,廣州,510640 2.廣西科技大學機械工程學院,柳州,545006
0 引言
正在興起的新一輪工業革命將導致全球工業體系、發展模式和競爭格局產生重大變革[1]。德國將這新一輪工業革命稱之為以信息物理系統為基礎的工業4.0[2],美國則稱之為工業互聯網[3]。中國于2015年7月發布了《積極推進“互聯網+”行動的指導意見》;2016年5月發布了針對制造業版的“互聯網+”——《關于深化制造業與互聯網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2017年7月發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將智能制造作為新一代人工智能應用之首;同年11月發布了《關于深化“互聯網+先進制造業” 發展工業互聯網的指導意見》。由此可見,“互聯網+”和“人工智能+”頻繁地出現在我國制造業頂層戰略規劃之中。
制造業是工業的主體和國民經濟支柱,世界各國對其極其重視,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后,工業化國家紛紛出臺“再工業化”戰略計劃。在新一輪工業革命中,我國出現兩種主要“版本”的制造模式:“互聯網+制造”和“人工智能+制造”。事實上,這兩種制造模式早已存在,前者被稱為網絡化制造,后者被稱為智能制造。從形式上來看,兩者的不同在于“+”前面的對象,即改造傳統制造業所采用的技術手段不同。從本質上來看,兩者都致力于通過虛擬信息空間與實體物理系統的融合來實現制造業的變革。
那么“互聯網+制造”和“人工智能+制造”究竟是什么關系?它們的未來又走向何方?本文對此展開研究,從兩者的發展歷程和歷史淵源,探討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以及未來發展走向。
1 互聯網+制造
“互聯網+制造”代表互聯網與制造的融合,這里的“+”既包含“加”、也包含“減”的含義。所謂“加”,就是充分發揮互聯網在生產要素配置中的優化和集成作用,盤活存量和提升生產效率;所謂“減”,就是去掉信息化孤島或障礙,淘汰落后產能和簡化生產流程。如果用集合來表示, “互聯網+制造”可視為互聯網與制造的交集,即“互聯網+制造”等同于“制造+互聯網”[4],這種融合亦稱為互聯網制造(網絡化制造),如圖1a所示。具體形式上,既有早期“制造+網格”發展出的制造網格,也有新興“制造+物聯網”所形成的制造物聯(網)[5],如圖1b所示。從更廣泛意義來說,就有“工業+互聯網”衍生出工業互聯網。

圖1 “互聯網+制造”含義及其示例Fig.1 The meaning and examples of “Internet+manufacturing”
“互聯網+制造”的發展可以概括為數字化制造與互聯網技術從單獨發展走向集成與協同發展,如圖2所示。1952年,Parsons公司與MIT合作,試制成功第一臺三坐標數控銑床[6],標志著數控(numerical control,NC)技術的誕生,并發展出計算機數控(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CNC)與直接數控(direct numerical control,DNC)[7],構成了計算機輔助制造(computer aided manufacturing,CAM)的核心。20世紀50年代后期以來,計算機輔助制圖經歷二維至三維的轉變,并拓展為包含構思、功能設計、結構分析等設計理念的計算機輔助設計(computer aided design,CAD)。在數值計算方法發展的推動下,20世紀70年代初期實現了計算機輔助工程(computer aided engineering,CAE)的實用化[8]。此后,設計與仿真分析逐漸集成為工程設計軟件的2個重要模塊。從初期研究開始,CAM與CAD便存在功能交互,并不斷深入集成為CAD/CAM。
為優化工藝過程設計,20世紀60年代后期出現了計算機輔助工藝規劃(computer aided process planning,CAPP)[9]。CAD、CAM、CAPP組成的工程設計自動化系統具有產品的概念設計、工程分析、結構與工藝設計及數控編程功能[10],上述技術的綜合運用在20世紀80年代初出現的柔性制造系統(flexible manufacture system,FMS)上得到了體現[11]。20世紀80年代初期出現的產品數據管理(product data management,PDM)解決了大量工程圖紙文檔的管理困境,并逐步擴展為產品開發全生命周期的數據管理[12],進一步完善處理CAD/CAM系統存在的數據管理問題。20世紀60年代,庫存物資管理問題引起了制造業對物料管理的思考,進而發展出物料需求計劃(material requirement planning,MRP),并在此基礎上發展出閉環的MRP。20世紀70年代,制造資源計劃(manufacturing resource planning,MRP Ⅱ)應用管理會計的概念來實現對物資信息與資金信息的集成,并于20世紀90年代擴展為更為全面的企業資源計劃(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13]。

圖2 “互聯網+制造”演化Fig.2 Evolution of “Internet+manufacturing”
自1973年提出計算機集成制造(computer integrated manufacturing,CIM)[14]以來,由CAD、CAM、CAPP、MRP Ⅱ等框架為基礎構成的計算機集成制造系統(CIMS)逐步推進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20世紀80年代,CIMS技術迅速向縱深發展,相繼提出了精益制造(lean production,LP)[15]、并行工程(concurrent engineering,CE)[16]等制造模式。CIMS具備數字化、信息化與集成化的特點,為互聯網技術在制造業中的應用提供了技術基礎。
互聯網Internet是現代集成制造的基礎技術,其功能與內涵隨著其發展歷程而不斷擴展。互聯網以ARPANET為起點,隨后科學計算網、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網等拓展了互聯網的應用范圍并推動互聯網協議走向標準化,最終在1989年出現了最為廣泛應用的萬維網(world wide web,WWW)。此后萬維網經歷了3個發展階段[4]:①Web1.0(1990~2000),用戶僅獲取網站信息,信息單向流動;②Web2.0(2000~2010),用戶獲取并產生網站信息,實現信息在用戶與社交平臺之間的雙向流動;③Web3.0(2010~),融合語義網、移動網絡、人工智能等技術,目前仍處于不斷發展之中。
隨著Web時代的到來,CIMS與Internet技術進入集成與協同發展時期,制造系統進入“互聯時代”。20世紀90 年代初出現具有代表性的敏捷制造(agile manufacturing,AM)[17],1999年提出以數字化、柔性化、網絡化為基本特征的網絡化制造(networked manufacturing),以實現無地域限制的社會協作與資源共享[18]。2000年后,互聯網技術的進步催生出更為復雜的制造網絡,信息物理融合系統(cyber-physical systems, CPS)[19]出現并致力于實現虛擬世界和實際物理世界互聯與協同。2006年,McAfee將Web2.0理念引伸到企業,提出了企業2.0(enterprise 2.0)概念[20]。
隨著傳感器、RFID等技術的廣泛采用,互聯網逐步走向萬物互聯的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IoT)時代[21]。基于物聯網理念提出的制造物聯(internet of manufacturing things,IoMT)[5]不僅實現生產過程中數字化裝備、智能設備的信息互聯,更進一步對產品的全生命周期信息進行管理。隨著云計算和面向服務技術的發展,云制造(cloud manufacturing,CM)[22]應運而生。以制造物聯、云制造等為代表的新興網絡化制造模式,需要結合大數據智能技術對具備大數據特征的制造數據進行處理,因此該類“互聯網+制造”模式實質上也是一種智能制造模式[4],由此也可以看出“互聯網+制造”與“人工智能+制造”正逐步走向融合與統一。
綜上,網絡化制造隨著互聯網的發展而發展,從最初的計算機集成制造走向人機物的三元集成制造(圖2),并通過物聯網和大數據等新一代信息技術與智能制造產生密切關聯。
2 人工智能+制造
“人工智能+制造”代表人工智能與制造的融合,如圖3所示。最初體現為誕生于20世紀80年代的智能制造(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IM)。此時的AI主要依靠符號智能實現決策,因此IM主要依賴人類專家知識來解決制造中的問題。近些年來,得益于新一代AI的發展,特別是以“大數據+深度學習”為代表的大數據智能的發展,誕生了新一代智能制造(多用smart manufacturing(SM)表示)[23-24]。

圖3 “人工智能+制造”含義及示例Fig.3 The meaning and examples of “AI + manufacturing”
人工智能作為一門在計算機中模仿人類智力的科學,已有70多年的研究歷史[25]。1943年關于M-P神經元模型的研究[26],通常被認為是AI研究的開端。1956年,Dartmouth College研討會首次使用“人工智能”一詞,標志AI研究領域正式誕生,人工智能研究工作進入第一個興旺期,在機器學習、定理證明、模式識別、問題求解等領域推出程序,并研制出了人工智能語言LISP[27]。在AI研究初期,學術界受控制論的影響甚重而形成行為主義學派,因此AI的研究方法以進化計算、強化學習為主[28]。20世紀70年代,AI研究陷入“寒冬”,直至20世紀80年代初,專家系統的成功開發與應用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效應,以符號主義為代表的AI迎來了蓬勃發展時期[25]。1980年后,Hopfield網絡與誤差反向傳播算法的提出,使停滯十余年的神經網絡研究步入恢復期[26]。近些年,以深度學習為代表的聯結主義AI迅猛發展,AI技術在圖像識別、語音識別、自然語言處理方面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性進展[29]。
20世紀80年代,得益于CIMS與AI的發展,各國開始嘗試AI與數字化制造的集成應用,智能制造應運而生。20世紀90年代初期,日本首先提出智能制造系統的概念與國際合作研究計劃。此后,各國競相發展智能制造,從初期的側重智能制造單元以及基于符號主義AI的制造專家系統,逐漸轉向人工神經網絡、模擬退火算法以及遺傳算法等技術組成的計算智能,并發展出模糊神經網絡、遺傳神經網絡等多種AI算法融合的智能方法[30]。
21世紀,因大數據和深度學習等新一代人工智能的發展,智能制造進入新的發展時期。2006年Hinton指出深層神經網絡具有優異的特征學習能力[31],由此興起關于深度學習的研究。智慧地球[32]概念的提出進一步推動了人工智能的研究,美國、德國、中國、英國、日本及韓國各自提出新工業計劃[33],德國提出的以智能制造為主要特征的工業4.0得到全世界的廣泛關注。
21世紀關于智能制造的研究側重于提高系統動力、快速適應性和資源有效性[34]。新一代智能制造SM具備了數字化、虛擬化、物聯網等新技術,以萬物互聯、數據驅動、自主智能等新形式發展[35]。對上述新技術、新形式進行應用的典型智能制造模式包括:采用先進分析方法與信息物理系統等工具,將大數據轉換為可利用、可操作的信息,從而實現制造過程預測的預測制造[36],以及基于大數據與主動計算而提出的主動制造[23,37]。
隨著新一代AI的發展,人們更加廣泛地將AI應用于制造業智能決策之中,并實現對產品質量監測、工藝效率及制造全生產周期的優化。同時,AI也使智能制造內容更加豐富,并對其產生顛覆性變革。
3 網絡化制造與智能制造走向融合
網絡化制造和智能制造分別隨著互聯網和人工智能技術發展而發展,當前都進入各自的新發展期。2010年前,計算機集成制造/網絡化制造占據主導地位,人工智能只是在制造的某些環節起到輔助作用,處理數據對象以結構化數據為主。20世紀90年代,互聯網進入Web時代,制造業“信息化孤島”[4]得以初步互聯,智能制造不再局限于利用人工智能、數據分析及統計等智能方法處理“孤島式”的制造問題。由于該階段的制造數據以結構化數據為主,數據結構簡單,專家系統、模糊推理等符號主義AI對其具有高效的處理能力,從而形成了許多以符號主義AI為基礎的制造資源集成系統。當互聯網進入Web2.0,人際網、社交媒體和企業2.0等得到深入發展,企業、客戶主動在網絡上產生包含制造、服務及社交等內容,具備結構化與非結構化共存特征的海量數據。網絡數據的規模化、復雜化對AI在數據處理、挖掘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推動了聯結主義AI的發展。
近些年來,隨著物聯網、大數據和機器學習等興起和發展,智能制造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并不斷與互聯網(網絡化制造)融合,互聯網成為了智能制造的基礎設施,形成了面向產品全生命周期的“互聯網+人工智能+制造”的新一代智能制造,如圖4所示。

圖4 從“互聯網+”到“AI+”的制造模式演進Fig.4 Evolution of manufacturing mode from “Internet+” to “AI+”
網絡化制造致力于解決“信息化孤島”問題,而智能制造致力于解決制造決策問題,但隨著物聯網的發展,通過萬物互聯解決“信息化孤島”問題之后,就需要解決更高層次的認識智能問題,同時也產生一個“副產品”——大數據[38]。基于知識(符號智能)的傳統智能制造,由于存在知識獲得等瓶頸,現在已轉向由原始大數據直接獲得知識或模型來解決生產中的問題,因此網絡化制造與智能制造走向融合成為必然。
由此可見,新一代智能制造以“互聯網+”作為基礎,融合了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和深度學習等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包括IoMT、云制造、信息物理生產系統等眾多制造模式。IoMT基于物聯網技術,解決設計、生產與服務過程的信息傳輸與共享問題,使制造數據能在更大范圍共享而實現全局優化;云制造對制造資源進行虛擬化與服務化,實現制造資源在企業間的流通與共享,為客戶提供按需生產的服務平臺,在企業之間開展更廣泛的協同制造;信息物理生產系統通過狀態感知、實時分析、人機交互/自主決策、精準執行和反饋,實現物理系統和信息系統的協同,以及人、設備與產品的連通與交流[24]。
這些從不同視角提出的新興智能制造模式,雖然側重點有所不同,但它們都具有一些共同目標。其一,相比于傳統的“互聯網+制造”僅在制造或服務某些環節對數據智能化處理,新一代的智能制造模式更注重產品全生命周期的數據分析與監控[39]。這得益于由傳感器、射頻識別等廉價設備構成的感知系統,它們分布于產品的全生命周期之中,能夠實時地獲得監測數據。其二,新一代智能制造模式更注重客戶體驗與需求,在社交媒體等服務大數據的驅動下,產品需求逐漸由市場導向轉為客戶需求導向,產品生產方式逐漸由“推式”轉為“拉式”,越來越多的企業實施制造與服務融合策略,為客戶提供個性化定制產品[23,40]。
4 大數據驅動的智能制造
大數據對智能制造提出了挑戰。從來源上,制造大數據包含PDM、制造執行系統等產生的產品設計與制造過程數據、ERP系統等產生的公司運營數據、供應鏈關系管理系統及互聯網客戶需求等產生的價值鏈數據,以及經濟形勢變化、政策變動等因素產生的外部數據[38]。相較于互聯網大數據所具備的規模性(volume)、多樣性(variety)、高速性(velocity)及價值性(value)的4V特征[41],制造大數據還具備制造領域特有的一些屬性:①時序特性,智能感知設備對制造過程不斷采樣,數據與該時間的生產狀態匹配而具有時序特性;②高維特性,加工過程用多個維度(工藝、環境、時間)參數來描述產品加工質量;③多尺度特性,制造過程中,在同一維度下用不同尺度數據相互配合來描述產品質量;④高噪特性,制造過程中存在的電磁干擾、振動等形式的噪聲影響測量結果,得到的是低信噪比的測量數據[38]。
制造與服務流程產生的以非結構化數據為主的海量數據,要求新一代智能制造能夠在大量持續變化的數據流中提取知識,并依靠知識關聯與存在模式,分析信息價值[42]。目前,可利用以深度學習為代表的人工智能對原始數據進行處理,將大數據轉變為可利用、具有價值的信息與知識,對制造及服務過程進行智能決策。
智慧制造是將未來互聯網的四大支柱技術(人際網(internet of people,IoP)、內容知識網(internet of contents and knowledge,IoCK)、務聯網(internet of services,IoS)和物聯網IoT[43])與制造技術融合而成的一種新型智能制造模式[43-44],它是社會制造(企業2.0)、IM/SM/預測制造/主動制造、云制造、制造物聯等智能制造理念的融合與拓展,如圖5所示。然而,正是IoP、IoS、IoT三者的集成導致了制造大數據的產生, IoCK(包括大數據)起到橋接IoP、IoS、IoT的作用,并通過對IoCK中的大數據提取可操作的信息/知識,最終實現了人、機、物的集成與智慧應用。
智慧制造實質上是一種社會信息物理生產系統(social-cyber-physical production system, SCPPS)[45],延伸和發展了工業4.0下的信息物理生產系統(cyber-physical production system, CPPS)[46]的理念,如圖6所示。CPS由基于IoT的物理系統和基于IoCK、IoS的信息系統構成,社會信息物理系統則是在CPS基礎上,進一步融合基于IoP的社會系統。首先,由IoT感知底層設備的原始數據;然后通過IoCK分析獲取大數據中的信息與知識,并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自動判斷決策;通過IoS將制造資源虛擬化與服務化,按照業務流程施效于物理系統;面對機器無法自主決策的復雜問題,可借助于IoP在人際社會中實現知識共享,通過人類群體智慧加以解決,同時IoP能收集互聯網中的客戶需求信息,進而按客戶需求進行生產,從而形成“物→數據→信息→知識→智慧→服務→人→物”循環的回路[24]。數據在系統中起到橋接各子系統的作用,并為智能決策提供原始數據。信息系統與制造技術融合形成了賽博制造(cyber manufacturing)。基于IoP的社會系統與制造技術融合形成社會制造,進一步與IoCK、IoS、IoT融合而形成社會信息物理生產系統,從而將群體智慧集成于制造系統之中。

圖5 “未來互聯網+制造”的智慧制造Fig.5 Wisdom manufacturingbased on “future internet+manufacturing”

圖6 “CPS/SCPS+制造”Fig.6 “CPS/SCPS+manufacturing”
大數據在制造、供給、經營管理及服務過程中的應用,使企業能及時適應市場需求的變化,做出更高效精準、利潤最大化的部署。因此,在大數據驅動下,企業制造生產更加主動,使客戶融入設計制造過程,實現小批量乃至單件的個性化定制。以某傳感器個性化定制為例,它要求企業按客戶在企業網絡系統中提供的需求設計生產不同型號的傳感器,這意味著企業在生產過程中需要不斷地切換生產,為此該企業從產品設計入手,將組成傳感器的部件進行標準化、模塊化,并制定相應的識別條碼,使機器實現條碼數據自動掃描,并通過表面貼裝機自動切換程序來貼裝相應型號傳感器的零部件,進而實現生產不同型號傳感器的零秒切換,同時也實現企業利潤的最大化;在制造過程中針對不同訂單的緩急程度,可對生產進行動態規劃,進而實現生產任務的動態調度及物料的優化配送,并可通過生產數據實現制造資源的實時監控與質量控制;此外,通過大數據還可優化包含庫存、財務、銷售分析及采購成本數據的經營管理服務以及包含市場預測與供給渠道信息的供應鏈管理服務,從而避免不必要的成本支出與損失[38]。
5 結語
新一輪工業革命在全球范圍內興起,制造業競爭格局面臨重大變革,多國紛紛提出工業振興計劃。互聯網+AI+制造融合的新一代智能制造已成為制造業發展新引擎,搶占新一代智能制造發展熱潮的先機,對我國制造業創新發展、競爭力提升,從制造大國走向制造強國具有重要意義。本文闡述了“互聯網+制造”與“AI+制造”各自發展歷程及相關制造模式,梳理了兩者走向融合的發展趨勢,并將新一代智能制造統一于社會信息物理生產系統理念之下。
“未來互聯網+制造”,特別是在“四網”高度融合的智慧制造(或社會信息物理生產系統)必然產生大量可供使用的海量原始數據。大數據計算被認為是繼實驗研究、理論分析和計算機仿真之后的第四種科學研究范式,并成為新一代人工智能基礎,因此如何利用大數據智能就成為新一代及未來網絡化制造/智能制造亟需解決的問題,也是制造系統從被動走向主動的關鍵所在。本文從宏觀視角上探討驅動制造業從“互聯網+”走向“人工智能+”的大數據之路,后繼工作將從微觀角度上細化相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