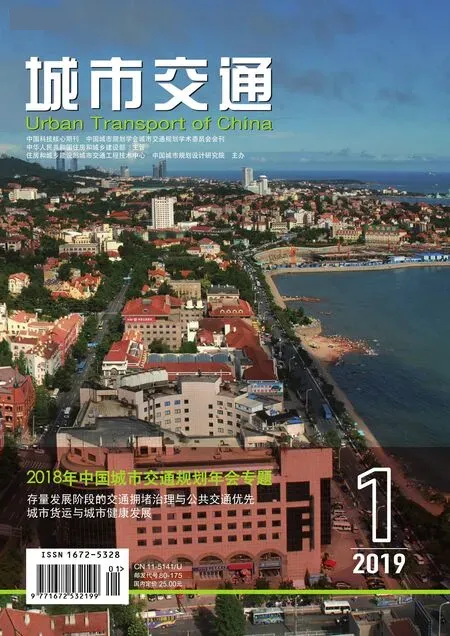基于服務導向的長三角城際交通發(fā)展模式
蔡潤林
(中國城市規(guī)劃設(shè)計研究院上海分院,上海200335)
0 引言
近期,長三角城市群一體化發(fā)展上升為國家戰(zhàn)略,實現(xiàn)更高質(zhì)量一體化發(fā)展的路徑和措施成為區(qū)域關(guān)注的焦點。隨著城市群經(jīng)濟社會水平日益提高、城市間產(chǎn)業(yè)分工協(xié)作關(guān)系日益緊密、區(qū)域交通基礎(chǔ)設(shè)施日益完善,長三角城際交通需求總量和頻次快速增長[1]。與此同時,長三角城際交通系統(tǒng)仍存在諸多不便和痛點。傳統(tǒng)的對外交通組織模式難以匹配城際出行人群對規(guī)律性、高頻次和高時效性的要求。高質(zhì)量的城際交通系統(tǒng)既是構(gòu)建長三角世界級城市群的重要支撐,也是更好地服務城際出行者的迫切需要。因此,需要突破城市對外交通的組織范疇,將城際出行的全過程鏈條和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納入考慮,更貼近出行者的實際需求。
既往關(guān)于城市群城際交通的研究集中于兩類。一類是研究城際交通影響下的城市(群)空間組織:文獻[2]基于高鐵和長途汽車客流數(shù)據(jù),分析了長三角區(qū)域中上海與南北兩翼相互間的關(guān)聯(lián)強度,并提出了區(qū)域網(wǎng)絡(luò)的均衡化演變趨勢;文獻[3]基于高鐵和城際樞紐選址,提出了城際交通布局應更注重城市功能價值和功能結(jié)構(gòu)重組,文獻[4]對珠三角城際客流特征和空間格局進行了類似研究。另一類是對城市群城際交通系統(tǒng)的優(yōu)化研究,特別是城際軌道交通系統(tǒng):文獻[5]分析了長三角不同空間尺度與多層次軌道交通網(wǎng)絡(luò)的匹配關(guān)系,從出行時間約束、設(shè)施引導等方面提出了以上海為中心的多層次軌道交通系統(tǒng)優(yōu)化思路;文獻[6]通過對城市群出行空間特征的分析,提出了城市群軌道交通體系的功能層次,以及其服務功能、技術(shù)特征和銜接要求等;文獻[7]總結(jié)了廣佛間城際客流特征演變趨勢,提出了應對同城化背景下的軌道交通銜接策略。
既有研究的局限性在于,對城市群空間和交通互動關(guān)系缺乏全局性刻畫,特別是對不同空間層次或典型地區(qū)的交通特征差異研究不足。另外,對城際交通的趨勢適應性和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如樞紐布局模式)關(guān)注不足,也使得研究的全面性存在一定問題。本文盡可能全面勾勒長三角城市群空間層次和交通方式的互動關(guān)系,并在此基礎(chǔ)上進一步構(gòu)建長三角城際交通發(fā)展的總體模式。
1 國外城市群城際交通發(fā)展借鑒
1.1 三種發(fā)展模式
參考國外發(fā)展較為成熟的城市群地區(qū)案例,其城際客運組織模式一般按主導交通方式劃分可歸結(jié)為三類。
第一類是以鐵路、軌道交通為主導的城際客運模式,以日本東京都市圈和法國大巴黎都市區(qū)為代表。此類模式一般適用于單中心放射的都市圈形態(tài),在空間結(jié)構(gòu)上有明顯的圈層化特征,針對不同的圈層匹配多層次的軌道交通系統(tǒng)制式。第二類是以公路為主導的城際客運模式,以美國東北部城市群為代表。城市群內(nèi)形成州際公路、國道、州內(nèi)公路、郡內(nèi)公路構(gòu)成的多等級公路系統(tǒng),服務于不同圈層,城市群空間沿交通干路蔓延式擴張。第三類是以鐵路、公路混合主導的城際客運模式,以大倫敦城市群為代表。由內(nèi)倫敦、外倫敦構(gòu)成的圈域型都市圈具有強大的城市中心,人口和就業(yè)密度由核心區(qū)向外遞減,城際客運分擔方式上個體機動化與公共交通方式相當。
1.2 規(guī)律和借鑒
城市群城際交通模式的形成與都市圈空間形態(tài)、交通設(shè)施和政策的引導密切相關(guān)。美國20世紀50年代后對公路設(shè)施建設(shè)的投入,以及城市郊區(qū)化的進程,使得城鎮(zhèn)空間的蔓延和小汽車出行模式互為促進。東京和倫敦由于發(fā)展過程中的鐵路和多層次軌道交通建設(shè),以及中心城對私人機動化的管制,滿足了不同空間圈層的通勤、生活出行需求。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即便是在美國東北部這樣高度私人機動化的城市群,也存在大紐約都會區(qū)這類高度依賴通勤鐵路和城市軌道交通出行的地區(qū)。
與上述國外城市群相比,長三角城市群地域更加廣袤,人口和就業(yè)密集程度更高,存在都市圈、城市密集地區(qū)、大城市毗鄰地區(qū)等多種差異化發(fā)展的子區(qū)域,需要更加高效率、多元化的交通系統(tǒng)予以支撐。
2 長三角城際出行特征
長三角城際客運交通聯(lián)系呈現(xiàn)較為明顯的空間層次差異化特征(見圖1)。以上海為中心形成了跨省界的大都市圈空間,上海與周邊的蘇州、無錫、南通、嘉興等城市城際聯(lián)系密切;南京、杭州、合肥三大省會城市與周邊地區(qū)共同形成了省會都市圈,圈層化特征明顯;而在蘇錫常、滬嘉杭地區(qū),依托區(qū)域交通廊道形成了城市密集地區(qū),次級城鎮(zhèn)間交通往來聯(lián)系頻密;同樣的,由于區(qū)域產(chǎn)業(yè)合作和分工,金(華)義(烏)一體化發(fā)展區(qū)、甬舟一體化發(fā)展區(qū)內(nèi)部相互間產(chǎn)業(yè)和社會聯(lián)系也在持續(xù)加強。在空間尺度上,長三角主要中心城市間距約150~300 km,相鄰地級市相互間距約40~100 km,相鄰縣級市相互間距約20~50 km。根據(jù)空間層次和尺度關(guān)系,將長三角城際出行劃分為跨區(qū)大尺度城際出行、都市圈城際出行、城市密集區(qū)城際出行、城市毗鄰區(qū)城際出行四種類型進行需求特征分析。
2.1 跨區(qū)大尺度城際出行
長三角主要中心城市間聯(lián)系通道距離超過150 km,且與區(qū)域主要對外廊道重合,此類跨區(qū)大尺度城際出行的突出特點是“體量大、需求高、增長快”。由于各中心城市均圍繞其形成了都市圈或城市密集地區(qū),聚集人口規(guī)模體量超過千萬級。例如,上海市域人口超過2 000萬人,杭州都市圈人口超過2 500萬人,南京都市圈人口超過3 000萬人,蘇錫常地區(qū)人口也超過2 000萬人。因此,在跨區(qū)城際客流走廊上需求增長非常迅速,而由于區(qū)域主要交通廊道集中且有限,走廊交通供需矛盾突出。根據(jù)相關(guān)研究統(tǒng)計,2011—2013年滬寧沿線城市城際鐵路客流總量增幅超過50%[8];2016年金華至長三角主要中心城市鐵路客運量同比快速增長21%。在此背景下,傳統(tǒng)的滬寧、滬杭走廊已呈現(xiàn)飽和狀態(tài),而新興的寧杭、通蘇嘉走廊在快速需求增長下供需矛盾也已顯現(xiàn)。
更重要的是,由于都市圈之間特別是中心城市間的企業(yè)關(guān)聯(lián)度不斷增強,跨區(qū)城際出行對時效性的要求不斷提升。表現(xiàn)為城際商務往來需求日益旺盛,對鐵路出行的依賴度提升(見圖2),高速鐵路體現(xiàn)其優(yōu)勢。以上海為例,2012年以來對外鐵路客運規(guī)模遞增12.5%,2017年對外鐵路出行分擔率達52.9%[8]。

圖2 2005—2015年長三角企業(yè)關(guān)聯(lián)度變化趨勢Fig.2 Trend of enterprises relevance degree in Yangtze River Delta(2005—2015)
2.2 都市圈城際出行


圖3 省會城市都市圈城際聯(lián)系強度Fig.3 Intercity transportation intensity in provincial capital metropolis circles
以上海、杭州、南京、合肥等區(qū)域中心城市為核心,形成若干都市圈,其城際出行的圈層特征明顯,并且存在緊密聯(lián)系的邊界效應(見圖3)。杭州都市圈的緊密聯(lián)系圈層半徑約為60 km,包括杭州與周邊的海寧、紹興、桐鄉(xiāng)、德清、安吉、諸暨等市縣;南京都市圈的緊密聯(lián)系圈層半徑為50~80 km,包括南京與周邊的揚州市區(qū)、句容、滁州市區(qū)、馬鞍山市區(qū)、來安、天長、博望、和縣等市縣;合肥都市圈的緊密聯(lián)系圈層半徑為40~70 km,包括合肥與周邊的舒城、金安、壽縣、含山、無為、定遠等市縣。
交通需求特征方面,一方面商務通勤類出行客流占比較大,并呈現(xiàn)高頻次、規(guī)律性特征。以滬蘇間出行為例,商務、公務和通勤出行占滬蘇鐵路出行量的40%,每月往返4次以上人群達40%[9]。另一方面,此類出行的向心性特征突出,出行目的地多位于中心城市的中央商務區(qū)或主要功能片區(qū),因而對于向心性公共交通(特別是軌道交通)的依賴性高。杭州的研究表明,至2030年杭州都市圈的向心性交通需求規(guī)模趨近城市內(nèi)部組團間的交通量,且受主城交通瓶頸制約,都市圈外圍至主城的客流需實現(xiàn)70%以上的公共交通出行分擔率。
2.3 城市密集區(qū)城際出行
城市密集區(qū)是長三角一類非常典型的地區(qū),其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較高,特別是縣級單元經(jīng)濟發(fā)達,相互間產(chǎn)業(yè)、經(jīng)濟和社會聯(lián)系緊密,不以行政邊界為阻隔。在此類地區(qū)中,城鎮(zhèn)空間的組團化格局較為明顯,市區(qū)中心性不強,產(chǎn)業(yè)和空間呈現(xiàn)沿交通廊道的連綿布局態(tài)勢。因而,城市密集區(qū)城際出行呈現(xiàn)需求網(wǎng)絡(luò)化、復合化和多元化的特征。
以最為典型的蘇錫常地區(qū)為例,城際出行空間分布表現(xiàn)為去中心化、均衡網(wǎng)絡(luò)布局(見圖4)。蘇州、無錫、常州三市中心城區(qū)與市域外圍地區(qū)的輻射聯(lián)系強度具有較大差異,而相鄰的縣級單元間交通往來聯(lián)系較強,例如常州—江陰—張家港間交通訴求強烈。因此,在此類地區(qū)中,整體城際交通格局并不是以中心-外圍的形式擴散,而是形成多條廊道交織的網(wǎng)絡(luò)化布局。
2.4 城市毗鄰區(qū)城際出行
城市毗鄰區(qū)指兩個城市毗鄰的新城、縣城呈現(xiàn)連綿化發(fā)展的地區(qū),從空間結(jié)構(gòu)上看,新城、縣城處于區(qū)域發(fā)展軸帶上,同時毗鄰地區(qū)自身發(fā)展軸帶相連(見圖5)。毗鄰地區(qū)的新城、縣城在用地布局上拓展方向相對,用地性質(zhì)上分工特征較為明顯,相互補充配合,呈現(xiàn)高度混合特征,同城化趨勢明顯。例如上海的嘉定新城與蘇州的昆山、太倉。
從城際交通聯(lián)系特征來看,一方面,大城市毗鄰地區(qū)的對外交通聯(lián)系突破了行政邊界,體現(xiàn)經(jīng)濟的主要指向。如滬蘇連綿地區(qū)的昆山和太倉,其主要對外聯(lián)系方向均為上海,而非行政中心蘇州。其中,昆山—上海日均客流量約4.7萬人次·d-1,高于昆山—蘇州的3.1萬人次·d-1;太倉—上海日均客流量約7 617人次·d-1,高于太倉—蘇州市區(qū)的6 623人次·d-1。這一特征在南京與毗鄰的句容市也有所體現(xiàn),手機信令數(shù)據(jù)統(tǒng)計表明,句容—南京日均客流量約9.8萬人次·d-1,是句容—鎮(zhèn)江客流的2.2倍。
另一方面,大城市與其毗鄰地區(qū)體現(xiàn)以職住分離通勤客流為主的聯(lián)系需求特征,主要包括在毗鄰地區(qū)居住人口在中心城市就業(yè)、中心城市居住人口隨企業(yè)搬遷至毗鄰地區(qū)就業(yè)兩類。以上海與昆山為例,根據(jù)大數(shù)據(jù)分析,在蘇州居住、上海就業(yè)的人群中,有56%的人口居住在昆山;在上海居住、蘇州就業(yè)的人群中,有47%的人口工作在昆山[10]。這一以通勤為主的聯(lián)系特征也使得設(shè)施對接成為毗鄰地區(qū)現(xiàn)階段的主要需求,如上海—昆山對接道路計劃由現(xiàn)狀7條增至11條,以服務二者之間的緊密通勤聯(lián)系需求。
3 不同交通方式的適應性分析
當前長三角城際客運交通系統(tǒng)由公路及長途汽車客運、鐵路客運、城市軌道交通、城際公共汽車、私人小汽車等方式構(gòu)成。結(jié)合現(xiàn)狀和未來趨勢,分別分析其在城際交通中的作用和適應性。
3.1 公路及長途汽車客運
長三角公路網(wǎng)絡(luò)發(fā)展較為完善,高速公路、一級公路、二級公路在相當長時期內(nèi)支撐了區(qū)域城鎮(zhèn)空間布局和產(chǎn)業(yè)發(fā)展。隨著城市空間規(guī)模擴張和出行時效性要求的提升,城鎮(zhèn)密集地區(qū)內(nèi)的高速公路逐漸承擔了市內(nèi)長距離機動化出行。蘇州市區(qū)范圍內(nèi)的京滬高速、滬常高速、蘇嘉杭高速承擔了大量市區(qū)范圍內(nèi)的出行,高速公路功能逐漸兼顧本地化服務。另一方面,城市快速路逐漸向市域連綿地區(qū)拓展,市域干線公路建設(shè)趨近于城市快速路標準,二者的建設(shè)標準、需求特征均呈現(xiàn)融合發(fā)展態(tài)勢。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市域干線公路的功能融合發(fā)展態(tài)勢,體現(xiàn)了城際出行對出行時效、出行質(zhì)量的要求不斷提升。

圖4 蘇錫常城市密集區(qū)城際聯(lián)系分布情況Fig.4 Intercity travel distribution in urban areas of Suzhou,Wuxi,and Changzhou

圖5 城市毗鄰區(qū)城際關(guān)系示意Fig.5 Intercity links in urban adjacent areas
公路長途客運整體呈現(xiàn)規(guī)模萎縮和功能弱化的態(tài)勢。一是公路客運運距不斷下降并趨穩(wěn),二是長途汽車客運規(guī)模持續(xù)下降。特別是滬寧城際、京滬高鐵相繼開通后,蘇州公路客運平均運距由50 km降至35 km,上海對外交通中公路客運出行分擔率由2010年27.0%降至2017年17.3%。
另一方面,響應品質(zhì)服務的長途汽車客運業(yè)態(tài)出現(xiàn),由蘇州、無錫、南通、常州等地長途汽車客運公司聯(lián)合成立的“巴士管家”,采用“互聯(lián)網(wǎng)+交通”提供門到門城際客運服務,取得了良好的業(yè)務發(fā)展和市場口碑。
3.2 鐵路客運系統(tǒng)
總體上鐵路客運發(fā)展迅速,城際出行對鐵路的依賴程度不斷上升。城際商務人群對時效性要求的提升和上海、杭州等地機動車限行政策的影響,使得高速鐵路對城際客運出行吸引力持續(xù)增強。上海對外交通中鐵路出行分擔率從2010年45.3%上升至2017年54.2%。若考慮長三角范圍內(nèi)的城際出行,應遠高于這一數(shù)值。此外,長三角傳統(tǒng)的主廊道+主樞紐鐵路組織模式,在鐵路客運規(guī)模快速增長態(tài)勢下體現(xiàn)出一定的不適應性,在上海虹橋(滬寧通道與滬杭通道間)、杭州東站(寧杭通道與滬昆通道間)等主要樞紐的客流換乘現(xiàn)象愈發(fā)突出。
長三角高速鐵路發(fā)展面臨的另一挑戰(zhàn)在于,現(xiàn)狀高鐵運力中長短不同距離客流相互擠占(見圖6)。以京滬高鐵和滬寧城際為例,二者速度目標值均為350 km·h-1。由于上海與南京間區(qū)段城際出行需求旺盛,高鐵區(qū)段能力結(jié)構(gòu)上供不應求,已達飽和運行狀態(tài)。從現(xiàn)象上看,京滬兩城間高速列車班次(旅行時間約為4 h 30 min)一票難求,滬寧段(特別是上海至蘇州區(qū)段)早晚高峰時段客票也經(jīng)常處于緊張狀態(tài)。從數(shù)據(jù)上看,2012—2016年,京滬高鐵上海至長三角沿線各市客流平均增長189%,而同期滬寧城際上海至長三角沿線各市客流平均降低14%。究其原因,主要包含三個方面:1)京滬高鐵的市場化運作使得追逐短距客流成為必然,客票收益的外部驅(qū)動高于系統(tǒng)效益的內(nèi)在提升;2)滬寧段高鐵運力不足,而該區(qū)段承擔著面向更大范圍的高鐵網(wǎng)絡(luò)化運營,導致長三角內(nèi)部城際規(guī)律化出行需求難以充分滿足;3)強者恒強的馬太效應,犧牲了部分長三角內(nèi)部列車班次,損失最大的是一般城市的城際出行需求。
3.3 城市軌道交通對接
隨著長三角各城市軌道交通建設(shè)的加速推進,城市密集地區(qū)和毗鄰地區(qū)的軌道交通對接和延伸訴求強烈。最為典型的是上海軌道交通11號線跨界延伸至昆山花橋,實現(xiàn)了長三角首個城市軌道交通跨市延伸服務。而根據(jù)最新批復的軌道交通建設(shè)規(guī)劃,蘇州S1線在花橋站與上海11號線實現(xiàn)換乘銜接。除此之外,太倉、吳江等地均在積極尋求軌道交通的毗鄰對接。
“花橋模式”盡管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滬昆交接地區(qū)的毗鄰出行,特別是因職住分離產(chǎn)生的通勤出行需求,但實際上無法適應和滿足城際間快速聯(lián)系訴求。昆山花橋至上海人民廣場軌道交通在途時間超過1.5 h,若考慮蘇州市區(qū)至上海通過S1線接駁則至少超過2.5 h,其時效性遠不及城際鐵路或高速公路方式。
3.4 城際公共汽車
城際公共汽車在解決毗鄰地區(qū)相互間通勤和日常生活交通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根據(jù)測算,毗鄰地區(qū)間每日交通聯(lián)系需求增長旺盛,昆山—嘉定4.0萬人次·d-1,張家港—江陰3.8萬人次·d-1。因此,鄰邊城市間積極探索公共交通跨區(qū)服務,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一種是采用長途客運方式(如嘉定—太倉快線)實現(xiàn)與城市軌道交通車站的一站式接駁,另一種是采用常規(guī)公共汽車模式(如K588杭州至湖州德清)由兩地協(xié)調(diào)運營。
3.5 私人小汽車
隨著家庭擁車的日益普及,私人小汽車因其舒適性和自由彈性成為城際出行的重要方式選擇。特別是長三角文化旅游景點眾多,周末或節(jié)假日私家車度假旅游已成風尚。蘇州景區(qū)2015年外來游客的自駕游比例已達27%;湖州太湖度假區(qū)、舟山普陀山等景區(qū)因自駕游帶來的對道路網(wǎng)絡(luò)、停車設(shè)施的沖擊難以重負。而從出行時效和距離范圍來看,自駕車方式仍存在較大的局限性,較為易于接受的范圍一般在2 h(150 km)內(nèi)。
4 長三角城際交通發(fā)展模式
4.1 總體模式
以往城際交通的組織模式是以城市對外交通的規(guī)劃建設(shè)為主來進行的,而隨著城際交通的規(guī)模、頻次和對品質(zhì)的要求提升,城際交通的特征愈發(fā)趨同于城市內(nèi)部組團間交通,要求兼顧系統(tǒng)整體效益和不同人群的出行需求,重塑城際交通服務體系。
必須實現(xiàn)的模式轉(zhuǎn)變在于,從固有的設(shè)施建設(shè)視角轉(zhuǎn)變?yōu)榉諏蚰J健T诩扔械囊猿鞘袑ν饨煌ㄔO(shè)施主導的模式中,更多強調(diào)的是對外交通樞紐和通道自身的標準和規(guī)模,更受關(guān)注的是建設(shè)環(huán)節(jié),在此過程中規(guī)劃、建設(shè)、運營環(huán)節(jié)單向傳遞,而服務僅作為被動派生品,終端效應突出,難以適應出行品質(zhì)的提升要求,也無法實現(xiàn)相互間的反饋互動。
在新的發(fā)展形勢背景下,特別是長三角更高質(zhì)量一體化發(fā)展上升為國家戰(zhàn)略,城際交通體系作為非常重要的支撐要素,必須滿足城際出行人群日益增長的高品質(zhì)出行服務需求,著眼于城際出行整體服務體系的構(gòu)建。要以服務水平作為基本導向和準則,審視城際交通體系的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和系統(tǒng)短板,從而指導增量部分的設(shè)施規(guī)劃、建設(shè)和運營并相互反饋,強化存量部分的有效更新以適應出行鏈的變化(見圖7)。
同時,還應體現(xiàn)不同群體的差異性,提供多元化的城際交通服務。通勤人群具有出行規(guī)律性、頻率高的基本特征,要求較高的時效性和可達性,偏好出行流程的簡單化、便捷化;商務人群出行起訖點往往位于城市中心或功能地區(qū),對出行時效性和舒適度要求高,偏好出行的直達性或無縫銜接;旅游人群的突出特征是對出行品質(zhì)要求高,景點間的鏈式出行較多,偏好良好的出行體驗。
長三角人口和城鎮(zhèn)分布密集,可利用的交通廊道資源極為有限,未來城際交通的構(gòu)建應更加強調(diào)建立在集約化和高效率之上的高質(zhì)量發(fā)展,因而由高速鐵路、城際軌道交通、市域軌道交通、城市軌道交通組成的廣義軌道交通體系將成為城際出行的主導交通方式和發(fā)展重點。
4.2 系統(tǒng)視角:主導交通方式的功能要求
從城際交通作為一個系統(tǒng)整體出發(fā),要綜合協(xié)調(diào)各個組成部分的相互聯(lián)系和制約關(guān)系,服從整體優(yōu)化要求,綜合考慮各不同空間層次的城際出行需求,選擇配置差異化的交通方式,通過綜合組織和管理來強化主導交通方式的功能性要求,以達到不同群體的服務準則要求。
4.2.1 跨區(qū)大尺度城際出行
高速鐵路(設(shè)計速度350 km·h-1或更高)在服務跨區(qū)大尺度城際出行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優(yōu)勢,特別是強化區(qū)域內(nèi)中心城市間的直達聯(lián)系方面,應優(yōu)先保障此類通道在高時效性下的供給。高速鐵路將以2.5 h時空圈覆蓋長三角主要中心城市間的聯(lián)系需求,宜作為城市群中跨區(qū)大尺度出行的主導交通方式(見圖8)。
優(yōu)先需要保障的廊道包括:京滬通道、滬昆通道、滬漢蓉通道、寧杭通道、合湖(杭)蘇滬通道、京滬二(沿海北)-通蘇嘉甬-沿海南通道。在功能組織上,應以高速鐵路為主導,適度分離短距離城際功能,釋放運力,優(yōu)先保障長距離出行并以此體現(xiàn)較高的時效性。

圖7 長三角城際客運發(fā)展總體模式Fig.7 Intercity passenger transportation pattern of Yangtze River Delta
以京滬高鐵為例,以上海為起點進行研究。目前上海至南京以遠地區(qū)(含)、上海至南京以近地區(qū)的運力分配約各占一半,且滬寧區(qū)間段作為運營組織的關(guān)鍵區(qū)段運力已基本飽和,導致短距區(qū)段運力不足、長距區(qū)段運力時效性難以繼續(xù)提升。若未來短距城際鐵路投入運營并轉(zhuǎn)移部分短距客流,并考慮功能優(yōu)化引導后,經(jīng)計算可至少釋放800萬人次·a-1運力服務長距離客流,且此部分運能有條件進一步提高其時效性。
4.2.2 都市圈城際出行
都市圈城際出行應遵循廊道輻射、分層組織的原則(見圖9)。都市圈商務緊密聯(lián)系圈層半徑一般約為50 km,主要服務于跨區(qū)商務客流,以1 h可達為基本約束,以城際鐵路和高速公路為主導交通方式;在規(guī)劃引導上應進一步強化向心式通道網(wǎng)絡(luò)和交通樞紐的銜接轉(zhuǎn)換作用,應推動城際鐵路、市域(郊)軌道交通線的統(tǒng)一規(guī)劃建設(shè)和跨界運營,構(gòu)建都市圈城際客運主體。

圖8 長三角跨區(qū)大尺度高速鐵路通道布局Fig.8 High speed cross-regional corridor layout in Yangtze River Delta

圖9 都市圈空間圈層和城際交通組織Fig.9 Space and intercity transportation organization of typical metropolis circle
都市圈通勤聯(lián)系圈層半徑一般不超過30 km,主要服務于每日通勤人群,出行需求與城市化客流無異,以1 h門到門為基本約束;在規(guī)劃引導上應以市域(郊)軌道交通線和城市軌道交通快線為主導,輔以快速路、定制化公交系統(tǒng),強化交通樞紐和城市功能中心的耦合,以及與城市軌道交通網(wǎng)絡(luò)的轉(zhuǎn)換作用。
4.2.3 城市密集區(qū)城際出行
城市密集區(qū)應以滿足網(wǎng)絡(luò)化、多元化出行需求為出發(fā)點,積極尋求多模式、多層次的網(wǎng)絡(luò)對接和貫通運營。主要城市中心間應依托城際鐵路和交通樞紐服務中長距離緊密聯(lián)系出行需求,次級中心或城鎮(zhèn)間在有條件情況下可考慮城際鐵路功能下沉或依托市域(郊)軌道交通線擴大服務覆蓋面。在城市密集區(qū)范圍內(nèi)組織城際班列網(wǎng)絡(luò)化運行(而非按通道運營),在主要廊道上積極創(chuàng)造條件實現(xiàn)城際鐵路公交化運營組織,特別是在高需求區(qū)間開行交路高頻班列。
在特色化地區(qū),著力實現(xiàn)不同系統(tǒng)模式間的對接共享,以跨區(qū)公共交通、道路對接、游線組織提升跨界交通品質(zhì)。
4.2.4 城市毗鄰區(qū)城際出行
城市毗鄰區(qū)更多要考慮同城化的交通組織,按同一城市標準組織跨行政邊界出行。將公交優(yōu)先延伸至跨界地區(qū),以軌道交通樞紐銜接換乘、常規(guī)公共汽車跨區(qū)運營和票制一體化,實現(xiàn)不同公交系統(tǒng)模式間的對接共享。在路網(wǎng)方面,從規(guī)劃和建設(shè)兩個層面做好道路對接,強化道路功能、建設(shè)標準、實施時序等方面的跨界協(xié)同。
4.3 用戶視角:交通樞紐模式革新
在關(guān)注城際交通系統(tǒng)的整體效益和功能發(fā)揮的同時,還應從使用者角度出發(fā),亦即城際出行人群的切身體驗,優(yōu)化城際交通的組織和服務。隨著城際出行群體的擴大,城際出行的便利性愈發(fā)受到關(guān)注,當前飽受詬病的莫過于城際出行的兩端接駁銜接問題。市內(nèi)交通樞紐接駁時耗往往大大超過高鐵在途時間,“高鐵半小時,兩端2小時”的負面效應突出;作為市內(nèi)交通最可靠的接駁方式,軌道交通又面臨重復安檢、閘機、取驗票、換乘等諸多環(huán)節(jié)制約,出行時間難以預估;高頻次、規(guī)律性的城際商務通勤人群要求在途和換乘公交化、壓縮站內(nèi)停留時間。以上痛點的解決,實際上對目前對外交通樞紐的服務和組織模式提出了革新的要求。
以往對外鐵路樞紐的規(guī)劃建設(shè)強調(diào)集中布局,有利于鐵路運行系統(tǒng)的效益最大化。上海虹橋站2017年接發(fā)量高達1.2億人次·a-1,集中了全市近60%的鐵路客流,而杭州東站對應數(shù)據(jù)分別為1.12億人次·a-1和80%。交通樞紐的集中布局帶來了市內(nèi)換乘接駁時耗長、通道和樞紐資源緊缺的負面效應。另一方面,隨著交通樞紐周邊形成面向區(qū)域一體化的樞紐地區(qū)(上海虹橋商務區(qū)最為典型),人群的活動軌跡表明交通樞紐與周邊功能空間呈現(xiàn)明顯的融合態(tài)勢,而樞紐地區(qū)的功能業(yè)態(tài)又以企業(yè)總部、會展、貿(mào)易等類型為主,區(qū)域城際人群占比高,周邊地區(qū)對樞紐的依賴程度提高(見圖10)。由于交通樞紐規(guī)模過大且建設(shè)模式傳統(tǒng),導致樞紐—空間界面隔離效應明顯,客流集散主要依靠到發(fā)層機動車和軌道交通換乘解決。而在交通樞紐周邊1 km甚至500 m范圍內(nèi)的接駁則成為最難的盲點,這恰恰與樞紐地區(qū)的融合發(fā)展趨勢相悖。
樞紐作為城際交通的關(guān)鍵界面,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城際交通的服務水平提升,因而有必要基于服務導向進行城際樞紐模式革新。這一革新應既考慮宏觀布局又關(guān)注樞紐自身的功能組織。
4.3.1 模式一:樞紐功能適度分離
未來城際通道將呈現(xiàn)層級化布局,特別是對超大城市、特大城市而言,城際廊道既需要跨區(qū)大尺度的高速鐵路系統(tǒng),也需要服務于都市圈和城市密集區(qū)的城際軌道交通系統(tǒng)。對于樞紐而言,隨著城際交通網(wǎng)絡(luò)的不斷完善,將催生若干區(qū)別于傳統(tǒng)門戶樞紐的城際樞紐。
此類城際樞紐主要面向長三角或都市圈范圍,服務于所在組團或片區(qū)的高頻次、規(guī)律性的城際商務、通勤出行,與服務于全市的門戶樞紐在空間和功能上實現(xiàn)分離。與傳統(tǒng)門戶樞紐的主要差異在于,此類城際樞紐有利于實現(xiàn)分散的空間均衡布局,與鄰近功能空間可有條件實現(xiàn)站城一體、無縫結(jié)合,在城際通道的運營組織上更易于實現(xiàn)公交化(見圖11a)。在線路和樞紐建設(shè)模式上,可選擇地下線敷設(shè)(如深圳福田站),與城市組團中心實現(xiàn)立體化、復合化布局,利用非機動交通縫合空間,提升人流集散效率。
以蘇州為例,城際軌道交通網(wǎng)絡(luò)化條件下采用相對分散的城際樞紐布局模式,將城際樞紐融入城市中心體系布局,規(guī)劃8個城際樞紐,結(jié)合工業(yè)園區(qū)、新區(qū)、姑蘇、吳江等功能板塊,服務其與長三角其他地區(qū)的快速聯(lián)系需求。粗略計算,融入功能中心的分散布局模式將節(jié)省城際換乘和接駁時耗達40%~60%,將大大提升城際出行的效率和體驗。
4.3.2 模式二:門戶樞紐地區(qū)的組合樞紐
門戶樞紐地區(qū)是超(特)大城市的一類典型地區(qū),圍繞空港、高鐵樞紐往往已形成面向區(qū)域的功能組團,既承載了交通門戶職能,也帶來了周邊地區(qū)密集的往來聯(lián)系(見圖11b)。在此情況下,片面要求樞紐的集聚布置,實際上有損于雙重職能的有效發(fā)揮。因此,大型門戶樞紐地區(qū)的組合樞紐模式成為行之有效的解決路徑。顯而易見,門戶樞紐功能強化的是面向國家甚至全球的超長距離客流,服務于全市甚至區(qū)域范圍,追求更高的時效性;而城際樞紐則主要面向長三角地區(qū),服務于樞紐地區(qū)自身的高強度、高頻次客流。二者在樞紐地區(qū)形成組合關(guān)系,既有效疏解門戶樞紐的客流和通道組織壓力,也能保障城際班列的組織效率。二者之間必要的換乘和代償關(guān)系可通過雙樞紐間的捷運系統(tǒng)或步行連廊加以解決,還可以與樞紐地區(qū)重要功能節(jié)點實現(xiàn)串聯(lián)。
以倫敦國王十字車站組合樞紐為例,該地區(qū)集中了圣潘克拉斯車站、國王十字車站和尤斯頓車站,三者功能分別為歐洲之星終點站、國內(nèi)鐵路樞紐和都市圈通勤列車,樞紐周邊集中了企業(yè)總部、商務辦公、大學、創(chuàng)意園區(qū)和住宅等,樞紐之間通過城市軌道交通銜接串聯(lián),也可步行到達(見圖12)。

圖10 虹橋樞紐人群活動熱力圖Fig.10 Thermodynamic activity chart of the crowd around Hongqiao Hub
組合樞紐在空間上適當拉開距離,有利于擴充樞紐空間界面,實現(xiàn)樞紐空間的功能多元化;在通道接入上,門戶樞紐以高速鐵路為主,城際樞紐以城際軌道交通為主,同時保證網(wǎng)絡(luò)互通;最重要的是,優(yōu)先考慮城際樞紐與功能中心的步行交通銜接,距離尺度和品質(zhì)滿足步行進出樞紐的要求。
5 結(jié)語
長三角更高質(zhì)量的一體化發(fā)展離不開高質(zhì)量城際交通系統(tǒng)的支撐,這就要求新一輪城際交通體系的完善應以服務為導向,不能僅局限在通道和樞紐設(shè)施自身的規(guī)模和標準,而應擴大著眼于城際全過程出行鏈的服務品質(zhì)提升。同時,城際交通系統(tǒng)的功能組織應更加注重差異化的空間層次和多元化的人群需求,體現(xiàn)城際出行服務的功能性和體驗感,城際樞紐所起到的作用將愈發(fā)凸顯。當然,城際交通服務體系的構(gòu)建仍存在諸多體制和行業(yè)壁壘,亟待跨行政體制機制的創(chuàng)新和改革,這也是后續(xù)將繼續(xù)關(guān)注和研究的方面。

圖11 城際樞紐布局模式Fig.11 Layout pattern of intercity hubs

圖12 倫敦國王十字車站樞紐地區(qū)案例Fig.12 Hub area case of King's Cross station in Lond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