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群抑郁癥狀與睡眠障礙的相關性研究
作者單位:100101北京市,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六醫院干部病房(王宏,楊媛,董宏艷);161000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齊齊哈爾市中醫醫院病案室(王丹)
睡眠障礙作為老年人最常見的睡眠問題,隨著中國社會老齡化,其發生率將不斷升高,因此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據文獻報道,約50%中國老年人存在入睡困難、睡眠時間短、失眠、日間嗜睡等睡眠問題[1]。長期的睡眠障礙會對老年人生理及心理造成諸多不良的影響,尤其表現為抑郁和焦慮癥狀的患病風險升高[2]。國內外相關研究指出睡眠障礙與抑郁、焦慮具有顯著的相關性[3-4]。然而針對中國老年人,基于主觀和客觀監測的睡眠特征與抑郁癥狀的研究結論尚缺乏。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通過主觀和客觀方式監測的睡眠特征與抑郁癥狀的關系。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16年9月至2018年2月入住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六醫院有睡眠障礙癥狀的老年病人594例,年齡60~78歲。入組標準: (1)年齡≥60周歲;(2)意識清楚,有良好的語言表達能力和閱讀能力,能夠進行有效的溝通;(3)對本研究內容知情同意,愿意配合。排除標準:患有嚴重的急慢性疾病以及傳染病,如嚴重的心臟衰竭、腎臟衰竭、肺部疾病、肝臟疾病、惡性腫瘤等。
1.2 睡眠時間與連續性 本研究采用Actiwatch腕式睡眠監測儀(Philips Respironics, Murrysville, PA, USA)對受試者進行7 d的平均睡眠時間和睡眠連續性的監測。整個過程在睡眠室中進行,并有兩名專業人員負責連接導聯和監測睡眠過程。測試結束后通過計算軟件自動對數據進行分析得出結論。本研究以平均睡眠時間<6 h定義為睡眠時間短,>9 h為睡眠時間長,6~9 h為正常睡眠時間[5];睡眠連續性以平均睡眠效率(入眠之后睡眠時間/總睡眠時間)為指標,平均睡眠效率<85%定義為睡眠連續性差[6]。另外,我們還計算平均睡眠潛伏期(min)。進行腕式睡眠監測時同步進行多導睡眠儀監測,記錄氣流、胸腹運動、腦電圖、心電圖、眼電圖、肌電圖及動脈血氧飽和度(SaO2)。根據診斷及分度標準[7],本研究以呼吸暫停低通氣指數(apnea hypopnea index,AHI)≥40次/h定義為阻塞性睡眠呼吸暫停低通氣綜合征(OSAHS)。
1.3 睡眠質量 分別采用女性健康倡議失眠評定量表(Women’s Health Initiative Insomnia Rating Scale,WHIIRS)和愛潑沃斯嗜睡量表(the Epworth Sleepiness Scale, ESS)評價老年人失眠癥狀和嗜睡情況。WHIIRS量表共5個自評條目,每個自評條目采用0~4分方式計分。WHIIRS總分為各個維度得分之和,范圍為0~20分,其中WHIIRS總分≥10分定義為存在臨床顯著性失眠癥狀。ESS量表共分為8個條目,主要收集測試者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遇見的場景,考察在各個場景下的困倦情況,每個條目按0~3分計分。ESS總分為各個條目得分之和,范圍為0~24分,其中ESS總分>10分定義為極度嗜睡[8]。
1.4 抑郁癥狀評價與分組 本研究采用CES-D(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評價老年人抑郁情況,共20個條目,其中4個條目為反向計分,采用0(沒有或幾乎沒有)至3分(幾乎一直都有)方式計分。總分范圍為0~60 分,其中CES-D總分<16分定義為無抑郁癥狀(正常組),≥16分為存在抑郁癥狀(抑郁癥狀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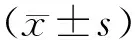
2 結果
2.1 基本資料 本研究共納入594例老年病人,平均年齡(68.34±8.57)歲,其中男329例(占55%),女265例(占45%),高學歷老年人132例(占22.2%);伴有心血管疾病20例(3.4%)、高血壓325例(54.7%)、糖尿病111例(18.7%)。正常組508例(85.5%),抑郁癥狀組86例(占14.5%)。2組年齡、體質量指數(BMI)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其他基本特征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1。
2.2 睡眠狀況 本研究中共計166例(27.9%)老人患有失眠癥狀(WHIIRS≥10分),75例(12.6%)患有日間極度嗜睡,87例(14.6%)患有重度OSAHS,34例(5.7%)患有睡眠呼吸暫停綜合征(SAS)(AHI>15次/h+日間極度嗜睡),181例(30.4%)睡眠時間短。抑郁癥狀組短時間睡眠、失眠、OSAHS和日間極度嗜睡率高于正常組,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0.05),但2組間在睡眠連續性和睡眠階段分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見表2。

表1 2組老年人群基本資料比較(n,%)
注:與正常組比較,*P<0.05

表2 2組睡眠質量比較(n,%)
注:與正常組比較,*P<0.05
2.3 睡眠時間、持續性與抑郁癥狀相關性 當校正年齡與性別因素后,風險模型結果顯示,與正常睡眠時間組相比,睡眠時間短和睡眠時間長的老年人群的抑郁癥狀患病風險均顯著增加,分別為正常睡眠組的1.61倍和2.4倍(P<0.05)。然而,當納入BMI、吸煙等其他因素后,睡眠時間長組患有抑郁癥狀的風險明顯降低,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睡眠時間短組仍具有統計學意義(PR=1.47,95%CI:1.11~1.94)。
當校正年齡與性別因素后,與睡眠連續性良好的老年人相比,睡眠連續性差會導致抑郁癥狀的患病風險增加53%(PR=1.53,P<0.05),并且當納入其他因素后,風險無明顯的變化,仍具有統計學意義(PR=1.50,95%CI:1.06~2.13)。見表3。

表3 睡眠時間、睡眠持續性與抑郁癥狀相關性
注:模型1: 校對年齡與性別;模型2: 校對年齡+性別+學歷+BMI+高血壓+糖尿病+吸煙
2.4 失眠、嗜睡、OSAHS與抑郁癥狀的相關性 當校正年齡與性別因素后,風險模型結果顯示,伴有失眠癥老年人患有抑郁癥狀風險是無失眠癥老年人的1.8倍(PR=1.80,95%CI:1.39~2.32),且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當進一步校正BMI等其他因素后,抑郁癥狀患病風險差異依舊顯著(PR=1.78,P<0.05)。
日間極度嗜睡也與抑郁癥狀具有顯著相關性。與無日間嗜睡的老年人相比,日間嗜睡可增加68%的抑郁癥狀患病風險(PR=1.68,95%CI:1.27~2.22),且納入更多的危險因素后,患病風險并無明顯的變化(PR=1.61,P<0.05);然而,OSAHS與抑郁癥狀患病率無顯著相關性。見表4。
3 討論
抑郁癥是老年人群中常見的心理疾病[9],其高患病率已成為威脅人類健康最為重要的精神衛生問題之一,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全球疾病負擔評估報告顯示,

表4 失眠、睡眠呼吸暫停癥與抑郁癥狀的相關性
注:模型1: 校對年齡與性別;模型2: 校對年齡+性別+學歷+BMI+高血壓+糖尿病+吸煙
至2020年,抑郁癥將成為繼冠心病后的世界第二大疾病負擔源[10]。在中國,老年人抑郁癥的發生率有逐步升高的趨勢[3],它不僅危害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生活質量,還給家庭和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
睡眠時間與睡眠連續性不僅會影響老年人群的生理狀況,而且也與情緒、注意力等精神狀況密切相關,相關的研究也越來越受到關注[11-12]。近期,一項隨訪2年的研究發現,睡眠時間較短或較長均會增加抑郁和焦慮的患病風險[11];此外,伴有失眠癥的人群發生抑郁和焦慮的風險是正常人群的1.5倍。Li等[12]在基于中國隨訪大樣本數據研究發現,與睡眠正常的老年人相比,睡眠時間<6 h的中老年人抑郁癥的發生風險增加45%。與此同時,有研究也證實了睡眠時間過長也是抑郁癥獨立危險因素。例如,近期的Meta研究結果顯示,睡眠時間過長與抑郁癥具有顯著負相關,與正常睡眠相比,會增加其發生風險[13]。本研究結果與既往研究報道一致,證實了睡眠時間長度與抑郁癥狀之間的U型關系:與正常睡眠時間的老年人相比,睡眠時間較短(<6 h)和較長(>9 h)都會導致抑郁癥狀發生率的升高。現階段,盡管睡眠與抑郁之間的具體發生機制尚不明確,但大部分學者推測的潛在機制如下:首先,由于夜間睡眠質量差引起的日間身體和心理疲勞可能會打亂晝夜節奏,引起荷爾蒙改變,從而導致抑郁癥的發生;其次,在抑郁癥人群,睡眠持續時間與炎癥水平升高密切相關。慢性低度炎癥是潛在連接睡眠和抑郁癥狀的生物通路;再次,一些學者認為,夜間睡眠時間較短可能是心理障礙的先兆之一[12, 14-16]。
與此同時,失眠等睡眠障礙也會引起抑郁癥狀。近期,國外一項僅納入正常人群(無抑郁癥狀)的前瞻性研究顯示,在隨訪7.5年后,睡眠質量差和失眠人群的抑郁癥狀發病率顯著升高,并且失眠人群是抑郁癥狀發病風險最高的群體,約為無失眠癥人群的2倍以上[17],此外失眠癥狀嚴重程度也會不同程度地影響抑郁癥狀。相似的,在一項納入21篇文獻的Meta分析表明,失眠癥人群的抑郁癥狀的患病風險是正常人群的2倍[18]。此外,LaGrotte等[19]通過前瞻性研究還發現,日間嗜睡是抑郁癥的前期癥狀,也會導致其發生風險的提高。本研究從中國老年人群入手,也證實了失眠癥和日間嗜睡均是老年人常見的癥狀,并且與抑郁癥狀緊密相關。在校正多個混雜因素后,失眠癥與抑郁癥狀相關性仍具有統計學意義。
綜上所述,本研究通過主觀和客觀方式監測睡眠情況,證實了睡眠時間、持續性與質量是老年人抑郁癥狀重要的預測因子。由此,應提倡建立早期干預睡眠質量的公共措施,從而有效地降低由睡眠障礙引起的抑郁癥狀的發生和發展。未來研究的方向需要進一步探索睡眠特征與年齡變化之間相互作用對老年人群抑郁癥狀的影響,為促進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提供一定的理論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