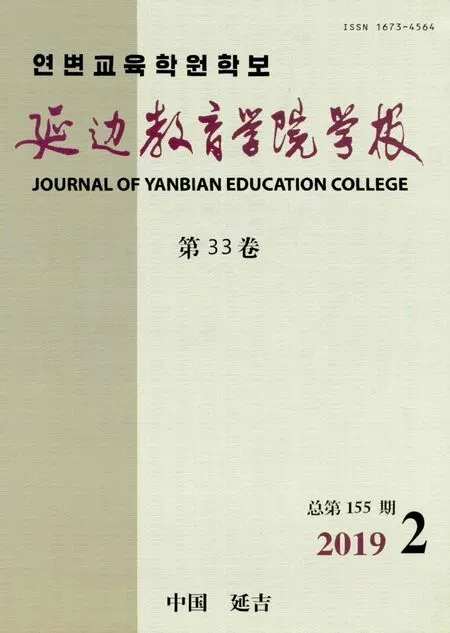網絡主播勞動關系的認定
王 健
網絡主播勞動關系的認定
王健
(華僑大學, 福建 泉州 362000)
由于網絡主播工作性質模糊以及現有的勞動法標準無法適用等原因,給網絡直播者的勞動關系的認定帶來了困境。本文從比較傳統勞動關系角度出發,找到網絡直播勞動關系認定的關鍵點和切入點,并引入網絡主播第一案例,進行學理評析。
網絡主播;勞動關系;非典型勞動關系;屬性界定
隨著信息技術和“互聯網+”模式在國內的不斷發展,現實生活中新生了許多與互聯網經濟有關的產業和職業,而網絡直播者就是其中的一個典型。據不完全統計,“2017年我國網絡表演市場整體營收規模達到304.5億元,各大直播平臺上有影響力的主播就已經超過40萬人。”網絡直播這一行業已在我國初具規模,但這一職業的勞動關系定位問題一直沒有厘清,現實生活中也因此引發了不少勞動糾紛問題。
一、勞動關系的界定比較
之所以要對網絡直播者的勞動關系進行比較,是因為其是非典型的勞動關系,和傳統的勞動關系認定存在著較大的差異。網絡主播的存在離不開網絡平臺和互聯網技術的支持,而網絡主播作為平臺的主體和核心資產,在接受著平臺運行者的管理同時,也獲得相應的工作報酬。由于網絡直播者的工作地點、方式、內容等均需要通過網絡平臺進行,這就構成了與傳統勞動方式最大的差別在于其始終依附了這個網絡平臺,同時這一平臺也在無形中弱化了勞動者的從屬性,造成了實務中認定網絡直播者為勞動關系的難度。
1.傳統勞動關系的界定
關于勞動關系如何認定的問題,我國現有的《勞動法》并沒有作出明確的規定,只是在2005年由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出臺了《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中就事實勞動關系如何認定作出了規定。第一條規定:“用人單位招用勞動者未訂立書面勞動合同,但同時具備下列情形的,勞動關系成立。一、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主體資格;二、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各項勞動規章制度適用于勞動者,勞動者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三、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用人單位業務的組成部分。”從現有的法律條文中我們也可以得出傳統的勞動關系的構成要件:首先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主體適格,就是一方面為勞動者提供崗位的用人單位須是符合法律規定的企業、民辦非企業單位、個體經濟組織等,另一方面作為勞動者需要有相應的從事勞動能力,諸如年齡、國籍、精神狀況等,同時還要符合法定諸如性別、工作能力等特定要求。其次,就是相應的生產關系要素,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簽訂合同,這一合同的主要標的就是勞動者為其提供勞務,這一生產要素還具有特定的人格從屬性。所謂的人格從屬性就是用人單位將勞動者納入自己的控制范圍之內,同時用人單位需要為勞動者提供勞務支付對價并對其因勞務工作產生的風險負責。第三個構成要件是勞動者的經濟從屬性,意思是其為用人單位提供的勞務必須是用人單位旗下的業務,是用人單位生產或服務內容的組成部分。這三個要件構成了傳統勞動關系的認定。
2.網絡主播關系的認定
對網絡主播關系的認定的前提是需要搞清楚其與傳統勞動關系的區別。筆者通過相關案例和邏輯推理歸納了以下幾點區別:第一,網絡主播的工作場所一般不受限制,可以選擇在家或者其他非固定公司場所工作;第二,工作方式離不開互聯網,對網絡的依賴是百分百的,離開了網絡就無法工作。第三,網絡主播這一工作是常態化工作,是一個可持續的一種狀態。在判定網絡主播就業模式是否系勞動關系時,需要與傳統的勞動關系認定標準進行比較。在這一過程中,關鍵是要認定其是否與網絡平臺系從屬關系,判定勞動者與用人單位是否系從屬性關系,其實也很簡單,如果一個網絡主播付出了勞動,而用人平臺支付了相應的報酬,這時候勞動關系就比較明確。但現實生活中并不完全都是這樣的,有的網絡主播會與網絡平臺公司簽訂相應的勞動合同,這就可以在法律上認定為勞動關系。也有一種主播是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這就需要通過考量是否系事實勞動關系,也就是其工作性質是否屬于公司組成部分以及工作是否受公司規章管控和監督[1]。如果主播僅僅是一時興趣,在家隨便開個直播,利用平臺進行工作,公司也會給與相應的報酬,但并沒有按照公司規定和勞動用人程序走的話,則不宜認定為完整意義上的勞動關系,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勞動從屬性的弱化。因此,對于網絡主播關系的認定問題,還需要結合具體情況來進行分析。
二、網絡主播關系認定過程中的關鍵問題
1.正確區分勞動關系與合作關系
正確區分網絡直播系勞動關系還是合作關系,對于網絡直播平臺和直播工作者都尤為重要。簡單來說,網絡直播者傾向于認定為勞動關系,因為可以從中獲取更多的保障,而對于網絡平臺來說,認定合作關系可以避開很多風險以及減少責任的承擔。筆者認為如果網絡主播的實際工作形式及利益分配等體現了雙方強烈的人身隸屬性,那么本質上就應該認定為勞動關系,就應該簽訂相應的勞動合同,而不是試圖通過簽署合作協議規避用人單位在勞動法項下的責任,否則如果出現了糾紛,直播平臺可能會承擔更多的風險與責任。當然,現實中如果網絡平臺想和主播簽訂合作協議關系的話,就應該合理避開類似于勞動關系的特征,比如在設計合同條款時,盡可能給予主播工作的自由,減少對其工作的監控和干預,盡量避開與勞動關系類似的條款。
2.直播平臺與主播之間的“合作協議”法律定性
其實,在現實生活中,由于網絡主播與平臺之間的關系復雜不明,造成了二者簽訂的書面合同往往表現為“合作協議”,這給實務部門在處理相關案件過程中設立了不少障礙,那么對于所謂的“合作協議”應該如何定性呢?第一,這個協議在法律文本上的定義并不是特別清晰,不能簡單從字面上把握訂立者的締約目的;其次,盡管有些網絡平臺為了降低自己的風險和責任承擔,在制定這個所謂合作協議條款時,盡可能避免擬定類似勞動合同條款,但在合同法上,關于合同性質的歸屬,并不會以名稱來判定的。對于這一問題,大多數學者支持認定為勞動關系,其主要歸結的思路也是從事實勞動關系角度出發的[2]。而筆者搜集了一些相關案例,但凡有簽署所謂的合作協議的糾紛,一般法院也都按照認定勞動關系來判,大多數法官的審判思路也是基于網絡公司與簽約主播有實質上的人身經濟依附性和從屬性關系來的。
三、案例分析——網絡主播要求確認勞動關系被駁回
有一名90后女孩阿嬌,因一次偶然的機會從事了網絡主播這個行業。據她本人透露,她每天在直播間里化妝唱歌跳舞等,有時候只是和平臺上的觀眾聊聊天,就會得到她“粉絲”們的紅包和賞金,短短不到半年時間,她就從一個不知名的女孩變成了擁有60多萬粉絲的網紅。一開始,阿嬌和上海某網絡科技中心簽訂《主播經紀協議》,并由該公司指定其在某網站上的直播間直播。這份協議對阿嬌的工作涉及的內容、雙方所需負的權利義務、合作洽談費用、收益報酬分配、違約責任的承擔等都進行了約定,除此之外,還制定了一系列阿嬌作為主播可以在該平臺上能夠從事的活動,諸如表演、錄制、播放、視頻等,也規定了其不可以從事的相關內容及違約條款,對阿嬌的工作內容做出了很多規范與限定,還約定該公司聘請阿嬌作為獨家主播,享有其全部主播事業的經紀權;協議期限36個月;同時還約定,公司每月向阿嬌支付保底收入5000元。經過該公司的精心包裝,阿嬌的名聲逐漸在網絡上傳開。幾個月過后,阿嬌以該公司未為其繳納社保為由申請仲裁,并終止了在該直播房間里的直播服務,提出了申請要求:第一、確認與經紀公司存在勞動關系;第二、經紀公司支付解除勞動關系經濟補償金2500元。仲裁委員會對其請求不予支持。于是,阿嬌以相同訴請訴至法院,亦被一審法院駁回。阿嬌不服判決,向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阿嬌在庭審中聲稱與該網絡平臺簽訂的《主播經紀協議》實際上是勞動合同,因其有約定每月保底工資5000元,并將收益三七分配,這屬于雙方對于工資的約定,可以證明雙方存在勞動關系。另外,根據勞動法和合同法的相關規定,經紀公司未按規定為其繳納社保,自己有權要求其支付解除經濟補償金。但該網絡平臺公司并不認可阿嬌的說法,其代理人認為二者的關系系普通合同關系而非勞動關系,因該主播工作主要在家,且靈活自由,未受到公司規章規定的約束,缺乏最基本的人身依附關系,不應當認定為勞動關系更無需支付經濟補償金一說。同時指出阿嬌以公司未繳社保為由,不顧公司利益擅自停播,本就是單方面違約行為,給公司帶來了巨大的損失,應該追償阿嬌的違約責任。
通過上述案情,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本案的爭議焦點系阿嬌與該網絡平臺公司之間是否構成勞動關系。筆者認為,認定勞動關系核心在于勞動者是否受到用人單位的管理約束,勞動關系是雙方當事人通過合意,由勞動者一方提供勞動、用人單位一方給付報酬所形成的,具有經濟人身從屬性的權利和義務關系。前述也提到了勞動關系認定的核心就是人身與經濟從屬性,也就是無論正式工作還是加班等其他組織活動,只要是在勞務關系存續期間,就要受到公司規章的約束和具體行為的管控[3]。本案來看,雙方簽訂了《主播經紀協議》,只看約定的條款,就會發現,在合同中雖然約定了雙方的權利義務以及工作的具體內容,但阿嬌作為工作者只是在家里完成公司工作的全部內容,人身相對自由;其次,雖然約定了工資的三七分,但工資來源幾乎全部是粉絲們的賞金,這與傳統上嚴格的經濟從屬性大不相同。因此,如果人身依附性和經濟從屬性這兩大屬性同時被弱化了的話,要認定其為勞動關系未免有些牽強。
四、網絡主播勞動關系認定的思路
無論是從基本的法理角度還是從現實案例出發,筆者歸納了網絡平臺因其想減少責任的承擔而偏向于認定為合同關系,網絡直播者想要更多的保障更愿意認定其為勞動關系。對于此,建議從合同目的解釋出發,當網絡直播平臺與主播簽訂所謂的“協議”時,條款中越是限定了主播的競業自由,設立了帶有獨家性和排他性的條款,裁判者就越應該認定其為勞動關系,因其締約目的是從自身利益考量,而缺乏對勞務人員的保障,從合同訂立的公平性和客觀公正的角度,將其解釋為勞動關系具有一定的妥當性和可接受性,這也是雙方利益衡量后的結果[4]。但這并不代表所有的協議宜按照勞動關系處理。因為現實中這些條款是大不相同且復雜多變的,并不能經由勞動關系得到很好的解釋。從平臺運行成本和主播特定要求情況下,筆者認為某些主播與直播平臺之間建立的是一種基于共同經營目的的商業性質的合作伙伴關系,對于這種協議認定為伙伴關系也許更符合商業邏輯,比如有些主播不想受到相關制度的約束,只是臨時性愛好主播亦或想借用平臺來提升自身的知名度,這時候認定為商業合作關系更能滿足雙方的利益需求。
新業態下,互聯網經濟在國內蓬勃發展,國內伴隨著互聯網新生了很多類網絡主播職業,諸如網約車司機、外賣送餐員等新型社會關系,但法律總是滯后性的,當面對新情況新問題時,可以參照網絡主播認定的思路解決這一類問題,在認定平臺企業和勞動者關系的時候,需要謹記勞動關系的本質特征,既不能一味依賴抽象規制,也不能陷入無法律主義的風險,對待新問題,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1]紀雯雯,賴德勝.從創業到就業:新業態對勞動關系的重塑與挑戰——以網絡預約出租車為例[J].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學報,2016(2).
[2]王全興.“互聯網+”背景下勞動用工形式和勞動關系問題的初步思考[J].中國勞動,2017(8).
[3]田野,劉霞.論彈性化背景下的用工自由與就業安全——從《勞動合同法》的修改爭議說起[J].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2).
[4]謝德成.轉型時期的勞動關系:趨勢與思維嬗變[J].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6).
2019—02—10
王健(1995—),男,漢族,安徽合肥人,華僑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經濟法。
D922.52
A
1673-4564(2019)02-007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