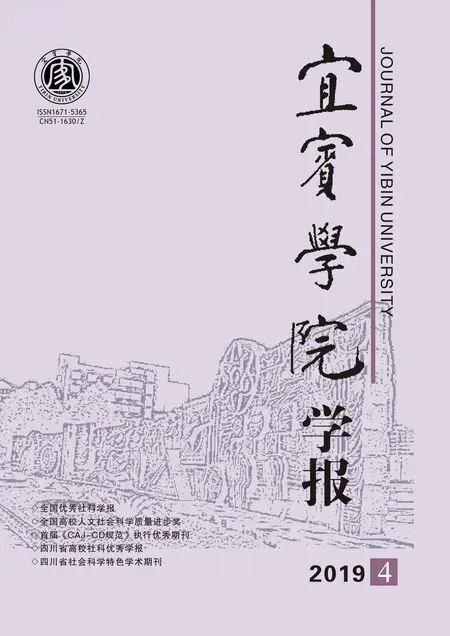家庭是形式
——唐君毅家庭哲學思想
陳張林
(蘭州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甘肅蘭州730101)
作為現代新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唐君毅被牟宗三贊譽為“文化意識宇宙中的巨人”。他以其強烈的文化意識,建構起了龐大的文化哲學思想體系。其中,他首論家庭,并將家庭生活視為文化活動形成次序之首位,其重點則在“論孝友之意義及家庭關系之當求恒常之理由”。該內容實超出此前思想家之貢獻,“可謂皆發前人所未發者”[1]自序二,18。
在唐君毅看來,家庭是中國人首要的生活單位。它既是個人走向社會的開端,又是人生的歸宿。因此,家庭及其日常生活并不是追求其他目的的手段,其本身即具完整的價值,亦即其自身即為一目的,就值得追求。對于這個意思,唐君毅說道:“儒家之所以重視日常生活,乃源于儒家之自覺的肯定全幅人生活動之價值,而教人之貫注其精神于當下與我感通之一切自然人生事物。此即使一切人生活動皆可自身為一目的。夫然,而飲食、衣服、男女居室、勞動生產之活動本身亦皆可自具備一價值而非可鄙賤,亦不只視為一謀身體保存、種族保存之手段。”[2]180這也就是說,在中國文化中,人的所有活動,并非呈現一個手段與目的的序列,而是各自都有其獨立的目的價值。但這并非否定超越的精神生活。形下的日常生活與超越的精神生活對于儒家而言,是相配合而和諧的。如果超越的精神生活不能充滿、貫注于形下的日常生活,則精神生活易陷溺于空虛,甚且“精神之有所跨過而有所泄露。由此泄露,而有所鄙賤。則阻滯其情之生動活潑,而有一自虐虐物之念潛滋暗長”[2]181。而如果形下的日常生活不能躍升至超越的精神生活,則容易沾滯于表面之物事,使生命壓縮、僵化,抹殺了生命的創造性。對于儒家而言,“人之道德修養,即賴在日常生活中禮樂之陶養”[2]179。在唐君毅看來,儒家在歷史上之成功處,也正在于其“能融攝禮樂文化生活于人民日常生活”[2]179。換句話說,傳統文化的生機恰在于其日常生活化,在柴米油鹽、行住往來之日常生活中為百姓所重復遵守與踐行。這種精神生活與日常生活之相和諧,一方面表現在“仁義禮智之德性”,一方面表現在“吾人之活動本身美化而藝術化”[2]181。此種日常生活之美化、藝術化,從“文”與“質”的關系說,則可說:“文必附乎質,質必顯乎文。日常生活為質,精神文化生活為文。文質相麗而不相離,即中國文化之精神之一端。”[2]182日常生活由此德化、美化而富含文化意味,有了精神之意義。
日常生活之常態,乃為家庭生活,是為家庭日常生活。家庭日常生活亦因其上述文化意味而有精神性。中國文化擅長從家庭日常生活中“發現至高之精神文化上、社會人倫上之價值”。這是儒家尊重自然在家庭方面之生理關系之尊重的表現。而家庭日常生活,本質上是一種道德生活。正是從此家庭日常生活的精神性、道德性上,唐君毅構建了其家庭哲學。
一、家庭成立之根據
盡管儒家尊重自然的生理關系,而且家庭成立的起源處也的確是依據自然生理上的關系(即性本能),但這是否就意味著儒家所謂的尊重家庭即只是尊重性本能,尊重種族之繁衍呢?當然不是。唐君毅說:“家庭之成立,初固依于男女生理的本能。然中國儒家思想所發現、所建立之家庭之意義與價值,則純為社會的、文化的,以至形上的、宗教的。”[2]148在唐君毅看來,性本能之說僅只能解釋家庭之所以出現的生理原因,而并非家庭成立的根據。恰恰相反,家庭成立的根據正在于超越性本能上而得挺立。
那么,這種超越性本能的根據是什么呢?是道德理性。唐君毅說:“吾之所以說家庭成立之根據在性本能之超化以使其道德自我實現者,蓋家庭之成立,乃處處根據于性本能之規范以實踐一道德。”[1]63儒家并不否認人的自然屬性,正所謂“食色,人之大欲存焉”。但就在規范“食色”上講,即將此自然屬性上提躍升至文化層面,而彰顯人的社會性、精神性。由此而建立人的家庭意識。家庭意識的實質乃是道德意識。道德意識即是道德自覺、道德理性。道德意識、道德理性的指向在于建立、完成人的完滿之人格,即道德自我。所謂道德意識,即是指自己自覺自己該做之事、支配自己以過道德生活之理性。唐君毅說:“什么是真正的道德生活?自覺地自己支配自己,是為道德生活。”[3]15這是自做主宰,自己規定自己的生活,是絕對自律的生活。簡言之,自己支配自己即是道德意識、道德理性,此支配過程之顯現即是道德生活,甚至可以說道德生活全幅即是道德理性,或反過來說,道德理性全幅即是道德生活。道德自我通過道德意識、道德理性所覺悟之善之延續、重復、充大而建立:“吾人有自覺的道德意識之見證,則此潛伏之善為我所自覺,遂得真對我為善而被保存。保存之,即延續之重復之,以充大此善之量。故吾人之自覺的道德意識多一分,則善之量充一分,大一分。……道德意識之發展無絲毫之間斷,其中無不善之存。而吾人之道德自我之建立即成為一絕對之歷程,而達至誠無息純亦不已之至善境地。”[4]448-449如達至此境地,則可說道德理性、道德意識、道德自我而為一。
道德生活的開端在家庭生活。道德活動,從邏輯上說始于夫婦之愛情,并延續至父母對子女之愛,擴展至兄弟姐妹之愛,以使父母兄弟姐妹間的配偶(性本能)關系不相亂,從而構建起基本的人倫關系,使人與禽獸區別開來。“人倫之始亦家庭之始,家庭之始即同于禽獸之本能之節制與規范與超化之始也。”[1]68那么,為什么有家庭?沒有家庭行不行?家庭于人而言為什么是必然的?
為了說清楚這種必然性,唐君毅借用了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他認為,家庭之所以是家庭的根本原因在于家庭是人的性本能之形式:“性本能至多為家庭成立之質料因。而家庭之所以為家庭,其開始一點即在節制規范此質料。家庭之所以為家庭,純在其形式。此形式乃人之精神活動道德活動自己建立,以約束提防條理原始之性本能,并實現吾人精神活動道德活動之道路。”[1]68家庭是形式,這是唐君毅很深刻的思想。家庭并不僅是人們習以為常的認知那樣,認為它只是一個社會的細胞,是一個組織。在唐君毅看來,家庭是我們精神活動、道德活動條理規范原始性本能之格式。也就是說,家庭不僅是存在論上的組織,還是功能性上的形式。作為家庭成立根據的道德理性,當然并不是從性本能的現實意義中引申出來的,而是使性本能不再是原始性沖動,從而使其具有了形上學意義。
唐君毅盡管借用了亞里士多德“形式與質料”概念,但他認為在西方哲學語境中,形式是“懸空”的。在他理解,形式之所以能成為形式,在于其“持續”。——形式的要義在于其能不斷保持。也就是說,家庭之形式是整體而言,分而言之,則有夫婦之形式、父子之形式、兄弟之形式。形式之能為形式,就在于“夫婦關系、父子關系、兄弟關系之持續上”。而所謂“持續”,并不是自然血緣關系上的自動延伸,而是“自覺的保存與預期之精神的努力道德的努力之事”。家庭之形式正在此種自覺地維護、護持夫婦關系、父子關系、兄弟關系的道德努力中得以表現,而得以支持與保證,由此而不虛懸。簡言之,家庭既是個人的日常生活的限制者、超越者,又是其自覺的道德活動所彰顯者、實現者。家庭是個體性本能條理之形式,而個體以道德活動體驗此形式、確證此形式,并因之而保持此形式。于此保持之努力而可見家庭意識:“故家庭之意識即一維持家庭之形式之意識。”[1]69于是家庭意識也正是家庭道德意識、道德自我,或者說道德意識、道德自我呈現于家庭。而個體依此家庭意識必超越個體而含攝家庭其他成員并條理化其關系。個體因此而自覺自己為家庭之一分子,為一受其他成員限制并共同維護家庭之形式之保持者。有此家庭意識之各個體彼此之間就須“節制、忍耐、犧牲,而相互之間則有同情互助相敬之事”。也正是在此“節制、忍耐、犧牲”使得自我不僅重視家庭之形式,而且在此過程中也就實現了其道德意志、道德自我。[1]70換句話說,家庭中各家庭成員以家庭意識而相互自我節制、忍耐、犧牲,是儒家道德理想主義得以實現的必由之路。沒有作為形式之家庭、持續家庭之形式之家庭意識,道德理想主義也就落了空,而個人之成德當然也就無處著落。
那么,在家庭中,個體是如何進階其道德意識、道德自我的呢?唐君毅認為要經過兩重超越。他認為,道德活動其實是“吾人能以對方之心為心而實現超越自我之意志”。正是在以對方之心為心的實踐過程中,自我完成了個體之超越而融攝了他人。這種融攝包含兩個階段、兩種內容:“蓋以對方之心為心,一方固包含對對方欲求之肯定,望對方之得所愿。一方亦包含對對方道德意志之肯定。”[1]70也就是說,在家庭生活中,既要肯定人的自然欲求,又要實現人的道德自我;既要現實化,也要理想化,——理想的超越性就蘊含在當下的實然性之中。在第一重超越中,個體以自己之道德理性出發而超越自己之欲求,以滿足家人之欲求,由此而對自己之欲求予以節制、忍耐、犧牲。——否定自己之欲求。在第二重超越中,個體自覺到家人同樣依據其道德理性而望自己亦能滿足自己之欲求,家人同樣對其欲求亦會加以節制、忍耐、犧牲,于是轉而以家人之心為心而肯定自己之欲求,以滿足家人之道德理性之伸展抒發。——肯定自己之欲求。經過肯定家人之道德理性而肯定自己之欲求,使自己的道德自我又得到躍升,實現了道德自我之絕對超越性。于是個體之道德理性、家人之道德理性都得到了全幅的實現,都各自肯定了家庭之形式,都自覺其為家庭之一分子,家庭成了實現道德理想的適宜場合。而由此所展現出來的家庭物質生活,不復為滿足自然之欲求,乃道德活動之展示。對于這樣的過程,唐君毅說道:“故吾人真正通過對方之心以為心,又將順吾人對對方之道德意志之肯定,轉而再肯定吾人之欲求。”[1]70之所以要經過兩重超越,是因為在第一重超越中,仍只是肯定己之道德理性而未肯認對方之道德理性,由是不免有自私之弊。此時之道德理性乃半截子的道德理性。只有經過第二重的超越,以己之道德理性融攝對方(家人)之道德理性,道德理性由是而得全幅伸展,是為道德理性之自我超越,是“超越自我之絕對超越性”。這樣,各個體在家中既實現了自然之物質生活,又實現了精神之道德生活,使得個體在家庭中既能暢遂生機而成就自然生命,又能自我超越而成就道德理想生命。于是自然生命因道德生命而光輝充盈,道德生命因自然生命而立地挺立。家庭由是而成為人一生所不可或缺之形式。唐君毅由此也就論證了家庭的永恒性:“了解家庭成立之根據,即知家庭對人為一必須有之存在的組織,亦一對人永當有之存在的組織。蓋家庭成立之根據,即在吾人之道德活動精神活動,乃所以實現吾人之道德理性者,則吾人之道德理性為永恒者,家庭即當為永恒者……吾人唯一可否定家庭當存在之根據,唯在吾人之可無性本能。若吾人無性本能,則家庭之形式無所規范,亦無所寄托而表現。然人若無性本能,則根本無人類之相續生……現在之人皆父母所生,即皆在家庭中存在,即皆對父母兄弟有責任,人對此家庭仍有維持存在之責任當實踐家庭中之道德。故家庭之存在與家庭之道德,乃人所不可離。人存在則家庭存在,家庭之形式對人乃一永恒規范形式,故家庭之道乃人之無所逃于天地間之道。”[1]74-75
二、家庭道德及其形上根據
既然家庭乃人之所不能缺者,而我們習慣上往往又從己身之性本能的欲求和延續子孫的目的著想,使得家庭似為可有可無之組織。因此,從上述所言之家庭意識(道德理性)而論家庭之所必須、所不可或缺,乃是從改變視角帶來的結果:“……須打斷人向下看、向前看、以論家庭所以存在之論。吾人之論家庭所以存在之根據,唯歸于人之不能亦不當無家庭意識。人之不能不當無家庭意識,乃依于吾人之皆當向上看向后看……”[1]37-38向上看、向后看,就會發現人皆由父母所生,并由此而意識到在己身之前即已有父母所建之家庭先存在。這個邏輯是理性不容不承認的。我們也就由此而建立起了確定不移的家庭意識、家庭道德。從這種向上看、向后看的視角出發,唐君毅主要闡釋了家庭道德的三大內容及其形上根據:一為夫婦常道與變道,二為孝之形上學根據與其道德意義,三為友之形上學根據與其道德意義。
(一)夫婦常道與變道
這里所謂常道指的是夫婦關系之持續。而夫婦關系之斷裂(離婚)是變道。唐君毅提出,夫婦關系是應當永續不斷的。理由有三:一是從子女端說。夫婦因愛而結合,而生子,故愛其子。愛其子則當以子之心為心。而子之心當愛其自己,由此而知父母之愛本身亦可愛,以是期望父母能夠繼續如此這般的愛下去。父母以子之心為心,則應求婚姻關系持續不斷。二是從父母端說。“人皆愛其父母,則子應以父母之心為心。”這就是說,父母因愛而生子,也會期望子之因愛而結婚、生子,因此體父母之心則亦應求婚姻關系持續不斷。三是從夫婦自身之關系說。由于人有自覺能力,因此對于起初之“形色之慕悅、生理之沖動”而愛具體對方之男或女,轉而“對相愛之關系之愛”,即對愛之愛。此是超越性本能之愛。此種愛首先表現為對婚姻之對方的照顧、體貼,由此而產生對己之節制,并引致對方對己之節制之感恩。由感恩意識的產生而使“夫婦間之情感之累積,與道義關系之加強”。夫婦雙方都以此道義意識而建立起相互信任之堅貞。至此,夫婦即以此“堅貞互信之道德”規范彼此關系。對于上述歷程,唐君毅有明確闡釋。他說:“男女之間從本能欲出發之愛,通過愛之愛,至道義關系之形成,至道義之限制本能欲,整個是一道德生活之發展歷程。在常態婚姻中,此種發展乃為無間隙而逐步上升者。至堅貞互信而道義關系乃居主位,本能生活即統于道德生活,而夫婦之道即完成。”[1]41在唐君毅看來,男女結婚后并非就是一直不變的直線型靜止狀態之關系,而是一個進階的、由本能欲而最終達至道義關系的發展歷程。此一歷程并非可以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夫婦雙方不間斷地努力以實現之。因此,夫婦之道“以永續堅貞為常道”。
男女婚姻既以永續為常道,則不得已之離婚即為變道。需注意的是,唐君毅并不否定離婚。他認為常道固當遵循,而變道亦非不道。但是行變道的條件在于自己之良心,只要良心自覺理由無可疑則可為之。而如果一個人處在可行變道之條件下卻自我犧牲以行常道,那么這個人簡直就是世之模范,是為更高的道德。唐君毅由此不僅對那些守貞節者充滿了崇敬,也對那些再婚之人充滿了肯定。總之,他認為對待變道的態度,應該是“君子尊賢而容眾”。這樣才不至于抹殺各種層級的善良,不會像古代那樣流于殘刻而以理殺人。
(二)孝之形上學根據與其道德意義
孝是人向上看向后看而對最切近之父母所產生之愛敬情感及其相應行為。人們論孝往往是從對待的角度,或是人類學上的發現,而否定孝之必然性。唐君毅則認為孝之為孝自有其當然性、必然性。那么,孝的根據何在?何以謂其為必然?欲顯此根據,唐君毅認為應從現實之我之“返本”入手。所謂返本,就是指理性地返回到我未出生之前之生我之父母那里,由此而實現超越自我并以此超越而觀現實之自我之過程。這種以超越自我而觀現實自我乃是道德活動的必由之路,是諸善之源。由此返本而意識到在我未出生之前,只有父母存在而我不存在。只有父母存在之時,所謂的“我”即是父母之我,也就是說我以父母之我為我;以父母之我為我,即意識到超越自我,無我、忘我,父母之我即我之我。——我與父母本為渾然一體。父母乃是超越之自己。孔子說仁乃“愛人”。那么愛從最初是如何顯現的呢?唐君毅說:“在現實世界中人皆知愛我,然道德生活之開始,即以超越單純之自愛而愛他人。人能愛他人之根據,在能忘我而以他為自。”[1]44在最初的能“以他為自”的地方,正在于以現實之我而返本于父母而知父母之我即我之我,由現實之自愛而返本地愛那無我之我,即父母之我。現實地看,父母是“他”;然返本地看,父母卻正是“我”。現實道德生活要求之“以他為自”,由此而返本地以無我之我而化解了“自”與“他”的隔閡而還歸于現實之“以他為自”之順適。唐君毅對此說道:“……吾人……自動的將自己之現實存在性,還歸之消納之于父母之現實存在性,將對自己之現實存在之愛上推而成愛父母之孝。”[1]44現實存在之愛父母,返本地看卻是愛自己。孝也就在這種返本意識中而得以確立。由此也就可以說孝“乃依必然之道德理性而說之必然命題,非自經驗之歸納而得之命題”。更進一步看,所返之本可及于我之無我之我、以父母之我為我,又可設想父母又返本而推知其父母之我而為我……以至無窮,以達于天地宇宙。于是就現實之我而言,父母祖宗與天地宇宙之全體,皆可在我之返本意識中而成為無我之我、忘我之我、超越之我。于是現實之我也當將對父母之孝推擴至天地宇宙,而對天地宇宙致其愛敬。
返本之道德性,并不在于其所返之“本”,——此本乃指父母、父母之心;而在于“能返”之自身,——此“能返”乃指自己之道德意識之活動。此“能返”即人之自覺的道德理性,用孟子的話說就是“良知”“良能”。由此“能返”至無我之我、以父母之我為我而對父母生出孝思。所以說孝的根據在于道德理性。
更進一步來看,孝乃必然之道德,其意義有如下幾個方面:第一,自己對父母不僅有自然血緣關系之接受,而且通過返本而達至無我之我之境,于是覺悟無我之時,我以父母之我為我,即只有父母而無我,父母即我。如此,則父母于我不特是一自然血緣關系之存在者,還是在道德理性之照察下的道德之存在者。換句話說,父母之存在于我而言不僅是自然存在,而且還是道德存在。我由此而對父母予以雙向肯定。此一點唐君毅并未明說,但是依其思路則是必然的結論。第二,現實之我由此返本之孝思,使得自己也得到雙重肯定。現實之我顯為一物質性存在者,有本能之欲望,然通過返本之孝思而達于無我之我,又通過此無我之我照察現實之我而知父母生我乃是他們道德自我之創造性超越。也就是說,我不僅是一物質性存在,而且還是一道德性存在。對于上述兩方面之過程,唐君毅將其稱之為“超越的我之兩重超越”:“孝之為道德生活,乃由超越的我之兩重超越。超越的我既超越其對父母宇宙之執以生我,而又超越對現實之我之執以孝父母宇宙。”[1]47第三,肯定人之欲望生活為應當。如上述所言,由返本而挺立之孝思,是首先到達于父母的,并由此轉進以達于天地宇宙。由此路徑所呈現之父母、天地宇宙皆為精神性之存在。即唐君毅所說的“由孝所培養之宇宙意識,正為最富生命性精神性之宇宙意識”[1]48。此一道德意識返本所肯認之父母,乃有本能欲望以具體生我者。此生為善,亦如天地宇宙生萬物而為善一樣。因此而可肯定欲望生活亦為善。唐君毅說:“肯定孝之作用有兩方面,一方是求超越現實之我,而以父母為我,以超越本能生活,實現超越的我。一方是透過父母與超越的我,以印可本能生活,使本能生活含道德意義,升華成道德生活,而孝遂為統一超越的我與有本能欲望之現實之我之生活,以成為一整個自我之道德生活,并將形上之我與形下之我,溝通而一貫之者。由是而孝不特是返本,而是成末。”[1]50第四,孝能促進夫婦關系道義化。在子女對父母致其孝思時,父母亦能感受此道德性、精神性活動,由此而增進父母對子女之精神之愛。而父母對子女之慈愛,也就進一步升華為超越本能之道德性、精神性之慈愛。“由是而父慈子孝之關系,亦成為純道義之關系。”[1]53夫婦雙方各以其對子女之純道義之慈愛為中介,更能增進夫婦間之道義關系。
(三)友之形上學根據與其道德意義
家庭中之關系有三種:一是夫婦關系,二是父子關系,三是兄弟關系。夫婦關系是交互關系,父子關系是因果關系,兄弟關系是并立關系。前兩種關系之道德性及其根據,已如上文所言。為了解釋兄弟關系之道德性之根據,并總結前兩種關系之道德性之原因,唐君毅創造了兩個詞,即現實境和理想境。所謂現實境,是指自己和對方的現實存在狀態;理想境是指自己從己之現實存在而追想己之未存在之時對方之現實存在狀態。他認為,夫婦雙方一時并在,是一現實境之關系;而父母對子女而言,子女未生之前,父母的存在乃為一理想境,而出生后其與父母為一現實境之關系,于是父母與子女關系實為現實境與理想境相交織之關系;而兄弟皆父母所生,其既為彼此獨立之現實境之關系而又互為理想境之關系。正是因為夫婦為現實境之關系,故其常道之根據只能從其彼此間之現實關系之精神化處(“愛之愛”)著想。而父子為現實境與理想境交織之關系,故其道德之根據既要從子之現實境而返于父母以呈現理想境,而產生純粹精神性之孝思;也要從父母之現實境出發而望子之未出生時之子之理想境,而產生“半精神性之慈愛”。——之所以說是“半精神性”,是因為子女初生,父母對其之愛還注目于其身體而有待于子女之孝思、孝行為中介,使其在子女之純孝思孝行之感召下而轉進躍升為純粹精神性之慈愛。但兄弟關系與前兩者都不同。盡管兄弟之道德可簡言之為“友”,但仔細分別則可說因其彼此獨立之現實境之關系而有“敬”,因其互為理想境之關系而有“愛”。
兄愛弟之根據在于父母自覺地對其愛情之愛之順延、客觀化。唐君毅說:“父母之愛情之客觀化為子女,而父母‘愛’其愛中之‘愛’客觀化即成子女間之愛,即兄弟之友愛。”[1]55而從兄弟角度說,則皆知彼此乃為父母所共生,由是自然產生共命意識。此共命意識乃是父母生命精神之客觀化之一貫性使然。此兄弟友愛之道德意義,適在于能增進父母之愛,維持父母之婚姻關系之持續以使父母之夫婦關系增一持續進階而道義化之外在力量。否則,兄弟紛爭而使父母見其愛之客觀化為無意義,由此即會削弱父母之夫婦愛情之持續、進階。需注意的是,唐君毅認為兄弟之友愛,還有一重要道德意義,即與孝相配合,使得兄弟不因彼此獨立而隔絕。他說:“孝者生命之返本而上溯也,友愛者使之念同為一父母所生而合源也。”[1]58返本上溯、合源之道德意識,使得父母、兄弟皆受一限制與規范,而維持家庭之形式。
弟敬兄則源于弟之自覺兄在己之未生前乃一理想境,而己乃為一“虛位”,弟由這種自覺的虛位感而在對兄之時自然生出“一承托之態度,同時對于我之現實活動加以收斂”,而“此種對對方之承托態度與對我之現實活動之收斂,即是敬之本質”[1]60。這樣,兄在弟之理想境中而得到肯定。換句話說,也就是現實之兄因弟之自覺其為理想存在而為弟之精神所包圍。于是可說敬乃弟對兄之虛位感而精神地生發出之純粹道德。這種純粹的精神性、道德性即為敬之根據。而敬的道德意義則在于承認個體之獨立性,使得兄弟既擁有共命意識而合源,又能保持其個體獨立而成就其私。如此,兄弟各自之私人生活亦因此而道德化、精神化。
綜上,調節兄弟關系的道德,統一言之而為友,分而言之而為愛與敬。此愛與敬有明顯的區別。唐君毅認為有如下四方面的不同:一是本質不同。愛的本質是發揚,由充實自己而潤澤對方;敬的本質是收斂,由虛己以承托對方。二是來源不同。“敬源于覺己有所不足,愛源于覺對方有所不足。”三是精神活動方向不同。“敬為現實活動之純粹超越”,向上;“愛為現實活動之擴展”,向下;并“于擴展中見最初現實活動之超越”,又向上。四是施與對象不同。愛“使未有而有”,故為長者向幼者施與;敬為承托與收斂,故為幼者向長者施與。[1]61
三、家庭道德之限制與社會道德之貫通
如上文所論,家庭成立的根據在于人的道德活動,在于人的超越自我之求實現。換句話說,家庭成立的根據不在血緣關系,而在家庭成員間的道義關系。在上述幾種核心的家庭道德之堅貞、孝、慈、愛、敬中,孝是絕對的、最高的、純粹的道德責任,因為人必有父母,卻不必有夫婦、兄弟。因此如果要對它們做一個價值層級上的排序,則可說孝最高,夫婦之堅貞次之,兄弟之愛敬又次之,父子之慈最易故為最下。
那么,是否這就意味著人之道德囿于家庭呢?如何找到突破家庭范圍而走向更為廣闊的社會呢?唐君毅的辦法是從歸謬來論證人之道德必突破家庭而進入社會。其思路如下:如果我們只限于家庭來講道德,只對家人盡道德責任,那么將家人推至極致即可發現,個人可既無父母在世,也無兄弟姐妹并存,又無夫婦更無子女,那么他即不必盡家庭之道德責任,結論就是他沒有家庭道德責任可盡。此一結論與人當盡其家庭道德責任相矛盾。唐君毅說:“凡主張人只能對家庭中人盡責任,即等于主張人可不對任何人盡道德責任。而人對家庭之責任,亦非必然者。”[1]77這樣的結果,就與上述家庭哲學全部沖突,即使絕對性之孝亦由此而被抵消。
因此,由此歸謬法而可得知,家庭道德與社會道德原是貫通的,都是個人仁心仁性的表露,本不能由經驗上有些人以家之私而害社會之公以得出家庭道德與社會道德為兩端之結論。經驗中,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人之只私愛其家庭者,皆為其所見之血統關系所蔽”。眾人往往容易以為血緣關系是家庭成立的根據,有血緣關系即有家,無血緣關系則無家。但正如唐君毅所說:“血統關系只為家庭中之本能的愛之基礎,而本能的愛并非家庭成立之真正之基礎。”[1]78之所以先建立家庭道德,是因為由家庭道德生活所培養之道德意識,才是真實的、具體的、具有生機創造性的道德意識。家庭只是道德自我最初的表現場域,最初的實現場所,本沒有只限于在家庭中流行之規定性。此道德自我自返本于父母而超越現實自我,進入無我之我、以父母之我為我,并進而返于天地宇宙萬物,以天地宇宙萬物為我,由此全幅的生命精神觀照萬物,則無物可逃于其間。故此自覺之道德理性本就遍照宇宙萬物,當然也就包括不特定多數人之集合之社會。由此遍照一切之道德理性,在家而可盡家庭道德責任,在社會亦可盡社會道德責任,當然在國也就能盡愛國之責任。因此,從道德理性、道德自我上說,家庭道德與社會道德本是一體之順展,本無隔閡可言。
四、唐君毅家庭哲學之評價
唐君毅的家庭哲學思想已如上所論述。至于其思想之價值,唐君毅本人即已有清醒之自覺。他自認為其家庭哲學的價值在于從道德理性上論證家庭當存在之必然性,由此而論證人盡其家庭道德之必然。他說:“故吾人必須建立吾人之家庭哲學,以反對錯誤的家庭哲學,使吾人能在自覺的理性上肯定家庭之當存在,以防止一切違背家庭道德之思想之出現,此即吾人之家庭哲學之價值。”而如果“人根本無違背家庭之道德之罪惡,或人本直覺家庭之道德意義,根本不疑家庭之當存在,則吾人之家庭哲學亦為多余”。[1]74實則家庭哲學必不多余,因為立說皆為常人“日用而不知”,于是因沒有自覺的道德意識而常常未盡到家庭道德責任。其結果必然是家道落而人道廢。唐君毅以其強烈的文化意識,對此可能之后果必不能接受。故其建立此家庭哲學,乃其自覺的道德自我之不容已的結果。他之所謂“多余”,實則由現實而言乃為“必需”。
眾所周知,家庭本是中國傳統社會中儒家所注目的領域。例如,孟子說:“國之本在家。”《中庸》有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而《周易·家人·彖》則說:“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周易·序卦傳》又說:“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此后歷朝歷代的儒學思想家無不在此思路上將家庭置于基礎性地位而加以強調和論述,由此而建立起了龐大、精深的家庭思想系統。但近代以來,面對西方的強勢入侵,國人在反省傳統思想文化時,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例如康有為在其《大同書》中就大力排斥家庭,認為國家、社會之一切罪惡之源皆可自家庭關系中找到,家庭不僅給個人帶來無窮之痛苦,而且還禍國殃種。而傅斯年以西方文化之個性為據,認為應該將舊家庭一掃而光,重建新式家庭。[5]104-108顧頡剛也作《對于舊家庭的感想》一文表達對舊家庭的痛斥。當然,“五四”時期的人們并不是主張完全拋棄家庭這個組織,而是要拋棄中國傳統的壓制個性成長的舊式家庭,冀以建立一新式家庭。
在當代,有學者認為中國文化重視家庭,今天的家庭仍然很重要,由是而建構了“家哲學”。其認為,與西方文化相比,這是中國文化最擅長的領域,也恰恰是西方文化的盲點和弱點。從文化交流的角度說,我們應該高揚傳統文化中的家哲學思想,以貢獻于西方,從而使中華文化走向世界。[6]而張祥龍出入西方之現象學與中國之儒學,也從中西對比中大力肯認傳統家庭文化,并認為今天應當從家庭入手來復興傳統文化。[7-8]還有大批的儒家思想研究者也對儒家的家庭思想文化充滿了同情的理解與弘揚。相比較而言,唐君毅的家庭哲學思想最突出的貢獻是其致思路徑和有關認識。他以超越的道德理性、道德自我為基線,縱貫地論證、肯認了家庭之當然性及家庭道德之必然性。其中最有啟發意義的是他將家庭規定為形式的思想,完全不同于我們所熟悉的所謂家庭是社會的細胞這樣經驗的、社會學的認識。還有其他諸如夫婦之愛之愛、敬的根據、現實性與理想性之雙重肯定等等具體思想都極具啟發性。當然,在他的家庭哲學思想中,也有一些牽強附會的地方,比如其論“女嫁男之理由”,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也發現家庭生活之種種現象不必有其當然之理由。這也提醒我們,在家庭哲學中不必去顧及搖擺之家庭現象。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唐君毅的家庭哲學思想還需認真加以重視。因為即使現在,家庭對于我們來講仍然是重要的生活領域,可以說人一生也沒有走出過家庭。而且,個人道德之培養,家庭的確是很重要的基礎性場域,——只有經過了家庭良好的道德培養,個人才能具備真實的道德素質。時代在變化,經濟意識橫掃精神世界,今天的家庭面臨諸多困難,以致有社會學者聲稱家庭已死,而普通人對家庭亦無維護之信心。當此之時,我們從唐君毅的家庭哲學中卻看到了其對家庭所持之堅定信念,而其論證之嚴密、觀點之鮮明,自有其不容辯駁之處,這對我們今天建構適合時代、提振家庭信心的家庭哲學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