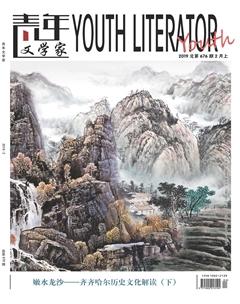站上遺存

如果從康熙二十五年(1686)站人駐驛開始計算,至光緒三十四年(1908)驛站裁撤,站丁這個特殊的群體在黑龍江整整存在了230余年。而站人及其后裔則在居住地繁衍生息,而今已經整整330年。
古驛路驛站安在?遺址遺跡遺物所剩幾何?2014年9月23日至29日,在齊齊哈爾市政協文史學宣委員會的組織下,由市文廣新局、相關縣(市)區政府、政協的支持、配合,部分專家、學者、作家、媒體記者組成“齊齊哈爾古驛站及站人文化”調查組,從嫩江縣(墨爾根驛站)出發,由北向南,沿著古驛道方向和大致地段,對訥河市老萊鎮(喀木尼喀站)、長青村(博爾多站)、拉哈鎮(拉哈爾站)、富裕縣友誼鄉富寧村(寧年站)、塔哈鎮(塔哈站)、黎明村(齊齊哈爾建城前卜奎驛站)、建華區鑫海家園小區(建城后卜奎驛站)、昂昂溪區榆樹屯鎮頭站村(特穆得黑站)、泰來縣大興鎮時雨村(溫托渾站)、肇源縣茂興鎮(茂興驛站)共計11個驛站遺址進行了考察。
站房民居
驛站站房的保留狀況比我預想的還要差,但民居保護稍好一些。
大站道上所有的驛站官房早己蕩然無存,但所在位置依然留存在站人后裔記憶深處。在他們的引導下,基本確定了具體位置。如在訥河老萊鎮,據當地退休教師孫洪閣(79歲)回憶,喀木尼喀站房在老萊鎮中心街北100米路西“何三狗肉館”樓后,與關帝廟舊址相鄰;在訥河市建華村,據站人后裔曹寶良(69歲)回憶,博爾多站房舊址在原長青村(己與建華村合并)村部,現為一朱姓人家居住;拉哈驛站遺址在四季青村,該市文管所進行了初步發掘并整理出部分遺物;在富裕縣富寧村,據站人后代姜黎(75歲)回憶,寧年站房在寧年村小學位置;在富裕縣塔哈鎮,據站人后裔趙宗連(77歲)回憶,塔哈站房在塔哈鎮豐達小區(原鎮政府所在地)位置;在昂昂溪區頭站村,據當地年老村民回憶,特穆得黑站房在頭站村小學位置;在泰來縣時雨村,據站人后裔王姓村支書(己退休)回憶,溫托渾站房在時雨村小學位置;卜奎驛站最初的地點在建華區王屯,該處遺址因鳳凰城的開發已無法確定。康熙三十一年(1692),卜奎驛站移入齊齊哈爾城。2008年,鑫海家園對這一棚戶區進行開發建設期間發現一口古井,市文管部門對之進行了GPS定位,鎖定在北緯47°21′03.7″,東經123°56′29.7″。而今,古井己深埋地下,但卜奎驛站可以以此定點。從驛站官房使用情況看,驛站裁撤后,官房多用于政府、學校等公用設施。
作為站人精神家園的關帝廟,也無一幸存。依靠當地站人后裔,也都指出了具體位置。如塔哈驛站關帝廟位于驛站站房北側。一些關帝廟內的大榆樹或柳樹現在仍然存活,如拉哈站關帝廟原址在第二小學內,老榆樹依舊健壯。
站人墓碑
此次考察的起始站之所以選擇在嫩江縣,是因為嫩江縣在站人文化保護方面走在了全省前列。例如,墨爾根至漠河古驛站驛道遺址已經是第七批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清代黑龍江北路驛站站官崔枝蕃及其家族墓地已經成為省級文保單位;通過爭取,投資近四千萬元的墨爾根古道驛站博物館已經投入使用,等等。這里需要介紹一下站官崔枝蕃。
崔枝蕃是漢軍旗人,并非站人。他擔任過墨爾根驛站站官,曾總管北路10個驛站。有的文章說崔枝蕃是第一任站官,這與史實出入很大。從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的記載可知,第一任北路站官是杜爾岱,南路站官是關保,均為滿族人,崔枝蕃只不過是雍正年間的站官而已。基于他長期服務驛站,頗有建樹,死后清廷授予他“文林郎”、“資政大夫”稱號,賜墓地一座。授予其夫人查庫他氏“夫人”稱號。統治者的封贈顧及生也顧及死,是做給后人看的。
崔枝蕃墓地群在高峰林場。這里被當年的風水先生稱為“二龍戲珠”寶地。沿蜿蜒石階而上,兩邊古樹參天。到達墓區,首先進入眼簾的是一座外觀完好的七孔透龍碑,上刻皇清誥命,滿漢文字漫漶,氣勢不減。墓區有青磚圍墻保護,南北長約40米,東西寬約30米。南墻居中設門并建木制牌坊,上懸匾額,配有楹聯,其中“松蔭懷古”令人印象深刻。崔枝蕃墓室用青磚砌筑,并用木炭、白灰、樺樹皮圍裹。墓前設有石桌、香爐,但己殘缺,綠苔染就方磚,滄桑百年。該墓約建于乾隆三年(1738),“文革”曾遭到破壞,后又多次被盜。主墓東北,另有崔枝蕃之子崔標(麻力圖,漢軍佐領)墓院,立有七孔透龍碑,上刻奉天承運碑文。據《嫩江崔氏族譜》記載,該墓建于嘉慶六年(1801)。在主墓正東還有7座一字排開的古塋墓院。這些墓院圍繞崔枝蕃墓,形成古墓群。
與崔氏站官墓不同,富裕縣是站丁墓保存最完好的區域。
寧年驛站,也就是今富寧村,距富裕縣15公里。在富寧村東北約6華里的東山(后人也叫它“老墳山”),有一處站丁姜純墓。
姜純被姜氏后人尊稱為“開基始祖”或“來江始祖”,1925年(民國十四年),姜氏第七代孫姜金棟、姜金發等人發起為先祖立碑活動,始有姜純墓碑。“文革”期間,姜氏家族祭祀活動被作為“四舊”被迫停止,墓前石碑、石桌、石碗、石杯遭到破壞。2006年,時值站丁戍邊320周年,姜氏后人己繁衍至第14代,約萬余人。為不忘歷史,自發捐款,為姜純修墓立碑并舉行了祭祖儀式。如今,該處墓園已經成為文保單位,成為承載站人歷史的遺存。查閱富裕縣編撰的《古道站丁習俗》,在富裕縣,還有站丁張永泰等人的墓碑。
車行富裕縣富寧村附近考察寧年站丁姜純墓時,站人后裔姜黎先生拄著拐杖與我同行。也許他也有一段時間沒來了,站在墓碑前久久的注視,記憶仿佛回到從前……
站人譜牒
調查期間,有幸見到多份站人家譜,表現形式有譜書、譜表、譜聯、譜單。富裕之家譜書,貧寒之家譜單。家譜多為記述式,條目完備,記錄詳盡。譜單多為圖表式,宣紙、高麗紙、黃紙均有,只列家族世系表。
《姜氏宗譜》復印件陳列在富裕縣文化館展柜之中。據姜氏后人傳說,姜純以前的族譜在先祖來江時已經丟失,清代《姜氏家書》是姜純后裔在其仙逝之后又重新整理的。我以為,應不存在丟失之事。作為“三藩”子孫,當時連性命都不保,何談家譜之說?我們見到的是新修《寧年驛站姜氏家族族譜》。家譜由三支:富寧為大支、小榆樹為二支、東房子為三支分別續寫,并由嫡長子、長孫、曾孫,一代一代的保存并負責續編。姜氏始祖、四世祖名單字,二世為“自”、三世為“文”。從第五世起:懷、保、金、德、成、常(第十世)。受文革破“四舊”影響,姜氏家譜數十年未能得到及時整理和續編,分散保存的家譜也己支離破碎,到“德”、“成”字輩,人員登記不全。姜氏家族重修族譜后排字:永增基發裕、訓聚貴國通、昌賢治源繼、盛余翕和繹,現己傳至到第十四代“發”字輩。為保取名規范,經族人研究,推出新字譜:乾坤恩澤廣、鈞厚沛兆豐、宏興利全濟、祥瑞昭宗榮。
在富裕縣,還有袁氏家譜、張氏宗譜、劉氏家譜、宋氏家譜、楊氏宗譜、李氏家譜均值得一記。
寧年站人家譜除姜氏外,還有四份。《袁氏家譜》由八世祖袁普祥立,成于道光十二年(1832)。偽滿康德七年(1940).第十一代袁金寶續譜至十一世。上個世紀90年代末,十三代袁廷國,再續譜至十六代; 《楊氏譜書》是光緒三十年由十代楊致和、楊致永續修。被后裔楊洪東于近年找到。序言記載,其先祖原在云南巧山縣馬蹄坡。“康熙二十五年(1686),奉差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城北寧年站予應服徭之額”;據《李氏家譜簡續》記載:李楷、李牧、李軾、李林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隨吳三桂原任偽總兵的叔叔李文淵由云南出發,于三月份到達北京。停留不久,發往了黑龍江寧年居住至今。同族一嫡兄弟,分派拉哈站。《李氏家譜簡續》一度隱跡,后由李國秋(曾任寧年村黨支書)尋到;宋氏家傳譜單,經第九代宋士英記憶并口述,由第十一代宋維新完成。因資料匱乏,內容不完整。
現知塔哈站人家譜有兩份。 《張氏宗譜》由二世始祖立譜,譜書、譜單完整齊全,保管完好,記錄詳盡。譜書序言記載了族源是“云南省貴州府文墨縣大槐樹張家莊一排二甲永合石氏,上輩先人黃堂正四品,紅袍黃帶子”的來歷,己續到十代;劉氏是塔哈站大家族,譜書、譜單保存均完整。譜單用高麗紙粘合,雙層制成。長約六尺,寬約五尺,可掛一面墻。氏名小楷寫成,字跡工整。譜書、譜單和供奉祭祖器具均保存在第十三代劉學敏家中。
由于相對封閉,在黑龍江大站道驛站上,站人家譜似乎并不鮮見。
在昂昂溪東南十五公里頭站村(特穆德黑),調查組見到三份家譜。頭站,有“曲、柏、王、石”四大姓。《王氏家譜》光緒二十六年(1900)九月初二日,王成志祖上立了家譜,有序有表,源流十分清楚,1927年(民國十六年)建了祠堂,供奉始祖爺爺、始祖奶奶,至今均保存完好。據序言介紹,其祖上來自云南竹村縣王家莊尾。在后來舉辦的站人文化論壇上,曲氏后裔為在場專家學者展示了上百年的四幅譜聯,極為寶貴。
站人家譜寫男不寫女,寫配偶只載姓氏。清代中期,妾入譜,排妻后。站人族源追溯心理強烈,視祖先為神靈供奉于北墻。晚輩不能隨便看譜,只有在祭祖立譜時,才能叩見。至于外人,更不準看了。
行至頭站村,我們在四百多歲、號稱樹王的古榆下稍作停留。樹大根深,枝繁葉茂,這,也許正是站人文化的寫照。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誰會相信站人還有這么多的遺存?由此證明站人文化的存在、延續并非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