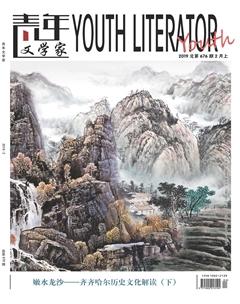寂寞官屯

無論檢索網絡學刊,還是查閱書籍文章,輸入黑龍江官屯、官莊、官地之類的關鍵詞,有關著作、論文實在少之又少。今天的學術界,與清代中后期移民招墾研究的火熱相比,官屯研究明顯冷清、滯后。實際上,清代黑龍江官屯與水師營、驛站性質是相同的,均隸屬于黑龍江駐防八旗,大概相當于綠營兵身份吧。相較之下,水師營、驛站被學者關注的程度更高。如此狀況,讓我想到這樣一個詞一一寂寞官屯。
屯墾之初
黑龍江將軍設立后,駐防屯墾與驛站設立相仿,計劃曾經一變、再變、三變。康熙二十二年(1683)四月,著手籌備雅克薩戰爭的康熙皇帝下定了筑城永戍的決心,把筑城地點從舊璦琿改為額蘇里,派遣500名達斡爾壯丁屯墾。
然而,本年七月,達斡爾子弟尚未起程,額蘇里漫天霜雪,糧谷絕產。康熙皇帝從長遠考慮,再次調整筑城地點,在原托爾加城舊址筑建新黑龍江城。康熙二十三年(1684)春,索倫總管衙門征派的500名達斡爾子弟披甲,分編8佐,每佐設佐領一名、驍騎校一名,在副都統銜索倫總管孟額德(達斡爾族)率領下前往駐防屯墾,戶部派遣侍郎薩海帶領500名盛京兵丁監督屯墾事宜。文獻顯示,康熙皇帝對于黑龍江種植的農作物品種有研究,指示多種植可以預防早霜的春小麥、大麥、油麥等。
康熙二十三年(1684)黑龍江城糧食產量如何,史料未詳。然而,康熙二十四年(1685)正月,黑龍江城佐領鄂色佐內出現“耕牛盡斃、農器損壞”的狀況。為此,戶部提出由理藩院如數購買耕牛送往黑龍江,由薩布素等營造農器。康熙皇帝認為,這是屯墾者不負責任,管理不力造成的,薩布素遭到嚴厲批評,鑒于征戰在即,暫停對其處分。此際,索倫總管博吉勒岱、扎木蘇先后休致,而索倫總管衙門卻承擔著參與籌備雅克薩戰爭的繁重任務。于是,康熙皇帝責成駐扎齊齊哈爾屯的欽差大臣、輕車都尉馬拉提出候選人名單。不久,原任奉天將軍安珠護,偵察英雄、達斡爾人倍勒爾被任命為索倫總管,安珠護成為負責黑龍江屯墾的第一位滿族索倫總管。作為名噪一時的奉天將軍被安置到黑龍江種地,安珠護的心里有說不出的滋味。
安珠護,史志文獻中也寫作安珠瑚,字介秋,瓜爾佳氏,滿洲正黃旗。他曾入國子監讀書,授翰林院檢討。承襲祖輩爵位,累晉輕車都尉。他曾任協領兼刑部郎中、寧古塔副都統、奉天將軍等職。康熙二十二年(1683),安珠護因“沽名釣譽”,想當文官并且在同僚面前大肆宣講,與將軍佟寶鬧矛盾不注意形象等問題被革職,發往寧古塔、烏喇效力。直到出任索倫總管,才算復出。
史料記載,從康熙二十四年(1685)至康熙三十三年(1694),安珠護一直在墨爾根、博爾多墾荒種地。安珠護在總管任上并沒有令康熙滿意。據《清圣祖實錄》記載,康熙三十三年(1694)末,康熙再次大光其火,批評他“自為總管后,猶不改故轍,邀取虛名,不能約束所屬之人”,最終被革去世職,不準子孫承襲。不久,安珠護去世,葬于吉林西團山。
康熙二十五年(1686)正月,時值第一次雅克薩戰爭結束后不久,原駐齊齊哈爾屯欽差大臣、副都統瑪拉,原黑龍江驛路驛站負責人,戶部侍郎包奇被派往“吉林烏喇至黑龍江”一線督理農務,耕種的主力是“蒙古、席北、打虎兒、索倫等人力”。臨行前,康熙諭示:“農事關系兵餉,須積貯充足,其在驛遞人夫,亦令合力播種屯田,爾等前往,務期農政修舉,收獲饒裕,年勝一年,懋著成效,以副朕意。”瑪拉、包奇沒有辜負康熙爺的期望,康熙二十五年(1686),黑龍江糧食取得大豐收。年末,康熙當著大學士們的面表揚道:“郎中博奇(包奇)所監種田地較諸處收獲為多,足供驛站人役之口糧,又積貯其余谷。博奇效力,視眾為優,其令注冊。此遣去諸員,可互易其地,監視耕種。博奇又復大獲,則加議敘。”(《清圣祖實錄》)從目前所見資料看,孟額德、瑪拉、包奇、薩海、安珠護等人是開拓黑龍江農業的先驅,而康熙皇帝應該說是黑龍江農業的奠基人。
官莊公田
查閱齊齊哈爾地名,在泰來縣的大興鎮,有前官地村、后官地村,在鐵鋒區扎龍鄉,有東官地村等與“官地”有關的地名。問當地人村名的來歷,沒有人能說得清楚。經過近些年的潛心研究,我才明白其中的奧秘。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清代的黑龍江將軍轄區與其他地方一樣,所有土地均屬國家所有。但按照所有制形式劃分,有官田、私田之允按生產產式劃分,則有官屯、公田,旗田、民田的區別。
旗田是八旗兵丁“計丁授田”,每人30畝,被稱為“份地”,供贍養家口以備行軍資裝之需。旗田所有者有使用權,但不得轉讓和買賣。由此,形成很多分布于各駐防城周邊的旗屯。
民田是民人(不在旗籍的自由民)耕種之田。在黑龍江,因水師營人、站人、官屯人雖隸屬八旗但非旗人,給予民田,出旗為民,或從水師營、驛站、官屯轉為民人的,往往采取寬松政策,默許其自謀生路,墾荒種田。
官屯也被稱為官莊,是與駐防相伴的戍邊屯墾形式,所產糧食是為了滿足公用性開支。黑龍江官屯正式設立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即瑪拉、包奇、薩海曾經督耕的屯墾事業,目的是“征取糧食,以充軍備”。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五月,墨爾根城有哈達陽、哈力圖等官屯20所,黑龍江城有官屯31所,共計官屯51所。康熙三十九年(1700)黑龍江將軍把墨爾根20個官莊定額男丁移到齊齊哈爾開墾耕種,齊齊哈爾官屯由此誕生。
據史料記載。黑龍江將軍轄區的官屯,呼蘭最盛。雍正十三年(1735),黑龍江將軍那蘇圖奏請在呼蘭地方設立官屯,得到清廷批準。從乾隆二年(1737)開始,呼蘭40所官屯正式耕種交糧。此后,黑龍江官屯陸續增設,至嘉慶朝,齊齊哈爾有官屯30個,領催3名,壯丁300名;墨爾根有官屯15個,領催1名,壯丁150名;黑龍江城有官40個,領催4名,壯丁400名;呼蘭有50個,領催5名,壯丁510名。至道光五年(1825),官屯仍在添設,被稱為新官屯。按照大清則例,舊官屯的莊丁屬于軍籍,新官屯莊丁則為民籍。到清末,黑龍江、墨爾根、齊齊哈爾及呼蘭先后設立官屯160所,有新舊壯丁1700名,官牛1665只。
公田是緊急狀態下由黑龍江將軍抽調八旗力量為補充官倉集中開展的耕種活動,有不定時、耕種時長不確定等特點。前面提到的索倫總管安珠護的墾荒事業,就屬于公田性質。從康熙三十一年(1692)開始,黑龍江城八旗官兵在黑龍江北岸高埠開辟1234坰公田,當年獲糧1057石有余。隨著公用性糧食開支的減少,官屯的大量建立,康熙三十三年(1694),黑龍江城公田與博爾多公田被取消。
康熙三十九年(1700)前后,黑龍江連年逢災。薩布素因“捏報屯種,浮支倉谷”獲罪,還糧入倉的任務交給了下一任將軍沙納海。康熙四十年(1701),黑龍江將軍衙門抽調齊齊哈爾城400名、墨爾根城100名,共計500名官兵,帶160套牛具前往伯都訥(今松原市)墾種公田。康熙四十二年(1703),齊齊哈爾倉儲滿額,公田停撤。這件事,方式濟《龍沙紀略》記載說:“卜魁初立城,值歲饑,將軍沙納海盡發倉谷以賑,并撥附采珠船以濟布塔哈、烏喇。引罪入奏。議于來歲屯種還倉,請敕蒙古助牛力。上允其請,溫語褒之。邊人至今感述其事。”
康熙四十九年(1710),齊齊哈爾、墨爾根兩城抽派官兵500名,分赴烏涅恩、克勒哲爾痕(烏寧克爾、珠爾亨)耕種。此次組建的公田開墾最終演變為常設公田。因距離齊齊哈爾城遙遠,成本高且不方便,乾隆三十九年(1774),將軍傅玉呈請將屯田改在齊齊哈爾附郭地方,由此,種地官兵始撤回,分布在今泰來縣前官地、后官地、依里巴等地。嘉慶九年(1804),黑龍江將軍觀明將屯田者由馬甲改為養育兵,以一增二,于是出現專門從事公田生產的八旗“養育兵”。至道光朝,齊齊哈爾340名(包括水師營兵20名),墨爾根180名,黑龍江300名。規定,每名養育兵每年交糧22石,糧食入備用倉。
官屯體系
黑龍江駐防八旗的每一部分都有各自的體系,官屯也不例外。
《黑龍江將軍衙門檔案》顯示,康熙三十四年(1695)之際,官屯仍由倉官管理,沒有專門的屯官。《黑龍江外記》也有“先是,齊齊哈爾、墨爾根、黑龍江、呼蘭既立官屯,事皆倉官兼理”的記載。
屯官,正七品,設置年份不詳。雍正十二年(1734)前,黑龍江屯官僅設一名。本年,戶部郎中達善奏請朝廷在黑龍江各城均設屯官,任期滿5年,在任候升。乾隆朝恒秀將軍在任時,改為每4年候升,并且“諸部人皆可為之。”這里所說的諸部人,指的是黑龍江駐防各族八旗人員。因此,屯官為旗人額缺。據徐宗亮《黑龍江述略》記載,“屯官無衙署,就家為治。屯戶一應大小事宜,歸其綜理,猶民戶之有州縣,四年一更,由八旗驍騎校筆帖式揀補,期滿以主事用。愿就武者,以防御用。倉官亦同,不準以主事用。”黑龍江將軍文緒曾奏請朝廷變通辦理,但被吏部駁回。
屯官雖小也是官。按照大清條例,屯官一般從黑龍江各城的筆帖式中產生,為“土缺”,也是不世襲的公缺。屯官任滿4年后可升為武職的驍騎校。若做文官,經考核為一等的任用為京城各部或盛京各部的主事,考核為二等的用為小京官。屯官有餉銀,每年45兩,俸米每年20石多一點。乾隆年間,黑龍江將軍都爾嘉認為“旗人本業在騎射,若雖文,有轉武時”,于是規定屯官按例參加春、秋季操演、騎射。
官屯收糧、存儲、出糧有規制。據《黑龍江述略》記載: “各屯交糧,則惟以縻為主。收分既定,由各屯官按丁催納,就各城官倉,車運交數,各倉官監司其事。遇有撥用,各城副都統咨商將軍核行,歲終報部,著為定例。”這個程序,一直維持了200余年。
屯官之下設領催,齊齊哈爾城3名,黑龍江城4名,墨爾根城1名,呼蘭城5名,年俸24兩。按規定,官屯領催的產生,由黑龍江將軍、各城副都統查驗,選擇能拉開滿弓的八旗兵丁補充。領催之下的“貼寫”等差使,則由黑龍江將軍衙門各司“指名咨取,兵司注冊”,不用請示將軍、副都統。官屯的屯丁不充當番子(類似警察)、仵作(類似法醫),也不參加軍事訓練。
領催之下,就是屯丁了,齊齊哈爾壯丁300名,墨爾根150名,黑龍江官400名,呼蘭510名。與臺站壯丁相同的是,舊官屯壯丁雖然入兵籍,但沒有俸餉,主要生活來源是種地所得。西清《黑龍江外記》說屯丁“無仕進之例。不應役,則自食其力。而屯丁請還籍,聽之”,說明屯丁有一定的自由度。關于屯丁來源,除原來遷移而來的官屯人及其后裔,流人也是來源之一。據《黑龍江外記》記載:“流人遇赦,不歸,例入官地安插。不則,自入伯都訥民籍,然后可居境內。非是者,謂之浮民,境內不留也。”安插官地的流人,未必全部進入官屯體系。更多的人自謀生路,成為浮民。
官屯風俗
在史志學家筆下,官屯與站人相仿,也形成一定的風俗習慣。《黑龍江述略》記載, “蓋四城之有屯丁,由盛京吉林省移徙時,風氣樸厚,習勞耐苦,不以耕鑿為艱”,保持了創業本色。“百余年來,世服其業,不特有資公用,亦且取盈蓄,較之索倫諸部落游獵、采捕,轉為利多害少。”在移民浪潮的大環境中,有地的官屯依賴資源出租,坐收漁利,不再苦苦經營。
比如,在婚俗方面。《黑龍江外記》記載:“滿洲、漢軍皆與蒙古通婚姻。然娶蒙古者多達斡爾,巴爾呼自相婚姻,或與蒙古通。營、站、官屯則滿洲、漢軍娶其女者,有之。”這一情況說明,在黑龍江,盡管營、站、官屯屬于八旗駐防體系的一部分,也一定程度通婚,但實際距離相差還是很大。 《黑龍江外記》記述了一則故事。“管屯女,殊色者,某協領欲娶之為二房,女不可,父母逼之,以死誓日:‘兒生官屯至賤,嫁三品至貴,特未必相安。且若家既有妻,而又娶婦,禮耶?聞者莫不訾女福薄”。西清為之慨嘆:“噫!此獨非巾幗中有丈夫氣者歟?惜佚其姓氏。”官屯地位,于此可知大概。
到光緒年間,屯丁的成分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除舊官屯屯丁外,有流人改為民籍入屯者,有出征官兵由南方兵營帶來各省民戶續入者,又有官宅奴婢有功主人、居三世以上準入官屯充丁者。另外還有闖關東難民避地出關到官屯租地生活者。由于官屯漢人的膨脹,到清末民初,黑龍江原官屯漢族姓氏,除常見的張、王、李、趙者之外,罕見的姓氏有戰、樸、闖、創、拱、菅、唱、揣、逯等諸姓。
清廷設立官屯的初衷是固本實邊。因此,對于黑龍江官屯給予涵養政策。清前期,黑龍江駐防體系,包括官屯等各方面均得到長足進展。然而,在清王朝逐漸走向衰敗的歷史大趨勢之下,官屯也日漸萎靡。據《黑龍江述略》記載:“將軍派員會同倉屯站官以有作無,以少報多,己不能免。及至分散銀兩,銀庫、戶司上下其手,各該管官從而侵蝕,其真得接濟實惠,十不及五。上損于國,下損于民,獨利歸于中飽,固不獨黑龍江省為然矣。”這一問題曾經演化成一場官司。嘉慶八年(1803)秋后,在向清廷奏報年終收成時,黑龍江將軍那奇泰主張多報,與齊齊哈爾城副都統玉恒、額勒德善等5名協領主張少報的意見發生嚴重分歧。后者聯合告發那奇泰。最終,對立雙方全部被革職查辦。
光緒三十一年(1905),署理黑龍江將軍程德全向清廷呈《統籌善后十四條折》,對黑龍江官屯弊病條分縷析,建議革除,得到清廷準允。程德全的改革,對原官屯屯丁給予了相應數量的土地,維持生計綽綽有余。多余的官地則被放荒賣出,就此,官屯變為民地,不復存在。黑龍江官屯起源于屯墾戍邊,是清廷的防務政策在黑龍江將軍轄區的體現。從總體上看,黑龍江官屯在歷任將軍主導下,呈現發展壯大的趨勢,在解決民生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至1917年(民國六年)二月,在齊齊哈爾磚城外東南隅,尚有管省垣官莊檔冊房舊址。當時己成為龍江縣立女子高等小學校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