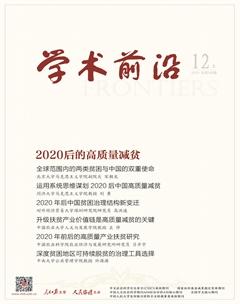2020后的高質量減貧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從1978年的7.7億減少到2018年的1660萬,貧困發生率由97.5%下降到1.7%,占同期全球減貧人口總數的70%以上,是全球最早實現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中減貧目標的發展中國家。到2019年底,全國將有95%左右的貧困人口脫貧,90%以上的貧困縣摘帽,再經過2020年一年的努力,困擾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將得到歷史性解決。
減貧工作是一項“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系統工程,未來伴隨著現行貧困標準的變化,返貧、新貧等絕對貧困問題仍然存在,相對貧困問題也將長期存在。對此,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了“提高脫貧質量”的總體性要求。2019 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鞏固和擴大脫貧攻堅成果,“及早謀劃脫貧攻堅目標任務2020年完成后的戰略思路”。因此,在2020年實現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脫貧這一階段性目標后,中國的減貧任務并沒有最終完成,而是要站在新的起點上,從實現第二個百年目標出發,著手研究并推動2020后中國高質量減貧,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的基礎。
2020年后在長期困擾中國農村的原發性絕對貧困全面終結的同時,農村貧困將呈現出新格局。一是農村貧困問題并未終結,相對貧困將會愈加突出。如何防止脫貧人口返貧,如何幫助徘徊在貧困邊緣的人口擺脫貧困,將是2020年后扶貧關注的重點。二是農村貧困從單維收入貧困轉變為包括資源、能力與機會的多維貧困。2020年后,隨著溫飽層面上的貧困問題得到緩解,農村貧困將出現經濟、社會、資產和生態等多維貧困新格局,因此,扶貧工作也應從多維貧困視角認識貧困現象、解決貧困問題,為貧困人口自身提供發展機會、促進貧困人口能力提升。三是農村潛存新一代貧困人群,需高度重視貧困的代際傳遞。農村教育資源不足,以及營養、健康和養育方面落后,對兒童(特別是嬰幼兒)發展產生不利影響;未來人工智能時代,貧困人群下一代的人力資本弱勢將轉化為就業困境,代際傳遞使這些人可能成為2020年后新的貧困主體;原始貧困家庭對下一代人力資本投資不足,社會階層分化會有可能進一步強化原貧困家庭的代際傳遞。總之,農村貧困新格局意味著2020年后扶貧策略亟需調整,相應地,產業扶貧在資源分配過程中需更多地兼顧貧困邊緣人群,更加注重貧困人口自身發展能力與抵御風險能力的提升。
“慮于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 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指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建立解決相對貧困的長效機制。”在新的農村貧困格局下,需要改變原有的城鄉扶貧二元戰略框架和以農村開發式扶貧為主導的路徑,2020年后的高質量扶貧需要設計城鄉一體化的扶貧戰略和政策,這同時也意味著需要將未來的扶貧戰略重點放在社會服務數量和質量的均等化方面。新貧困格局需要新的扶貧戰略,而實施新的扶貧戰略需要建構適應新的貧困形勢的新體制。面臨扶貧管理的碎片化與扶貧工作要求整體性推進之間矛盾的日益突出,我們需要建立綜合性的貧困治理機制和貧困治理結構,并開展扶貧制度的供給側改革。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取得貧困治理的巨大成功,這種成功背后的原因歸根到底是建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之上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開展貧困治理的政治保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從根本上促進了貧困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保障了貧困人口共同享受發展成果。2020年后,中國的貧困治理即將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中國的貧困治理結構也將因為新階段、新形勢的演進,而出現新的戰略變遷,精準研判一系列的戰略變遷可為2020年后中國貧困治理的高質量推進和新的相對貧困治理長效機制構建提供有益參考。本期特別策劃,我們邀請了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為2020后的高質量扶貧建言獻策,敬請讀者垂注!
——《學術前沿》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