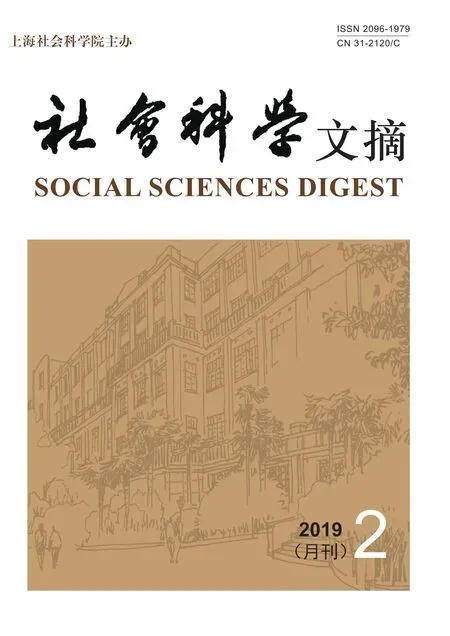國家形象研究的學術譜系與歷史困境
19世紀末,在西方及其追隨者——日本的劇烈沖擊之下,中國人堅守了幾千年的“天下想象”不得不走向了終點,從此西方從中國人想象中的“低劣他者”一躍成為了“巨大的他者”。中心與邊緣的轉換,使得中國人被迫失去了理解“自我與他者”關系的傳統模式。在自我與他者中心位置的轉換過程中,現代中國一方面丟失了自己的傳統身份,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西方他者的目光中重新追尋自己新的身份。在這過程中,對傳統中國的懷念與鄙夷,對現代中國的憧憬與茫然,對西方他者的羨慕與憎恨,一同構成了追尋之路上的復雜心態。國家形象的焦慮就此凸顯,有關中國形象的研究也由此越來越被中國學人所關注。然而問題是,由于國家形象問題在中國出現并不是一個自發的結果,而是外力作用的直接結果,那么這種特殊的境遇對中國形象的建構和研究會不會構成一定的影響,在這背后又是否潛藏著不為我們所覺察的風險?這正是本文試圖探討的主要問題。
國家形象研究的基本路徑
既然國家形象問題肇始于“與他者的相遇”,那么,如何正確地認識“他者”以及“自我與他者”的關系,自然就成為了很多學者研究異國形象或自我形象的一個根本出發點。然而,正如李普曼所說,直接面對的現實環境實在過于龐大、復雜和短暫,“雖然我們不得不在這個環境中活動,但又不得不在能夠駕馭它之前使用比較簡單的辦法對它進行重構”。正是由于意識到了這一點,眾多學者在對“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展開深入探討的同時,也把研究的觸角深入到了形象生成過程中“現實與想象”的關系,并試圖揭示其背后的權力運作機制。
縱觀國內外的相關研究成果,大致都是在“自我與他者”“現實與想象”這兩個脈絡上展開的,并在不同領域相繼形成了“比較文學形象學”“跨文化形象學”和“信念體系和形象政治研究”這三個相對成熟的研究版塊。不過,這三個研究版塊雖然都是在“自我與他者”“現實與想象”這兩個脈絡上展開的,但是由于進入的路徑不同,三者在研究對象、研究目標、研究視角、學術主張上逐漸漸行漸遠,最終發展成為了今天的三個相對獨立的研究版塊,具體區別詳見下表。
東方主義的范式危機
中國形象作為一個“特殊”的研究對象,在國家形象研究的學術譜系中,一直頗受國內外學者的青睞。這類研究雖然視角各不相同,但多建立在一個共同的理論假設之上——中國是西方的文化他者。這個理論假設不僅主宰了西方的中國形象研究,也深深影響了中國本土的國家形象研究。

國家形象研究的學術譜系
(一)中國形象研究中的東方主義
這些研究通常在問題提出之初,就主動將中國置于西方他者的位置之上,從而不僅表現出了濃重的“西方情結”,也表現了深深的“受害者情結”。這集中體現在:他們普遍比較重視西方的中國形象,忽視世界的中國形象;重視異域的中國形象,忽視本土的中國形象;重視負面的中國形象,忽視正面的中國形象。在這過程中,“東方主義”不僅成為了他們使用最為“得心應手”的理論武器,更成為了他們在思維上無法走脫的一種統治方式。具體表現在,它們對“東方主義”的借用,既體現在直接將“東方主義”用作了理論批判的武器,更體現在將“東方主義”自覺的內化為一種思維方式。異域的研究如此,本土的研究更是如此。由此,一個不得不提出的問題是,中國形象研究為什么走不出東方主義的窠臼,在這背后潛藏著怎樣的認識風險和理論陷阱?
(二)東方主義在中國的陷阱
自1990年以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猜疑與打壓并沒有因為冷戰的結束而停止,反而不斷升級,這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中國內部的民族主義情緒。與此同時,在中國全球化程度不斷深入的情況下,不少知識分子也開始有意識地批判西方中心主義。在這兩股力量的共同推動之下,東方主義迅速成為了中國學者批判西方中心主義和西方文化霸權的有力武器。
1.民族主義的陷阱
在東方主義的指引下,一些學者一旦發現所謂“負面的中國形象”就奮起反擊,且不論這些論述來自何方,都一概貶斥為西方文化霸權下的“陰謀”產物。很多中國形象研究,都主動成為了《東方學》在中國的“注釋”。為此,周寧提醒那些研究者:在看到西方“否定的中國形象”時,千萬不要忽略了“積極的中國形象”的存在。如果我們不加辨析地將東方主義移植到中國,就極易“培育一種文化自守與封閉、對立與敵視的民族主義情緒”。換而言之,當中國學術界揮舞“東方主義”這一利器對西方的中國形象和西方現代性(主要是殖民性)展開批判的同時,極有可能為中國的思想界埋下狹隘的民族主義隱患。
2.本質主義的陷阱
事實上,東方主義在中國,不僅成為了滋生狹隘民族主義的溫床,也成為了部分知識分子為文化本質主義搖旗吶喊的旗幟。一些學者在采借薩氏理論對西方殖民性及其文化霸權進行批判時,更像是有意忽略了薩氏的自省和德里克的警示。他們不僅堅持將世界劃分為“東方”與“西方”,更不斷強化中國文化或中國體制的特殊性。一個典型的現象是,在中國的國家形象研究中,到處充斥著類似“西方的中國形象”“中國的西方形象”等這類高度約化的論述,這些論述顯然高度漠視中國形象在不同時空里的變化與差異。它們抹去的不僅是世界外部的差異,還有中國內部的差異,從而不僅影響了我們認識世界,更影響了我們觀照自我。
(三)東方主義未盡的問題
東方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不僅存在著滋生狹隘民族主義和文化本質主義的風險,其刻意遮蔽或無意中忽略的問題,如對他者聲音的忽視以及對他者形象跨文化傳播歷程的避而不談,同樣也影響了中國知識界對自我與他者的認識。由于薩義德有意或無意地忽視,東方國家在他的理論世界里,一直只能扮演著沉默的他者角色。中國的很多學者在采借他的理論范式的同時,往往也因此而忽視了東方國家在東方主義結構里所發揮的主動性,從而遮蔽了觀照他者和反省自我的一個重要視角。
1.他者的聲音
在薩義德那里,“東方學的意義更多地依賴于西方而不是東方,這一意義直接來源于西方的許多表述技巧,正是這些技巧使東方可見、可感,使東方在關于東方的話語中‘存在’”。很顯然,在描繪東方學譜系的過程中,他并沒有給東方人留下回應的機會。對此,德里克提出了嚴重質疑:“‘東方人’是否像薩義德的研究所說的真的緘默無言?不能表現自身呢?”事實卻是,在西方對東方進行東方化的過程中,東方人也在主動地利用西方的東方化成果,并且創造性地對西方的論述進行了挪用與改造。忽視東方人的參與,我們就不能真正發現東方化是如何發生的。
2.他者形象的跨文化傳播
薩義德的《東方學》不僅忽略了東方人的參與,對于西方制造的東方形象在東方國家的傳播歷程也絕口不提。這就使得我們在看到西方對東方構成鉗制的同時,卻忽略了東方國家主動傳播西方的東方形象的幕后動機和具體路徑。自甲午戰爭以來,西方的中國形象就頻頻通過各種媒介陸續地被介紹到中國,并且在中國國族認同的重建過程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但是在中國形象的研究中,絕大多數學者都不約而同地將目光鎖在了西方的文化機制如何生成了中國形象,卻絕少有人關注這些形象在中國的傳播與演化進程。
不可否認,東方主義的出現,的確為當代的社會科學重審西方現代性和東西方關系提供了一個新的范式、新的視角;然而,它對他者能動性和他者聲音的漠視,卻在無形中為它后來的傳播與運用設置了重重障礙和盲區,無法掙脫的本質主義傾向則進一步加劇了它的范式危機。
走出中國形象的話語迷思
由此可見,對于中國形象研究而言,東方主義帶來的障礙不僅在于它作為一種理論范式遮蔽了我們本應傾聽的他者聲音,更在于它作為一種思維方式,限制了我們提出問題和思考問題的邊界。在東方主義的理論范式里,“西方的文化機制如何生成了中國形象”,“中國形象在西方的現代性想象和思想脈絡里扮演了怎樣的角色”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得到了很多學者的共同關注;但是,“中國如何參與了西方中國形象的生成”、“西方的中國形象在中國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是如何傳播的”、“西方的中國形象如何參與了這些國家的自我想象”、“現代中國的自我想象又如何利用了西方的中國形象”等這類課題,卻因為超出了東方主義的理論視野,鮮少有人提及。不僅如此,在現有的研究中,中國的很多研究者因為受東方主義思維方式的影響,始終未能走出西方話語霸權的分析框架和本質主義的窠臼,從而致使他們的研究都或多或少地充溢了民族主義的義憤,部分研究甚至直接淪為民族主義情緒的簡單宣泄。
因此,在借鑒東方主義對他者形象和西方現代性反思成果的同時,如何走出其一并帶來的理論陷阱和認識盲區,并且在思維方式上掙脫對它的依賴,對當前的中國形象研究來說顯然顯得尤為重要。然而現實的問題是,走出東方主義何以可能?
(一)作為話語的中國形象
福柯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符號和語言的世界。……許多人包括我在內都認為,不存在什么真實事物,存在的只是語言,我們所談論的是語言,我們在語言中談論。”他指出,話語雖然是由符號構成的,“但是,話語所做的,不止是使用這些符號以確指事物。正是這個‘不止’使話語成為語言和話語所不可減縮的東西,正是這個‘不止’才是我們應該加以顯示和描述的”。國家形象研究顯然也無法掙脫語言之網,事實上也只有通過語言,我們才能讓國家形象得以表述和識別。但是作為學術研究,我們更應關注的是作為話語的中國形象,并從中發現福柯所說的符號背后的“不止”。所以筆者傾向于將國家形象看作是一種指涉自我與他者關系的話語系統。在表述上它表現為對他者和自我的描述和評價,在指涉上則呈現為知識與權力的關系。
(二)回到中國現代性的自我想象
走出東方主義的理論陷阱和思維方式,重新深入到形象話語的“歷史脈絡”和“社會譜系”中,并從中發現它們的行走軌跡及其背后的動力機制,是當前學術界破解“中國形象”話語迷思的重要途徑之一。這就需要我們盡快回到自我的想象,學會傾聽他者的聲音,從而在時空的坐標系中重新“發現”中國形象。
1.在自我的想象中發現中國形象
東方主義的理論范式和思維方式給中國形象研究帶來的最大隱患,就在于它將學者的全部興趣吸引到了西方的話語霸權上,從而致使他們忽略了內部的抗爭與分歧。邵建認為,“當下的中國文化,并不需要過多地考慮如何抵抗西方霸權,相反,現在最迫切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國知識分子文化在內部(而不是外部)如何重建一個主體”,如果“無端把并不構成實際威脅的外部問題熱炒放大,以圖獲得所謂全球性文化格局的遼闊視野”,“卻忽略或淡化了文化問題在內部的急迫性”不能不說是理論把握上的錯位。相反,更多采用柯文所主張的China-centered視角和研究取徑,在自我的想象中重新發現和審視中國形象,對于我們認識中國形象的意義和中國現代化的進程顯然更有意義得多。
2.在自我與他者的互動中發現中國形象
就東方的東方主義,德里克曾提出了一個特別有意思的問題,東方主義到底是一個“事物”還是一種“關系”?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西方”的中國形象在中國或其他國家經過二次傳播或反復傳播以后,已經失去了它的本來面目。如果我們依然把它看作是西方拋向東方的一個事物,無異于又再次走進了東方主義的理論陷阱。因此,只有在自我與他者的互動中,我們才能發現這些形象話語是如何生成、又是因何轉化的。
3.在時空的坐標系上發現中國形象
德里克也曾提醒我們,東方主義的本質主義傾向不僅是時間上的同質化,也是空間上的同質化。就中國形象而言,長期以來我們不僅在時間上忽略了那些諸如“東亞病夫”“黃禍”之類嚴重約化話語的動態變遷過程,同時也在空間上抹去了西方和中國的內部差異。正如某些西方學者提醒我們的,在西方從來沒有一個一成不變的中國形象,也沒有什么“一致”的中國形象。同樣,即使在中國,也很難有一個統一的抑或一成不變的中國形象。
20世紀90年代以后,就在“黃禍”“東亞病夫”“睡獅”等一個個國族符號逐漸淡出歷史舞臺的時候,“中國威脅論”又成為了中國當代史上的一個新的話語神話和形象標志。因此,未來的中國形象研究如何打破有關中國形象的一個個話語迷思,并從新的歷史視角出發,刻畫出它的“歷史脈絡”和“社會譜系”,進而揭示其背后的生產機制,對于我們理性地認識他者和自我無疑都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那么,走出文化本質主義的窠臼,在時空的坐標系中重新發現并解讀中國形象,對于當前的國家形象研究來說不啻于是一個新的契機與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