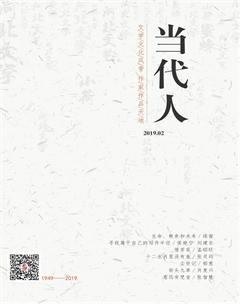寂靜的冬天
又一個冬天來了。但這一年一年的冬天,總讓我覺得哪里不對勁兒。也許是它太溫暖了,不像冬天,進入12月份,門前的小河還沒有封凍嚴實,還聽得見淙淙的流水聲。節氣已到小寒,不見一片雪花,村莊顯見的沉寂而枯燥。起先,我沒往心里去,直到有一天,走在寂靜的村邊小路上,望著遠處大楊樹稀疏的樹梢和頭頂上如鉛灰幕布一般的天空,突然發現:連一只麻雀也看不到!一股惆悵陡然升起,霧一樣彌漫開來。
我不由得回想起過去。小時候,一到冬天,麻雀鋪天蓋地而來,比平時多了幾倍。寒冷的季節,它們在野外很難找到吃的,只能奔著村莊而來。遺落在糧倉外的谷粒,曬在房頂上的薯干,凡是看得見的糧食,一星半粒都成為麻雀的美餐。那時,大人孩子對麻雀都只有一種態度:厭惡。在困難的年月,糧食金貴,人還不夠吃。最讓人生氣的是,它們與雞鴨爭食。那時家家戶戶都是好不容易擠出一點糧食喂雞喂鴨,偏偏在這時候,麻雀總是不請自來。它們幾十只或上百只,眨眼間就把撒在地上的糧食吃光,雞鴨根本搶不過它們。記得母親喂雞的時候,天天在旁邊看著,轟麻雀。
我們小孩子,對麻雀自然也談不上憐惜,反而將它們視為野味。夜里這些麻雀住在屋檐下、廂房中、墻窟里或樹洞上,我們白天偵查好它們的住地,晚上去摸。摸到三五只是經常的事。聽說最好的烹飪辦法是油炸,但是想著褪毛麻煩,再說哪有那么多油呢,就用最省事的辦法,燒著吃。先用黃泥包裹麻雀,再放到火盆或灶膛里烤,有十五分鐘就熟了。
如今,我已經四十多年沒吃過燒麻雀了。小時候燒麻雀那奇香無比的味道,牢牢地印在我腦海,以至于不論過去多少年、不論吃過多少美食,在我心目中,燒麻雀都勝過任何山珍海味。那時的冬天,盡管我們穿的是破衣爛衫,吃的是稀粥咸菜,外邊寒風似劍,雪如鵝毛,但因為有了逮麻雀和燒麻雀的經歷,我們玩得忘乎所以,活得有滋有味。
現在的冬天,為什么一只麻雀也見不到了呢?它們都到哪里去了?仔細搜尋記憶的碎片,記得前幾年冬天,偶爾還能見到幾只,而今年冬天,我連一片雀毛都沒見到。就是其他鳥兒,如喜鵲、烏鴉、長尾巴連子等,也是少得可憐。
思索它們的去處,想不出;問別人,別人也答不來。苦思冥想加上查閱資料,終于有一天,我悟到了謎底。原來,這些年村里普遍使用有毒農藥和滅草劑,種田是省事了,但野草卻遭受滅頂之災。野草沒了,藏在草叢里的蟲子也就沒了,螞蚱、蟈蟈、蛐蛐、蜻蜓都變得少見,鳥雀們吃什么,又怎么孵化下一代呢?長嘆一聲,原來人與自然的疏離,是從去除那一棵棵不起眼的野草開始的。
這些年,村莊變得越來越干凈,田間地頭變得越來越清潔。但當那些小時候見慣了的精靈從這土地上成批地撤離,才猛然發現,村莊已不再是我小時候的村莊,田野也不再是我小時候的田野。我像一個患了肌無力的人,想挽住一條流逝的河,卻眼看著它從指縫間流走,消失得無影無蹤。
我是個讀書人,本來是有些環保意識的,可是有一次,我也在莫名的恐懼驅使下,使用了劇毒滅草劑——百草枯。
那是去年。我家院子很大,種了幾種蔬菜,院中還有水井,我堅持不用滅草劑,野草們以超乎尋常的生命力回饋我,一層一層地瘋長,鏟不動,拔不掉,剪不斷。我經常見到螞蚱,看到七八種鳥兒來我家菜地里捉蟲,兒時的生活仿佛又回到了身邊,我重新享受著田園的意趣,甚至有些沾沾自喜,仿佛做了一件功德。然而,一天傍晚,我下班回來,猛然打開院門,卻見至少五六條蛇占據了我的“私家花園”!它們在草叢中半隱半現,最大的一條有茶杯粗,兩米長,居然已爬到了月臺之上!恐懼瞬間壓頂而來,我想逃,可是邁不開步,一陣頭暈,勉強扶住院門才站穩。幸虧蛇們見有人來,扭動著身子迅速鉆進草叢,瞬間不見了。我的“魂魄”過了好久才回到驚呆的軀殼中。是茂密的雜草吸引了蛇!驚怒之下,第二天我就買來滅草劑,接連噴灑三次,把雜草徹底滅絕。
坐在重又變得寂靜的院子里,這一切恍然似夢。我像一個剛從夢中醒來的人,慢慢地回神兒,越來越覺出不是滋味。麻雀,小鳥,已經被我變相地“趕”走了!小時候我也見過蛇,為什么現在再見到它們卻如此害怕?缺少雜草的世界,連蛇都少了藏身之地,它們出現在我的院子,恐怕也是無奈之舉吧。這一方小小天地里的豐饒,成為它們的樂土,而我,卻不能接納它們,還把它們視為仇敵。
不由得想起美國作家蕾切爾·卡遜寫的那本書——《寂靜的春天》。而我以及所有鄉民,正在經歷更加寂靜的冬天。直到現在我才明白,沒有麻雀的冬天不能叫做冬天,因為少了冬天最主要的風景。這一個個小黑點如同鋼琴上的黑鍵,沒有它就無法敲擊出冬天的樂章,這一個個小黑點也像冬天的眼睛,沒有它冬天就是喑啞的盲人。當有一天,四季都變得寂靜,那么我,又該如何自處?
(劉海清,河北省作家協會會員。文學作品及評論散見于《名作欣賞》《閱讀與寫作》《中國教育報》《中學語文》《詞刊》等。)
編輯:安春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