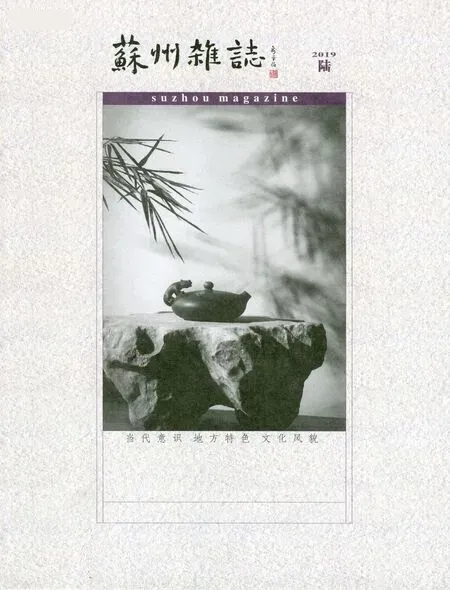黃裳與江澄波的書緣
姚一鳴
己亥年初夏,思南讀書會在上海思南公館,舉辦了“黃裳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與會的嘉賓有李輝、陳子善、陳麥肯、陸灝及黃裳先生的女兒等,主持人為曹可凡。那天早早地便趕到了思南公館,以為人會很多,便搶了個好座位,可以聽得清楚一點。思南文學之家內座無虛席,紀念會在曹可凡淳厚的嗓音中開始。
《文匯報》資深編輯陸灝首先發言,他說黃裳的生日是六月十五,其實是陰歷,而不是陽歷,我們是提前給他過了,黃裳曾說他和《水滸》里的蔡太師是同一天。陸灝的話引起了臺下陣陣笑聲。陸灝是進文匯報社時和黃裳認識的,并成為忘年交,陸灝主編的刊物和副刊都刊發過黃裳晚年的大量文章;華東師大退休教授、新文學研究專家陳子善接著發言,他高度評價了黃裳在散文創作領域取得的成就,并說在黃裳生前曾幫他舉辦過一次作品研討會,黃裳并未到會,但提出王元化和一些青年作者必須邀請。《人民日報》資深記者、作家李輝和黃裳也有較多的接觸,初次相識是在《人民日報》辦的散文年會上,以后李輝和黃裳多有通信,其中的一百多封收入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的《黃裳致李輝信札》中,李輝曾編過一本《黃裳自述》(大象出版社),據說黃裳十分滿意;復旦大學資深編輯陳麥青最后發言,他回憶了和黃裳在出版《清代版刻一隅》(修訂本)過程中的點點滴滴,對黃裳先生豐富的版本知識和精到的淘書眼光十分佩服。

江澄波
這次“黃裳先生百年誕辰紀念會”對談的大多為黃裳散文創作的成就,以及和黃裳交往的故事,對于黃裳在晚年打筆仗的戰斗性,多有提及,而有關黃裳的藏書及版本書話等涉及較少,只有陳子善提到他以前去文廟淘書后,常常會順路去黃裳那里,黃裳會問起有何收獲,陳子善把淘到的書給他看,黃裳看后沉默不語,陳子善說這是他看不上眼,偶有被黃裳稱贊的,那必是精品。黃裳是個散文家,也是個藏書家,他對書的感情是超乎常人的,一輩子淘書、藏書、讀書、寫書,為之傾注畢生精力。他寫的有關書的文章,都是膾炙人口的美文。愛書如命的黃裳晚年也賣過書,這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關于這段賣書的經歷,黃裳在《買書記趣》一文中曾寫道:
“我的藏書,幾經淘汰,像大浪淘沙似的,所剩殘余,已多少著錄于幾本‘書跋’與‘淘書記’中。其最晚的一次淘汰,是在劫去藏書部分發還之后。我將一些殘零書冊,以及自己不喜歡的本子,一股腦兒處理掉了,交給了舊友在蘇州古舊書店工作的江澄波君。江澄波君一九九七年出版了他的著作《古刻名抄經眼錄》,記錄了他平生所見的善本書,這本是我過去向他提出過的意見和希望。出奇的是其中竟有我所處理的一種‘嘉慶刊本《碧城仙館詩抄》’,說起來它本是沒有資格收入‘經眼錄’,連聊陪末座的資格也沒有……”(《海上亂彈》文匯版)
黃裳所敘嘉慶刊本《碧城仙館詩抄》不入法眼,是因為厭惡作者陳文述,而郭沫若曾通過阿英向黃裳借閱過此書,為研究《再生緣》(作者陳端生與陳文述有親戚關系)。“不料它因曾經郭老披覽,竟得廁身于‘古刻名抄’之列”,黃裳認為是貽笑大方了。
愛書的黃裳晚年賣書,其實是有緣由的,這些多年積藏起來的古書,帶給他快樂的同時,亦有痛苦的回億。從上世紀八十年代初開始,陸續發還了黃裳部分的藏書,雖十去八九,但黃裳看到這些重新歸來的書,還是很激動,但那時他的居住環境已發生了變化,家里已放不下這么多書,無奈中只好處理了一些他認為不好或不喜歡的書。但黃裳在處理書時,為什么不賣給上海的舊書店,而是舍近求遠,聯系了蘇州古舊書店,是因為他和在蘇州古舊書店的江澄波相熟,還是上海的舊書店在黃裳被“投機倒把”調查時作了證明,個中原因只有黃裳自己最清楚。
對于黃裳的賣書經過,作為知情者的江澄波也在文章中有所描述。年過九十的江澄波,如今還在蘇州平江路鈕家巷堅守著一家舊書店,這家名為“文學山房”的舊書店,是江老先生傳承前輩的書香,為舊時的蘇州書業留下一段念想。最近,北京聯合出版公司出版了江澄波的《吳門販書叢談》,是耄耋老人對舊時販書的回憶,以及對歷代古刻和名抄本的鑒賞和解讀,以及對愛書人的回憶。94 歲高齡的江澄波老先生,可能是年齡最大的著書人了。《吳門販書叢談》收有“與黃裳先生一個甲子的‘舊書緣’” 一文,細述了黃裳賣書的過程。
“在‘文革’后期,上海圖書館落實政策,把當年從他家抄出去的古書發還。由于經歷長達十年,黃裳家里房屋早已作了調整,一時難以容納。他就寫信告訴我,要我在一星期之內到他家里去,把他理出之書收購回來。我們隨后去了三個人,看書以后扎成二十五大包,其中大多數是清代康熙至道光時刊本的詩文集。在議價過程中,他提出了一個條件,就是他知道我們店里有二冊金農用宋紙印的《冬心硯銘》和《畫竹題記》,他準備用名人鄭曉舊藏的嘉慶刊本《皇明詔令》二冊交換。當時我認為,既然他舍近(上海古籍書店)而取遠,寫信給蘇州,這是對我們的信任,于情于理應該滿足他的要求。后來他在寫文章時表達了他的心聲,認為非常滿意。這批書運回店中以后,剛好有天津社會科學圖書館的館長來蘇訪書,見到以后同我們商量說,館里正好有一批經費,要求全部提供給他們。經請示領導后,黃裳的這批書全部供應給了他們……”
江澄波的回憶較為詳盡,對于黃裳賣書的前因后果也交待得仔細,這批書由蘇州古舊書店收購,又被天津社會科學圖書館買下,可謂是適得其藏,唯一遺憾的是江澄波未錄書名,不知黃裳剔除的是什么書。在文中有一段特別有意思,“他(黃裳)提出了一個條件,就是他知道我們店里有二冊金農用宋紙印的《冬心硯銘》和《畫竹題記》,他準備用名人鄭曉舊藏的嘉慶刊本《皇明詔令》二冊交換。”后來蘇州古舊書店答應了黃裳的要求。那么金農用宋紙印的《冬心硯銘》和《畫竹題記》又是什么好書?
《冬心硯銘》(《冬心齋硯銘》)和《畫竹題記》(《冬心先生畫竹題記》),是金農自刻詩文集,用仿宋體,倩名工撫刻,用宋紙模印,是仿宋刻本中佳品。據徐康《前塵夢影錄》記載曾見徐乃昌舊藏冬心集多種,皆用舊紙開花紙印,有冬心自鈐名印,后歸鄭西諦。金農自刻小集,且肆意求精,是以雕版印刷的極高成就。黃裳在《姑蘇訪書記》一文中,亦提到了《冬心先生畫竹題記》:
“記得去年,我還在這里(蘇州古舊書店)得到過一本乾隆原刻的《冬心先生畫竹題記》,總共不過十來葉,可是用的是舊紙,大字仿宋寫刻,墨光如漆,前面還有一張高翔畫的金農小像,用的是雍正中刻《冬心先生詩集》前小像的舊板,不過后面的題贊卻換了方輔題、楊謙寫的篆書。關于冬心自刻書的紙墨之精,徐康在《前塵夢影錄》里曾經講起過。他說,這種自刻書用的是宋紙,印刷用墨取的是搗碎了的晚明清初佳墨碎塊,在中國雕版印刷史上可以算得是非常突出的精制品,這就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清初經過百十年安定休息,經濟上升,文化繁榮的面貌。《畫竹題記》的用紙,是一種深黃色極厚實的竹紙,簾紋很細,還夾雜著一些未能溶解的植物纖維,是一種較粗的古紙,我不敢斷定這是否宋紙,但和宋代印刷佛經的用紙是相近的。”(選自黃裳《銀魚集》)
江澄波與黃裳從上世紀五十年代即相識,那時黃裳在文匯報社工作,逢休息或節假日,黃裳便和夫人小燕一起到蘇州去訪書,給江澄波印象最為深的是黃裳淘書極為仔細,連殘本書也不放過,而每得好書,總是回上海后寫信給江澄波,還托付有新文學毛邊書也給他留著。江澄波進蘇州古舊書店工作后,黃裳與之交往更為密切,有時書店收到好書,便會寫信通知黃裳,如明萬歷刊本《煙花小史》就是如此;同時黃裳也會讓書店代銷一些書,如天一閣舊藏手稿本《史記摘麗》等。
黃裳2012 年9 月逝世后,江澄波曾寫文悼念,文中寫道:“我與黃裳相識于建國初期,結下書緣情誼,書信往來一直延續至今年(2012 年)春節以后,雖然我先后任職文學山房、古舊書店、文育山房,但是我們兩人之間對古籍的交流,卻從未間斷過,屈指算來已達六十個年頭。對我來說,他不僅是一位愛淘古書的老讀者,承他不棄,在業務上也給了我諸多幫助,因此也可以說是我的老師……”(江澄波《吳門販書叢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