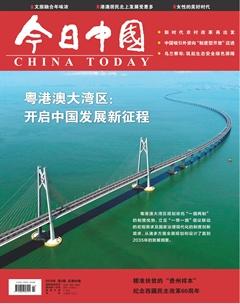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開啟中國發展新征程
文|田飛龍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于2019年2月18日正式發布,為中國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及塑造開放型經濟體提供了最為直接且最具潛力的實踐指南。
千呼萬喚始出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于2019年2月18日正式發布,為中國新一輪全面深化改革及塑造開放型經濟體提供了最為直接且最具潛力的實踐指南。粵港澳大灣區規劃依托“一國兩制”的制度優勢,立足“一帶一路”倡議聯動的宏觀需求及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制度創新需求,從經濟、社會、文化、制度等諸多方面全面規劃和設計了直到2035年的發展綱要。《綱要》開啟了中國發展新征程,是中國改革“南部驅動力”的再次釋放。
這份《綱要》的出臺具有深刻的國際國內背景:其一,國際層面的逆全球化、民主民粹化、中美貿易摩擦等,不僅導致國際經濟發展與全球化信心受挫,也導致中國對自身技術短板的深刻反思,這些因素推動中國制定更高水平改革開放的發展規劃,對上述不利因素予以回應;其二,國內層面,十九大報告對“兩個一百年”發展做出戰略性規劃,“一帶一路”建設深入發展,但核心的技術突破與制度創新需要國內基地作為載體,粵港澳大灣區是兼具國內改革前沿與全球化因素的最佳區域,適合承載這一改革的引領任務;其三,《綱要》對“一國兩制”從側重“兩制”的初期發展向側重“一國”的融合發展的轉型,提供了具體愿景和制度性安排,豐富了“一國兩制”實踐內涵及發展指向,同時也為治理港澳的本土主義提供了優良方案;其四,《綱要》為港澳經濟轉型升級及參與和支撐“一帶一路”提供了直接的機遇和動力,也在政策保障與人員流動上做出了最為有利的安排。
這些國內外的背景因素,是中國改革開放遇到的新問題和新挑戰,也是推動改革開放深入發展的動力來源。《綱要》的出臺表明,中央繼續推進改革開放的意志更加堅定,戰略更加成熟,自主性及引領新一輪全球化的方向感更為明確。中國的改革開放,不是尾隨西方的亦步亦趨,而是堅持在學習中批判,在批判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正是有著這種清晰的自主性邏輯,中國的改革開放才能夠在全球化的浪潮中經受風險考驗,逐步走出一條自身的發展道路。也只有這樣的“自主性現代化”道路才不僅對中國最為有利,也對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發展具有更為直接的啟示。中國的“一帶一路”不僅是經濟資本的輸出,也是自身現代化經驗和模式的分享。當然,改革開放40年,中國的現代化發展還有若干課題需要繼續探索,繼續按照自身方式形成具體經驗,粵港澳大灣區就是中國“第二輪現代化”的火車頭,是戰略性引擎。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制定過程是科學民主的:一方面,《綱要》建立在對世界其他灣區科學考察與比較、灣區內城市經濟產業科學調研、灣區發展與“一帶一路”合理對接的基礎之上,確保灣區規劃真正立足地方實情、國家戰略需求及全球競爭格局,具有顯著的科學性;另一方面,《綱要》的制定過程充分體現了協商民主和公平參與,港澳地區從政府到產業界再到普通市民,均通過不同渠道和方式對灣區發展規劃提出意見和建議,港澳與廣東還以地區協商的機制對規劃綱要中的基本架構形成充分的共識,中央在這些民主程序基礎上做出最終決策。國家規劃行為本身就是“一國兩制”下中央管治權合理行使的體現。之所以能夠做到科學民主,與整個國家的法治化進程及民主決策文化與能力的顯著進步是分不開的。中央專門成立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港澳特首被納入作為成員,這對于從中央層面保障和支持灣區合理有序發展具有重要的組織法意義。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是對“一國兩制”實踐內涵的重大豐富和發展。“一國兩制”在改革開放之初成形,有著重大的國家理性內核與改革開放戰略意義:一方面,“一國兩制”是一種現實主義和包容主義的憲制方法論,通過合理容納不同制度元素促成國家統一和改革發展,將制度差異性勢能轉變為更高水平發展的動能,這就使得“一國兩制”成為國家現代化與國際化整體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另一方面,“一國兩制”有著堅實的國家理性內核,即國家對港澳的高度自治授權與港澳對國家的持續性貢獻的理性結合,這種共贏式憲制平衡顯然需要不斷尋找最佳作用點和作用方式,粵港澳大灣區就是“一國兩制”在新時代的最佳作用方式。粵港澳大灣區實現了支撐國家更高水平改革開放與持續保障港澳繁榮穩定的理性結合,因而從根本上回應和回答了在新時代如何繼續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推動國家發展的重大問題,切合了“一國兩制”的初衷初心。
更進一步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還將推動探索中央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的具體制度機制,因為大灣區的深度融合必然涉及內地與港澳的制度競爭、互動、交流與融合,這是一個良性的制度整合過程,不是“內地港澳化”,也不是“港澳內地化”,而是內地與港澳根據共同建設目標及各自制度優勢進行的“協作性制度創造”。為了實際解決大灣區建設瓶頸而進行的這種制度創造與融合,是“兩制”向“一國”回溯性建構的理性化過程,所產生的具體制度增量與成果,直接服務于大灣區。
當然,粵港澳大灣區深度融合發展必然會遭遇種種困難和挑戰:其一,制度差異性帶來的制度壁壘與制度摩擦成本,這是“一國兩制”優勢下的副產品,如果大灣區建設不重視及時研判和消除這些障礙因素,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灣區內人員和資源的自由流動及創造性發展;其二,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的“軟文化沖突”,這主要體現在港澳社會的國際化與現代化程度相對較高,而內地城市的文化觀念與社會管理模式與之仍有較大差異,這種“軟文化沖突”也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大灣區內部的融合發展,限制港澳居民尤其是專業精英人士的認同和歸屬;其三,港澳與內地的“雙向開放”難題,既然是一個大灣區,就不能僅僅是內地城市對港澳單向開放和提供更多便利,也需要港澳對內地合理開放,這種雙向開放固然由于體量差異而不可能對等,但也需要逐步放寬及可比較;其四,香港社會還存在一定的本土主義與港獨威脅,存在這些反對力量背后的國際勢力,他們顯然會構成大灣區融合發展的阻礙性因素,如何從香港本地法治及國家管治的角度合理管控和遏制這些干擾,確保參與大灣區建設的香港社會是一個憲法與基本法秩序鞏固的穩定社會,也是對中央和特區的一個挑戰;其五,一定程度和多種形式的地方保護主義需要通過民主協商、制度管控、政策協調等方式予以壓制及化解,從而達到大灣區產業分工與利益分享的最優化及公平性。
總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有效落實了十九大報告相關目標,形成了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具體戰略框架,提出了聚焦高科技、新興產業與制度性融合發展的一系列具體建設目標與方案,更是為“一帶一路”之技術標準與制度標準的實驗和成熟提供了最為有利的政策保障。粵港澳大灣區將再次驗證中國改革的地緣擴展邏輯:改革起于南方實驗,惠及全國。在新時代背景下,這一探索更可澤被“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助力人類命運共同體之理想性建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