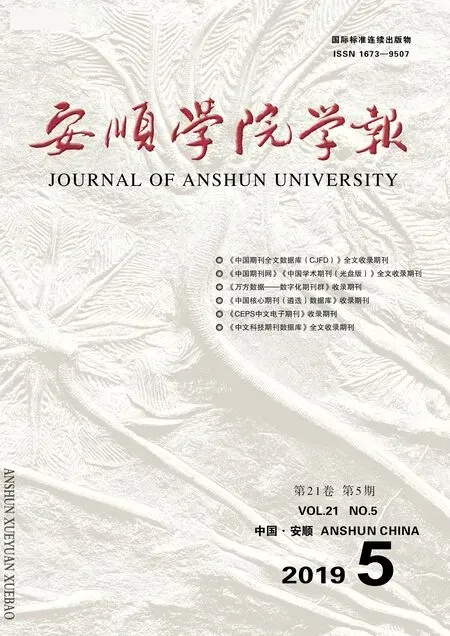屯堡地戲的蟄伏與復蘇
——訪地戲專家沈福馨
吳 羽 張定貴 呂燕平 董天倩
(1、4.安順學院旅游學院,貴州 安順561000)(2.安順學院政法學院,貴州 安順561000)(3.安順學院屯堡研究中心,貴州 安順561000 )
訪談時間:2019年9月17日。訪談地點:貴陽沈福馨老師家中。被訪人:沈福馨。訪談人:吳羽、呂燕平、張定貴。記錄、整理:董天倩
一、被訪人基本情況
沈福馨,1948年2月生于貴州安順。1965年于安順二中畢業后,進入貴州大學歷史系學習,1969年畢業。1970至1984年在安順144廠工作,任教師、宣傳干事。1984年任貴州省美術家協會《貴州美術》雜志執行副主編,是貴州省美術家協會會員、中國民俗學會會員,國家一級美術師。美術作品曾經多次在中國美術館展出,并發表于《美術》《美術觀察》等報刊。著有(含參編)《貴州安順地戲面具》《安順地戲》等6部專著,發表《戲劇活化石——地戲》等12篇論文。
二、關于地戲復蘇
吳羽:外界對屯堡文化的認知一般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是1902年,鳥居龍藏在飯籠鋪(今安順市平壩區天龍鎮)“發現”在當地被稱為“鳳頭雞”“鳳頭苗”人群。第二個階段是20世紀50年代,民族識別時費孝通率隊到安順一帶,明確指出屯堡人是漢族軍事移民集團。這些“民族”各地就有不同的名稱,如堡子、南京人、穿青、俚民子等。 第三個階段則是在20世紀80年代由地戲復蘇,特別是地戲出國引起了人們對屯堡文化的關注。
沈福馨老師是第三階段的親歷者,今天想請您給我們介紹一下這個階段的情況。沈老師,請問您從什么時候開始關注地戲和地戲面具?
沈福馨:我對地戲關注由來已久,但是對它的研究卻出于偶然。1965年安順二中畢業后,進入貴州大學歷史系學習。在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下,大學期間對專業學得不多,但是自小就喜歡的畫畫卻堅持自學了下來。1970年,進入安順144廠工作,首先是在廠子弟學校當了4年多的教師,什么課都上,語文、數學、科學、美術等。后來進入144廠工會工作,主要是搞宣傳、出板報,還兼任放映員。這個時期也堅持畫畫,主要以山水畫為主。當時還自己用鋼板刻印了《歷代名畫記》《圖畫見聞志》。1982年、1983年左右,廠里面把我調到了廠務辦公室。工作內容主要是打電話通知開會、看報紙,覺得無趣,就萌生了離開144廠的念頭。經過一番周折后,調到了貴州省美術家協會。
接觸地戲是一種偶然,是因為要完成一篇論文的寫作,才開始了對地戲的調查,并不斷擴大和加深。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民間藝術逐漸活躍起來。當時王朝聞先生要在貴州召開民間藝術家研討會,就讓我寫一篇論文參會。剛開始想寫安順蠟染或者普定的泥哨,但是蠟染關注的人太多,寫的文章也不少;泥哨知道的人不多,但是它在工藝、藝術價值上又稍有欠缺。經過幾番思索后,選擇地戲作為研究對象,于是開始了對地戲以及地戲面具的關注。
吳羽:您大概是什么時候開始接觸地戲?為什么會選擇周官一帶進行田野考察?
沈福馨:小時候就看過表演,第一場是在安順東關看的。當時雖然聽不懂唱詞,但是在大人的講解下,大概知道表演的是一些歷史故事。在寫“民間藝術家研討會”參會論文的時候,開始去搜集與地戲有關的資料。我外婆家是劉官鄉老幫寨的,這個村子雖然以漢族為主,卻沒有跳地戲,但是周邊的周官村、劉官都有。我的大舅是一位老學究,知道的東西不少,也比較能說,從他那里我知道了不少關于地戲的知識。也因此,把調查的第一個點選在了周官村。很多時候,去調查時并沒有遇上跳地戲,地戲面具是不輕易示人的,這個時候就需要有人居中介紹,然后買香蠟紙燭去,先做完簡單的開箱儀式后,才可以打開箱子,看地戲面具。
吳羽:您當時去做地戲調查一般是怎樣進行的?
沈福馨:那個時候沒有現在這么發達的交通網絡,主要是騎自行車、步行。當時在144廠上班,去搞地戲調查只能是偷偷地做,因為這在其他人看來是不務正業、是搞迷信活動。因此,只能利用一周一天的休假時間去鄉下做調查。星期六下班了,口袋里面揣幾個饅頭,騎著自行車就下鄉了,到村里面住,方便第二天早起做調查。雖然辛苦,但是一心就想把地戲推出去,讓更多的人知道,讓它能夠名正言順地出現在大眾的視野中。
吳羽:和您當時做調查相比,屯堡村寨的前后有哪些變化?
沈福馨:當時的屯堡村寨是很窮的。例如有一次到雞場去做調查,調查的農戶只能提供一張床,陪著我們去做調查的工作人員晚上就只能睡在農戶的玉米堆上將就一晚。
吳羽:從現在的認知來看,屯堡人因為較好的地理環境,以及手工技藝,經濟條件會不會好一些?
沈福馨:東部大的村寨經濟好一些,南邊以下的就要差很多。就地戲這個群體來說,神頭有一定的地位,所以稍好些,但是雕匠不行。例如我們去東屯調研時遇到的宋姓羅,就在一個黑黑的小屋子里面雕東西,只有一個小窗戶透進來一點光線,米飯也吃不起。我們在周官調查的時候,有一次住在胡永發家。當晚正好下大雨,半夜的時候我們旁邊的屋子就坍塌了。
吳羽:當時社會對地戲的認知程度是怎樣的?以地戲為代表的屯堡文化是不是處于一種蟄伏的狀態?
沈福馨:開始接觸地戲時,整個社會大環境都不是太好,還是處于被壓制的境地。跳地戲活動改革開放后才慢慢恢復。當時的屯堡文化應該算是一種蟄伏的狀態。
吳羽:您通過深入的田野調查寫出來的文章在社會上的反響怎樣?
沈福馨:當時寫了《安順地戲和地戲臉子》這篇論文,王朝聞在會上對這篇文章進行了高度評價,在國內學者中影響很大,當時參與的專家學者就對地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要來看地戲表演。于是在1984年,在省里面安排下,由頭鋪地戲隊在安順地委禮堂舞臺拉上幕布表演了《岳傳》,這是改革開放后地戲的第一場表演。看完表演后,王朝聞寫了文章“地戲的開打”,從美學的角度對地戲進行了分析,進一步增加了地戲的影響力。
三、關于地戲出國演出
吳羽:1986年地戲出國,可以說是屯堡文化研究的關鍵性事件。您作為這個事件的親歷者,請給我們講述一下這件事的始末。
沈福馨:王朝聞的文章“地戲的開打”,影響很大,并傳到了法國。著名畫家謝景蘭女士,看到這篇文章以后很感興趣。謝景蘭后來回到貴州后,因為有位同學是安順的,就找到我了解關于地戲的情況,回法國后把地戲介紹給了當年法國秋季藝術節的主委會人員。謝景蘭因為在法國藝術界有較高的聲望,組委會對地戲也產生了興趣,加上當年藝術節以“中國年”為主題,所以就決定把地戲加入藝術節中。
但是地戲在國內是被壓制的,影響也不大,所以文化部并不同意推薦地戲參演。當時文化部向法國藝術節主推的節目有“紅樓夢”“昆曲”等,但是法國方面堅持加上地戲,并表示如果沒有地戲,就不推中國的其他節目。最后,地戲和中國的其他節目一起登上了法國的藝術節,后來還到西班牙演出。 這次地戲出國,在法國演了了十多場,在西班牙演了兩場。藝術是互相交流的,地戲在法國演出后,法國的藝術家曾表示,他們的演出吸收了地戲的一些表演技巧。
吳羽:此次地戲出國的具體情況如何,為什么會派蔡官地戲出國,影響如何?
沈福馨:這次出國演出,前后一個月左右,先到法國,后來又去西班牙。地戲隊選的是蔡官的,因為蔡官離144廠近,更加了解那里的情況,交通便利,加上蔡官本身也雕刻面具,所以是比較合適的。此外,貴州還派出了黔東南的侗族大歌隊伍,他們原定的負責人因故沒有去成,侗族大歌隊后來的手續都是由我代辦。
吳羽:這個事件增加了地戲的影響力 ,當時應該有很多的媒體在報道這件事?
沈福馨:是的,當地的專家、各種媒體報紙,包括《人民日報》《貴州日報》,法國的《巴黎時報》等。在此之前,地戲在國內、在當地人看來,是不了解的,是迷信活動且見不得天的。通過這件事,至少得到了官方的認可,跳地戲活動,還有雕刻地戲面具,能夠正大光明地進行。
四、地戲調查
吳羽:和臺灣王秋桂教授聯合進行的地戲調查,以及聯合出版的《貴州安順地戲調查報告集》是對屯堡文化的第一次比較系統的文化調查與研究,有很大的影響。現在很多數據都來源于這個調查報告。請問這次活動是如何展開的?
沈福馨:在王秋桂之前,也有一些國外的學者關注安順地戲。1988年,我帶陶官屯的匠人到倫敦大學參加“世界面具學術研討會”,在那里展演,我還做了關于地戲的主題發言。1989年還組織去德國,當時只有部分人員到了德國。在這之前,楊正金先到了德國,因為國內環境的變化,被迫流落街頭,只好用帶過去的面具來換錢。
臺灣學者的話,在王秋桂之前,蔣勛、林懷民等人也來調查過。王秋桂是20世紀90年代初期來做調查的,主要由兩個臺灣清華大學的學生參與調查。調查組住在詹家屯,對詹家屯以及周邊村寨的地戲表演以及地戲面具雕刻情況進行調查。1993年,由我帶隊,帶領詹家屯地戲隊到臺灣巡回演出,在臺灣清華大學展覽面具,與當地的師生進行交流座談。
吳羽:這次地戲調查的周期有多久?有沒有一些資助經費?文稿撰寫如何分工的?
沈福馨:第一次調查用了一年的時間,后來根據實際調查情況又延長了一年,前后一共兩年的時間。經費不多,我們這邊一個人只有幾百塊的差旅費,由地方政府負責。這次調查,除了更進一步地摸清安順地戲及地戲面具雕刻的基本情況外,臺灣方面還幫助出版了民間戲劇相關一系列的書籍,共30本。同時,中國戲劇學會、英國丘吉爾基金會,以及與王秋桂教授有來往的法國、美國等學者也陸續來安順調查。這期間,還有一些國外的商人對地戲表演感興趣,通過王秋桂教授,想要把地戲表演進行包裝,推上商業舞臺。但是王秋桂教授以及我們都認為地戲表演是一種神圣的藝術形式,可以關注它、研究它,但如果商業化,將會褻瀆它的神圣性。故而對于商業性的邀約,我們都拒絕了。
在文稿的撰寫上,落款為安順的基本上由我來撰寫,臺灣部分的由王秋桂以及他所帶的幾名學生負責。
吳羽:在做地戲調查時使用的規范標準,包括量表、問卷等是怎么確定的?
沈福馨:我自己在早期做調查的時候,都是需要了就直接跑到鄉下去看。這樣的調查比較被動和隨性,沒有規律。后來,在吸取之前的教訓之后,會比較有目標地做一些準備,也能夠獲得更多的資料。在與王秋桂教授合作調查的時候,他們帶來了很規范的調查指標體系,比如說地戲演員使用兵器的尺寸、由什么材料制成等,都一一問清楚并詳盡記錄。至于調查中所采用的表格由我設計,其中包括人口、劇目等都采集到了相關的信息。通過這個表格,我們獲得了更多的基礎數據。因為當時安順三百多堂地戲,在每天都跑去調研的情況下,耗時至少一年多,不能一一親自去做調查,只能通過表格,搜集相關基礎的信息。
記得在法國博物館參觀的時候,還對法國人把木工房、鐵匠鋪中所有的東西都展示出來感到奇怪。在經過這次調查后,認識到前人的詳細記錄,可以為后人的研究提供更多的原始材料。所以,這次調查搜集到了很多珍貴的資料和數據。
五、地戲(面具)的特點
吳羽:您把安順地戲分為東路地戲和西路地戲,主要有些什么區別?
沈福馨:西路地戲在表演的時候有帳篷,服裝上的繡樣要簡單一些,比如蔡官、陶官等;東部地戲沒有帳篷,他們在服裝上繡樣多。在唱法上,東部地戲七字全部唱完,西部的只唱前面四個字,后面的三個字不唱,由其他人應和。東西兩路地戲表演上的差異,和他們的始祖來源不同有關。西路地戲所在地區的屯堡人祖籍以江西為主,東路則是來自朱元璋的老家安徽。來自江西的西部屯堡人信五顯菩薩,而來自安徽的東部屯堡人信汪公。屯堡人都帶來了各自母源地的信仰,并在地戲中也就體現了出來。
呂燕平:有人把地戲分為高樁地戲和矮樁地戲,而且有使真假刀槍的區別。您怎樣看?
沈福馨:這些現象在當時調查時沒有發現,應該是后續的演變,也可能是當時地戲調查中沒有發現的特殊情況。
吳羽:您認為安順地戲面具雕刻各個派系有些什么特點?
沈福馨:安順地戲面具雕刻,可以分為蔡官鎮下苑村的吳氏派、劉官鄉周官村的胡氏派,以及西屯齊二派。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從事地戲面具雕刻的人基本上都以這三派為主,從現存的地戲面具來說也是這樣的,都可以看到一些各派所雕刻的面具作品。至于有人說周官的面具雕刻是從黃臘六保傳過去的,個人認為這種說法不可信。20世紀80年代我去六保的時候,村中沒有雕匠,只是在六保旁邊的村里里面看到齊二雕的面具,可能是文革燒毀面具時被偷偷藏起來的。
各派雕的面具,有比較明顯的區別性特征。例如去雞場調查的時候,看到一個面具,覺得就是吳氏派的作品。但是問持有人,他們卻否認了。后來遇到吳氏派的雕匠,得知雞場的那堂面具確實是他們雕的,但不是以吳氏的名義,而是借用了其他人的名義去雕的。從橫向上來說,胡氏面具的頭盔上有四個角,龍的造型有三層以上;黃炳榮這一派的面具,要比其他派系的面具要大一圈,而且喜歡用一些吉祥的圖案和語言,我認為這和黃炳榮以打陪嫁家具起家有很大的關系。他的面具比較高、厚,整體要重一些。此外,他的技術比較純熟,功夫深、刀法精致。蔡官吳氏,來自雙堡楊家,在“三輩還宗”后現在改姓楊了。吳氏派最早的是吳少懷,他的面具喜歡用一些奇形怪狀的造型,使用的動物形象也比較多,比如龍、牛、馬、虎、魚等,整體上要比周官靈秀一些。東屯雕面具的在湖壩坡,調查時遇到的雕匠叫宋姓羅。這一派的面具要比其他派長一些,臉型比較喜歡用奇形怪狀的,臉上的花紋要復雜一些。
從縱向上來說,明代的面具比較簡略,小一些,頭盔的裝飾比較簡單,龍的形狀也比較抽象。到了清代,造型上要復雜一些,花功夫也更多了。
吳羽:20世紀80年代,周官把儺戲的因素引進地戲面具雕刻。您認為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沈福馨:我認為這是商業運作帶來的。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地戲面具商業化,人們傾向于新奇古怪的東西,就找地戲面具雕刻匠人訂做。因此,可以說是地戲面具的雕刻匠人去雕刻儺面具,而不是把儺面具的元素融入地戲面具雕刻中。從傳統上來說,應該說是地戲面具影響其他的儺面具。例如,齊二的雕的地戲面具“笑嘻嘻”,這是元代士兵的形象。到了后期的“歪嘴老苗”,則是在“笑嘻嘻”的基礎上更加丑化了。而儺壇戲中的秦童,則是借鑒了“歪嘴老苗”而來。
吳羽:如果往前追溯,安順地戲面具雕刻藝人最早的是哪些?
沈福馨:在調查的時候,見過的藝人,他們能知道的最早就是齊二、胡五公。我去周官調查時,胡紹南已經七十多歲。
六、當時的地戲研究情況及相關觀點
呂燕平:在少數民族村寨中也有地戲。您怎樣看待這個現象?
沈福馨:在歪寨、花溪大寨有地戲表演,但是不多,以漢族村寨為主,可以看成是調北征南帶來的劇種。在云南和順古鎮考察時,也發現那里有類似地戲的劇種。它位于滇黔古驛道的線上,應該是當時的軍隊帶過去的。還有威寧地區的撮泰吉,其中也有地戲的影子,是否受到地戲的影響?我有這個猜想,但是沒有進一步去印證。
呂燕平:您祖上是怎么到安順的?
沈福馨:我家祖籍浙江,在清代的時候做生意過來的。父親在舊州工作,母親是周官旁邊的老幫寨的。至于是沈萬三的后人的說法,個人認為不太可信。
張定貴:現在看到的安順地戲分布圖是您繪制的吧?
沈福馨:是的。當時找到測繪院的朋友,拿到貴州原始地圖,然后根據地戲調查所得到的數據,繪制而成的。
吳羽:當時安順做地戲田野調查的還有其他人嗎?
沈福馨:當時從學術角度去做調查的沒有。安順的王欽廉在雕面具,為了做生意,他經常到周邊去了解地戲以及地戲面具的情況。
吳羽:20世紀八九十年代年代對屯堡文化或地戲進行研究的學者有哪些?情況如何?
沈福馨:那個時期有謝振東、庹修明、顧樸光、潘朝林、皇甫重慶等也進行屯堡文化研究。外國也有一些學者在關注地戲的研究作品,但是因為當時沒有現在這么發達的網絡,所以在國內沒有看到。我的《安順地戲》和《貴州安順地戲面具》書稿完成比高倫的《貴州地戲研究》要早,但是因為經費原因直到1989年才出版。
訪談者按語:20世紀80年代以來,屯堡文化因為地戲為外界所關注,從蟄伏走向復蘇。在這一階段中有幾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一是20世紀80年代初地戲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沈福馨所撰寫的關于安順地戲的論文,引起了王朝聞的關注,并撰文對地戲進行了美學分析,擴大了安順地戲在全國的影響力。二是1986年安順地戲的出國,讓地戲從幕后從向了臺前。因為法國秋季藝術節主委會的堅持和地戲在法國和西班牙展演的巨大成功,使地戲在國際舞臺上的大放異彩,也使安順地戲得到了國內官方和民眾的認可,讓國內對地戲的認知更加深刻。三是20世紀90年代初與臺灣王秋桂教授對安順地戲的合作研究,是第一次對以安順地戲為代表的屯堡文化進行系統的田野調查,并進行了深入的學理性分析研究。沈福馨在各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中均起到了關鍵性的作用。 另外,沈福馨是1982年最早進行了地戲調查與研究,并以6部著作和12篇文章的成績,成為當時屯堡文化研究的中堅力量。沈福馨理所當然是這一階段的標志性人物,對屯堡文化的復蘇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正如沈福馨所堅持的,通過調查和研究,讓曾經被視為迷信活動的地戲能夠被官方認可,光明正大地出現在大眾的視野里;讓雕刻地戲面具的匠人,能自豪于所擁有的技藝,并代代相傳。這就是前輩學者對學術研究的初心,也是他們對傳統文化藝術神圣的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