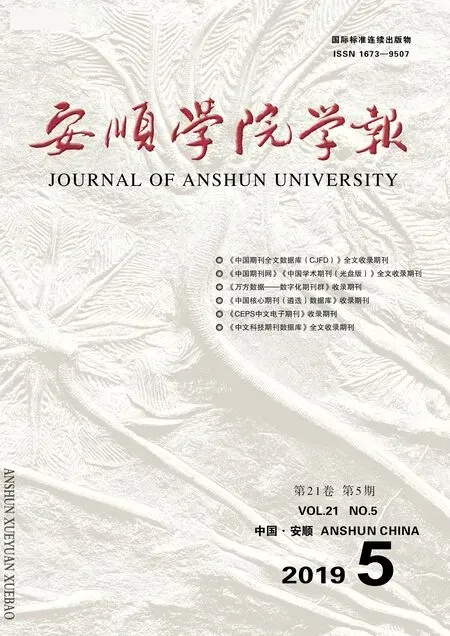郝敬《尚書》學辨偽研究
江鎏渤
(重慶師范大學文學院,重慶 401331)
郝敬(1558—1639),字仲輿,別號楚望,湖北京山人,萬歷乙丑(1589)進士,世稱“郝京山先生”,晚明時期著名的經學家、思想家。有《九經解》《山草堂集》傳世。郝敬及其《九經解》對明末清初學界產生了重要影響。《明儒學案》稱郝敬“明代窮經之士,先生實為巨擘”[1]1313,并肯定《九經解》的價值,言其“疏通證明,一洗訓詁之氣”[1]1313。毛奇齡、閻若璩、陳啟源、崔灝、焦循等等清代學者多受郝敬及其《九經解》影響,《京山縣志》曰:“道光間,《皇清經解》出,諸經學家如毛西河、閻百詩、陳啟源、崔灝、焦循,無不征引郝氏經解,推為大儒。”[2]405下欄
《尚書辨解》為《九經解》之一,為《九經解》所建立的經學體系之關鍵環節,集中體現了郝敬對《尚書》一經所作的關注,在《尚書》辨偽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尚書》歷戰國處士橫改以及秦火燔亂,真偽最淆,郝敬針對此特點,自序其作《尚書辨解》之意云“晚出古文,托名孔壁,良苦真贗,夐不相襲,而二千年來碔砆溷其良玉,不可以弗別也,作《尚書辨解》部第二”[3]95下欄。由是可見,辨偽是郝敬《尚書》學所關注的核心問題。郝敬運用分注今古文、考辨章法、考辨史實等三種辨偽方法對《今文尚書》《古文尚書》《孔傳》、大小《書序》進行了全方位辨偽,以文本編纂策略為基礎,既注重發掘《尚書》之大義,亦關注歷史考證。從而產生了“‘伏書’存圣人刪定之旨”“‘虞廷十六字’非往圣心傳”“《書小序》無微言大義”三種辨偽思想,對體認《尚書》的原本意義具有重要作用,作為明代“回歸原典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為閻若璩、惠棟等《尚書》辨偽名家提供了思想資源,促成了清代學者辨偽《尚書》的風氣。本文試圖就郝敬《尚書》學辨偽展開討論,集中探討郝敬《尚書》學之辨偽方法與思想,以期藉此窺得郝敬《尚書》學大體的面相。
一、郝敬《尚書》學辨偽方法
儒家經典中《尚書》真偽最淆。漢唐的學者重在對《尚書》之名物、典章、制度等問題的考訂,宋代以降,疑古改經風氣大盛,《尚書》真偽問題才逐步成為學術議題。宋元明三代學者圍繞《尚書》辨偽陸續有一些探討,郝敬辨偽《尚書》即產生于此種背景之在中。他主要采取了三種辨偽方法:在文本編纂上,他反對《孔書》的編纂方式,分注《尚書》今古文,以期讀者能一目了然。其次,他憑借著良好的語言文字功底對《尚書》的文勢、文風、文意進行考察,梳理《尚書》文本的內在邏輯,發掘經書大義。除了考察《尚書》文本之外,郝敬還力圖從史實中尋找旁證來考證《尚書》之傳衍。
(一)分注今古文
分注今古文指對《尚書》的《今文尚書》《古文尚書》(有時還兼分注大小《書序》)進行分開注釋,其為對《孔書》合注今古文方式的反叛。合注今古文的編纂方式源自《孔書》,為歷代《尚書》注疏沿用。宋元明重要《書》說體例多尊崇《孔書》,而不區分今古文,如(宋)林之奇《尚書全解》、(宋)蘇軾《書傳》、(元)陳櫟《書集傳纂疏》、(元)董鼎《書傳輯錄纂注》、(明)劉三吾等《書傳會選》、(明)王樵《尚書日記》。由此可見合注今古文作為學術傳統,具有巨大向心力。在此種學術背景中,能夠對《孔書》編纂方式展開懷疑者寥寥。(元)趙孟頫《書今古文集注》首開分注《尚書》今古文的方式,在元明兩代卻少有學者發現其價值。而《尚書辨解》關注并沿用了趙氏的注疏方式,于《辨解》前八卷專釋《今文尚書》,而《古文尚書》以及大、小《書序》則于后兩卷另注。
分注今古文為郝氏提供了巨大的闡釋空間,方便他分別討論今古文,進而更加清晰地表達自己的經學觀念。他不認可宋代學者針對《今文尚書》進行的改訂,認為《今文尚書》傳自孔門,縱使經過秦火,其篇章次第、文章字句仍準確無誤。如《尚書辨解·梓材》解題云“此亦周公為武王言,訓康叔也。篇中有‘若作梓材’之語,因以命篇。……首篇戒慎刑,明設官之意。次篇戒崇飲,革沉湎之俗。此篇戒刻厲,培忠厚之基。古語淵慤,讀者因疑為錯簡,今繹其義,圓婉周匝,其孰為錯簡乎?”[4]212下欄《康誥》篇首四十八字錯簡最早由蘇軾《書傳》提出,在宋代幾乎成為定論,而郝敬卻不認可此說。他從分析三篇主旨出發,認為《康誥》“戒慎刑”、《酒誥》“戒崇飲”、《梓材》“戒刻厲”,其主旨層層推進,先后次序甚明,不應有錯簡。通過對蘇軾“錯簡”之說的懷疑,郝敬表達了他維護《今文尚書》的立場。其維護《今文尚書》的立場于《尚書辨解》中可以大量見到,如《書集傳》解“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永保民”,曰“其句讀不同”[12]157、“文義不類”[12]157,認為“今王惟曰……庶邦丕享”與此作為前后文不匹配,“獨吳氏以為誤簡得之”[12]157,而郝敬則不認同《書集傳》之說,他總括《書集傳》所釋之兩節為一,以“今王惟曰……永保民”為“再申言立監之意”[4]212下欄,指出此一節為周公勸康叔寛刑治民之言,“仁厚屬之教”[4]212下欄。又如《書集傳》解《多士》末尾“王曰……爾攸居”一節,以多方篇末之“王曰:‘我不惟多誥’……又曰:‘時惟爾初……’”為參照證據,認為這是《尚書》的用語習慣,指出“‘王曰’之下,當有闕文”[12]173,意為它應如《多方》“王曰”下有所指。而郝敬則連“又曰”下之“時”為句讀,釋“又曰時”為“彼時”,解構了《書集傳》的立論,指出此節“因上言遷居以后之利”[4]225下欄,并認為“又曰時”為圣人溫柔敦厚、諄諄教民的體現,“圣人告人委屈如此”[4]225下欄。此外,宋儒解讀《堯典》《益稷》《金縢》《洛誥》等篇目多認為其中有“脫簡”“闕文”,郝敬均不予吸收,而用自己的觀點進行疏通闡釋。
而注解《古文尚書》時,郝敬則對其展開大力排詆,認為它們為后世偽作。如其注《大禹謨》首節曰“禹名文命,司馬遷《本紀》因之,相傳舊矣。今謂‘文命敷于四海’,非名非事,語不分曉。祗承于帝,與敷于四海意不屬。突引禹言‘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等語,與‘祗承于帝’亦不甚屬。‘黎民敏德’,與‘克艱’意亦不甚屬。此后段段零碎,集句成文,前后氣脈都無管顧。”[4]第268上欄討論《大禹謨》首節字詞句的運用,認為其文法上存在缺陷。就單獨文句而言,郝敬指明,“文命敷于四海”中“文命”為禹名,《史記》等記載已詳,以此推之,以禹“文命”之名后加“敷于四海”則語意不明。不僅如此,他認為此節句子之間的意思也不相連貫,有明顯拼湊的痕跡,“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后接“祗承于帝”“黎民敏德”后接“克艱”錯誤相似,前后文句突然轉化主語,導致文意不接,明顯違背了文法。郝敬與呂祖謙、蔡沈等疑經卻仍以發掘大義言說《大禹謨》相反,其注釋集中討論《大禹謨》字詞、篇章上的文法缺陷,并對它展開直接批評,充滿了懷疑的精神,“此后段段零碎,集句成文,前后氣脈都無管顧”[4]268頁上欄。郝敬對《五子之歌》《湯誥》《微子之命》《君陳》《康王之誥》等《古文尚書》篇目亦展開了同樣的批評,在以《古文尚書》為理學基礎的明代《書》學中具有強烈的反叛意識。
郝敬在《尚書辨解》中采用分注今古文的編纂策略,并以此為基礎分別對《今文尚書》《古文尚書》進行不同的闡釋,否認宋儒對《今文尚書》進行的脫簡、闕文等說法,明確指出《古文尚書》的缺陷。這表達了他對《今文尚書》的信任,對《古文尚書》的懷疑,對宋代疑《書》思潮進行了回應。說明他在疑經的傳統脈絡上又有新變,并具有經學建設意識。
(二)考辨章法
章法指篇章之謀篇布局,其主要涵蓋文勢、文風、文意等。考辨章法則指分別就文章文勢的連貫性、文風的時代性、文意的契合性進行考察,從其與時代之順逆來斷其真偽。郝敬在《尚書辨解》中便由此切入,進行辨偽。
1.文勢
文勢,亦稱“文脈”。文勢指向篇章內部段、句之間的邏輯關系。郝敬注解《古文尚書》,多立足其文本,從其文勢不通之處力證其偽。如郝敬訓釋《泰誓上》“惟受罔有悛心”至“予曷敢有越厥志”一節,云“夷居,平居也。既于兇盜,即箕子所謂殷民攘竊神祗之犠牷牲,用以容也。罔懲其侮,不止其慢也。‘天佑下民’七句,取《孟子》引《書》辭填補,前后不屬,本謂命德討罪,天下不敢違,此為武王自言。曷敢有越志,語意未順。”[4]280上欄郝敬指出“天佑下民……予曷敢有越厥志”取材于《孟子》,本為《孟子》所引《尚書》文句,此段用意明顯與《孟子》之意不合,其表意和整節不連貫,有特意添加的痕跡。梅鷟《尚書考異》辨偽《泰誓》僅言其文句多蹈襲自《孟子》,而郝敬則更深一步從文勢上看出其荒誕不合。相同的討論還廣泛存在于其解《大禹謨》《仲虺之誥》《伊訓》等《古文尚書》篇目。
2.文風
文風指的是篇章的氣質和風格,歷代作家受各自時代文風的影響,他們的文字自然也會打上時代的烙印。根據文風來辨偽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辨偽者的知識素養和語言敏銳度。《朱子語類》卷七十八、七十九多從文風詰難《尚書》,但僅及大、小《書序》及《孔傳》。郝敬以朱子的觀點為基礎,對大、小《書序》《孔傳》之文風多有評論,而較朱熹又進一步,把從文風辨偽的方法用到了《古文尚書》上。其與朱熹相似者,如《尚書辨解》卷九評論《書大序》說:“按《序》不類西漢語,西漢文字樸直,此婉麗有六朝風氣,后人擬作也[4]259下欄。朱子認為《書大序》之文風不類西漢,其為似后世偽造,云“《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5]2634。郝敬則指出《書大序》“婉麗有六朝風氣”,其懷疑與朱子如出一轍。此外,郝敬有從文風辨《古文尚書》之偽者,直接點明《古文尚書》之文風不類上古,而反觀朱子對《古文尚書》的懷疑,則少有從文風之時代性出發。可見,郝敬在朱子的基礎上又更進了一步。如其解《胤征》云:“其浮藻類《左》《國》,無忠代樸直之味”[4]272下欄,他認為《胤征》之文風類于《左傳》《國語》,與夏代忠厚之文風不相符合。郝敬從文風分析單篇《古文尚書》,并進一步對《古文尚書》之整體文風進行懷疑,其《讀書》云:“《孔書》四代文字一律,必無此理”[4]118下欄,意為《古文尚書》虞夏商周四代之篇目之間文風無明顯區別,不符合語言發展的一般規律。
3.文意
從文意辨偽是指文句所表之意是否與篇章的題旨相契合。郝敬認為《書小序》《古文尚書》所表達的意思膚淺,與其篇章題旨不相合。如《尚書辨解·咸有一德》解云:“《伊訓》以下五篇辭皆淺泛,無古人坱圠沈冥之意,列之《禹謨》《湯誓》《盤庚》間,絕不類,其非古書無疑也。”[4]276下欄“《伊訓》以下五篇辭皆淺泛”指《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表意一覽而盡,與《禹貢》《湯誓》《盤庚》等真篇之“坱圠沈冥”、動輒更數端相差甚遠。又郝敬解《伊訓》“惟我商王”至“墜厥宗”一節,言其“文采歷錄,徑情直發,一往便終”[4]275上欄、“語雖正而響盡意竭,無復黯然之思”[4]275上欄,指出《伊訓》雖文采飛揚、講究音韻,但是文義膚淺,終非上古手筆。另外,語意膚淺表現為文句浮泛、粗疏,指示不明,與《尚書》國史實錄的性質相違。如《尚書辨解·微子之命》解云:“語浮泛而少筋骨,轉換數字,凡命皆可用”[4]284上欄,他指出《微子之命》文句浮泛,稍微轉換一下其中個別詞語則可以用于其他任何冊命,認為《微子之命》定非周初封微子之實錄。類似的討論存在于其解《說命》三篇、《伊訓》《太甲》三篇等《古文尚書》篇目中。
(三)考辨史實
考辨章法主要從文學角度對《尚書》進行關照,除此,郝敬還從史實層面對《尚書》加以考辨。他將史實分為兩類:其一為歷史真實,其二為價值真實。歷史真實具有外向性,立足于歷史事件本身,偏向于歷史考證。而價值真實則具有內向性,存在于人的精神信仰中,偏重于經書大義的發掘。這兩種真實互為表里,共同構建著郝敬的辨偽方法。
1.歷史真實
從早期文獻的記載來探尋文本的源流可為論證提供堅實的證據,屬于歷史考證的范疇,在清代以后蔚為大觀。這種方法最早由朱熹等宋代學者有意使用,如朱熹探尋《孔傳》的源流,便以《尚書注疏》記載參證,認為《孔傳》不可信。(明)梅鷟《尚書考異》中,歷史考證大量運用,如《尚書考異》卷一引《史記·儒林傳》《漢書·藝文志》《后漢書·儒林傳》《隋書·經籍志》相關的記載討論《孔傳》源流。郝敬考辨《尚書》之源流亦運用了歷史考證的方法,與朱熹、梅鷟等人桴鼓相應,為乾嘉考據學提供方法啟示。
《時習新知》卷六曰:“未嘗言孔安國作《傳》。……亦未嘗言有孔安國《傳》也。當時若有《孔傳》,賈、馬、鄭三子,必不匆匆作訓注,且二史安得遺之?”[6]823下欄《尚書辨解》卷九曰:“漢惠帝時,魯共王壞孔子宅,得《古文書》上獻,班固、劉歆亦嘗言之,第云安國獻《書》,未言詔安國為《傳》也……其所謂十六篇者,在今二十五篇中否,不可考,但哀帝朝劉歆請置博士,廷議不可,大臣龔勝以去就爭,師丹劾歆改亂舊章,則當時已疑之,是用湮沒不傳……好事者,因緣偽增至二十五篇,托安國為《傳》,甚不足信也!大抵漢初獻書,不言發自冢中,則云出自壁間,實多后人補撰。”[4]261上欄—下欄
郝敬從《漢書》《后漢書》以及賈逵、馬融、鄭玄之經說中尋找材料,對“漢武帝詔孔安國作《傳》”一事進行考證。關于《孔傳》,郝敬認為,《漢書》《后漢書》皆未言“孔安國作《傳》”之事,且賈逵、馬融、鄭玄等東漢晚期經學家均未引用孔說,可見他們都沒見過《孔傳》,由此《孔傳》之來源便不當在西漢,“始末悠謬”[4]259下欄。在論證《孔傳》為后世書的基礎上,郝敬進一步申明,據《漢書》《七略》之記載,與《孔傳》相關之十六篇本《古文尚書》真實存在,可是十六篇本《古文尚書》自產生之日其就不被學者認可,龔勝、師丹均反對其立于學官,足見它不可信。由此以推,今存二十五篇本《古文尚書》縱使其衍生自十六篇,也亦僅是偽托之作。郝敬以史實為依據推測《古文尚書》的源頭,認為《古文尚書》源自挾書令廢除之后形成的造偽風潮之中,“大抵漢初獻書,不言發自冢中,則云出自壁間,實多后人補撰”[4]261下欄。郝敬追溯兩漢針對《尚書》的相關記載,結合史料進行考證,體現了學術研究方法的新動向,后世乾嘉之學將此種歷史考證發揮到極致。
2.價值真實
董玲認為郝敬為學“重視經中之道,而非經之文辭,亦即重視經書所承載的圣人精神而非經書本身”[7]183,郝敬在價值真實層面考辨《尚書》真偽體現了其經學的這種特征。以圣人的道德對《尚書》記載進行逆推以辨別文本真偽最早由《孟子》使用,《孟子·盡心下》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8]1034孟子立足于《武成》所記與圣人形象不合,認為《武成》(《逸周書·世俘》)非《尚書》真篇。武王為至仁,“無敵于天下”,紂為至不仁,他們之間民心有向背,武王伐紂應當輕松取勝,不至出現“血流飄杵”的慘烈戰況。
郝敬借鑒《孟子》重視價值真實的辨偽方法,以此塑造理想的圣人形象。他認為《泰誓》抹黑武王、《蔡仲之命》抹黑周公,分別把圣人記載成了暴戾、殺親的惡人。郝敬解《泰誓下》曰:“直斥獨夫受,略無顧忌,末引文王,尤為失類”[4]281下欄,指出《泰誓》中“獨夫受”“惟我文考……惟予小子無良”等文辭不僅怨憤,而且矜夸,與武王圣人形象不合,以致后人認為武王非圣人,“忿憤如《泰誓》,夸如《武成》,何以為武王?故論者有武王非圣人之疑……此皆起于誤信《泰誓》,而不察其為偽作耳。”[4]281下欄又郝敬解《蔡仲之命》云:“三監雖流言,周之宗社未有傷也。輒殺一兄、囚一弟、貶一弟,……司馬遷無識,信為實錄。后世薄夫,遂謂義可滅親、兄可殺、弟可誅,則是《書》為口實,而周公為戎首矣!……篇首序事煩瑣,非三代之手筆。”[2]284下欄郝敬解《金縢》指出,三監流言亂國,成王殺管叔、囚蔡叔、貶霍叔,此事非周公所為,而《蔡仲之命》則認為周公殺兄囚弟、大義滅親,與他釋《金縢》有矛盾。由此他申明《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為庶人”等記載不是實錄,其附會成王之事于周公,極大地玷污了周公名譽,后世王莽、曹操、朱棣顛覆君主往往以周公為口實。郝敬帶著悲憤的情緒去解讀《蔡仲之命》,認為其記載誤后人多矣,“司馬遷無識,信為實錄。后世薄夫,遂謂義可滅親、兄可殺、弟可誅,則是《書》為口實,而周公為戎首矣!……篇首序事煩瑣,非三代之手筆”[4]284下欄。他從周公的道德性出發展開解讀,認為若信《蔡仲之命》為實錄,則周公為“戎首”。而周公道德高尚,并不會作出殺兄囚弟之事,由此,他指出《蔡仲之命》為后人有意偽造。
上述兩例以武王、周公之善辨《泰誓》《蔡仲之命》之偽,郝敬亦有從反面進行辨偽者,如以穆王之不善辨偽《君牙》《冏命》。據史,穆王是有名的盤樂之主,其事不足為后世取法,本應摒于《尚書》之外,而偽書為了湊足百篇之數于《尚書》中增多《君牙》《冏命》二篇。《尚書辨解》曰:“夫子刪《書》以《呂刑》有仁人之言,故存之。后世遂偽增《君牙》《伯冏》。圣人何取于穆王,而錄其辭反多于成、康乎?”[4]289上欄《尚書》之《呂刑》《君牙》《冏命》記穆王事,《呂刑》為穆王命呂侯制定的法典,《君牙》《冏命》為穆王時的人事任命。郝敬以穆王的道德出發,結合孔子刪《書》之旨,認為穆王本不為孔子取法的對象,《呂刑》因有“仁人之言”而存于《尚書》,而《君牙》《冏命》兩篇記記述穆王任命君牙、冏,純為表彰穆王之作。按理:穆王之功不過成王、康王,《尚書》錄其辭不應多于此二王。依此,郝敬判斷《君牙》《冏命》為后世偽篇。
郝敬的辨偽被古國順《清代尚書學》列入“心疑”《尚書》諸家,為《尚書》學史上開辨偽風氣者之一。以辨偽方法言之,郝敬辨偽《尚書》采取了文本編纂、文學解讀、歷史考證、經義探析等各種方式,明顯非“心疑”能概之。郝敬辨偽《尚書》在應當具有更高的學術地位。
二、郝敬《尚書》學辨偽思想
郝敬具有強烈的傳道意識,其辨偽《尚書》終究歸向于求圣人之意。他力圖從各方面發掘《古文尚書》、大小《書序》《孔傳》之偽,既而形成了“《伏書》存圣人刪述之旨”“虞廷十六字非往圣心傳”“《書小序》無微言大義”三種辨偽思想,促成了他《尚書》學體系的構建,表達了他回歸原典的企圖。
(一)《伏書》存圣人刪述之旨
《伏書》,即伏生傳本《今文尚書》,在漢代發展為歐陽、大小夏侯三個本子。疑辨《伏書》始于劉敞《書小傳》,至宋代蔚然成風,有宋一代呂祖謙、蘇軾、蔡沈等人均對《伏書》表達過懷疑,認為其中有文字有脫簡、闕文,其篇次亦有可調整者。郝敬針對宋人對《伏書》的懷疑,對《伏書》的文獻來源、思想內容、文字等方面進行了解讀,以確認《伏書》具有完整性,存圣人刪述之要旨。
首先,他認為《伏書》來源最正,已能完整概括四代之史實,《孔書》為后世增多。《讀書》謂:“夫子刪定之季,周室東遷已久,典籍散亡。計當日所定,四代《書》亦應不多。伏生所授二十八篇,四代(規模)已具,恐未止三之一耳。……《書》辭深奧,故伏生所記止此。假如二十五篇者,雖多可不至于遺忘,亦真與偽之別也。”[4]119上欄郝敬指出《尚書》在周東遷之后就已經散亡嚴重,《伏書》大體上保存了《尚書》文本,接近四代之規模。同時,郝敬申明《孔書》則書辭淺顯,若此真為周室所傳,伏生不至于遺忘簡單篇目而專記深奧之文。
由此,郝敬進一步表達了他的態度,他認為《伏書》經過孔子刪定,思想和內容上都達到很高的層次。《伏書》內容全真、不容改易,且其思想實為圣人撰述,在二十八篇里有完美體現:“后人何幸,因伏生所授,得見四代鴻寶,二十八篇真足為萬世國史之宗。”[4]118上欄郝敬不信前儒對《今文尚書》的改動,認為朱熹、蔡沈分《洪范》為經、傳喪失了《洪范》原本之旨,是“割裂”之舉。“世儒不達《洪范》之理,割裂九疇之序,舉目遺綱。”[4]179下欄又反對宋代諸家“錯簡”之說,如解《康誥》曰:“周之典章,大抵出周公手……先儒謂為武王作,欲移置《金縢》前,以篇首‘惟三月’至‘大誥治’四十八字為錯簡,移置《洛誥》周公拜手稽首上。今以篇次考之,洛成雖在七年,而初基則自茲始。諸侯咸會,故洪《大誥》。非錯簡也。……說者不深思,議改舊章,非也。”[4]202下欄胡宏首創武王作諸誥之說,蘇軾、朱熹、蔡沈據胡宏之說而認為周初諸誥有錯簡,又欲移諸誥之篇次。郝敬認為《大誥》《康誥》《梓材》等篇目多為周公以武王口吻而作,諸篇與周初史事符合,聯系緊密,依次推進。他指出,諸誥不存在錯簡的問題,更不存在篇次混亂的問題,《伏書》的文本完整,存圣人刪述之旨,其云:“《伏書》二十八篇,編次井然,斷不可易也。”[4]237上欄以《金縢》至《洛誥》為例,郝敬于《金縢》至《洛誥》諸篇中建構出了成王元年至成王七年的史實,從中討論周與殷、周公與三叔之間、成王與周公之間等關系,認為周公求代武王死、成王誅三監、周公東征、周公營洛、周公再東征等諸事件之間有著連貫的脈絡,雖然這些事件只能了解其大概,但是脈絡清晰,蘊涵了深刻的倫理價值,即存有孔子刪定之旨,“千載之下,不能詳考其事,而刪定意緒隱然可尋,在讀者熟思耳。”[4]229下欄
(二)“虞廷十六字”非往圣心傳
《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被稱為虞廷十六字,并被視為往圣心傳要訣。歷代學者雖懷疑其為后世偽造,卻又回護它,努力將它融入理學的建構中,如《書集傳》《書傳會選》《尚書日記》依此句解釋心、性、氣等理學概念。他們為何對虞廷十六字有如此矛盾的態度?從朱熹之言可窺見原因:“《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5]2718。他們認為《古文尚書》諸篇中有很多精辟之句(虞廷十六字即其一)承載著重要的義理,若摒之在外,則不益于理學體系的構建。
郝敬表現出與他們相反的態度,不信虞廷十六字為往圣心傳。雖然虞廷十六字義理混融,但其理實為后世之理。郝敬云:“先儒謂此十六字為心學之要,似也。然自是三代以后語,在《禮記》《中庸》《大學》《孟子》及南宋理學諸書,則此語為名理,在古神圣面授,則為贅言。……況舜、禹覿面相授,有是呶呶者與?其辭甚深刻,而其旨反淺狹,酷似后儒理學家言。愚以言而辨其偽,非以言不善而詆其偽也。”[4]269下欄—270上欄郝敬指出虞廷十六字辭與旨不相匹配,其辭甚多而其旨反狹,置之于《禮記》《中庸》《大學》《孟子》及南宋理學諸書則可,而置之于虞廷間則不似。于此,郝敬主要從文風的時代性出發去判定虞廷十六字非往圣心傳,較之《堯典》《禹貢》之“簡奧”,與《皋陶謨》之“精深淹雅”,虞廷十六字則顯得“呶呶”。若《大禹謨》與《堯典》《禹貢》《皋陶謨》同為真,那么便不會出現此種情況。郝敬《論語詳解》“堯曰”章進一步指出:“圣人之為天子非逸樂也……堯言廣大精微而遠略而詳,文運方啟,混沌初開,故其言錯落,而其旨隱約,意象渾淪……舜亦以命禹,只字無容增減,《古文尚書·大禹謨》別增‘人心道心’等語,正落后世理窟,其全篇文氣亦渙散,殆后人補輯,使舜當日于‘允執厥中’上更饒別語,此章豈得無述而直云舜亦以命禹乎?舜既瑣瑣解釋,二千年后,子思何須作《中庸》?”[9]445下欄郝敬申明堯舜時混沌初開,故“其也言錯落,其旨隱約,意象渾淪”,其言貴精而不在多。一方面,虞廷十六字其文其渙散、毫無精細之意,與上古渾樸尚精之風違背,次則《論語》之言僅及“允執厥中”,足見十六字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精微惟一”為后世所增。此外,此十六字如此詳盡闡說“人心”“道心”,其思想的系統性已經接近《中庸》,堯舜禹“傳心”重在傳遞情感體驗、注重“十六字”之實效性,而無有意建構思想體系的動機。
(三)《書小序》無微言大義
《書小序》似《春秋》有微言大義,源自西漢《尚書》歐陽學、《史記》之“孔子序《書》”之說,而后《漢書·藝文志》又增益此說為“《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于堯,下訖于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10]1706,明確提到孔子曾作《書小序》共百篇,深刻影響了后世對《書小序》的解讀。此闡釋傳統下,學者普遍認為《書小序》為孔子作,能以微言現大義。直到宋代林之奇、朱熹等學者才開始對此產生懷疑,他們認為《書序》非孔子作,由此帶來對《書序》之微言大義的解構。蔡沈承師之說于《書集傳》中黜《書小序》,不以冠篇首,以注解形式落實了宋代學者的觀點,并在元明清三代成為學界共識。
郝敬繼承了蔡沈對《書小序》的懷疑,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意見。關于《書小序》的作者,郝敬認為《書小序》言語多荒贅,為周秦人手筆。《讀書》云:“《書序》非夫子作,其篇目混淆,語多孟浪,繁簡不中節,殆周秦間人制作。”[4]115下欄他指出《書小序》之文有“篇目混淆”“言語多不合理”“繁簡不適”等問題,根本不可能有“春秋筆法”“微言大義”。“篇目混淆”,指《書小序》劃分篇目多不合理,違背圣人刪述之意。如郝敬解《堯典》《舜典》序云:“《堯典》一篇,并載舜事,書成于虞,故稱《虞書》。二圣際會,一德終始,故古史合典,以別于革命之代。后人顧謂闕略略,割‘愼徽’下為《舜典》,非作者之意矣!”[4]262下欄郝敬以《古文尚書》之《堯典》《舜典》為一篇,而《書小序》直接把二者分開說,不明“二圣際會,一德終始”之意。同樣,郝敬對《益稷謨》《盤庚》《顧命》等序言也持此態度。“言語多不合理”是指《書小序》之言不合語言習慣,由此導致字句不便理解。如解《分器序》云:“邦諸侯,不成語”[4]265上欄,抓住其中的“邦諸侯”,認為“邦”與“諸侯”不能成句。又如解《君奭序》“召公不悅”云:“召公不悅,語不明,起后人之疑”[4]266上欄,言《君奭序》“召公不悅”表述不清,使后人誤以為周公攝政不還而召公勸之,“起后人之疑”。此外《高宗肜日》《康王之誥》《畢命》等篇目之序言亦存在“言語不合理”的問題。“繁簡不適”意為《書小序》之言說存在于篇目中,無精練題旨之思,顯得累贅。如郝敬釋《五子之歌序》云:“按五子作歌之由,已具本篇,何用復說?若《詩序》自無此病”[4]263上欄,以《詩序》之精練作為《書序》之參照,認為《五子之歌序》言說五子作歌的原因,與《五子之歌》正文重復。又如郝敬釋《蔡仲之命序》云:“篇中自有序,此亦贅語”[4]266上欄,指出《蔡仲之命序》述“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4]266上欄,于《蔡仲之命》正文中別無二致,累贅多言。同時,郝敬認為《周官》《文侯之命》等篇目之序也有相似缺點。
郝敬通過闡釋《書小序》的諸缺點,認為《書小序》明顯非孔子所作,更無微言大義。經學史上視《書小序》有微言大義的代有其人,如漢代許慎、鄭玄,唐代孔穎達,宋代二程(程頤、程顥)、蘇軾、呂祖謙、張九程、鄭伯熊,清代莊存與、劉逢祿等人。認同《書小序》有微言大義的學者,常認為《書小序》經孔子作,與《春秋》一樣關注于討論“圣人理想人格”“君臣大義”“一字褒貶”等問題。在宋代疑經思潮的影響之下,林之奇、朱熹、蔡沈等學者對《書小序》持不同的態度。由此,疑《序》與信《序》兩個陣營相互論爭。郝敬“《書小序》無微言大義”的思想,發軔自《書集傳》,而通過對《書小序》之錯誤展開更加詳盡分析以解構其“微言大義”的觀念,對《書集傳》之說有新發展,深刻影響了后世。程元敏《書序通考》認為《書小序》為周秦間人作,無微言大義,或許即受了郝敬的啟示。
三、郝敬《尚書》辨偽之學術意義
學者們對《尚書》的辨偽一環緊扣一環,由懷疑到確定最終定讞,他們之間存在著彼此承襲、影響的關系。承襲指專指后代學者接納前代之說,而影響則主要存在于一代之學術思潮里。
先從承襲說起。學界對《尚書》展開大規模的疑辨始于宋代,《四庫提要》云“閩洛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斥以為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11]1上欄,恰當地概括了宋代經學斥“經師舊說”而“獨研義理”的疑經風氣。宋儒的疑經風氣于《尚書》一經表現為對今古文《尚書》、大小《書序》《孔傳》真偽的懷疑。其《尚書》的疑辨成果最終被蔡沈收納于《書集傳》,在元明兩代學界繼續發揮影響。郝敬的辨偽《尚書》即產生于此種承襲的背景之下。郝敬主要從兩個方面對宋儒進行承襲:首先,郝敬繼承了宋代學者對《古文尚書》、大小《書序》的懷疑,而其態度更加鮮明、直接,無宋儒回護之意。其次,郝敬對宋儒懷疑《今文尚書》多有駁正,他信奉伏生所傳二十八篇為圣人刪述之原本,以建構他的《尚書》學體系。綜上所述,郝敬的《尚書》辨偽在傳統的脈絡之中又有新變,把辨偽《尚書》進一步塑造成為了主要學術議題,對閻若璩、惠棟等清代學者產生了重要影響。
再從同時代學者間的影響上討論。林慶彰《明代考據學研究》認為明代中期以后學界興起了一股回歸原典的運動。回歸原典指向探求圣人之原本,從經典中汲取思想資源,郝敬辨偽《尚書》亦可列入這場運動之中。他每解一經,都事先做辨偽工作,為其闡釋經學提供可靠材料,如其解《易》信《易卦》,解《詩》信《詩序》,解《周官》認為其非周公作、為后世王霸之書等。就《尚書》一經而言,郝敬“回歸原典”的方式與其他學者亦存有不同,如郝敬與同時代之梅鷟偏向于解構《尚書》相比,明顯偏向于重建《尚書》代表的價值體系。郝敬以《今文尚書》為主要載體,摒棄《古文尚書》《書小序》“周公殺兄”“周公遷殷頑民”等論題,重新建立了“圣經”之倫理價值體系,正如其《讀書》云:“《孔書》與二十八篇,良苦較然,豈千余年來無一識者?以呂易嬴,久假不歸,依附圣經攻之,有投鼠之忌。”[4]117下欄郝敬通過辨偽《尚書》重新確立《書》教的意義,在晚明復雜的思想背景中,以《尚書》辨偽為主要詮釋內容,借經典立言,塑造著時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