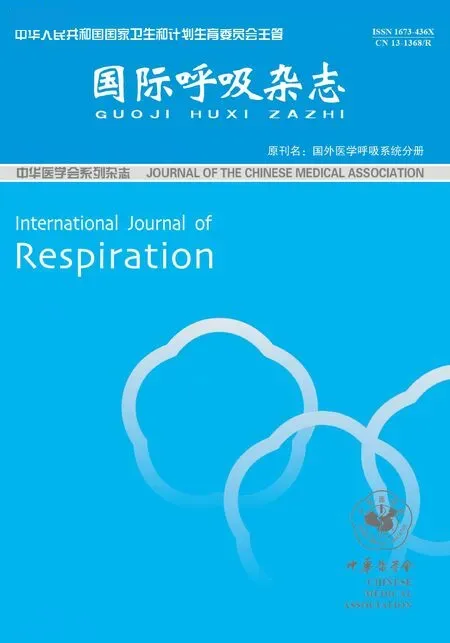微生物組學在哮喘中的研究進展
曠健 黃榕 劉沉濤
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兒科,長沙410008
目前已知,大量的微生物定居在人體的皮膚和黏膜表面,從宿主或其他微生物汲取賴以生存所需要的營養,高度適用于人體的復雜結構。微生物組學指寄居在人體內的微生物種類及其基因和基因組的總和。不同個體、不同軀體部位和不同時間的微生物組學組成均不相同[1]。黏膜免疫細胞和分子與人體暴露的細菌之間形成錯綜復雜的網絡,精確調節組織中免疫耐受和炎癥之間的平衡。生命早期形成的微生物群在宿主的成長和免疫系統發育中起重要作用[2],延遲或被改變的這些微生物群將增加過敏和哮喘發病的風險。本文著重綜述微生物組學在肺部免疫調節中的可能機制,腸道和呼吸道微生物群改變在哮喘發病中的作用。
1 微生物組學作用的免疫機制
目前已知細菌通過多種機制參與誘導免疫耐受和抑制炎癥。微生物群的細胞壁成分和代謝產物都參與調節宿主對微生物和環境刺激的免疫反應。部分共生菌如雙歧桿菌、乳酸桿菌、梭狀芽胞桿菌增加小鼠調節性T 細胞比例[4-5]。其中,梭狀芽胞桿菌通過刺激ILC3產生IL-22,有助于加強內皮屏障功能,降低腹瀉時小腸黏膜的通透性[6]。大腸桿菌和乳酸桿菌通過刺激樹突狀細胞中維生素A、色氨酸和血紅素加氧酶1代謝,來促進誘導調節性T 細胞[7-8]。來源于脆弱類擬桿菌的莢膜多糖抗原A 通過直接作用于類漿細胞,從而促進CD4+T 細胞分泌IL-10[9]。來源于長雙歧桿菌的表面多糖可抑制腸道和肺部Th17反應[10]。攝入外源性長雙歧桿菌后,健康志愿者周圍血中Foxp3+T 細胞增加,牛皮癬、潰瘍性結腸炎患者血清前炎癥因子CRP水平降低[11]。此外,腸道微生物代謝物短鏈脂肪酸,如醋酸鹽、丙酸鹽和丁酸鹽,可通過G 蛋白耦聯受體結合,抑制組氨酸去乙酰化酶,促進樹突狀細胞和T 細胞反應[12]。人腸道細菌產生的大量生物胺影響機體的免疫反應和炎癥反應[13]。在小鼠模型中,微生物產生的精胺、組胺和牛磺酸可激活宿主NLRP6 炎癥小體信號通路,促進內皮細胞分泌IL-18,并促進下游的抗微生物多肽分泌[14]。
2 微生物組學在哮喘模型中的研究
多個不同的動物研究支持微生物組學在氣道疾病發病中的作用。在不暴露于任何病理或非病理微生物的無菌(germ free,GF)動物中發現,微生物群有助于降低過敏性氣道炎癥。Herbst 等觀察到,卵蛋白 (ovalbumin,OVA)激發后,GF小鼠中的2型氣道炎癥和氣道高反應明顯強于共生微生物定植的無特定病原體 (specific pathogen free,SPF)小鼠。將GF小鼠與清潔小鼠共同飼養3周后,GF小鼠的2型氣道炎癥和氣道高反應降至清潔小鼠水平,提示腸道和氣道共生菌具有保護作用[15]。此外,生命早期共生菌定居的GF 小鼠腸黏膜固有層和肺內的自然殺傷細胞減少,從而減少了過敏性氣道反應的嚴重程度;然而生命早期之后定植菌對疾病表型沒有影響,也不影響調節性T 細胞或自然殺傷T 細胞的發育[16]。此外,重建腸道微生態社區有益于防治由于新生小鼠的抗生素治療導致的調節性T 細胞減少和Th細胞2型反應增強[17-18]。
Gollwitzer等模擬嬰兒氣道微生物定植條件下,研究了不同年齡 (3、15、60 d)的小鼠對屋塵螨 (house dust mites,HDM)誘發的過敏性氣道炎癥的敏感性。結果發現:暴露于HDM 后,新生小鼠較年長小鼠易誘發氣道嗜酸粒細胞增多,2型細胞因子釋放增加,并表現出較高的氣道高反應性。年長小鼠的這種保護作用與小鼠肺組織定植的細菌數量和GAMMA-變形桿菌和厚壁菌向擬桿菌優勢轉移有關。這項研究表明,小鼠體內在生命早期缺乏特定的細菌種類將影響之后免疫調節機制的形成,并使機體免疫平衡漂移至過敏而不是免疫耐受[19]。小鼠口服補充特定微生物如雙歧桿菌、Clostridium cladeⅣ和ⅩⅣ,或莢膜多糖PSA 脆弱擬桿菌后,通過誘導調節性T 細胞相關IL-10分泌的抗炎反應,減輕過敏性氣道炎癥[20]。除了腸源性調節性T 細胞遷移到肺部后產生抗炎作用外,微生物群產生的代謝物直接影響肺免疫應答[21]。高纖維飲食增加了大腸桿菌和放線菌的種類,并減少厚壁菌和變形桿菌,由此抑制小鼠過敏性氣道炎癥[22]。微生物對Dtryptophan、維生素A,或生物胺代謝的作用還可調節肺內Th細胞介導的2型變態反應[23-24]。多項研究表明,小鼠呼吸道直接暴露在微生物產物如內毒素或含Cp G 的寡核苷酸將抑制經典特征哮喘發病[25-26]。例如,鼻內大腸桿菌暴露將保護OVA 致過敏性氣道炎癥小鼠模型[27]。Suijs等[28]證明長時間暴露低劑量內毒素或農場灰塵可保護HDM 誘導A20小鼠哮喘。
3 腸道微生物在哮喘中的作用
腸道微生物群是人體最大細菌集落,由含有超過800萬個基因的500~1 000個不同的細菌菌種組成,并影響宿主免疫系統[29]。在3歲時,兒童腸道微生物群的組成達到成年人水平。歐洲的成年人腸道菌群優勢菌群主要包括擬桿菌、厚壁菌、放線桿菌、變形桿菌等,胃、十二指腸、近端小腸優勢菌群還包括鏈球菌、厭氧菌,雙歧桿菌[30]。腸道微生物群可通過多種機制影響遠距離部位 (如肺)的免疫應答:與健康志愿者比較,哮喘患者腸道分泌組胺的細菌數增加[31],組胺通過作用于組胺2 受體保護肺組織[32]。生命早期腸道微生物群受許多環境因素影響,如生活在微生物豐富的環境 (例如農場、頻繁接觸家畜和寵物、或多樣化的飲食)中與兒童哮喘呈負相關[33-36]。嬰兒分娩方式顯著影響細菌定植,剖腹產嬰兒腸道通常定植更多的葡萄球菌屬,桿菌科目 (Bacillales),丙酸桿菌科,棒狀桿菌科,而較少定植不動放線桿菌屬;經陰道分娩嬰兒的腸道定植梭狀芽胞桿菌增加[37]。除外分娩方式和飲食,母體妊娠期使用的抗生素或生命早期抗生素治療持久地影響微生物群,如減少放線菌,增加擬桿菌和變形桿菌[1]。
多項研究發現生命早期腸道菌群失調增加哮喘發病風險。出生后1個月內定植的艱難梭菌與年齡在6~7歲前兒童喘息和6~7 歲哮喘患病有關[38]。與非哮喘兒童相比,發生哮喘學齡期兒童在出生1周或1個月時腸道菌群多樣性降低,但是與出生后1 歲時腸道菌群多樣性無明顯相關[39]。此外,腸道菌群中相對低豐度雙歧桿菌、阿克曼菌屬和糞桿菌屬,而相對高豐度特殊真菌 (假絲酵母)的新生兒,發生過敏或哮喘的風險增高。因此,生命早期腸微生物失調與增加哮喘發病風險有關[40]。然而,目前尚不清楚腸道內的微生物失調是否可以直接驅動哮喘發病,或者腸道微生物失調通過改變免疫應答模式促進哮喘發病。
4 呼吸道微生物在哮喘中的作用
由于既往認為健康人氣道組織是無菌的,所以在2007年啟動人類微生物計劃之初,研究者們未收集氣道組織標本[41]。然而,不久之后一些研究者和研究團隊的報道:健康人呼吸道微生物群的組成,及呼吸道微生物群在呼吸道疾病發病中的重要作用[42-44]。目前公認,健康呼吸道黏膜中含有眾多細菌菌群[45],其中,上呼吸道中細菌密度最高,鼻腔和鼻咽部每鼻拭子可達到103~106個活菌。健康人氣管和肺內采集的支氣管肺泡灌洗中估計細菌數量約有102個細菌/ml[45-46]。呼吸道中常見的6種優勢類菌群為厚壁菌、變形桿菌屬、擬桿菌屬、梭桿菌、嗜酸桿菌和放線桿菌[47]。Helty等[42]研究表明,哮喘和COPD 成人患者的上氣道,以及兒童哮喘下氣道中變形桿菌,尤其是嗜血桿菌占優勢。Huang等[43,48]報道:癥狀控制4周后,采用吸入氟替卡松治療的哮喘患者氣道微生物多樣性與支氣管高反應性呈正相關。此外,與輕中度哮喘患者相比,重癥哮喘患者氣道中克雷伯氏菌豐度增高,變形桿菌與Th17 相關基因在氣道上皮中的表達呈正相關,肥胖型哮喘患者急性加重時,痰中桿菌類/厚壁菌屬更為豐富。然而,放線菌與哮喘控制無明顯相關[49-50]。嚴重哮喘患者還與長期攜帶肺炎支原體和衣原體密切相關,為此目前歐美國家開展了多個臨床試驗來探討大環內酯類抗生素在這組患者中的應用[51],但是研究得到的結果尚存在爭議,需要進一步臨床試驗。
氣道微生物在生命早期迅速增長,并且在之后的生命進程中受環境、健康狀況和年齡的影響。已經證明,出生方式 (經陰道分娩或剖腹產)、在生后的第1 小時生活環境,和出生后3~4個月的生活環境暴露是呼吸和腸道菌群塑造穩定發展的至關重要階段[52-54]。人體與動物研究表明:吸入攜帶微生物和微生物因子的塵埃粒子,通過調節先天免疫和適應性免疫反應,參與哮喘的發生、發展[28,55],但具體機制不清楚。目前兒童呼吸道微生物組學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于: (1)微生物如何在健康嬰兒上呼吸道定植?(2)環境因素,如母乳喂養、生活在農場、兄弟姐妹、日托、寵物家庭、吸煙和抗生素使用對呼吸道微生物群的影響? (3)早期呼吸道微生物定植伴隨著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發生,如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和流感病毒,是否參與哮喘發病的作用機制[56-58]? Teo等[53]進行前瞻性隊列研究兒童自出生至2歲不同時間點鼻咽部微生物群菌群。這個隊列中的健康嬰兒在出生后2個月齡時最初被定植葡萄球菌或棒狀桿菌屬,隨后穩定定居異球菌或莫拉菌屬;而鏈球菌,莫拉菌或嗜血桿菌定植與出生后60周內病毒相關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相關。另一項研究報道,在出生后4周齡時呼吸道定植肺炎鏈球菌、流感嗜血桿菌和/或卡他莫拉菌的嬰兒,將增加5歲時哮喘發病風險[44,59]。此外,上呼吸道定植葡萄球菌屬和莫拉菌屬的健康嬰兒在出生后2年內呼吸道感染率較低[52,59-60]。有趣的是,盡管生活在傳統農場的阿米什兒童和工業化程度較高農場的哈特族兒童具有相似遺傳性,生活在傳統農場的阿米什兒童中哮喘和過敏性疾病的患病率很低,而來自工業化程度較高農場的哈特族兒童哮喘和過敏性疾病的患病率較高。研究者發現,阿米什住宅環境灰塵中的微生物和內毒素負荷較高[55],由此推測氣道微生物多樣性與HDM 過敏呈反比[61-62]。但是,目前還不知道是否粉塵相關微生物群的保護作用是由于多種細菌吸入和進一步呼吸道定植的作用,或者是吸入細菌代謝物的作用。
5 前景展望
目前,盡管已知微生物群顯著影響宿主免疫系統成熟和免疫活性,但是這些免疫調節機制的分子基礎才剛剛開始闡明。尚不清楚:氣道微生物失調是否直接導致哮喘發病,抑或者僅僅參與肺內免疫反應;新型細菌菌株及其組分的鑒定,和細菌調節黏膜免疫機制等。兒童前瞻性出生隊列與橫斷面研究提高了我們對健康兒童或患病兒童的氣道或者消化道中保護性細菌定植時間窗的認識。然而,需要進一步的作用機制和流行病調查研究來揭示不同細菌菌株、宿主、過敏原和病毒之間的復雜聯系。健康成人、哮喘患者和其他慢性病患者之間的氣道微生物群差異已經進行了深入的研究。部分研究展現了哮喘患者的臨床特征和呼吸道微生物差異表型。然而,為了了解哮喘患者疾病表型和內型,哮喘易感性和疾病進展之間的聯系,仍需要大樣本、多中心的縱向和前瞻性分析。
利益沖突所有作者均聲明不存在利益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