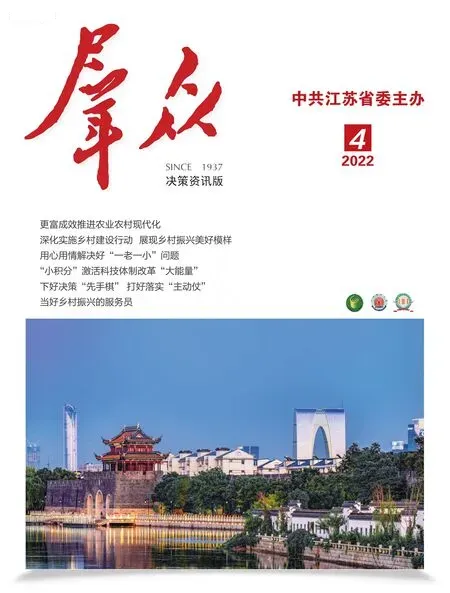曾國藩的“四字官德”
潘春華
晚清名臣曾國藩在30余年的仕宦生涯里,為國為公。清統治者推崇他“學有本源,器成遠大,忠誠體國,節勁凌霜”。毛澤東對曾國藩曾有較高的評價。曾國藩獲得如此高的評價,這和他處世治事堅持“廉、公、謙、慎”的四字官德緊密相關。
廉,即廉潔,是為官第一要義。曾國藩生活節儉,住不尚奢,衣不尚新,食不尚精,一般一餐只吃一菜,所以有“一品宰相”的雅號。曾國藩不管是在地方任職還是宮廷掌印,從來不取一文來歷不明的錢。平時與同僚的往來,也從不攜禮而入,也不允許別人送禮。他曾經在日記中寫道:“一切事都必須檢查,一天不檢查,日后補救就困難了,何況是修德做大事業這樣的事!”在他身后,也并未留下多少遺產給子孫。曾國藩曾說“予自三十歲以來,即以做官發財為可恥,以宦囊積金遺子孫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總不靠做官發財以遺后人,章明鑒臨,予不食言。”如此看來,曾國藩此言確是擲地有聲。
公,即公私分明,處事公正、正直,堅持原則,不徇私情,是為官之道。曾國藩在宦海生涯中能做到公私分明,樹立良好的官德形象,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對其師穆彰阿的態度。曾國藩初入官場能嶄露頭角、迅速升遷,與穆彰阿的提攜是分不開的。然而穆彰阿為人并無政治操守,結成穆黨,打擊清流。在這種情況下,曾國藩并沒有追隨穆彰阿,也沒有運用手中的權力作為謝恩的籌碼,而是立公立德,在政治上和穆彰阿劃清界限,在私人關系上,一生執弟子禮甚恭。特別是后來穆彰阿下臺,眾叛親離,曾國藩卻一直和穆家保持親密的關系,甚至穆彰阿死后,曾國藩還對其子孫多有照顧。后來,曾國藩在他的家訓中探討過這件事,他說,在對待自己的一些“道不同不相為謀”的上級時,能做到六個字就行,就是“近其人,遠其事”。
謙,即謙虛、謙和,是一種氣度和胸懷。古人認為:“謙乃君子之德”。《易謙》中說“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意為以謙卑培育自己的德行,曾國藩做到了這一點。他最初練湘軍,是既無權也無錢,而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練成的湘軍,其戰斗力卻大大超過大清的正規軍八旗和綠營。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曾國藩虛懷若谷、禮賢下士。曾國藩認為,傲氣太盛,說話太多,這兩條是歷代士大夫和近世官場導致災禍的重要原因。因此,曾國藩在處世治事、待人接物中,始終把“謙”看成“須臾不可離之道”。他聽說彭玉麟是個人才,雖然家貧,無一官半職,但是曾國藩不惜降尊紆貴,三次去請,終于使彭玉麟出山相助。曾國藩對自己的幕僚也是如此,堅持每天早上和幕僚們一起吃早飯,大家暢所欲言,關系融洽。曾國藩這種謙謙君子、禮賢下士的胸懷,使得幕僚里人才濟濟。晚清有一句話叫“天下督撫,半出曾幕”,就是說督撫一級的官員,有一半出身于曾國藩的幕僚,可見其網羅人才之盛。
慎,即慎獨,是一種至高的修身境界,也是曾國藩的可貴品質。曾國藩一生在慎獨上下足了功夫,在他看來,慎獨是修身之根本。其一,他認為慎獨在于養心。舉頭三尺有神明,“能慎獨,則內省不疚,可以對天地質鬼神。人無一內愧之事,則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寬平,是人生第一自強之道,第一尋樂之法,守身之先務也。”其二,他始終把慎獨放在修身之第一和根本的地位。他在《君子“慎獨”論》中,仔細考察古人修身的功夫,認為成效顯著的有四項:慎重獨處,就會心胸泰然;莊嚴恭敬,就會身體強健;追求仁義,就會心悅虔服;正心誠意,則神靈也會欽敬也。其三,慎獨是“日課四條”之“體”。他總結自己一生處世經驗,寫了著名的“日課四條”,即慎獨、主敬、求仁、習勞。他認為慎獨是根本,是“體”,其他三條是枝葉,是“用”。
責任編輯:段培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