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肯德基做晚打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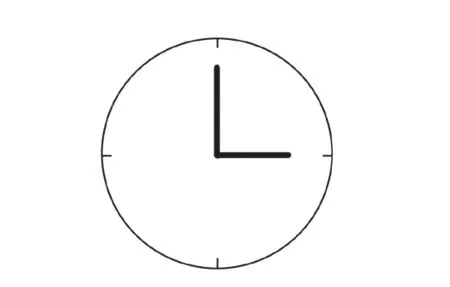

一
2003年夏天,我在肯德基得到一份兼職,做了晚打烊。
那天晚上,一個女人領著一個五六歲的小男孩走了進來。我瞄了一眼掛鐘,十點五十五分。我跟同事臟辮撇著嘴對視了一眼。
“哇!還沒有關門啊,小志!我就說吧!”女人滿眼驚喜地對小男孩說。小男孩緊緊拉著女人的裙子,露出一個怯生生的笑。
如果在平常,我跟臟辮一定會對他們說:“對不起,我們要打烊了。”但是這對母子讓我們很難開口。女人三十來歲的樣子,容貌甜美,好像也蠻開朗。小男孩看起來很乖,臉上有一種不相稱的警惕。
女人一邊往前臺走,一邊問兒子:“快快,小志,你要吃什么?”
我們希望他說他不餓,但是小志低聲說:“我想吃漢堡。”
見習經理大頭一邊配餐一邊問道:“在這兒吃,還是帶走?”
女人說:“在這兒吃。”
大頭愣了一下說:“我們馬上就打烊了。”
女人抱歉地笑笑說:“不好意思,我們想吃完再走。”
二
大頭下班走了,我們有意無意地觀察著那對母子。小男孩專心地吃漢堡,女人則滿臉愛意地看著他。
“好吃嗎?”女人問。小男孩點點頭說:“好吃。”過了一會兒,小男孩用一種想讓人感到驚訝的語氣說:“媽媽,我覺得我能吃掉整個漢堡啊!”女人被兒子天真的表情逗笑了,她摸摸男孩的頭說:“真棒!你慢點兒吃。”
吃了幾口漢堡,小男孩又問:“媽媽,是不是我很快就能成為大男子漢啦?”女人說:“對對,你今天開心嗎?”男孩說:“開心!”“那明年你過生日媽媽還帶你來吃肯德基,好不好?”小男孩說:“好!”
正在一旁掃地的臟辮突然直起腰問:“哎?小朋友今天過生日啊?”女人說:“是啊。”
臟辮突然沖我甩甩頭說:“去拿一份生日套餐。”
總配櫥柜里還有一對烤翅、一小份雞米花以及一些薯條,我都給劃拉上了,又接了一大杯可樂。
我端著托盤,堆著笑臉對那位漂亮媽媽說:“這是我們的生日活動,生日當天任意消費即可獲贈。”
女人看起來驚喜極了,小男孩顯然比媽媽還興奮,有一種兒童特有的全身心的快樂。
“我們不會耽誤你們下班吧?”女人抱歉地問道。臟辮說:“不會,我們還早呢,你們慢慢吃。”
三
當我們把活干了個差不多,猛然發現已經十二點多了,他們還沒有走。女人正出神地望著窗外,而小男孩已經睡著了。
“什么情況?”我問臟辮。臟辮說他去問問。為了不被人覺得像趕客,臟辮假裝很隨意地問道:“孩子睡著了啊?”
女人看了臟辮一眼,木木地點一點頭。但是通過她的眼神你就知道,她的思緒完全不在眼前,好像在一個虛無縹緲的遠方。
“那個……我們很快就要下班了。”臟辮不得不坦白說,但是女人再次把臉轉向了窗外,沒有接茬。
“不對頭!”臟辮說,我們躲進廚房,“嘰嘰咕咕”了好一陣后,不得不再次回去問她:“要不要幫您叫出租車?孩子睡著了……”
女人慢慢地轉過頭來,那種明亮的笑容又掛在了臉上:“我們可以在這里過夜嗎?我們沒有地方去了。”她的眼神卻慢慢黯淡了下去。
我們隱約覺得這個女人有問題,但總不能把孩子喊醒,把他們趕出去吧?
最后我跟臟辮一咬牙,得,就當是在網吧上了個通宵吧。
女人趴在桌上睡著了,我跟臟辮關了門,留了一盞燈,找張桌子坐了下來。
四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我跟臟辮幾乎同時被一陣很大的叫喊聲驚醒。那個女人正瘋狂地拍門,眼淚流了一臉。小男孩不知所措地站在一邊,滿眼恐懼。
我跟臟辮一下就清醒了!怎么了?女人哭著沖我們喊了起來:“你們憑什么把我們鎖在這里?把門打開!”她已經完全歇斯底里了。
“快快,快拿鑰匙。”臟辮一邊指揮我,一邊向女人解釋,“我們不是鎖你們,我們是怕店里進人……”
女人還在不停地叫喊。在臟辮開鎖的間隙,我拉拉男孩的小手,聲音顫抖地問他:“小朋友,你媽媽怎么了?”小男孩驚恐地搖了搖頭,他也不知道媽媽是怎么了。
“你放開我的孩子!”女人哭著,一把把孩子拽了過去。

我跟臟辮完全蒙了。我們看著他們奪門而出,我忍不住奮力喊了一聲:“小朋友!”
他們沒有停,也沒有回頭。在凌晨慘白的月光中,一大一小兩個瘦弱的身影急急忙忙走遠了。
我看了看表,三點十五分。
第二天上班的時候,對于昨晚的事,我閉口不提,但是大頭帶著懷疑的目光問我:“昨晚沒事吧?”
我說:“沒事啊。”
過了一會兒,大頭慢悠悠地對我說:“那個女人以前常來,她有病。一開始她婆婆還經常來找她,后來就干脆把她鎖起來了。哎,昨晚她婆婆沒來找她嗎?”
我斬釘截鐵地說:“沒有!”
半年后,我在本地的報紙上看到一條新聞:一個老人死在了家中,被鄰居發現后報警。經記者調查,鄰居是被小孩帶去的。小孩的爸爸死于一次意外,媽媽也瘋了。
我懷疑這就是那晚我們遇見的那對母子,我心里很不好受。
有時候,我站在店里,走在街上,希望能再次遇見那個小孩,希望某天晚上,他的媽媽又帶著他,一臉明亮地把門推開……
劉振摘自豆瓣網,本刊有刪節 圖:點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