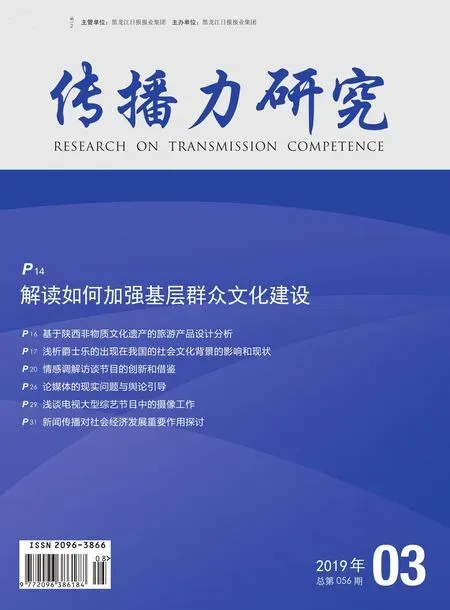從缺席到引領(lǐng):論科幻電影背后隱形的文化張力
張梅 張夢雨 重慶郵電大學(xué)移通學(xué)院
一、淺嘗與缺席:中國科幻電影的熒幕初探
隨著科幻電影的多元化創(chuàng)作,逐步形成軟科幻與硬科幻之分,軟科幻多以科學(xué)想象為支撐,其核心內(nèi)容多為反映人文、宗教、哲學(xué)方面的思考。而硬科幻則是基于嚴(yán)密的科學(xué)基礎(chǔ)上對未來科技發(fā)展的預(yù)言性創(chuàng)作,通常伴隨著大場面的展現(xiàn),如今觀眾在電影市場上樂于消費的多為后者,中國科幻電影的缺席也正是基于硬科幻電影創(chuàng)作的基礎(chǔ)之上達成的行業(yè)共識。
實際上,中國科幻電影并非完全空白,1938年的《六十年后上海灘》就是一次科幻類型的嘗試,1958年北京電影廠拍攝的《十三陵水庫暢想曲》以及1963年上海科學(xué)教育電影制片廠拍攝的《小太陽》都屬于科幻電影,只是中國科幻電影自創(chuàng)作之初就未形成市場化的量產(chǎn)趨勢,對科幻類型的涉獵多半淺嘗輒止。在好萊塢《星球大戰(zhàn)》的強勢引領(lǐng)下,1980年上海制片廠再一次拍攝了《珊瑚島上的死光》,影片改編自童恩正的同名科幻小說,被公認(rèn)為是內(nèi)地最早的科幻電影作品,1980年上映后,掀起了一陣短暫的科幻片創(chuàng)作熱潮。
不難看出,中國科幻類電影的起步并不算晚,但早期幾乎所有的科幻創(chuàng)作都無以為繼,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科幻題材電影在1960年--2000年期間,創(chuàng)作總量僅十余部。其深層原因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長期浸染有著重要關(guān)聯(lián),中國有著悠遠而豐富的民族文化,溫故知新、經(jīng)世致用的文化觀使得中國的文化底色中更注重對歷史的回顧。類型片的出現(xiàn)和批量性創(chuàng)作的深層文化基因通常伴隨著人們對現(xiàn)實世界的認(rèn)知和恐懼,正如愛情片是對現(xiàn)實世界中純愛關(guān)系欠缺的恐懼,科幻片的創(chuàng)作與敘事母題往往顯現(xiàn)出對于未來和未知的恐懼,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何民族歷史較短的美利堅民族會對科幻如此鐘愛,短暫的歷史文明使得美國人更樂于探索未來領(lǐng)域,以期獲得更為豐富的自我認(rèn)知,而中國的豐富歷史儲備使得中國人對未知的恐懼要弱化許多,所謂以史為鏡,歷史的豐富性消解了對未知的恐懼。
除卻文化基因,民族歷史的發(fā)展進程對中國科幻電影的發(fā)展也起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在好萊塢科幻電影大行其道的年代,中國近代史上的反法西斯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正風(fēng)起云涌,反思戰(zhàn)爭的現(xiàn)實主義風(fēng)格與宣傳政治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一度成為中國電影創(chuàng)作的主流。此外,優(yōu)秀科幻文學(xué)作品與硬性的技術(shù)支持是科幻電影長足發(fā)展的重要基礎(chǔ),科幻文學(xué)創(chuàng)作氛圍的欠缺以及科幻電影開發(fā)的資金與技術(shù)的缺乏,都使得中國電影人不敢輕易觸碰科幻這一“空白領(lǐng)域”。
二、前景與前進:中國科幻電影的熒幕之光
2014年,劉慈欣的科幻文學(xué)作品在各大平臺嶄露頭角,聯(lián)動反映下的科幻電影逐步打開創(chuàng)作僵局,《鄉(xiāng)村教師》、《流浪地球》、《超新星紀(jì)元》、《三體》等文學(xué)改編版權(quán)的業(yè)內(nèi)爭奪,掀起了科幻電影創(chuàng)作風(fēng)潮。
(一)文化底色:《流浪地球》中的“濃濃鄉(xiāng)愁”
《流浪地球》自上映以來,便被稱為中國硬核科幻電影的開山之作。電影的特效畫面體現(xiàn)了業(yè)內(nèi)特效技術(shù)的高水準(zhǔn),片中被凍結(jié)的萬里長城、東方明珠、奧運大廈以及白茫茫的冰原,都為影片塑造了末日感以及地球即將毀滅的恐懼感,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地下城中大量的中國紅元素,與春節(jié)檔的喜慶感相呼應(yīng)。
《流浪地球》以地球毀滅為主線,人類在地表建造出巨大的推進器,并帶著地球開啟了在宇宙中流浪,尋找新家園的旅程。編劇對原小說進行了二次創(chuàng)作,將中國人傳統(tǒng)的家國觀念融入影片并使這一核心觀念貫穿整部影片,引導(dǎo)著整部影片的走向,將中國人安土重遷,落葉歸根的傳統(tǒng)觀念表現(xiàn)的淋漓盡致,而回家和希望這兩個概念一直帶動著影片在往前走,中國人對鄉(xiāng)土的留戀,對家人的不舍,這種情感在影片中被不斷放大,傳統(tǒng)的那份“淡淡鄉(xiāng)愁”在電影中也升級為了“濃濃鄉(xiāng)愁”。中國科幻的內(nèi)核一直有別于歐美科幻的個人英雄主義,《流浪地球》體現(xiàn)的是一種將全人類團結(jié)在一起“集中力量辦大事”的理念。電影弱化了中國人的身份,將整個人類當(dāng)做一個命運共同體,將“天下大同”作為中國人對美好社會的一個共識和一直以來努力的方向。
(二)荒誕喜劇:《瘋狂外星人》的科幻式臆想
而另一部在春節(jié)檔上映的科幻片《瘋狂外星人》,同樣改編自劉慈欣的小說《鄉(xiāng)村教師》。上映首日,該片以4 億票房穩(wěn)居榜首,此后卻因口碑不佳形成兩極分化,質(zhì)疑多來自于該片科幻元素不足和主題表達與故事呈現(xiàn)方式不匹配,內(nèi)容低于期望等。其實該片共有939 個特效鏡頭,上百位動畫師參與了影片制作,尤其是片中外星人奇卡的面部運用了時下流行的“動作捕捉”技術(shù),猴子歡歡也是特效制作而成,完成了傳統(tǒng)科幻電影中難度較大的生物特效,導(dǎo)演寧浩認(rèn)為最好的特效是應(yīng)該隱身為故事服務(wù)的,不能成為評價科幻片好壞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瘋狂外星人》最為亮眼之處實則是其科幻外殼下民族優(yōu)越感的臆想表達,影片將美國精英階層以戲耍的方式進行了徹底的調(diào)侃與解構(gòu),將與外星高等生物建交的榮譽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轉(zhuǎn)交給了中國的底層耍猴人,憑借中國傳統(tǒng)的酒桌文化消解了美國精英階層的優(yōu)越感,形成了獨有的中國本土化科幻電影的敘事范式。
三、科幻類型繁榮背后的文化自信
上世紀(jì)二十年代,好萊塢電影技術(shù)日趨成熟,在經(jīng)過《人猿猩球》和《2001太空漫游》的創(chuàng)作熱潮后,好萊塢科幻電影日趨壯大,開啟了科幻電影的黃金創(chuàng)作時代。經(jīng)過一個世紀(jì)的工業(yè)發(fā)展,好萊塢已成為科幻大片的代名詞,其百年來的科幻電影制作經(jīng)驗幾乎成為中國科幻電影學(xué)習(xí)和借鑒的全部來源,同時也成為評判中國科幻電影的行業(yè)標(biāo)準(zhǔn),如何在好萊塢科幻電影的強勢陰影下,開啟自主創(chuàng)作之路成為擺在中國電影人面前的難題。
以好萊塢科幻電影為標(biāo)桿,對科幻類型電影的軟硬之分成為中國科幻電影創(chuàng)作道路上的瓶頸和技術(shù)鴻溝,《流浪地球》作為一部本土化的硬科幻電影不僅在票房上獲得了佳績,在主題立意與藝術(shù)表達上同樣交出了一份令市場和觀眾滿意的答卷。在《流浪地球》上映之前,中國科幻電影一直空白,即便創(chuàng)作了《逆時營救》、《機器之血》、《機器俠》等科幻影片,其市場表現(xiàn)和口碑評價也是差強人意,這些包裹著科幻外衣的劇情片完全無法與好萊塢科幻電影相提并論。應(yīng)該看到,《流浪地球》的最大貢獻并不止于飄紅的市場前景或人氣暴漲的上座率,而是中國科幻創(chuàng)作背后體現(xiàn)的文化自信與技術(shù)自信,正如《流浪地球》的主演吳京所說,中國科技的說服力已大大增強,一部中國類型的科幻片可以提升中國人的志氣。
《流浪地球》的出現(xiàn),無疑是中國電影工業(yè)體系日趨成熟的體現(xiàn),是我國科技綜合實力的證明,同時也彌補了硬科幻的“隱痛”。影片開頭所呈現(xiàn)的無數(shù)個推進器噴射出暖白色的巨大光柱的畫面是在經(jīng)過一千多張,概念圖的篩選后最終確定的樣本,這一恢宏場景的再現(xiàn),幾乎再現(xiàn)了原著精髓。影片揚長避短,著重于宏觀場景的設(shè)計和氣氛渲染,避開了一些容易出錯的細(xì)節(jié)展現(xiàn),最為關(guān)鍵的是,影片70%的特效都由國內(nèi)團隊制作而成,擺脫了特效制作依賴國外團隊的傳統(tǒng),實現(xiàn)了一次中國電影工業(yè)引領(lǐng)中國電影市場前行的儀式化之舉。《流浪地球》作為一部現(xiàn)象級電影,它確實開啟了中國科幻電影的起點,為國產(chǎn)科幻累積了好的經(jīng)驗,它所帶來的意義超越了電影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