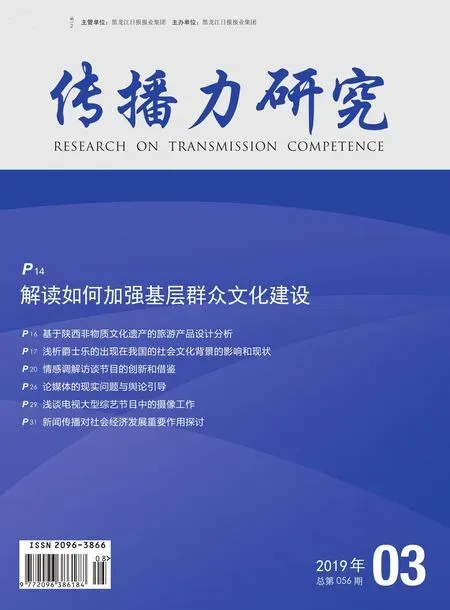《印度之行》中印度人的身份危機與重建
王慧 四川外國語大學成都學院
作為20世紀英國著名作家之一,福斯特的作品以其靈巧多變的寫作技巧和深刻的主題而著稱,《印度之行》被認為是福斯特最優秀的小說。在這部小說發表后,東西方許多批評家對其中的反殖民主義多有稱道。后殖民主義的主要理論奠基者認為,西方的思想和歷史文化不斷加深和強化西方中心主義及其種族優越論,因而塑造出一個個“東方形象”或“他者”形象,以定義和言說他們想象中的所謂東方。通過后殖民主義的相關理論,分析西方傳統中根深蒂固的種族觀、身份觀,對于分析被矮化民族的身份危機的構成原因,以及民主、平等的身份觀念的形成十分必要。
后殖民主義理論的奠基人之一,愛德華·賽義德在《東方主義》分析了伴隨著歐洲殖民歷史而形成的“西方中心主義”,以及這種文化思想引領之下所建構的關于東方的知識話語。賽義德指出,東方主義是歐洲在進行領土擴張時對東方形成的認識和意象。西方那些關于東方的知識話語充滿了對“他者”東方的想象,而這種想象是一種扭曲了的想象,并非東方本土的真實面貌。東方--西方,原始落后--優越先進,這種二元對立的東西方觀念本身就是一種文化霸權的表現。殖民者在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下所展開的殖民活動,需要有合理化的理由為其鋪路,所以被殖民的目標地需要被描述為原始落后的“他者”,他們才能打著要在上帝的指示下去“開化”野蠻民族的旗號,實施真正野蠻的殖民行為。他們掌握著話語權,附加了一種低等的身份在殖民地人民身上,從而進一步導致了他們的身份危機。霍米·巴巴認為殖民主義話語的強大影響使得被殖民者疏離本民族文化、語言和傳統,使其演化成一種“介于兩者之間的”、“近似白人”的一類人。
作為小說中的絕對主角,阿齊茲是身份危機最突出的人物。造成其身份危機的一個原因是他在學習歐洲先進的現代醫學知識技術過程中,受到了歐洲現代啟蒙思想的影響。這使得他一方面嚴守英國殖民者的等級制度,穿著考究溫順謙卑,試圖使自己和英國人平起平坐,或者“比英國人更像英國人”,這種對強勢文化的模仿來自于一種想要融入其中的欲望,而這種欲望會導致這些邊緣人否認本族文化,無法對印度文化產生驕傲和深刻認同感,認為自己優越于其他印度人,其他印度人屬于“第三等”人。但另一方面,他又在英國殖民者面前自卑不已,在經歷了英國殖民者的歧視和傲慢對待之后,他意識到殖民者從未等同地對待過他們。
阿齊茲在印度人和英國人這兩者身份間搖擺,無法融入其中任何一個。因此,他的文化身份無法定位,精神上也處于無家可歸狀態。他的身份因文化差異處于錯位狀態。這種錯位的身份表現在阿齊茲對待自己婚姻的矛盾態度上:根據印度傳統婚姻是由父母安排的且沒有雙方的愛情作基礎,但是他接受的西方教育卻不斷促使他要在真正愛情的基礎上結婚。阿齊茲在身份觀上的矛盾兩極化,分解了他本應完整的文化身份意識。當他躺在床上假裝生病時,在迷糊之際隱約地感到對印度社會現實的不滿和惡心。而阿齊茲所體驗到的惡心和惡心只不過是初始階段反抗意識的表現。反抗意識在法庭審判一幕達到了高潮。他開始仇恨殖民統治者,探尋和呼吁民族國家的誕生。阿齊茲起初發現伊斯蘭教所體現的非極端宗教政治能夠為印度民族國家的建立提供出路和方向。他以回望的方式尋找文化之根,尋找自己的精神家園。但是,英國殖民者對他的指控和審判卻使他從“詩人式”的感傷中幡然覺醒,終于意識到伊斯蘭傳統的局限性。
阿齊茲尋找到通過建立民族國家來重建身份。而民族身份的建立是最困難的。在《印度之行》中福斯特指出了印度人建立民族身份的方式可以是暴力的方式,正如法農指出的建立民族身份的唯一方式就是通過暴力反抗,擺脫殖民統治的去殖民化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暴力過程。英國殖民者在印度人民身上強加了弱者的他者形象,而且殘暴的殖民統治會加劇兩個族群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而且,殖民者面對日益復雜和混亂的社會狀況無法有效解決和改善,只能加速印度人民暴力反抗的進程。其次,福斯特也在小說中通過阿齊茲的視角指出印度人民各種宗教群體應當團結起來,把殖民者驅逐出去。最后,福斯特也強調印度人民尤其是知識分子要保持自我覺醒和升華,認識到本土文化的卓越之處以及歐洲殖民統治的真相。只有被奴役的印度人逐漸覺醒和團結起來,建立一個民族國家來對抗和擺脫歐洲殖民主義統治才有可實現性。因此印度之行也可解讀為印度人覺醒,擺脫了殖民者奴役、建立民族國家,重建身份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