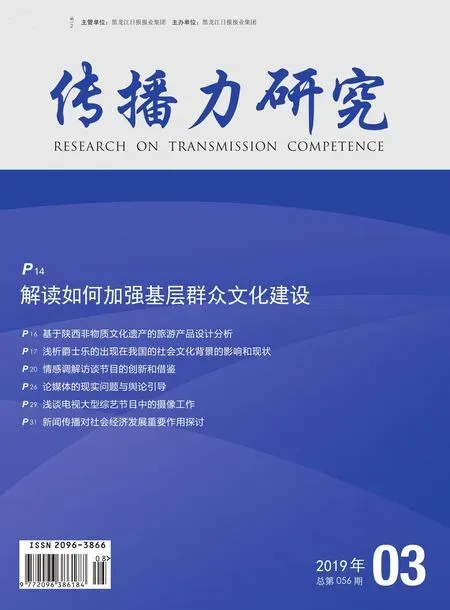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新轉(zhuǎn)向
——社會建構(gòu)論
梅汝陽 西北大學(xué)新聞傳播學(xué)院
作為新聞研究與歷史研究的一個交叉領(lǐng)域,新聞史研究一直是中國新聞傳播研究的一個重要分支。2007年,復(fù)旦大學(xué)信息與傳播研究中心和《新聞大學(xué)》編輯部專門組織了一個中國新聞史研究現(xiàn)狀筆談,試圖從體例、視野等角度對中國新聞史研究進(jìn)行反思,以此為開端,國內(nèi)的新聞史研究學(xué)者開始對過去的新聞史研究進(jìn)行系統(tǒng)的梳理。在此背景下,國內(nèi)新聞史研究開始邁入一個新的階段,其中社會學(xué)的相關(guān)研究成果尤其引人注目。
文化史學(xué)家彼得·伯克認(rèn)為,“如果說社會學(xué)是對單數(shù)的人類社會的研究,;那么歷史學(xué)則不妨看作是對復(fù)數(shù)的人類社會的研究[1]。”隨著后現(xiàn)代主義潮流的引導(dǎo),歷史學(xué)與社會學(xué)理論的結(jié)合已成趨勢,著名華人學(xué)者李金銓就曾強(qiáng)調(diào),“新聞史不妨借用一些社會科學(xué)的概念和理論來燭照史料,洞察史實背后的曲折意義和內(nèi)在聯(lián)系[2]。”本文所談的社會學(xué)新思潮——社會建構(gòu)論在新聞史研究領(lǐng)域的介入,最早在1978年邁克爾·舒德森出版的《發(fā)掘新聞:美國報業(yè)的社會史》一書中得到體現(xiàn)。國內(nèi)學(xué)者陳昌鳳在《中國新聞傳播史·媒介社會學(xué)的視角》一書中開始嘗試引進(jìn)“社會史”的互動視角:“本書試圖在新聞傳播與社會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的關(guān)系中梳理和論述中國新聞傳播的變遷與發(fā)展。”[3]無獨有偶,同一年李彬出版的《中國新聞社會史》中也提到了對“社會史”范式的借鑒。不過,廣泛借鑒社會建構(gòu)論的理論成果對新聞史進(jìn)行書寫,則是以黃旦、孫藜等人主導(dǎo)的“新媒介報刊史書寫”團(tuán)隊為開端,筆者將在下文中對該研究團(tuán)隊的成果有所涉及,在此不多做贅述。
一、“沉浸式”的歷史觀
作為結(jié)構(gòu)功能主義的集大成者,美國社會學(xué)家塔爾科特·帕森斯以其“一般社會行動理論”聞名于世。在他看來,“不管在什么場合運用一般的行動圖示,現(xiàn)象都是按這個共同的參照體系來描述的[4]。”,正如吉登斯所批判的,這樣的行動體系“沒有任何行動,只有需要支配或角色期待驅(qū)使下的行為[5]。”如果對過去中國新聞史研究進(jìn)行一些反思和觀察,就會發(fā)現(xiàn)同樣的病癥。國內(nèi)學(xué)者借用庫恩的范式理論,將近現(xiàn)代新聞史劃分為“革命史”和“現(xiàn)代化”兩種書寫路徑[6]。“革命史”書寫范式就是“以中國共產(chǎn)黨的、革命的、進(jìn)步的新聞傳媒的歷史為主體,以新聞傳媒在政治斗爭、思想斗爭的作用為基本內(nèi)容的新聞史書寫”[7]。此種范式強(qiáng)調(diào)階級沖突對歷史發(fā)展的推動作用,因此在歷史敘述中有選擇地讓歷史場景中的新聞人物和事件“出場”和“退場”,從而失去了對新聞事業(yè)本身的聚焦。而另一種“現(xiàn)代化”范式則是以戈公振的《中國報學(xué)史為代表》的新聞史書寫。他自覺地為報紙賦予引導(dǎo)公眾輿論的作用,并將其看作推動近代中國民主化進(jìn)程的重要陣地,也就是一般意義上的“現(xiàn)代化”范式[8],該范式受近代中國西學(xué)中用的影響而忽略中國自身的特殊國情。它是以西方為模板,將本國的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等各個方面與西方比照,按此進(jìn)化邏輯講述歷史的角度,其實際上與前一種“革命史”范式都是一脈相承的[9]。
以上兩種范式,究其本質(zhì)都脫離不開一種預(yù)設(shè)的歷史規(guī)律,不管是通過敘述中國共產(chǎn)黨報刊歷史為主體從而導(dǎo)向政治合理性,還是通過參照西方報刊發(fā)展歷史研究本國報刊歷史以分析中國近代化路徑,都逃不過以論帶史的色彩,便如吉登斯嘲諷的“舞臺是固定的,而行動者只根據(jù)已經(jīng)替他們寫好的劇本進(jìn)行表演[10]。”在對過去中國新聞史研究存在的問題進(jìn)行反思的過程中,寧樹藩先生提出了“本體意識”的觀點。寧樹藩先生認(rèn)為,過去中國新聞史完全依附于政治史、思想史,這已經(jīng)成為制約中國新聞史研究深入開展的重大阻礙。他覺得,在新聞史研究中,我們需要回歸新聞“本體”,專注新聞事業(yè)本身的發(fā)展變化,從而揭示新聞事業(yè)的內(nèi)在規(guī)律。一方面要關(guān)注報刊的社會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關(guān)注報刊自身成長的歷史[11]。面對結(jié)構(gòu)功能主義理論帶來的巨大慣性,如何才能擺脫預(yù)設(shè)的歷史規(guī)律和社會發(fā)展的“整體論”制約,回歸新聞“本體”,對新聞史有一個更加原貌式地再現(xiàn),或許提倡“沉浸式”社會觀察的吉登斯可以給我們一些歷史哲學(xué)上的啟發(fā)。
作為建構(gòu)主義的繼承者,吉登斯在反思舊有的社會學(xué)方法時提出了結(jié)構(gòu)化理論,他認(rèn)為人類是作為歷史具體情境中的行動者存在著的,人類是有主動性的行動者,但同時這種主動性又被結(jié)構(gòu)化的社會所制約,因為社會本身的結(jié)構(gòu)是人類在無意識中被動地形成的,而意義、規(guī)范和權(quán)力等要素如何通過互動促進(jìn)社會的結(jié)構(gòu)化過程,便是他研究的聚焦點——結(jié)構(gòu)化理論[12]。在對結(jié)構(gòu)化理論的闡述中,他認(rèn)為社會學(xué)的觀察者不能僅僅滿足于一種保持距離的“觀察者”角色,而“必須沉浸于一種生活形式中”,其目的并不在于使我們成為這種生活形式中的一份子(畢竟歷史研究也不可能穿越),而是通過沉浸在生活形式中去找到如何作為這種形式中“實踐總體一部分”的辦法。這樣一種基于行動者與社會結(jié)構(gòu)框架下的社會觀察方法,正是吉登斯在結(jié)構(gòu)化理論框架上向外延伸的結(jié)果。
基于這種沉浸的視角,歷史學(xué)家得以進(jìn)入一個由主體的積極行為所構(gòu)造的世界,而不是由某種客觀規(guī)律或整體趨勢造成的世界。這一“沉浸式”的史觀相對于過去“革命化”和“現(xiàn)代化”范式最大的區(qū)別在于,在歷史書寫者眼中,不應(yīng)存在一個預(yù)設(shè)給定的客體世界。歷史研究者往往面對的是一系列偶然排列的孤立事件,而其最關(guān)鍵的任務(wù)便是根據(jù)某一普遍規(guī)律將各種孤立的事實串聯(lián)起來,從而呈現(xiàn)一幅連貫的歷史圖景。這一普遍規(guī)律在以上兩種范式中,表現(xiàn)為階級斗爭和現(xiàn)代化、民主化的歷史規(guī)律。隨著某一普遍規(guī)律被強(qiáng)調(diào)成為唯一的“普遍性”來作為串聯(lián)歷史的線索,歷史書寫便會僵化,失去生機(jī),即吉登斯所謂的照劇本表演。歷史書寫者要擺脫“普遍性”的唯一視角,并不代表要放棄對歷史線索的關(guān)注,關(guān)鍵在于,這一線索需要歷史書寫者自身沉浸到作為歷史現(xiàn)實的史料中去感受,而不是不論研究對象特殊性的“拿來主義”。
“沉浸式”的史觀強(qiáng)調(diào)的乃是兩方面,一是專注于個案研究的共時性“沉浸”,在同一社會結(jié)構(gòu)下,不同主體的行為和互動作用產(chǎn)生了一個瞬時的歷史畫面,從而使歷史更加生動活潑;二是歷時性的歷史書寫,在這一過程中行動者與社會結(jié)構(gòu)在不斷地互動之中,構(gòu)建了歷史,其趨向作為一種共通的經(jīng)驗成為歷史現(xiàn)實的脈絡(luò)。
從共時性的角度對新聞史進(jìn)行“沉浸式”觀察,在于以一種開放的視角看待媒介與參與新聞傳播活動等主體的關(guān)系。黃旦曾在《報紙革命:1903年的<蘇報> ——媒介化政治的視角》以“媒介化政治”視角考察報紙革命,探究《蘇報》是如何卷入政治同時也改變了政治,媒介在交往與溝通過程中,黃旦開放性的敘述角度使不同的主體與環(huán)境產(chǎn)生關(guān)系的行為和方式得到了生動的呈現(xiàn)[13]。基于不同媒介角度的實踐活動中,張園的口頭演講和《蘇報》的印刷報道在同一媒介場景下表現(xiàn)出差異,同是張園演講,演講者與聽講者的媒介實踐活動不同,同是《蘇報》宣傳,撰稿者和讀報紙從事的媒介實踐不同。這種開放的視角下,是不同行動主體構(gòu)建歷史的互動過程。
歷時性的新聞史構(gòu)建,關(guān)鍵在于將新聞傳播與社會變遷之間的互動關(guān)系展現(xiàn)出來,美國新聞史學(xué)家邁克爾.舒德森曾在《發(fā)掘新聞:美國報業(yè)的社會史》一書中提出了一種新的“社會史”范式。著名學(xué)者陳昌鳳指出,“社會史”取向是指“由社會學(xué)理論先導(dǎo),解釋和研究傳播和社會之間相互影響的各種問題……在社會語境中觀照媒介,將新聞的生產(chǎn)與社會的變遷聯(lián)系起來,為我們的新聞史研究提供了一種很值得借鑒的指向[14]。”李彬在《中國新聞社會史》一書中嘗試引進(jìn)“社會史”范式進(jìn)行新聞史書寫,將“新聞傳播作為社會運動的一個有機(jī)環(huán)節(jié)”,同時關(guān)注新聞本體的內(nèi)在聯(lián)系和新聞與社會的外在聯(lián)系[15]。這種范式舍棄了對單一主體的僵化描繪,在這種全面的考察下,新聞傳播活動不僅作為一種行動者自身發(fā)展的互動過程被展現(xiàn),還被置于一種行動者與具體歷史情境相互作用的場景中進(jìn)行呈現(xiàn),使得新聞史成為活生生的歷史。當(dāng)然,李彬在歷時性的宏觀敘述中,雖然注意到整體的“大歷史”放在行動者與具體歷史情境中進(jìn)行考察,但在微觀層面的互動場景敘述上,則因其刪繁就簡的原則而未曾得到很好的詮釋。
由此可見“沉浸式”的歷史觀察,是指在這幅由行動者和社會結(jié)構(gòu)共同構(gòu)建的歷史圖景中,不存在預(yù)先設(shè)定的劇本,歷史書寫應(yīng)當(dāng)從一個提前寫劇本的任務(wù)變成了如實評述觀感的任務(wù),由是歷史方顯它自己本來的面貌。
二、媒介實踐范式的轉(zhuǎn)向
隨著個人行動—社會結(jié)構(gòu)的社會學(xué)分析框架的普及,學(xué)者們開始警惕行動者與社會結(jié)構(gòu)之間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從科學(xué)知識社會學(xué)到現(xiàn)代的諸多社會學(xué)家試圖超越行動—結(jié)構(gòu)的嚴(yán)格對立,他們以實踐為路徑,使活動免于遭受社會結(jié)構(gòu)的嚴(yán)格控制。其中建構(gòu)論者吉登斯、布迪厄尤為突出,吉登斯的“結(jié)構(gòu)化”理論,將社會中行動者的實踐活動通過社會結(jié)構(gòu)組織起來,成為一種“模式化的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布迪厄認(rèn)為,實踐存在的意義在于,它是構(gòu)成社會的社會結(jié)構(gòu)和行動者的心態(tài)結(jié)構(gòu)這兩種結(jié)構(gòu)存在并不斷更新重建的基礎(chǔ)和源泉[16],這一系列理論的實踐轉(zhuǎn)向,對當(dāng)代媒介研究也產(chǎn)生了一定的理論啟發(fā)。
英國學(xué)者尼克·庫爾德利認(rèn)為,一系列的實踐轉(zhuǎn)向啟發(fā)了我們要從整體上來把握媒介實踐和社會實踐之間的關(guān)系。一方面,我們要分析我們用媒介干什么事,說什么話;另一方面,我們要分析使用媒介可以從事哪些類型的活動,這些活動的運行機(jī)制是怎樣的,這些作用機(jī)制對我們有何影響。基于以上問題的思考,尼克.庫爾德利提出了“媒介化”、“場域”和“媒介儀式”等概念,他試圖用三個概念搭建起一個解釋圖式[17]。
從特點上來說,庫爾德利的媒介實踐范式有兩大重要取向:去中心化和去二元論[18]。在人人皆可化被動為主動的今天,媒介行為早已沒有特定的中心和指向,如今的傳播主體、受眾甚至媒介自身都可以抽象為社會中的行動者,參與構(gòu)建社會中的媒介行為,因而產(chǎn)生了去中心論;而去二元論則是指對行動者和社會結(jié)構(gòu)這一對立思維的一種舍棄,這一思維在媒介領(lǐng)域具體表現(xiàn)為個人是因主觀情感而從事媒介行為,由社會規(guī)范主導(dǎo)個人的媒介行為,去二元論則意味著在兩者之間尋找另一種平衡。
近年來,黃旦、孫藜領(lǐng)導(dǎo)的“新媒介報刊史”團(tuán)隊從不同的角度對媒介實踐范式的特點作出回應(yīng)。黃旦認(rèn)為,媒介實踐范式的理論特點能夠規(guī)避結(jié)構(gòu)功能主義對新聞史研究一直以來造成的影響:“這樣的實踐進(jìn)路可以有保留接受,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功能主義以及反映和被反映,受眾或效果等的研究[19]。”金庚星在《媒介的初現(xiàn):上海火警中的旗燈、鐘樓和電話》一文中,通過上海火警行動中不同媒介矩陣與救火事務(wù)的聯(lián)動敘述,將媒介與社會變遷的歷史互動展現(xiàn)在我們面前[20]。在上海火警傳播機(jī)制的變遷中,原本由人工瞭望、日旗夜燈組成的火警傳播系統(tǒng),隨著鐘聲、電話的加入,傳播系統(tǒng)又為之一變,隨之而來的是社會救火事務(wù)的風(fēng)格轉(zhuǎn)變。媒介自身的變遷,使得與媒介相關(guān)聯(lián)的社會行為、社會機(jī)構(gòu)的變遷也同時變化。這一過程中,作者專注于與火警媒介所關(guān)聯(lián)實踐活動從而擺脫了報刊文本分析和文本效果研究等固化的議題,通過實踐消解了工具理性。
1956年丁淦林在其《中國新聞史研究需要創(chuàng)新——從1956年的教學(xué)大綱草稿說起》一文中介紹新聞史教學(xué)大綱對新聞史研究的影響:一是以政治形勢的變化為依據(jù)劃分歷史時期;二是只關(guān)注黨的報刊和少數(shù)進(jìn)步報刊;三是強(qiáng)調(diào)報刊作為階級斗爭工具在政治、思想斗爭中的作用[21]。相對歷史而言,報刊不僅需要擺脫工具論的色彩,更要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個體去和社會存在聯(lián)系。一方面,將非黨報刊地位邊緣化的意識應(yīng)當(dāng)?shù)玫礁恼涣硪环矫妫覀儾荒苤粚罂鳛橐环N社會工具滿足社會發(fā)展需求,從而自有取舍其意義,這是在今天必須要做的去“功能主義”的任務(wù),至此再看媒介實踐的研究取向,則尤顯必要。
這里需要提出一些疑惑,在“新報刊史書寫”的一系列文章中,作者通過對實踐活動的描述,試圖規(guī)避媒介或社會主體的“使用與滿足”框架、媒介與行動者之間的主客二元思維,然而卻將媒介構(gòu)建為社會主體,這或許是對“工具論”矯枉過正產(chǎn)生的一種強(qiáng)效果論,這樣的書寫模式是否是因為作為歷史構(gòu)建主體的行動者不夠多元而產(chǎn)生的影響。
三、總結(jié)
相對于過去中國新聞史存在的“革命化”范式、“現(xiàn)代化”范式,歷史書寫在社會建構(gòu)論的引導(dǎo)下,使社會行動者作為具有主動性的構(gòu)建者,在一種具體的歷史情境中,以飽滿的生命力去與社會結(jié)構(gòu)發(fā)生互動從而顯其本真。當(dāng)然我們也要警惕在歷史書寫中過度強(qiáng)調(diào)媒介作為構(gòu)建者所發(fā)揮的主動作用,從而將其存在和發(fā)展的偶然性夸大,碎片化、斷裂的歷史敘事并不意味著一定的社會歷史規(guī)律的消亡,避免歷史規(guī)律的預(yù)設(shè)不應(yīng)同時消解報刊存在和發(fā)展的規(guī)律。
當(dāng)下中國新聞史研究重點在于對舊有范式有足夠反省意識的同時,能夠深入學(xué)科本身以一種創(chuàng)新意識引導(dǎo)學(xué)術(shù)資源對學(xué)科研究的基礎(chǔ)、方向和角度進(jìn)行重造,正是在此背景下社會建構(gòu)論才能夠生發(fā)出其特有的意義。如果要從社會建構(gòu)論紛繁復(fù)雜的理論內(nèi)涵中尋找中國新聞史研究的進(jìn)路,應(yīng)該遠(yuǎn)不止以上兩點,就本文的意義而言,它所代表的是一種反思性的、突破性的理論自覺。事實上,當(dāng)下中國的新聞傳播研究已走到一個新的路口,結(jié)構(gòu)功能主義帶來的整體論、決定論;技術(shù)決定論、工具論;實用主義的研究偏向所導(dǎo)致的學(xué)科根基的散亂;如此種種都絕不是單單一個社會學(xué)理論框架所能解決的。社會建構(gòu)論取向的介入,代表的是后現(xiàn)代視野下的一種不斷反求諸己的自我意識,一種敢于突破的理論自覺。